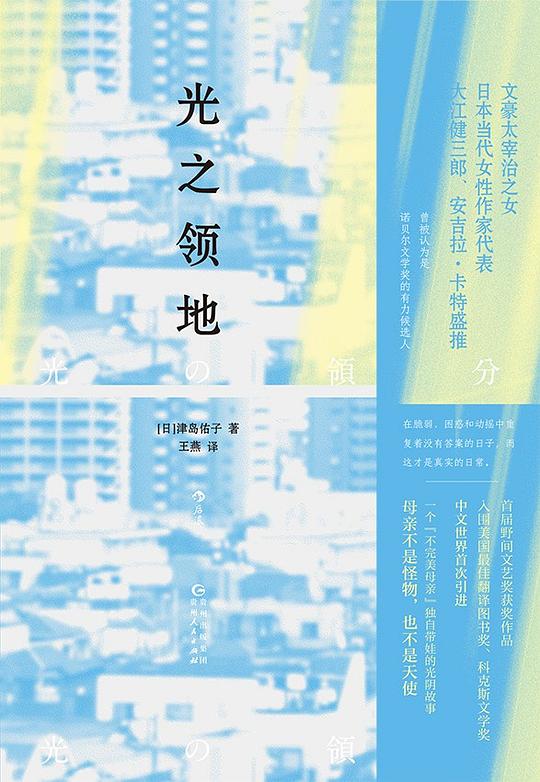
光之领地离奇失踪
书名:光之领地
1
0

吉克隽逸 2023-10-15 17:42:53
“娜拉当初是满足地生活在所谓幸福的家庭里的,但是她竟觉悟了:自己是丈夫的傀儡,孩子们又是她的傀儡。她于是走了,只听得关门声,接着就是闭幕。”
娜拉走后怎样鲁迅1923年12月提出的问题,到今天也不断有人尝试回答——不是她们原本就想定了要回答,而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一代又一代的女性,如果不是怀抱着憧憬和希望大概也不会走进婚姻、更不会怀孕生子、进入育儿现场,但大部分都发现自己变成了娜拉。
有人发现自己被困于《坡道上的家》、也有人成为《第八日的蝉》。
有人从困境里破茧成蝶、发现《我本自由》,也有人成为《困在记忆里的母亲》。
有人写出《钢琴教师》并朝体面生活那华美的袍上吐一口痰、也有人成为《逃走的伸子》。
她们每一个都是娜拉,不同版本的娜拉。
在《光之领地》里,娜拉没有只身逃走,她带走了刚上幼儿园的女儿。她离开的身影绝不是一个完美的榜样,但却很具体、很个人、很真实:
她带着女儿离开了那个百无一用的丈夫,虽然没要回借给他的钱、无法指望他付抚养费、常常听说他又跟哪个女人打得火热,甚至还总在犹豫是否该回到他身边、至少维持家庭表面上的完整。
每次周围人劝说她为了孩子回到丈夫身边、劝说她如果离开了这个垃圾男只会遇到更垃圾的男人时,她也会动摇。
她甚至做不了一个完美妈妈——她和孩子反复生病、她在照顾孩子的家务和精神负担面前摇摇欲坠,甚至出现了今天的我们能轻松识别的抑郁症状——长时间的睡眠、无法起床、无法把孩子按时送到幼儿园、需要靠喝酒鼓起面对新一天生活的勇气……
津岛佑子描写的娜拉带娃出走的场景实在太真实,甚至我们可以从其他女性的真实经历中找到几乎一模一样的描述。比如女性主义的祖师奶奶之一Iris Marion Young在她著名的《像女孩那樣丟球:論女性身體經驗》就讲过她妈妈单身抚养她时陷入类似的抑郁和酒精滥用状况,她和兄弟姐妹曾经一度被社会福利部门带走。Young作为女性主义和女性身体经验的集大成者之一,甚至都表达过对母亲失职的愤怒,但随着年纪增长、自己也成为另一种娜拉,她也开始反思和共情不完美的母亲作为问题背后娜拉面对的困境。
津岛佑子描写的,其实就是这种困境。
她的娜拉有工作,因此解决了鲁迅说的“最要紧的”“经济”问题。虽然工资很少、付完房租所剩无几,甚至还时不时得去填百无一用丈夫实现文艺理想的坑。
她的娜拉有欲望,虽然在更多人道德的标杆之下,一个女人一旦成为了母亲、尤其是单身母亲,就应该自动自我阉割,上演儒教贞节牌坊下寡母守贞、含辛茹苦拉扯大孩子的性别脚本。
她的娜拉会在孩子睡下之后的漫漫长夜里感到无法忍受的孤独,独自出门去小酒馆在年长的陌生女人那里寻找跟成年人说说话的可能。
她甚至需要寻找一夜情的对象来解决自己的生理需要——而她对这个对象的选择往往都呈现出一个决策能力受损的成年人的样子。
在2023年,有了更多的社会研究和心理学实证研究,如今我们知道这是严苛环境、压力和过度情绪和照护劳动共同导致的判断力和毅力作为心理资源的严重受损。如果把这些看似“狗血”却很真实的困境都归咎于一个女人道德上的缺陷,那将是极为不公平的。
这本书为数不多的书评中,有一位读者说津岛佑子比角田光代更超前、写得更好。我很同意。这本《光之领地》写于1979年,在2023年读却完全不觉得落伍。上野千鹤子曾说过女性主义者在继承前辈的语言上遗失了很多本可以继承的遗产,读这本1979年开始就发着光、但却不为我所知的娜拉故事,我也有同感。津岛佑子在写作上的视野和成就,并不输给她那个名满天下的爹(太宰治)。
我喜欢她的温柔的清醒、并不惧怕点穿娜拉哪怕在出走之后都冲不破的牢笼:
“当时丈夫说那是我自作自受,并没停止对我的辱骂。当他不再让我听见他的声音时,我还以为我的诉求他听进去了。但其实没有。对丈夫来说,我成了他憎恶的对象。为了女儿,丈夫无论如何也要把我降服在他的势力范围内,拧断我的手脚。”
我也喜欢她的隐喻和表达,比如用逃逸的家养牡丹鹦鹉比拟离开之后彷徨着四处敲打锁闭的铁屋子的娜拉:
“女儿的生日过后不久,我梦见了一只鸟。丈夫不是在电话里,就是在图书馆的门口,有时是在我住处的楼下,他不分场合地责骂我,问我到底是怎么想的,问我为什么那么恨他,甚至哭着不断地问我:到底是因为什么而我总是一声不吭地看着他,心里想我并不恨你,只是害怕得张不开口了而已。”
“在图书馆,我打了个盹。”
“看见有只鸟从一棵落叶树的树枝上飞下来。那是一只大大的、红脸绿羽毛的热带鸟。”
“最近这段时间,不少原本是家养的鸟飞到了外面,就像那只牡丹鹦鹉之类的,许多就变成了野生的鸟。不远处传来了这样的说话声。”
“啊,牡丹鹦鹉…我刚说完,又有一只和刚才那只一模一样的鸟飞了过来,栖息在另一条树枝上。“果然,真的多起来了。”随着这念头的闪现,越来越多的牡丹鹦鹉飞了过来,整棵树被牡丹鹦鹉裹了个严严实实。”
“树上挤满了色彩缤纷的羽毛,有些像熟透了的果实,重重地落在了地上。为什么只有这种鸟多起来了呢是因为它的生命力很强韧吗梦中的我惴惴不安。”
而她对母职、尤其是单身母亲作为孤立无援的女人面对男人逃脱之后扣在自己身上的育儿牢笼则有直白、诚实的描写,仅仅是她的诚实就已经有了巨大的力量:
“睡眠不足的日子一直持续着。白天在图书馆工作时,我经常会打盹。傍晚赶去幼儿园接女儿的时候,浑身乏力,连头都拾不起来。和女儿走在路上,路过点心店她就哭闹着要冰激凌。看见猫咪,不管有没有车就跑上马路去追,没走几步又吵着让我背她。我的忍耐几近极限。这孩子,难道是在考验我的耐力吗把我的身体拽来扯去的,是在嘲笑我吗”
“女儿长得像她父亲。我故意不看她的脸,只拉着她的手。回到住处一直到她睡着的时间,我也尽量无视她,一个人躺下装睡。接着,女儿就会在半夜哭起来。”
“怎么做才能让女儿睡得安稳呢连想都没想过。我更在意的是自己睡眠不足,得让自己不被女儿的哭声吵醒才行。我开始在睡前喝下远超自己酒量的威士忌。可是,不管醉得多沉,还是能听见女儿的哭声。因为醉酒,大脑昏昏沉沉的,哭个不停的女儿更给我火上浇油,真想用湿毛巾把她的嘴巴和鼻子捂上。但我没那么做,而是不轻不重地打了她的脑袋,然后去厨房把胃里的东西都吐在了洗碗池里。我一边用水管的水洗脸,一边嘟囔着救救我,救救我吧。”
“那天夜里,我又烂醉如泥。女儿的哭声如海浪声。”
“醒来后,发现女儿还活着,我揉了揉惺松的睡眼,定晴看了看,只见她的手和脚都在抖动。梦中女儿父亲的哀叹还回响在耳边。我伸手摸了一下女儿的胳膊,又摸了摸她的后背,温热而柔软。她还活着。一时竟搞不清这是现实还是梦境。”
“希望死去的女儿可以复活,这个不可理喻的愿望竟如此轻易地成了现实。可即使是做梦,我也无法不感恩女儿的复活,忍不住把活着的女儿紧紧地抱在怀里。为什么上苍会把女儿继续活着的好运赐给我这样的人呢真不可思议。”
“等回过神来,发现女儿咬着我的睡衣袖子睡着了。我把她放回被子里,脱下她的睡衣和内裤,拿着去了厨房。厨房的窗户没挂窗帘,窗外的霓虹灯和路灯把房间里映得通明。我把脏衣服扔进洗衣机,登楼梯上了屋顶。还有几处亮着灯的窗户,我数了起来。那天夜里,女儿少有地睡到了天亮,没再哭了。”
“第二天早晨,女儿揪着我的头发把我揪醒了。一看表,已经八点半。我急急忙忙地给女儿穿好衣服,让她喝了牛奶再出门。嫌女儿走得太慢,就抱起她往幼儿园跑。突然我想,在内心的某个角落,我是希望女儿死去的吧。否则就不该在梦里梦见女儿的尸体。女儿的身体很重,我双臂麻木了,视野也变模糊了。我紧紧地抱着那份沉重,继续跑着。”
在这本《光之领地》里,津岛佑子频繁地使用了梦作为一种隐喻。当我把这个娜拉故事跟鲁迅1923年的话对比时,这个隐喻跨越时空发出了更大的震动。鲁迅说:
“但娜拉毕竟是走了的。走了以后怎样伊孛生并无解答……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
在1923年,鲁迅的实用主义让他没有别的办法,只能不去叫醒娜拉,因为娜拉出走后无路可走。我很高兴在1979年,津岛佑子的娜拉不仅出走、而且带娃出走,不仅离开了那个始作俑者的一无是处、只会挥舞道德大棒的男人,还在严苛的气候中找到了一片生存的微小生境。
这个微小生境仍旧风刀霜剑严相逼,但逃出了笼子的家养小鹦鹉仍旧相信她有坚韧的生命力。正如津岛佑子自己的人生证明了一个制造了孩子却反复跟不同女人殉情、早早退出了养育现场的父亲和单身母亲在那个年代面临的严苛环境也并不能抹杀娜拉艰辛中求生存、艰辛中拉扯大孩子的生命力。
关于津岛佑子的另一个小惊喜是我一直以为这本《光之领地》是我读的第一本她的书,搜了一下才发现我在十二年前读过她的《微笑的狼》并且非常喜欢,虽然当时我没记住她的名字。现在想来,那时在图书馆无意中发现的那套“中日女作家方阵”确实为作为女性的我打开了一条新的道路,尽管彼时我还并不明白那条路意味着什么、它通向何方。
相关推荐
钢琴教师
小说叙述了埃里卡一位女子在母亲极端变态的钳制下心灵如何被扭曲和情爱如何被变异的痛苦历程。书中描写了如共生体一样不正常的母女关系。尽管埃里卡已经年过而立,但她仍时刻处于母亲的监视之下,不能越雷池一步,甚 埃尔夫丽德·耶利内克 2023-04-01 08:32:04园丁与木匠
孩子不是无意义的打闹,而是在学习社交互动;孩子不是在简单地玩玩具,而是在探索世界;孩子不是因为无聊才问为什么,而是在寻找答案。那么,当孩子在玩的时候,他们到底在学习什么呢?他们是如何学习的?而对于父母 [美]艾莉森•高普尼克(AlisonGopnik) 2023-03-31 02:28:48孩子如何学习
-出生42分钟,婴儿就能模仿大人的脸部表情;6个月大宝宝就能区分各种语言的不同;3岁孩子能在两分钟内测试5个科学假设……人们一直以来认为孩子的学习是被动的,需要教导,但科学证明学习是孩子与生俱来的本能 [美]艾莉森•高普尼克/[美]安德鲁•梅尔佐夫/[美]帕特里夏•库尔 2023-03-31 02:29:21速效学习辅导法:60招化解父母焦虑
在当今社会,如何学习才是最重要的问题。教育学教授、学习问题专家斋藤孝的畅销书《学会学习》在日本上市仅一个月就销售超过了20000册。这本书介绍了60种简单易行的学习辅导法,可以快速地缓解父母们对孩子学 [日]斋藤孝 2023-03-31 02:29:52给爸爸妈妈的儿童性教育指导书
一本书为中国父母讲明白儿童性教育。本书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委托编写的《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为主要理论框架,给出了儿童性教育的指导标准。帮助父母按照科学、全面的性教育指导理论,对孩子进行专业的性教 明白小学堂 2023-03-31 02:31:28好妈妈就是家庭CEO
在本书中,作者提出了“好妈妈就是家庭CEO”的理念。这种理念不仅将妈妈视为孩子的首席教育官,更将其视为先进教育理念的首席执行官。这一理念的提出打破了妈妈们原有的自我认知,赋予“妈妈”这个角色更为深刻的 熊莹 2023-03-31 02:32:04© 2023-2025 百科书库. All Rights Reserv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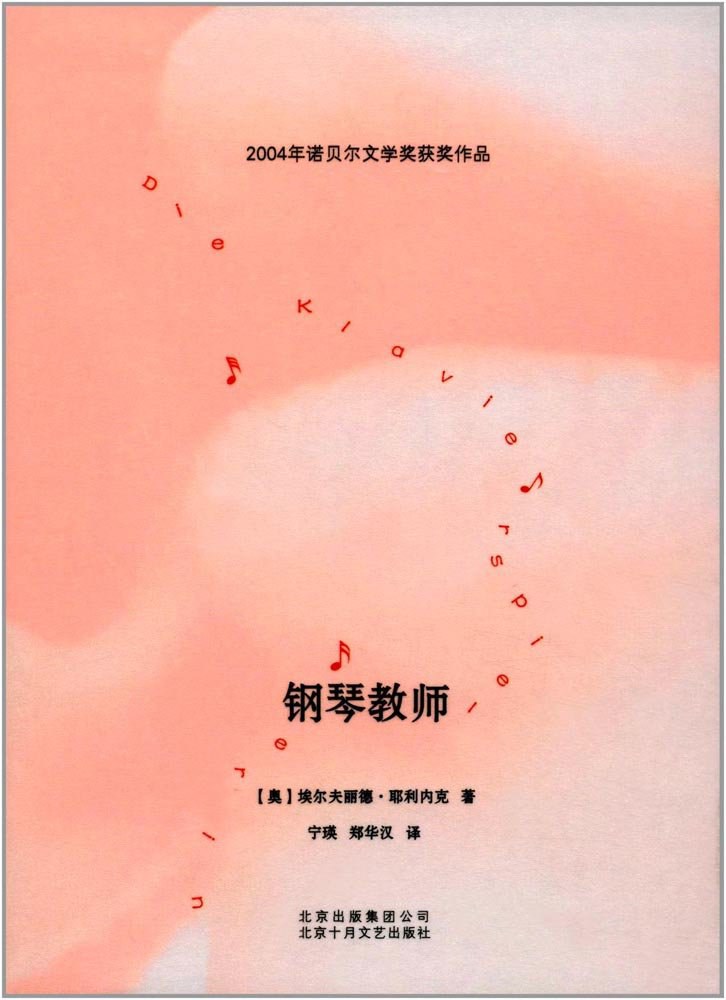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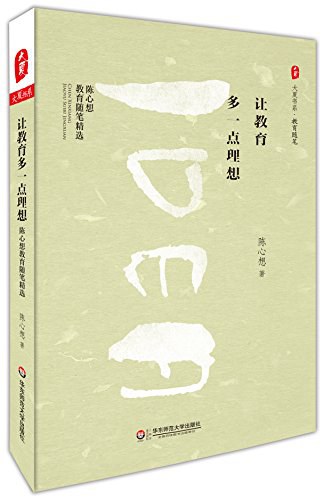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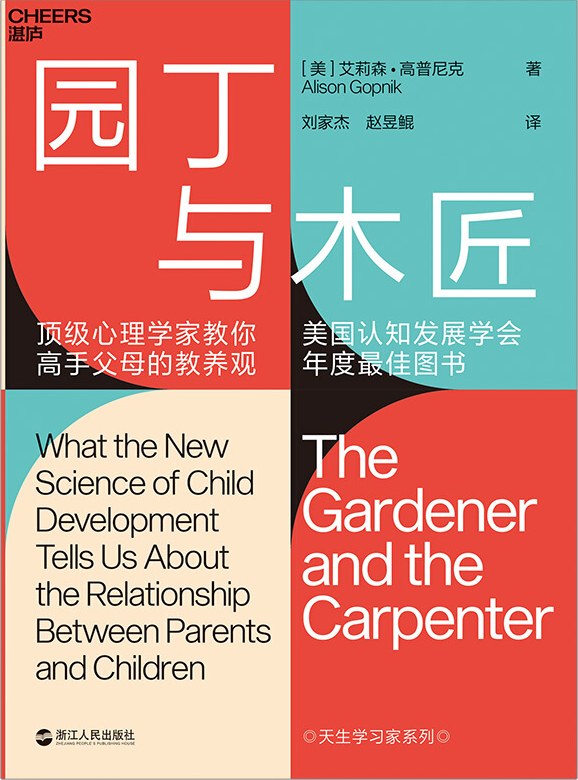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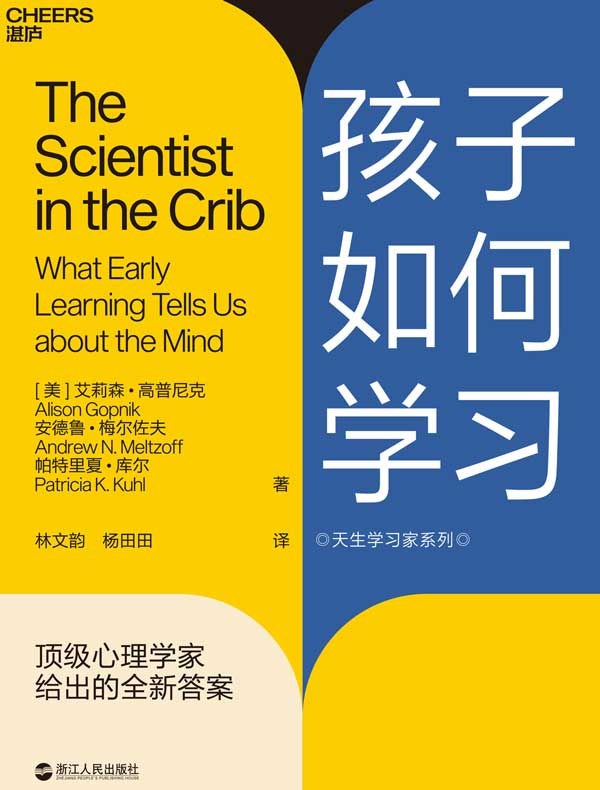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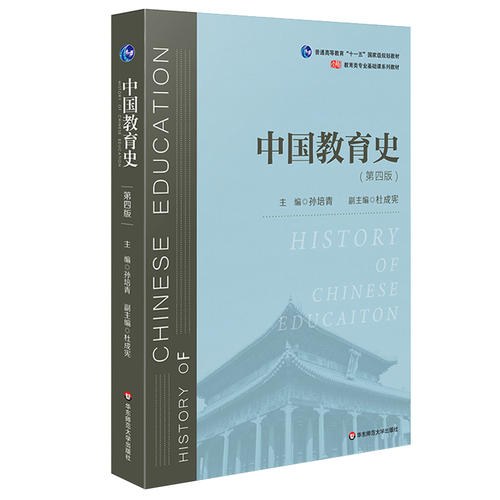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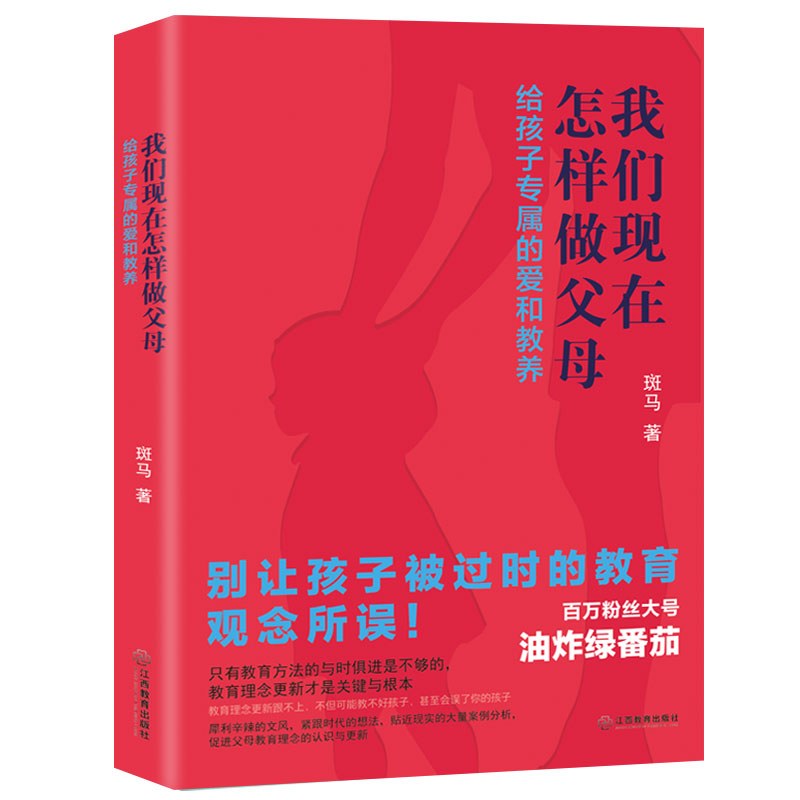


发表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