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堂吉诃德的眼镜:小说十二讲摘录
书名:堂吉诃德的眼镜
1
0

霸气小魔女 2023-07-22 11:31:36
《堂吉诃德的眼镜:小说细读十二讲》张秋子
第一讲《密室》:文学中的时空 洛丁根,他已经发现了世界是由各种“偶然”组成的,甚至连河边一块恰好出现的潮湿的石头,都令他感受到了恶心。生命的必然之轻几乎承担不起命运的偶然之重,我们几乎无法接受任何“意外”。博尔赫斯的名篇《环形废墟》也在讨论这个问题,他的写作明确地让我们意识到,如果说时间的循环是把意义放到了原点,那么空间的循环则彻底放逐了意义。社会学家们为生活中的这种秩序感正名,彼得·伯格在《现实的社会建构》中认为,日常生活里经验层面上的稳定性是人类社会的必然产品。我们依靠惯例、制度让周遭的生活变得易于理解又很省力气,不必冒险试错。文学始终讨论的是一种有限的、例外的、部分的义域,它关注的是大网下面的海域;而社会学关注的则是大网本身。
第三讲《好人难寻》:文学与恶的距离 当代法国哲学家巴塔耶注意到“孩子”与“恶”之间的神秘关联。他认为,好的作家总有点邪性,乐于保持着一种“不负责任的、孩童般”的态度,与成人世界所要求的规矩、责任、秩序感相反。比如卡夫卡,他一门心思只想写作,对一切世俗的工作和婚姻都犹豫抗拒,写作的狂热也带上了孩子气的味道,因而被巴塔耶认为是有点邪性的。尼采首先注意到善恶的概念在不断滑动。他认为被一个时代感受为恶的东西,通常是以前曾被感受为善的东西的不合时宜的尾音,是某个更古老理想的返祖遗传。康拉德在《黑暗的心》中流露出与尼采相似的观点:文明只是胜利者对弱者建立的暴力秩序,弱者要反抗的话,只能同样以暴力还击。文学与道德中的恶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古典世界存在一种善恶的不对称性,只有文学中会大量描写具体的恶。然而随着道德与文学的分离,近代社会宗教影响的衰落和对善恶划分的怀疑,恶开始具有了一种反抗和反叛的意味。最终,道德与文学同步教化的关系断裂,当代作家越来越喜欢谈纯粹的恶,以此发起对道德的攻击与质疑,他们的作品也越发摆脱对读者的道德责任。
第五讲《幸福》:文学中的“意义感” 在意义发明的前夜,人与意义浑然一体。但在某一个时刻,一场人与既定意义的脱钩发生了,被称为“大脱嵌”。个人由前现代的整体性宇宙秩序中脱离出来,把自己看成是“独立自由的个体”,开始为“自我”谋划新的意义。这个变化可以从卢梭开始算起。而“大脱嵌”在文学中最典型的体现就是:文学在客观世界的“参照点”逐渐消失。比如莎士比亚的剧作中,如果出现人类社会的行为,那么自然世界、客观世界也会出现对应的反映。人们曾相信人的行为与自然世界密切相关甚至对应。
第九讲《旅客》:文学与自我 《旅客》中,讲述人小时候常常因为看到灰色影子而感到惊恐。这大概是一种象征:人的主体意识还不完全,小说用其表现生命的懵懂与混沌意识。他觉得死亡倒不可怕,最可怕的是那些反复出现、不变的、猜得到的、杂乱无序的、我们对此无能为力的、相互撕扯着的东西。此时,未来还没全部涌来,一切也都不可知,包含在未来维度的自我就像一个尚未明晰但显然可感的存在,我们并不知道自己会长成怎样的人,那个未来之我的形象就成了一种恐怖的诱惑,一种充满拒绝的靠近。到了长大衰老的时刻,人对自己的认知近乎完成,虽然不一定真的认清。托卡尔丘克用一个戏剧性的情节来描述人的成长,小说中的讲述人说到姐姐每晚用“兴奋又虚张声势的音调来吓唬他”,给他讲鬼故事。他成年后感谢姐姐,正是那些故事给
相关推荐
现实的社会建构
彼得·伯格是一个奥裔美国社会学家,以其在现象社会学领域的研究和新保守主义观点的代表性而闻名。他与卢克曼私交深厚,在长期合作中有着紧密的联系。他的主要研究兴趣包括宗教社会学和经济发展的社会学理论。他的社 [美国]彼得·伯格/[美]托马斯·卢克曼 2023-12-07 00:11:59幸福
牛津通识读本第100种重磅出品,带你领略收获美好人生的科学指南。该书让你告别心灵鸡汤,用理论解读幸福。彭凯平,积极心理学家、清华大学心理学系教授,为此作序推荐。自古以来,幸福一直是人类毕生追求的目标, (美)丹尼尔·M.海布伦(DanielM.Haybron) 2023-03-26 23:09:25园丁与木匠
孩子不是无意义的打闹,而是在学习社交互动;孩子不是在简单地玩玩具,而是在探索世界;孩子不是因为无聊才问为什么,而是在寻找答案。那么,当孩子在玩的时候,他们到底在学习什么呢?他们是如何学习的?而对于父母 [美]艾莉森•高普尼克(AlisonGopnik) 2023-03-31 02:28:48孩子如何学习
-出生42分钟,婴儿就能模仿大人的脸部表情;6个月大宝宝就能区分各种语言的不同;3岁孩子能在两分钟内测试5个科学假设……人们一直以来认为孩子的学习是被动的,需要教导,但科学证明学习是孩子与生俱来的本能 [美]艾莉森•高普尼克/[美]安德鲁•梅尔佐夫/[美]帕特里夏•库尔 2023-03-31 02:29:21速效学习辅导法:60招化解父母焦虑
在当今社会,如何学习才是最重要的问题。教育学教授、学习问题专家斋藤孝的畅销书《学会学习》在日本上市仅一个月就销售超过了20000册。这本书介绍了60种简单易行的学习辅导法,可以快速地缓解父母们对孩子学 [日]斋藤孝 2023-03-31 02:29:52给爸爸妈妈的儿童性教育指导书
一本书为中国父母讲明白儿童性教育。本书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委托编写的《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为主要理论框架,给出了儿童性教育的指导标准。帮助父母按照科学、全面的性教育指导理论,对孩子进行专业的性教 明白小学堂 2023-03-31 02:31:28© 2023-2025 百科书库. All Rights Reserv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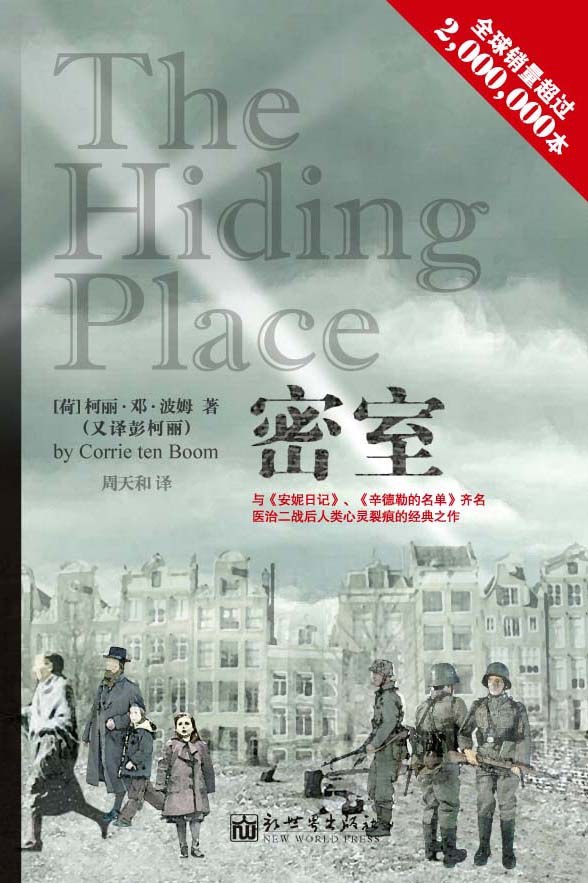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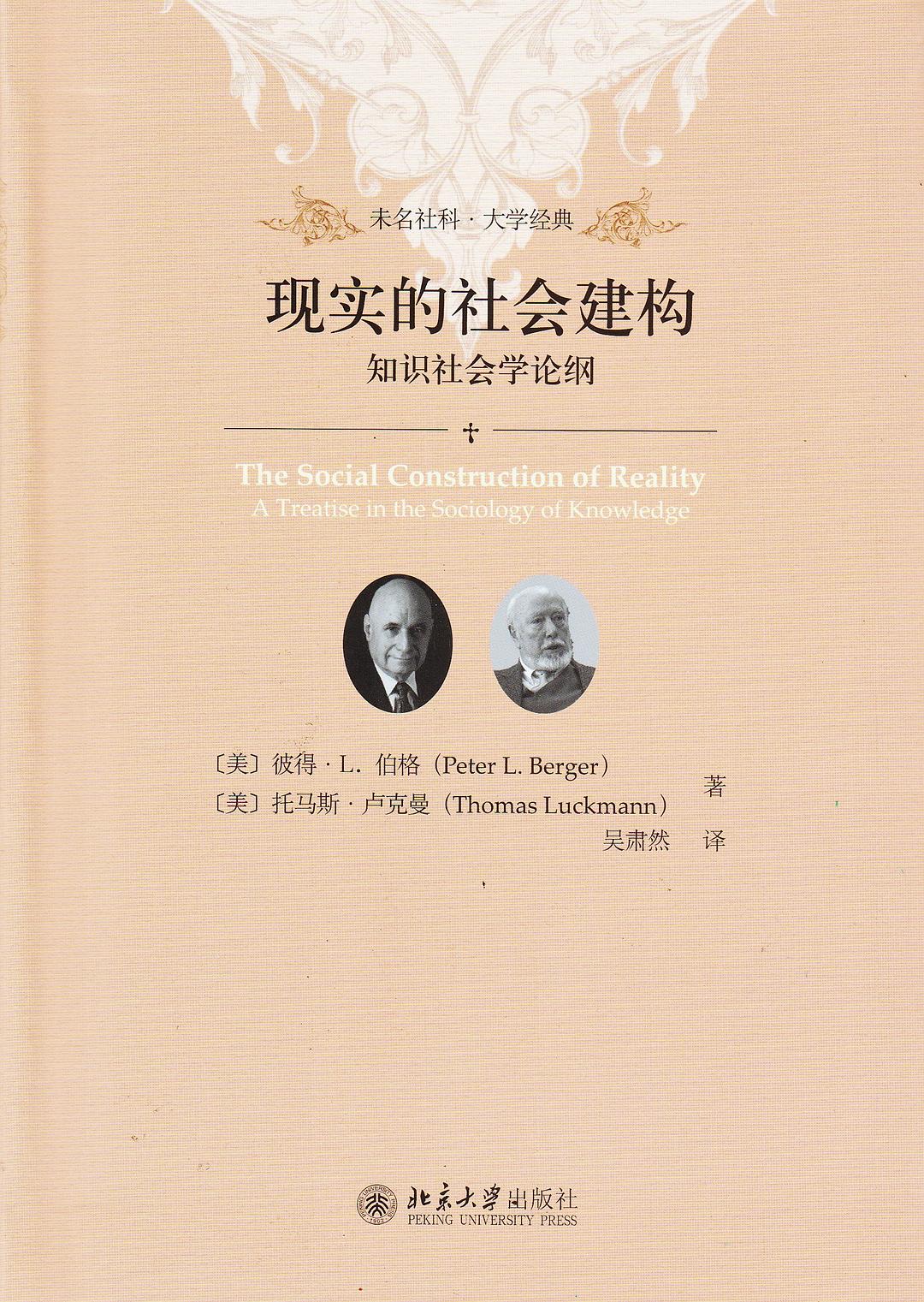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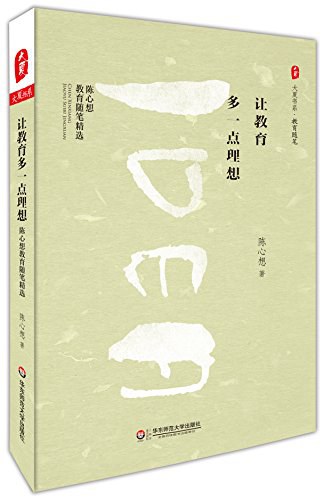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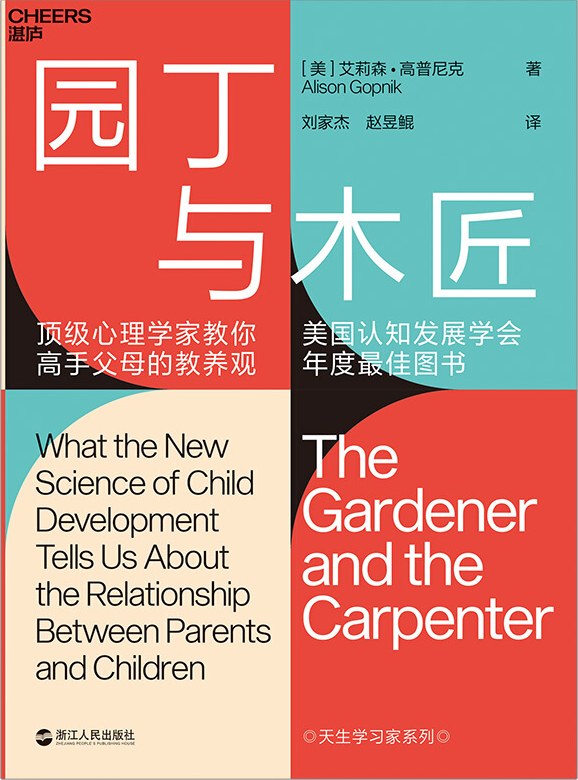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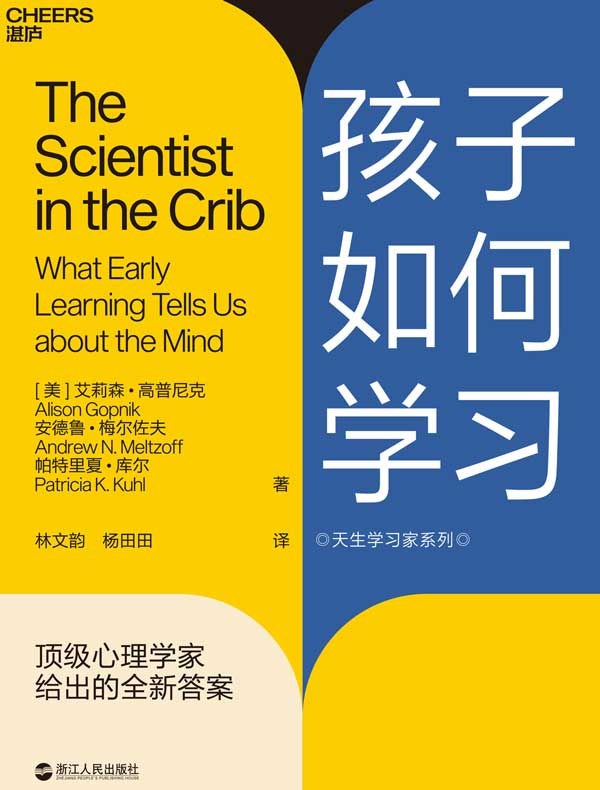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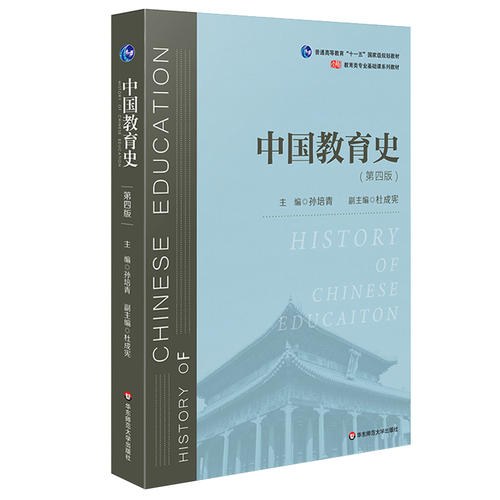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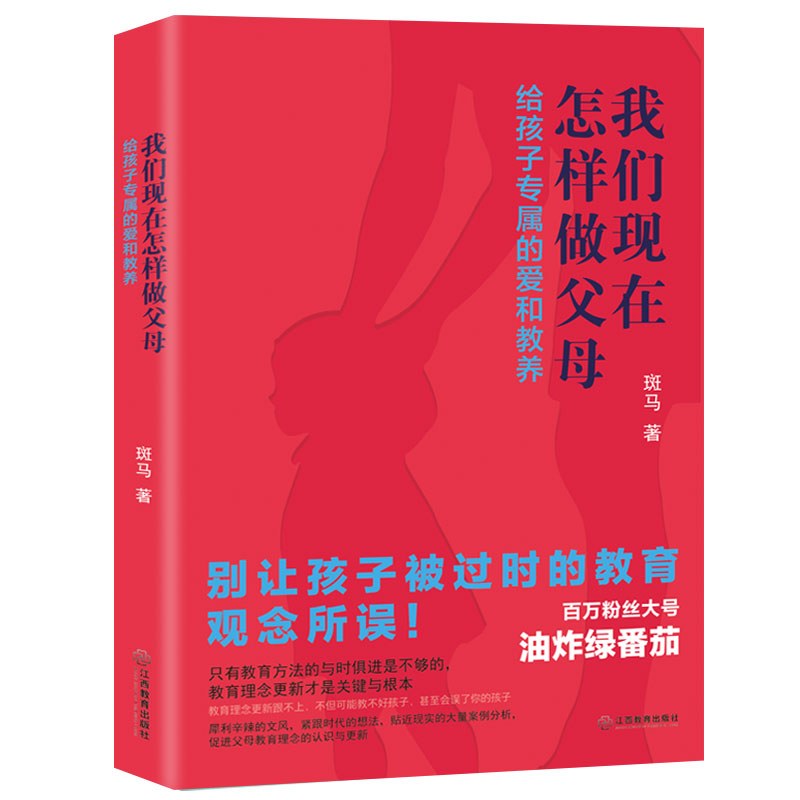

发表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