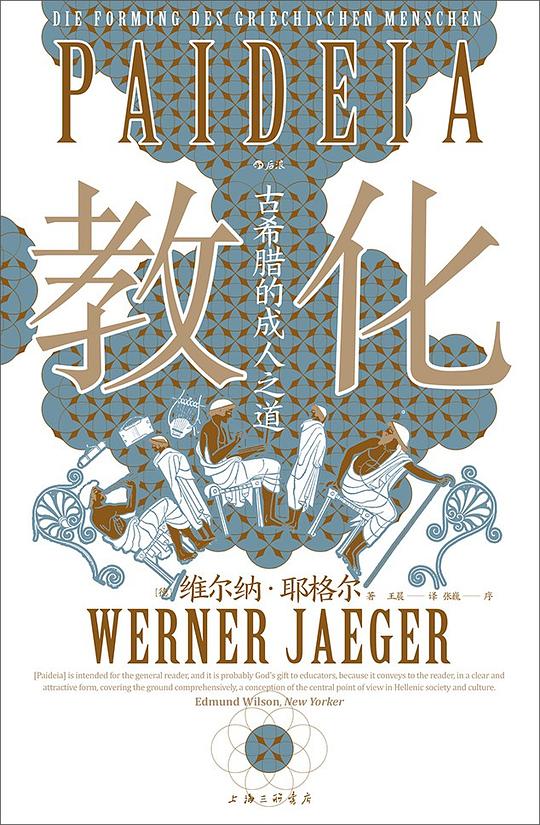
"时代综合教化"
书名:教化
1
0

完美小仙女 2023-09-13 10:43:32
古希腊教化(Paideia)旨在陶铸理想之人,把人教育成他们永恒和本质的形式,即作为理念的人,让灵魂向着神明和真正的存在攀登,离开形成与消逝的可见世界的泥沼。这种诞生于贵族典范教化的传统在柏拉图的理念论中达到顶峰,直至马拉美的诗篇亦有回响:“当我述说‘一朵花’,我的声音便遗忘、放逐了花的所有轮廓,作为超越花萼的真正理念与温存之美,如音乐般徐徐升腾,那是一朵在所有花束中都无法觅得的花。”古典学的研究动力源于追摹现在与过去的精神联系,以语言符咒和文学遗产,从时间坟墓里唤起千秋伟人的思想意绪,如西塞罗所言:“人生一世有何可为?莫不过记载旧日事迹,将其编织进古代先祖的生命中去。”就像两千多年后,当丘吉尔想唤起英国直面德国威胁的激情时,他自比“德摩斯梯尼”,将希特勒称为“腓力”。在此意义上,西方伪史论即使为真,其意义也被大大削弱了,毕竟“人世间最强大的权力也是短暂的,只有看上去弱不禁风的精神之花才会不朽,即便最幸运民族的尘世命运也只是这种智慧的整个历史创造中的一天。”对于自诩古希腊传人的现代西方人,如伊索克拉底所言:“和只与我们拥有共同祖先的人相比,与我们共享教化的人是更崇高意义上的希腊人。我们必须把对教育和教化不敬的人看成像渎神者一样可憎。”换言之,西方古典文明没有历史,它不过是现代社会的素材。轴心时代的文明都将个人置于更广大的宇宙-伦理秩序中,由此,人的全部行为都是有意义的整体,将生命奉献给观看更高的神圣秩序。这是一个综合的时代,没有人不会被古代先贤“带着人类少年时光和创造性天才的清新晨风走出人昏暗内心”的时刻感动。对于希腊人而言,其“自由在于,他们将自己作为组成部分纳入城邦的整体及其法律。国家只是为与其本质上相同的正义之人的肖像提供了空白的画框。”如此才能理解柏拉图对诗歌和音乐自由的攻击,因为悲剧要对整个城邦的精神负责,也才能理解色诺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对斯巴达国家教育形式的推崇。几乎所有哲学教科书对古希腊哲学的介绍都未将古典学范畴下的成果综合予以考量,对神话/宗教、文学艺术、自然科学、具体科学乃至实用技艺对哲学的影响考量不足,例如因果论、目的论可能都诞生于物理观察或者经验医学,以及诗人对这些现象兼具诗意与哲理的表达。而历史研究也很少能照顾到这些细索的成果,比如伊索克拉底的修辞学派对雅典政制史写作的影响。“教化”确实可以作为古典文明研究的背景,将诗歌、音乐、竞技/战争、数学、天文、造型艺术、法律、戏剧、修辞、历史、哲学、医学等等均纳入照看。堕落的民主制和随之而来的僭主制,雅典和斯巴达的对立,对政治领袖的幻想,泛希腊思想以及与波斯/马其顿的对抗……如修昔底德所言“注定将以同样或类似方式重新发生”。这类“恶毒”的隐喻就像神显,使人堕入更为消极的生命观,就像晚年的欧里庇得斯“学会了赞美对某种超越理性边界之宗教真理的谦卑信仰所带来的幸福,即使他没有这种信仰。”以下文字值得全文引用,揭示了人作为道德主体理应拥有的关于“选择”的知识和态度:“未来的僭主克里提亚斯写了一部悲剧,宣称神明是城邦统治者的巧妙发明,为了避免人们因为没有证人而违法,他们把神明塑造成仿佛永远在场但看不见的证人,知晓人的一切行为,从而通过对神明的敬畏让人们服从。从这点来看,我们就理解了柏拉图为何在《理想国篇》中构思了巨革斯指环的寓言,这个指环能让佩戴者从身边人的眼中隐形。指环区分了两种人:一种是出于内心正义性而行事正直的人;一种只是外表合法,其唯一动机是顾及社会形象。德谟克利特在伦理学中赋予了内心羞耻这个古老的希腊概念以新的意义,他抛弃了在法律面前的羞耻这种被安提丰、克里提亚斯和卡里克勒斯这类智术师的解释,代之以人们在自身面前的羞耻这种了不起的想法。智术师的成就在于其天才的形式教育艺术,而他们的弱点在于,作为其教育内在内容来源的精神和道德实质存疑。但那是所有同时代人的通病。”
相关推荐
园丁与木匠
孩子不是无意义的打闹,而是在学习社交互动;孩子不是在简单地玩玩具,而是在探索世界;孩子不是因为无聊才问为什么,而是在寻找答案。那么,当孩子在玩的时候,他们到底在学习什么呢?他们是如何学习的?而对于父母 [美]艾莉森•高普尼克(AlisonGopnik) 2023-03-31 02:28:48孩子如何学习
-出生42分钟,婴儿就能模仿大人的脸部表情;6个月大宝宝就能区分各种语言的不同;3岁孩子能在两分钟内测试5个科学假设……人们一直以来认为孩子的学习是被动的,需要教导,但科学证明学习是孩子与生俱来的本能 [美]艾莉森•高普尼克/[美]安德鲁•梅尔佐夫/[美]帕特里夏•库尔 2023-03-31 02:29:21速效学习辅导法:60招化解父母焦虑
在当今社会,如何学习才是最重要的问题。教育学教授、学习问题专家斋藤孝的畅销书《学会学习》在日本上市仅一个月就销售超过了20000册。这本书介绍了60种简单易行的学习辅导法,可以快速地缓解父母们对孩子学 [日]斋藤孝 2023-03-31 02:29:52给爸爸妈妈的儿童性教育指导书
一本书为中国父母讲明白儿童性教育。本书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委托编写的《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为主要理论框架,给出了儿童性教育的指导标准。帮助父母按照科学、全面的性教育指导理论,对孩子进行专业的性教 明白小学堂 2023-03-31 02:31:28好妈妈就是家庭CEO
在本书中,作者提出了“好妈妈就是家庭CEO”的理念。这种理念不仅将妈妈视为孩子的首席教育官,更将其视为先进教育理念的首席执行官。这一理念的提出打破了妈妈们原有的自我认知,赋予“妈妈”这个角色更为深刻的 熊莹 2023-03-31 02:32:04打破你的学生思维
重新优化后的语句并排版分段:这本书踏实质朴,包含大学生最关心的99个问题,例如不知道自己的优势在哪里、到底要怎样做出选择以及如何规划职业发展方向。这本书鲜活真实,回答者从亲身职场阅历中提供独到见解,拓 北京职慧公益创业发展中心 2023-03-31 02:32:38© 2023-2025 百科书库. All Rights Reserv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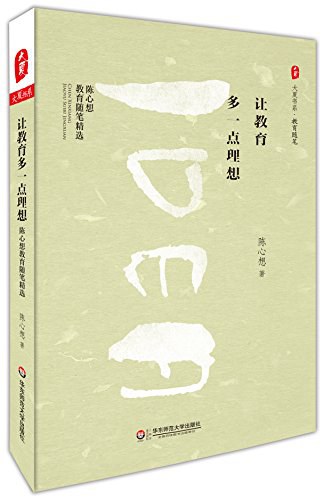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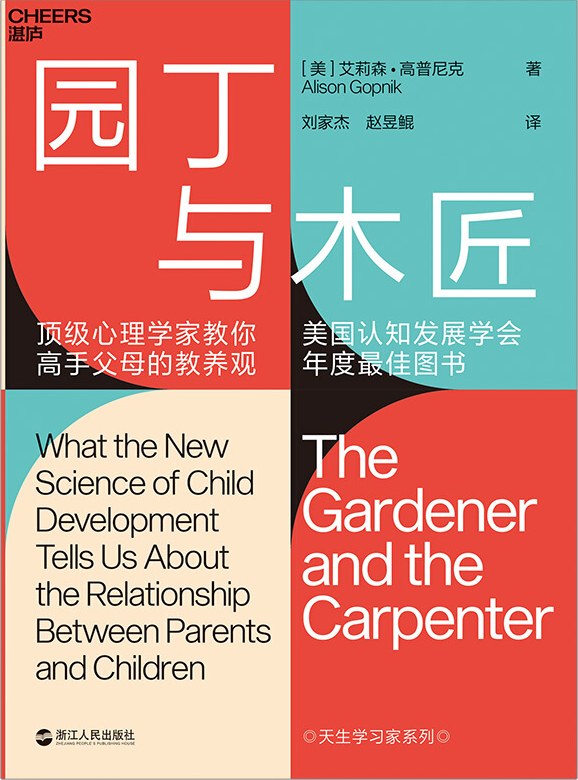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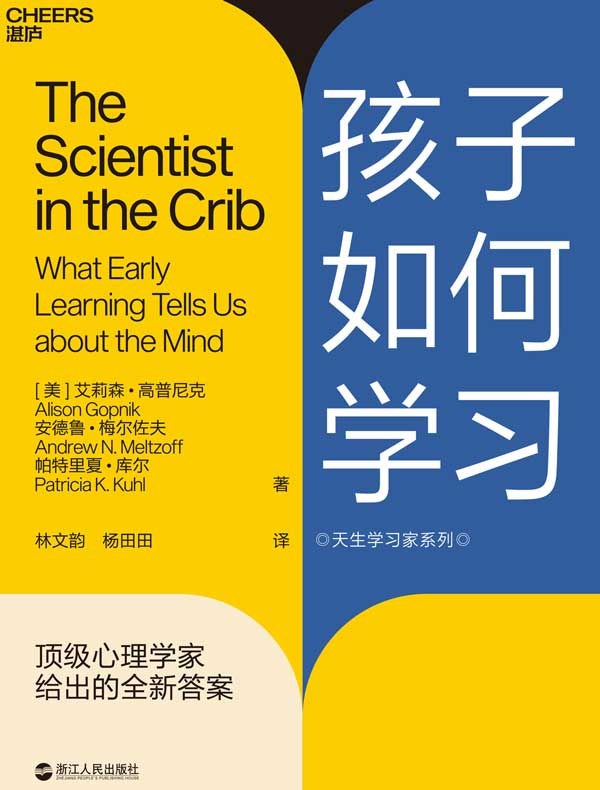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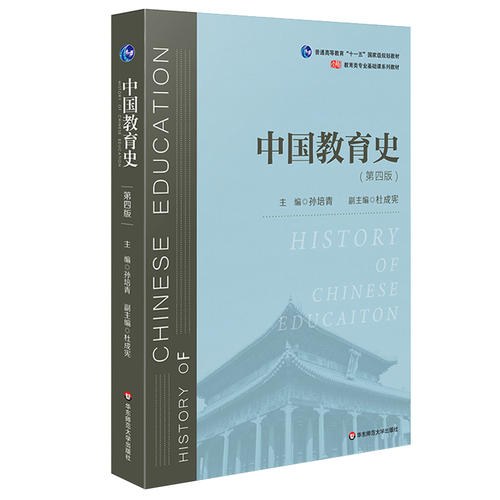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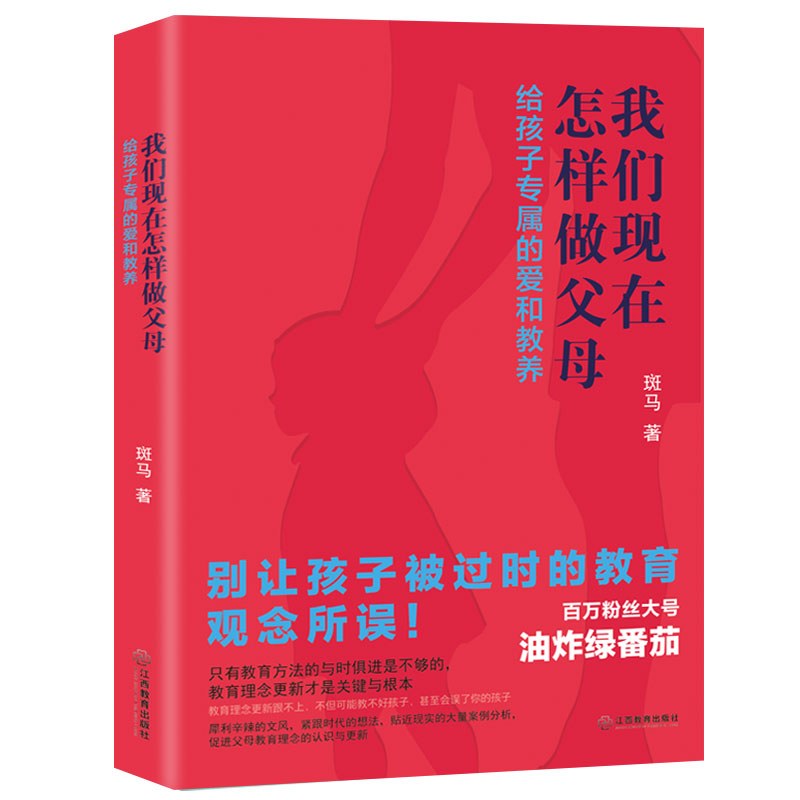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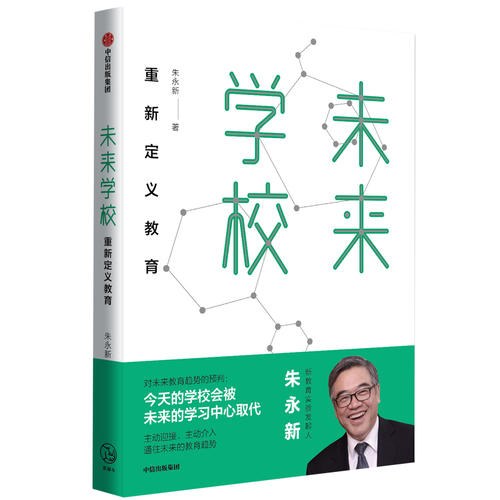

发表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