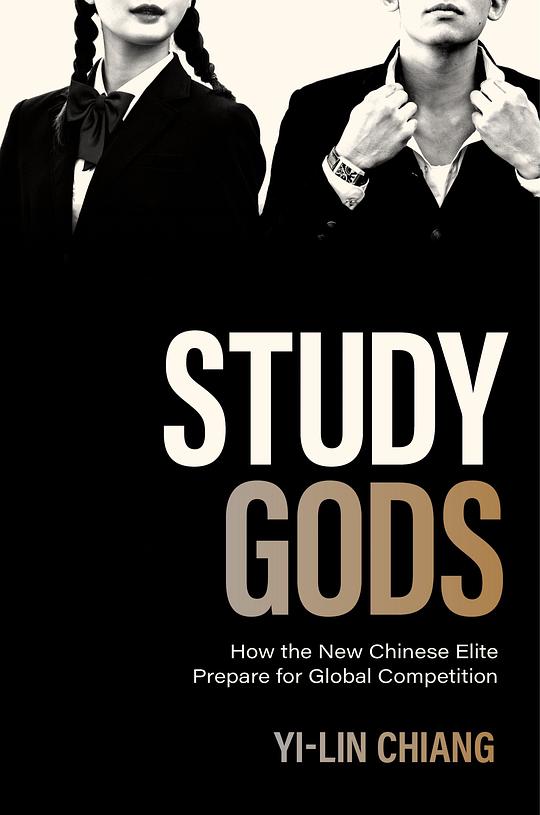
《Study Gods》"社会与精英的相互塑造"
书名:Study Gods
1
0

壮年大叔 2023-09-24 23:06:55
本周看的书《StudyGods》讨论了高中时期社会精英的培养。尽管有人提及本书样本量太少,我还是认为书中的对象都十分典型。模型当然并非世界,但它有助于我们理解世界。在我国,教育的目标是进入顶尖大学。高中时期,学生可分为学神、学霸、后进生、差生。划分标准由两条线组成:一是能否进入顶尖大学(能的话是学神、学霸),二是能否轻易进入顶尖大学(能的话是学神)。
这一体系是全社会共同构建的,无法避免。作者并未评价这一体系的优劣,正如无法评价不同国家教育体制下所塑造的精英。国家并非是不可突破的边界,但对于其他阶层,这一体系正在持续产生何种影响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首先是学生之间、学生与家长之间、家长与学校之间的影响,其次是在学生毕业后的工作和生活中。
如果追求世俗的成功,那么熟悉这一体系的规则,并朝着体系所设定的目标走是不可避免的选择。
1. 关于成年后的期望的想法与一个人的社会经济背景密切相关。儿童的家庭背景、个人和人口特征以及与之接触的人将决定他们的结果,这些影响在整个青春期发生并产生意义。
2. 精英们对地位再生产的基本规则非常熟悉,这是他们在追求地位再生产方面成功的原因之一。
3. 学生们害怕从地位阶梯上跌落下来,以至于他们常常拒绝追求更高的地位。然而,在每个群体中都有一些后进生通过努力工作上升到社会地位,他们也目睹了其他人努力并成功地成为“学霸”。尽管在他们周围的流动性情况下,学生们通常认为地位的结果是不可改变的,超出了个人的控制。天赋论在学生中造成了一种无力感,促使他们在理解学校地位结果时采取一种坚忍的态度。学生们经常将地位的结果归因于命运。
4. 一个学生在耶鲁发现自己不够学霸资格后,她本能地想通过成为一个学习狂来保持自己的地位,努力学习。当她努力工作的策略失败时,她立即寻求表现出轻松,以避免降低地位。毕业后,她故意找了一份无法与在耶鲁或首都大学读书的朋友们相媲美的工作。尽管知道其他人认为她大材小用,她仍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份工作,以显示自己的轻松(“省去了找工作的麻烦”)...她在纽约市每天工作到深夜。公司对她的表现很满意,因此在找工作之前就给了她一份工作机会。然而,她没有在公开场合或在她的男友面前提及这些努力,她仍然是耶鲁大学的毕业生。她表面上的轻松掩饰了她的努力。
5. 年轻的精英们习惯性地用考试成绩和后来的工作表现将彼此分为不同的地位群体,就像他们在高中时所做的那样。因为这些评估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同伴关系,学生们在以后的生活中会本能地使用同一套规范来接近、回应和与同伴互动。因此,青少年时期的同伴互动成为他们成年早期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同伴互动模式的前身。
6. 值得注意的是,华庭的母亲在面对华庭的愤怒时表现出害怕的迹象(颤抖、站在一边、哭泣、走开)。华庭后来就读于香港中文大学。然而,看到学校不满意的地位,她转学到牛津大学第二年。在我们的文字交流中,华庭说她的父母对她的成就感到非常高兴。当我询问相关的额外费用(估计每年56,000美元)时,她回答说,在英国接受高等教育的费用是“没那么高”。后来她对这个话题置之不理,声称她的父母从来没有对费用表示过任何关心,声望才是最重要的。
7. 低成就者婉茹与母亲的亲子互动与高成就者与父母的亲子互动形成鲜明对比。与华庭的母亲不同,婉茹的母亲一点也不害怕女儿。邓女士可以在公共场合随意羞辱女儿,多次要求女儿站在自己的毕业照后面。尽管这些行为显然让婉茹很不高兴(面无表情,假笑),但母亲并不在意。
8. 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与学生的身份结果密切相关。家长在支持学生身份制度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仅提供资源和参与学校,当年轻人有资格与全球精英竞争时,父母使他们能够毫无后顾之忧地竞争。因此,这场迈向全球精英地位之争不仅涉及年轻一代,也涉及他们的精英父母。
相关推荐
园丁与木匠
孩子不是无意义的打闹,而是在学习社交互动;孩子不是在简单地玩玩具,而是在探索世界;孩子不是因为无聊才问为什么,而是在寻找答案。那么,当孩子在玩的时候,他们到底在学习什么呢?他们是如何学习的?而对于父母 [美]艾莉森•高普尼克(AlisonGopnik) 2023-03-31 02:28:48孩子如何学习
-出生42分钟,婴儿就能模仿大人的脸部表情;6个月大宝宝就能区分各种语言的不同;3岁孩子能在两分钟内测试5个科学假设……人们一直以来认为孩子的学习是被动的,需要教导,但科学证明学习是孩子与生俱来的本能 [美]艾莉森•高普尼克/[美]安德鲁•梅尔佐夫/[美]帕特里夏•库尔 2023-03-31 02:29:21速效学习辅导法:60招化解父母焦虑
在当今社会,如何学习才是最重要的问题。教育学教授、学习问题专家斋藤孝的畅销书《学会学习》在日本上市仅一个月就销售超过了20000册。这本书介绍了60种简单易行的学习辅导法,可以快速地缓解父母们对孩子学 [日]斋藤孝 2023-03-31 02:29:52给爸爸妈妈的儿童性教育指导书
一本书为中国父母讲明白儿童性教育。本书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委托编写的《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为主要理论框架,给出了儿童性教育的指导标准。帮助父母按照科学、全面的性教育指导理论,对孩子进行专业的性教 明白小学堂 2023-03-31 02:31:28好妈妈就是家庭CEO
在本书中,作者提出了“好妈妈就是家庭CEO”的理念。这种理念不仅将妈妈视为孩子的首席教育官,更将其视为先进教育理念的首席执行官。这一理念的提出打破了妈妈们原有的自我认知,赋予“妈妈”这个角色更为深刻的 熊莹 2023-03-31 02:32:04打破你的学生思维
重新优化后的语句并排版分段:这本书踏实质朴,包含大学生最关心的99个问题,例如不知道自己的优势在哪里、到底要怎样做出选择以及如何规划职业发展方向。这本书鲜活真实,回答者从亲身职场阅历中提供独到见解,拓 北京职慧公益创业发展中心 2023-03-31 02:32:38© 2023-2025 百科书库. All Rights Reserv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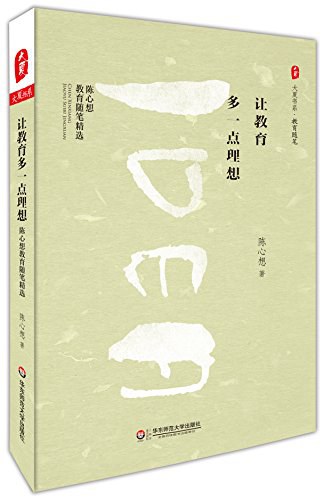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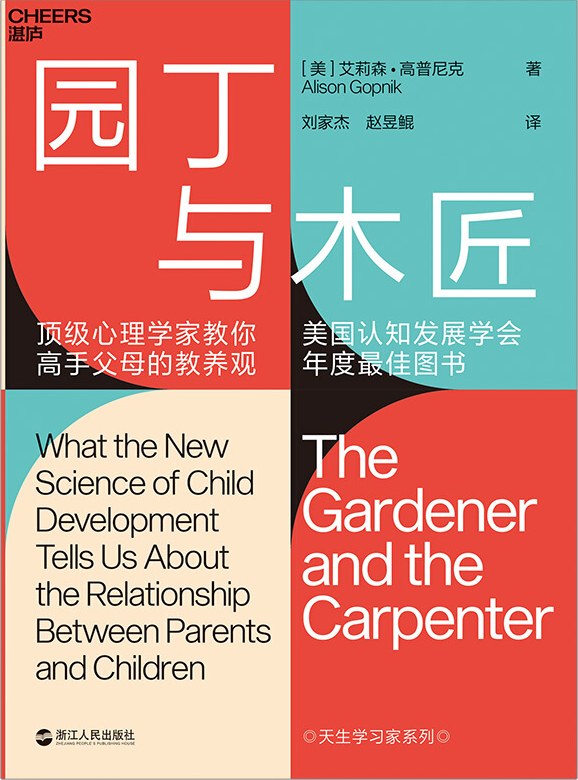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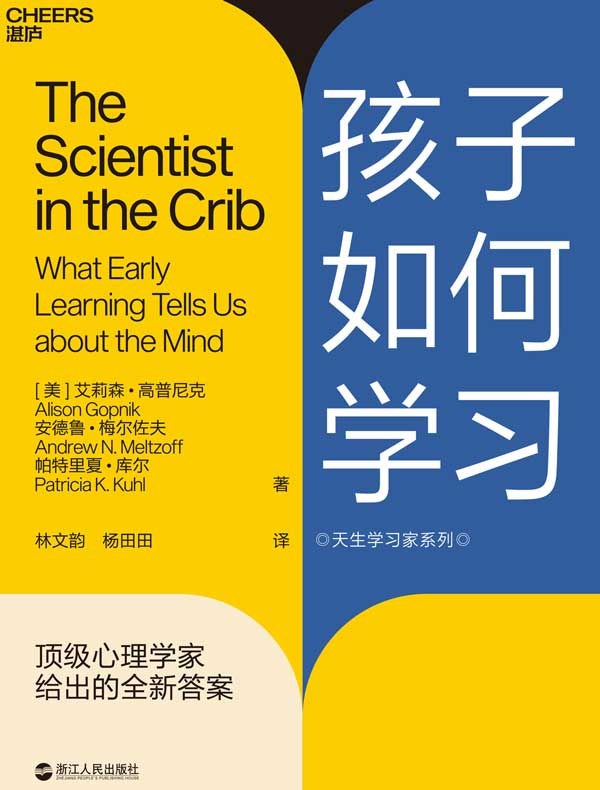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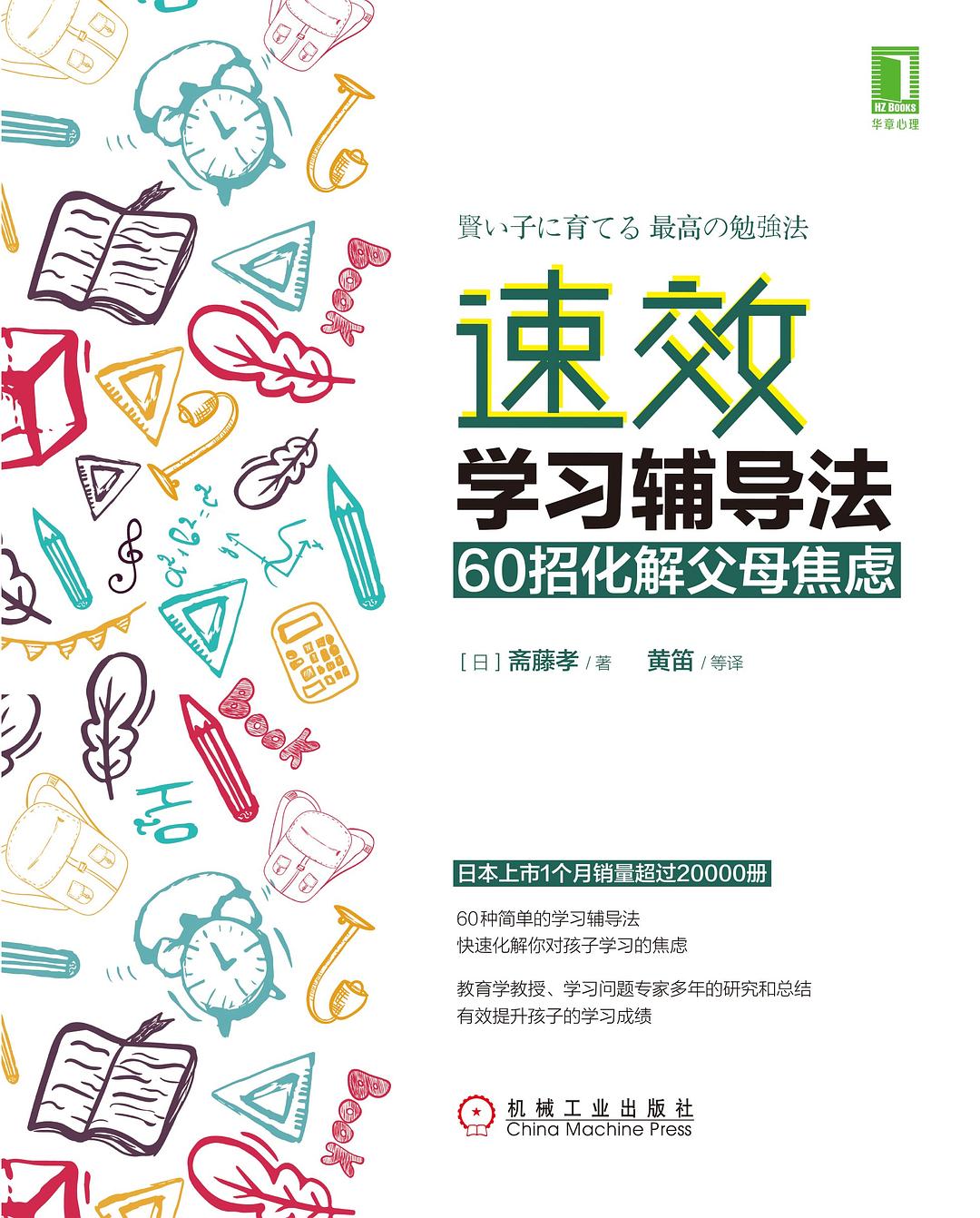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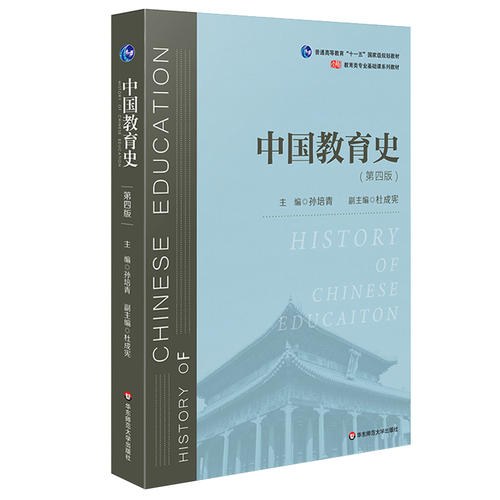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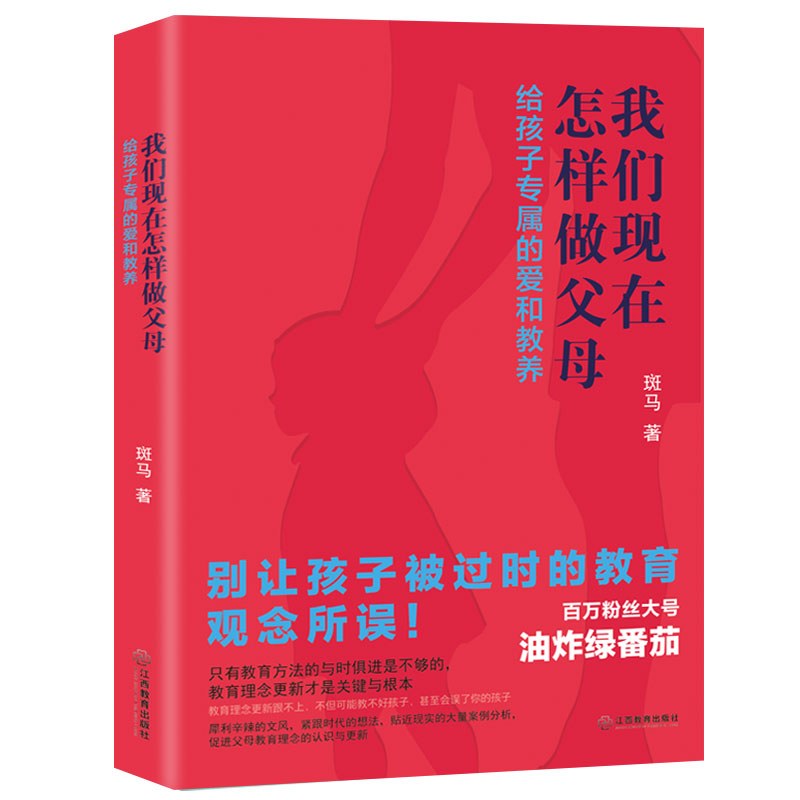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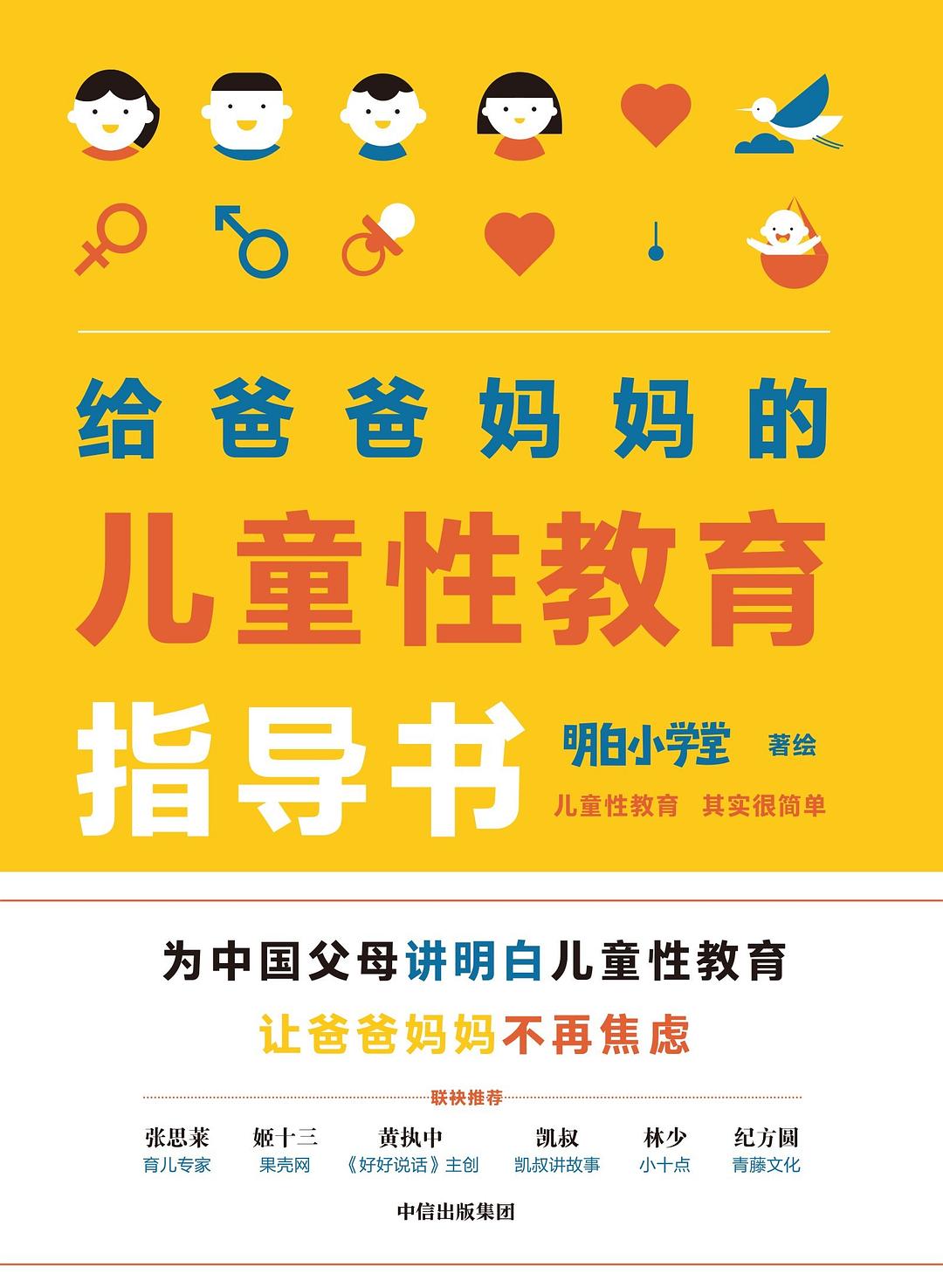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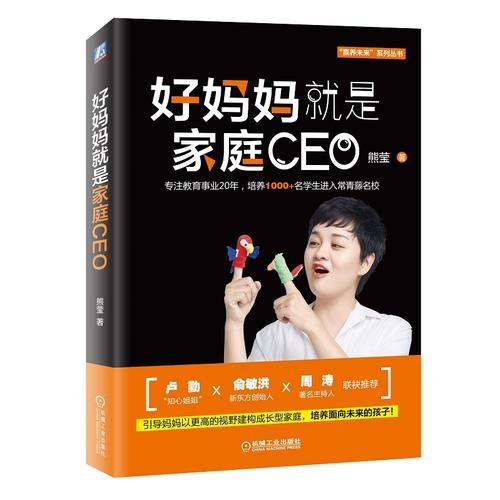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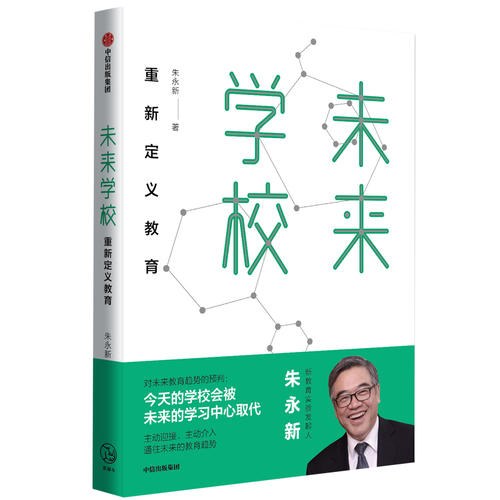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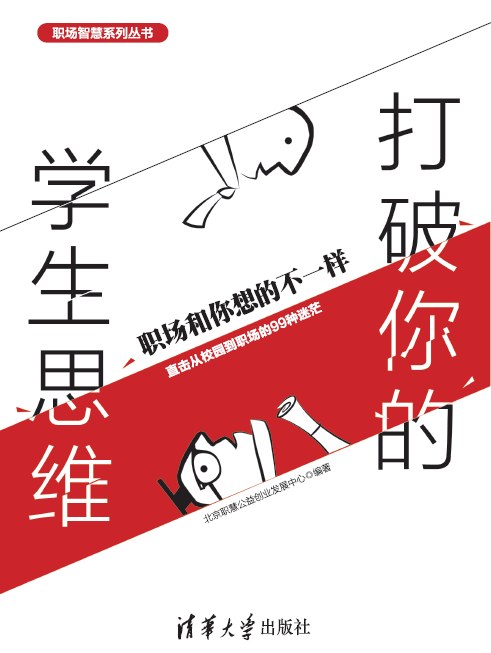
发表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