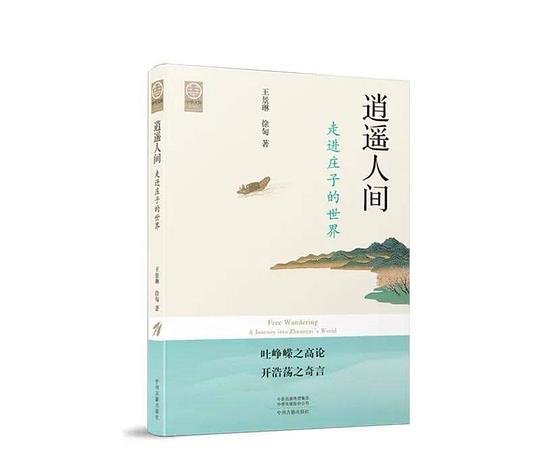
《逍遥人间》逍遥庄子-心灵航行
书名:逍遥人间
1
0

帅气小皮球 2023-09-17 09:17:50
(文章刊于《中华读书报》2023.6.7日)文/俞耕耘《逍遥人间:走进庄子的世界》一书可谓庄子的导引之作。从书名可见,作者强调了两大要素:庄子对理想世界的虚构,对现实世界之俯察。《庄子》是两种世界的交战交融。在《庄子的世界》之后,王景琳、徐匋写出这部更贴近大众理解的新作,实现了深且易,精与通的书写效果。《逍遥人间》的结构也如内、外、杂篇一样,既包含对庄子其人,《庄子》其书,庄子其交游与时代的周边介绍,又有对文本专题的核心阐发与细读。作者并未因袭于旧说,而是不断以反诘、论辩及追问形式,与历代庄子注解者“对话”,提出新解。这也是此书融合新知读物与研究专著的书写姿态,既有文化通识之面向,又不失学术考论之谨严。如庄子以托寓为主,譬喻虚构为能事,关切个体精神生存,很少对国家治理有直接性论述。然而,这并不意味庄子对政治理想存而不论。书中探究了这种隐而不显的建构——至人、神人和圣人的层级、比类与秩序。一反前人注解将三者等同的旧说,阐发了至人之民、神人臣子和圣人君主对应的政治序列。它看重文本语境间的隐秘关联,通过人物的出现、连属类型,暗示庄子的论述逻辑。在我看来,三者实质都归于“忘”的境界,在于忘己,忘事功,抑或忘天下。换言之,作者在不同篇章,找出了可以化约,比附和共通的隐喻符号。如庄子提及圣人,就谈尧治天下民,平海内政,欲让位许由,求无名之治。讲“圣人之才”,就提卫灵公和齐桓公的治国之才。而那些形体怪异,或残或缺的畸人,不过是考验君主认知层次的“案例”而已。“像卫灵公、齐桓公这样的君主,不能说没有‘圣人之才’,但仅仅有‘圣人之才’却没有‘圣人之道’,还是成不了圣人君主的。”他们还没有放弃残与全,美与丑的观念,距离万物一,道通一的认识境界还差很远。这种解读的真正意图,乃是暗示庄子的政治理想,始终与审美理想、生存论同构在一起。圣人君主的提法,很容易使人联想西方“哲人王”的构想,德行与智慧和权力的同一同构。《逍遥人间》凸显出庄子与先秦诸子的殊异之分,也阐释他何以成为“异数”,超拔而绝尘。这全在于作者以阶层归属,生存位置和心理认知诸方面,把握庄子作为出离者、外位者和反观者的身份。无论儒、墨、兵、法与纵横,都是政治的实际参与者,其学派学说无一例外都直接指向政治实践。所谓道德教化、礼乐秩序、变法改革、刑名之学皆是治理模式。甚至,兵家也始终将用兵,视为内政的配合延伸。可以说,诸子之学大多是社会精英,文士阶层匡世的方案竞逐。然而,庄子跳脱这类著述“比武”“竞选”思维。他远离权力中心与社会上层,而以边缘和外位心态,乐于做一个观察家、同情者与批评家。从老子到庄子,道家因为关注人心人欲,天道恒常,性命之理,从而更贴近个体生命,人类生存的整体关切。“他选择了站在文人士子的阵营之外,从人心、人性、人的生命的角度来挖掘并分析这一切苦难、灾祸产生的根源”。如果从人类和自然的宏大论域反观现实,那个兼并纷纭,诡诈倾轧的战国,本微不足道。这种清醒劝谕,饱含庄子对文士阶层命运的悲悯剖析——如对知识论的再思,对价值论的反省,对人格异化的批判。我认为其内核归于:如何于乱世“全其身”,怎样安生、重生与养生。这种看似悲观的保守,实质是对时代环境的自我估量,它出于生存智慧。庄子始终都在处理各种相对关系:如大知小知,材与不材,用与无用的对立统一。反观大多文士都汲汲于声名,置于险境,还不自知,无法善终,难得保全。作者看重庄子对人心的分析,“无己”和“丧我”,才是去私与齐物的关键所在。战国诸子相互攻击诘难,往往正是偏狭聚焦于利害的结果。“大知闲闲,小知间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所言,描摹了“热衷于是非之争的文人士子的神态情貌”。然而,小大之辨并非是层级高下的差别,如果认为大就比小优越,就并不符合庄子齐物的核心。无论言论的小大,“听起来振振有词,其实不过是自说自话,并不能得到任何的证实,也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这一感慨也切中如今人文学科的要害。研究者能得到庄子本人的认同首肯吗?如果能得到,就叫“证实”。结果是当然得不到。所以,“知”与“解”不必纠结,谁比谁更优越,没有终极评判。回到战国,那些沉溺于终日论辩“心斗”,求取“小成”与荣华之人,无限内耗生命,为外物奴役,终究扭曲异化,失于生命本质。这类士人对声名的求取,与如今学院里对职称之追求,全然相类。庄子不屑于此,虽有批判,却也无奈同情,心有悲哀。庄子正视完全“去成心”并不可能,因为人受形而有身。从而,最优解是“坐忘”。它对应虚、静、明的心态,是遗忘己心,而并非去除。反之,则有“不忘以待尽”的结局,只能等待老化和死去。这一悲哀与海德格尔所言一生所“烦”,向死而生的命题殊途同归。书中重视庄子的言说策略和理论面向,他对于乱世的理解,显然超出社会现象的分析维度。我将其概括为,庄子看重一种“心因”性,偏向以精神现象,生存状态审视政治现实。即使谓之政治心理学色彩,也并无过分,人心的通病最终会成为社会症候。庄子“着眼于个体的人,从人的行为、心态、本能、本性上深入挖掘。”知、心和物是一套发生逻辑,人格异化对应于社会关系,形成臣子算计狡诈,国君暴戾无厌的现实。“这样的问题无法完全归罪于政治制度或者社会环境。庄子深刻地意识到人心本身的缺陷、人的各种欲望、人心的复杂而萌发出的种种‘恶’也是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因素。”《逍遥人间》也论述庄子的世界方法论问题——“游”。可以说,庄子之“游”,融合认识论,存在论和方法论的枢要。它在《逍遥游》《人间世》《齐物论》《大宗师》《德充符》中反复出现,其核心是处世与安生的态度与方法。可以归结为,不同于入世和出世的“游世”。精神自由的超脱,离不开周旋于俗世,只不过是“对这一切外在的观念统统不以为意,不固执己见,不偏狭拘泥,而以一种超脱虚空的心态”,做到安顺。作者的眼光在于把“缘督以为经”作为保生、全生、养亲和尽年的策略原则,将“庖丁解牛”之故事譬喻视为一种实操注解,如此可避刑之祸,名之累。“督”为中间路径,解牛的“游刃”也在筋肉之“间”。我想,它暗示游走于缝隙的生存技术,犹如一种“界限的本体论”,永远处于阴阳交咸的边界上,技近乎道,又彰显道。在材与不材之间,以无用之用来保全,悬置了世俗价值的评判体系。“庄子似乎从来不忌惮使用任何在世人眼中卑贱、粗俗、浅陋、污浊的事物来强调保命的意义”。其目的在于用缺、残和畸等特征,质疑世人对“用”和“材”的固有观念。《大宗师》进一步提炼出现世生存态度,即“真人”的态度。不同于圣人,神人和至人的序列,真人与众人相比,强调一种可修炼,可企及的理想生命状态。其与中正平和的人格有所互通,同时也是道家养生思想的体现。“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出入往来终始,全都“受而喜之,忘而复之”。庄子从身体生理,说到心灵状态,最后得出“不以心损道”,与道同一的结论。作者从中指认,所谓大宗师正是真人的存在。大宗师自成身教,行不言之教,天下士人自归其下,非招致而来。这与真人的“不谟士”,是暗合相通的。更重要的是,书中分析了真人具体的历史性。从古之真人到今之真人,是有现实承载的,而非抽象概念。真人是人间的效法榜样,大宗师是现实世界的真人。我想,这种论述实质揭开庄子沟通儒道的一个隐秘路径。庄子并非简单“非儒”,从他赞赏尧和许由的事迹,就能见出端倪。真人“以刑为体,以礼为翼,以知为时,以德为循”。庄子用刑、礼、知、德概括了一整套治理模式。我认为,这别有深意,如果我们反观儒家所言,礼乐刑政是也,就能窥探出庄子理论灵活兼容的现实考量。在本质上,庄子从预设前提上,消解了儒道的鸿沟,天人关系既非对立,也不超越,而是齐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与天为徒,其不一与人为徒。天与人不相胜也,是之谓真人。”齐一不是合一,而是本就是一,天是自然,人亦是自然,社会现实关系也是自然。《逍遥人间》重游庄子的世界,建构了庄子精神之渊海。此作的难得,是呈现庄子的心性气质,我称为诗性哲学的双重性——既立足于人间,又托寓出意象世界。“《庄子》内篇实际上记述的就是庄子从倾心营造藐姑射之山,又眼见它一步步坍塌的全部心路历程。”逍遥与无待,只是高蹈寄托,《齐物论》是一个转向,“抨击更多于向往,孤傲更多于憧憬”,到了《人间世》已变为一种悲哀、无解和漠然。这实质表明了叙述心态的不断沉降,是庄子从理想主义、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和批判主义的心灵史。
相关推荐
萤火谷的梦想家
艾莉森•麦吉出生于1960年,是美国《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同时也是大都会州立大学创意写作课的教授。她的作品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并出版,也曾被提名普利策奖,并获得苏斯博士奖金奖、克里斯托弗图书奖、美国 [美]艾莉森•麦吉/[美]克里斯托弗•丹尼斯/绘 2023-03-27 16:50:25© 2023-2025 百科书库. All Rights Reserv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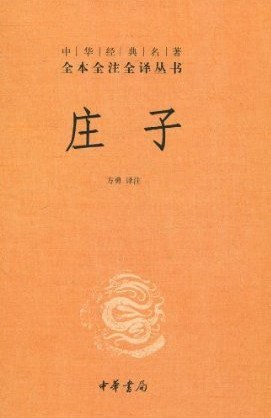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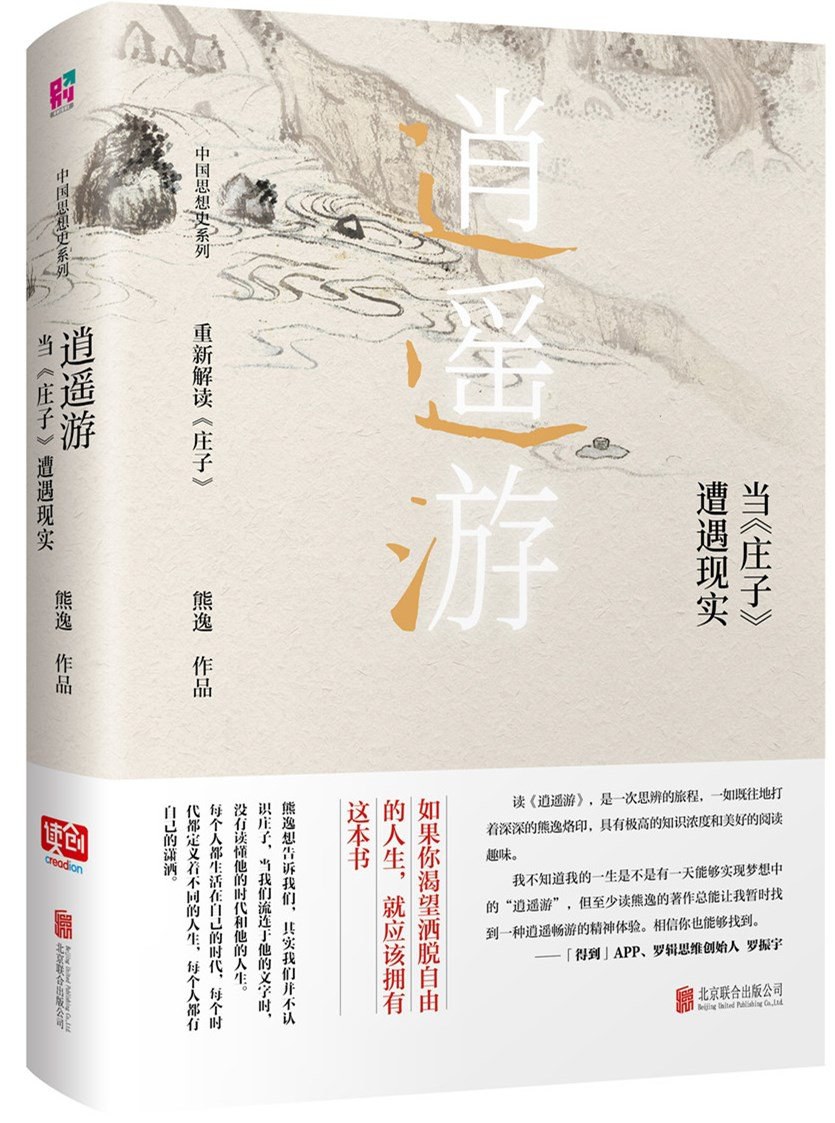








发表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