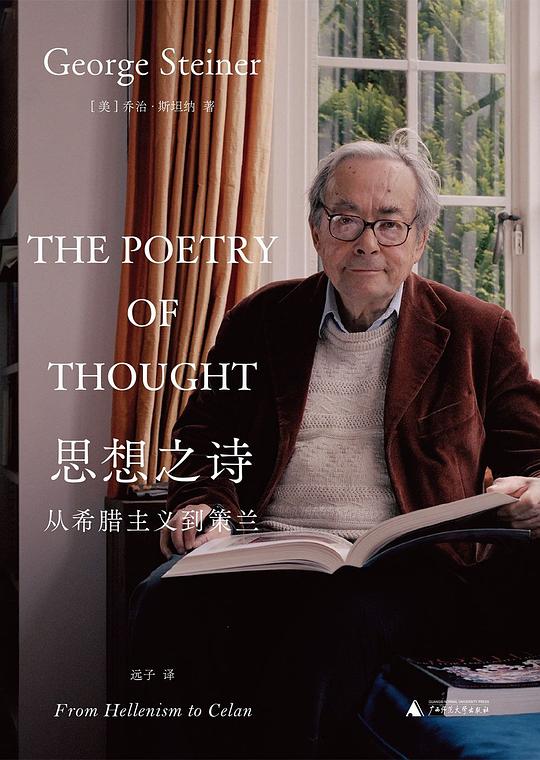
思想之诗:哲学与诗的无言奇境
书名:思想之诗
1
0

飞鸟集 2023-09-08 19:28:48
哲学的修辞本来天然充满诗意的节律,它始终无法否认自身探求真理的内核之内的文学重心。语言和文字既不能像音乐一样体现无限共同的却又歧义的多重涵义,也不能像数学般是精确的、通用的、可证伪的而拥有最简洁的优美。
我们回到爱奥尼亚,一切似乎都起自这个古希腊的边陲小岛。为什么形而上学和诸种学科、音乐和文学能够出现?那时候它们还没有被明确的区分,哲学在今天拥有着众学科之母的头衔,而诗的最本质的源头或者说逻各斯则有挑战它或至少并驾齐驱的资格——它甚至早于哲学。人类关于“抽象”的能力真的只能用“奇迹”形容,2600多年前的先贤们“赋予了无用之物首要的地位”,虽然至今依然还在为是非功利争论不休。思想与诗都同样追求着最初的不可复现的“本源”,人们用诗或者其他符号念诵它们为“一”为“道”为“存在”为“整理”,巴门尼德和笛卡尔跨越千年发出音调:“我思”时“存在”。哲学解释,而诗,试图超越。
我们一直用思想和诗,既解释世界、现实,又极力探索桎梏着思想的文字的边界,越是不能越是想要超越它、摆脱它,摆脱文字甚至摆脱思想本身,思想到了极致就是对思想本来的限制。完整的冗长在晚近的时候让位于残片的审美,也有人曾追问如今看到的残缺是否在古早的一开始拥有过完整。如果苏格拉底是某个节点,赫拉克利特最初用诗吟唱神秘和真理,巴门尼德仍然在规则形成之外倾听,而恩培多克勒更“精微”。卢克莱修唤起拉丁范式的“理性”。但丁则是杂合性的,他包容与涵盖。文学和戏剧张力在柏拉图这里,我相信苏格拉底的“不朽”生命是由他重新建构的。但他否认了自己,转而希冀在秩序中创造绝对的理智。
文学和戏剧张力在柏拉图这里,我相信苏格拉底的“不朽”生命是由他重新建构的。但他否认了自己,转而希冀在秩序中创造绝对的理智。对话体的形式是柏拉图关于记忆与文字之间的妥协,后来也继续发挥着显著的作用。伽利略、休谟、瓦莱里……他们的《对话》中形而上学和现实看见之间有了实在性的转圜。瓦莱里坚信“意义或观念只是影子,而表达的结构具备某种实在性。”人类用文字留住出转瞬即逝的“一点灵光”。如果我们始终无法厘清“从意识到自我意识再到理性的概念化,语法是如何将这种既发生在自我的直接性里,也发生在与他者的相遇里的转变外化出来?”那么我们如何理解黑格尔?语言、文字都萦绕着法则的阴影,我们默认语法决定着思想的模式,那么使用两种不同语法的思想如何碰撞出真实的火花?两个思想的合奏能否容纳第三第四个“伴音”(翻译、转译)?马克思对现实描写的催人泪下完全媲美雨果、欧仁·苏或狄更斯;尼采是“一位将抽象思辨、诗歌和音乐融为一体的哲学家”;伯格森的直觉主义启发了普鲁斯特和意识流写作,至于弗洛伊德,如果没有“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式的”,西方文学的走向可能截然不同……诗歌容纳哲学,哲学成就文学。最后一个被描述的诗人是策兰,该如何形容他?“生活的陌生人”,还是匆匆过客?静静顺延着作者的述说由自己的思绪翻滚,他确实带我们领略和窥见(即使以前并不认识)到从古希腊开始,诗人与哲学家那些隐喻、晦涩,彼此统一又对立,相互映射又分道扬镳的企图。
相关推荐
哲学的底色
作者的目标是让本书变得容易理解,读者只需轻松阅读即可获益。真、善、美、自由、公平、正义是人类追求的主题,也是哲学的根本意义。在本书中,作者采用通俗易懂的叙事方式,让哲学思想逃脱晦涩难懂的语言,使读者可 [美]莫提默·艾德勒 2023-03-25 16:12:16美学权力
【编辑推荐】1.作者在哲学家从认识论和形而上学等不同的面向对“美学”进行理论奠基时,看到了“接受理论”或者“艺术理论”的困境。她指出纯粹理论化的不足,并对抵制“美学”彻底抽象化做出了努力。2.作者圣吉 [法]巴尔迪纳·圣吉宏 2023-05-26 02:56:51康德《实践理性批判》句读
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是他哲学体系中的重要部分之一,于1788年出版。相比于前一部作品《纯粹理性批判》的任务是研究人类认识力先天要素之规定,本作则关注于理性实践中的先天原理,考察其可行性、范围和限制。 邓晓芒 2023-03-25 16:13:27游世与自然生活:庄子评传
庄子是战国中期伟大的思想家,他所关心的许多问题仍存在于当代,他的思考仍启迪着今人。颜世安教授以隐者传统和道家思想为背景,以郭象所注三十三篇本《庄子》为依据,博采庄子研究众家之长,从全新角度解说庄子,阐 颜世安 2023-05-26 02:39:07古典柏拉图主义哲学导论
:这本书对于柏拉图主义哲学史进行了全面的梳理,时间跨度长达九百年,涵盖了从学园开始到晚期新柏拉图主义的整个历程。书中详细研究了代表性人物的主要观点和彼此的思想联系,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柏拉图主义哲学的全 梁中和编著/梁中和 2023-03-25 16:14:25如果我们错了呢?
用有意思的知识,验证有价值的思维方式。《如果我们错了呢?》是美国知名哲学思维畅销作家查克•克洛斯特曼挑战传统文学、文化与科学知识的上乘之作。这本书被《出版人周刊》、《科克斯书评》等13家媒体评选为年度 [美]查克•克洛斯特曼 2023-04-10 20:30:38© 2023-2025 百科书库. All Rights Reserv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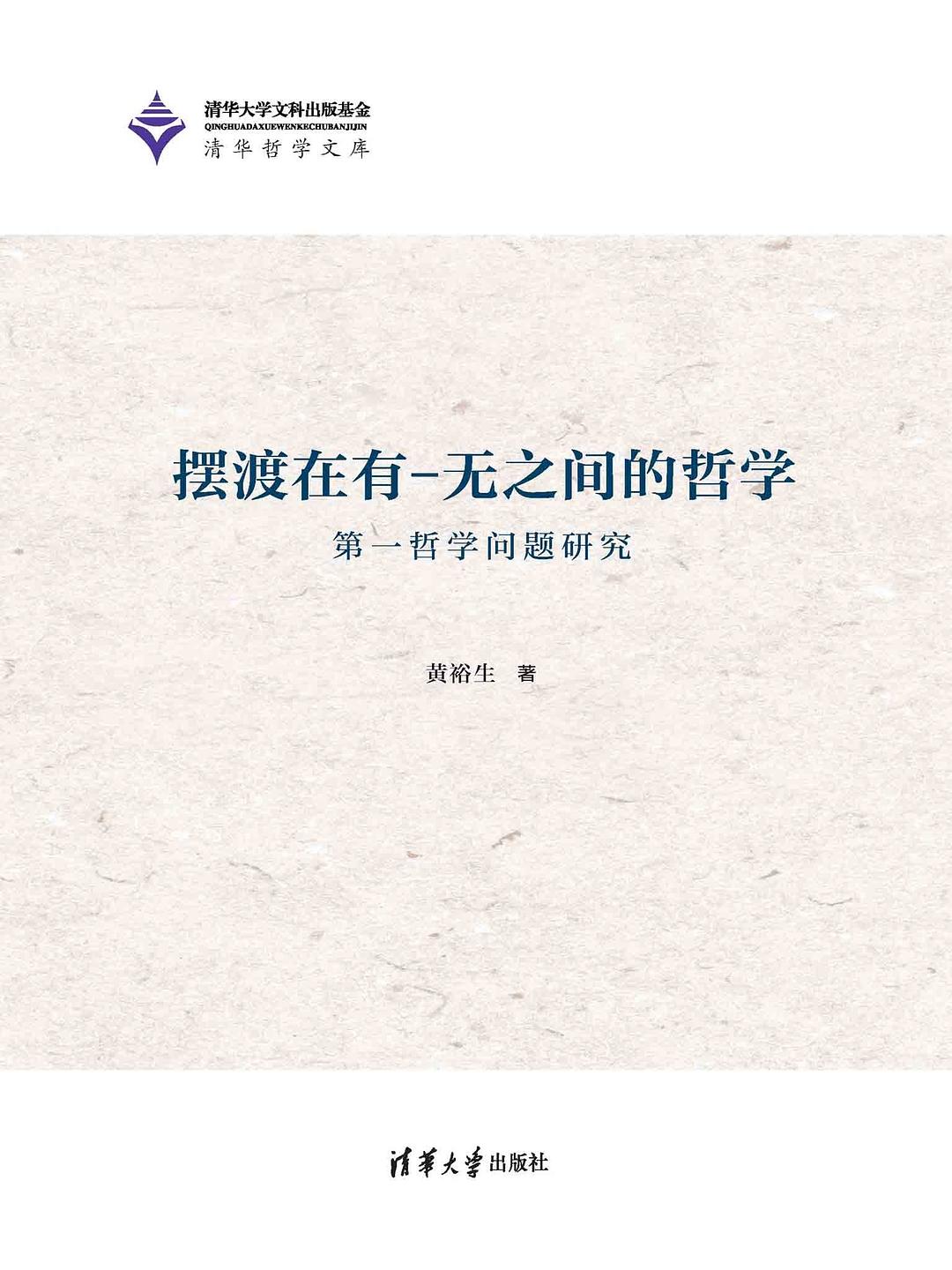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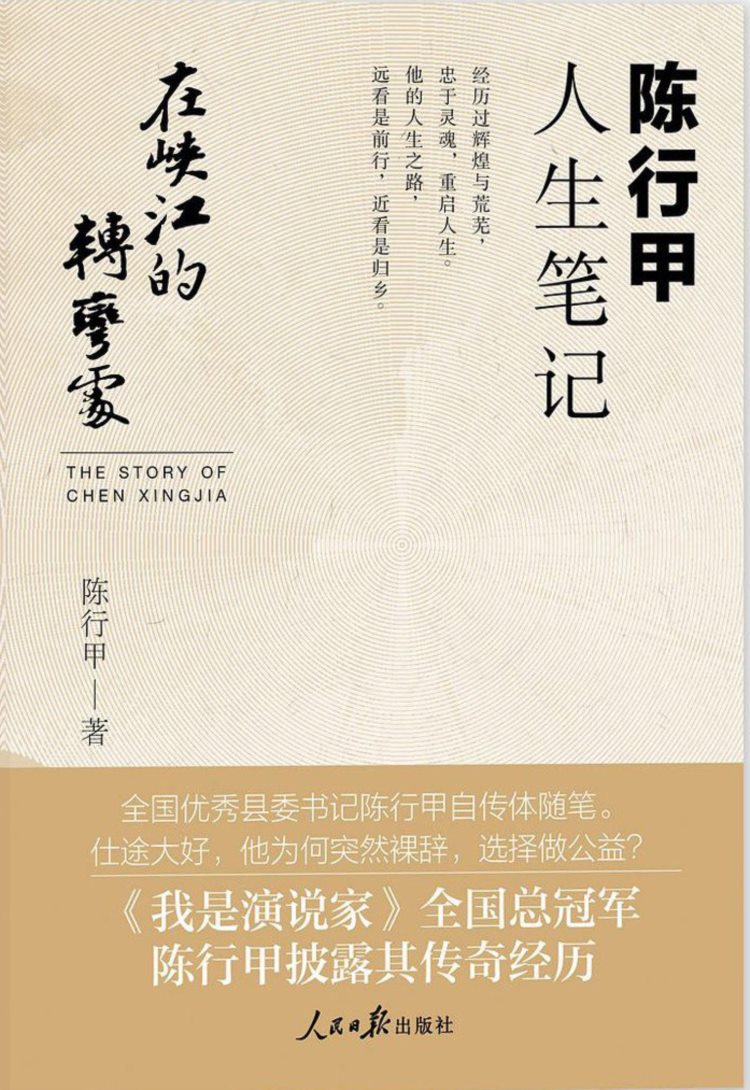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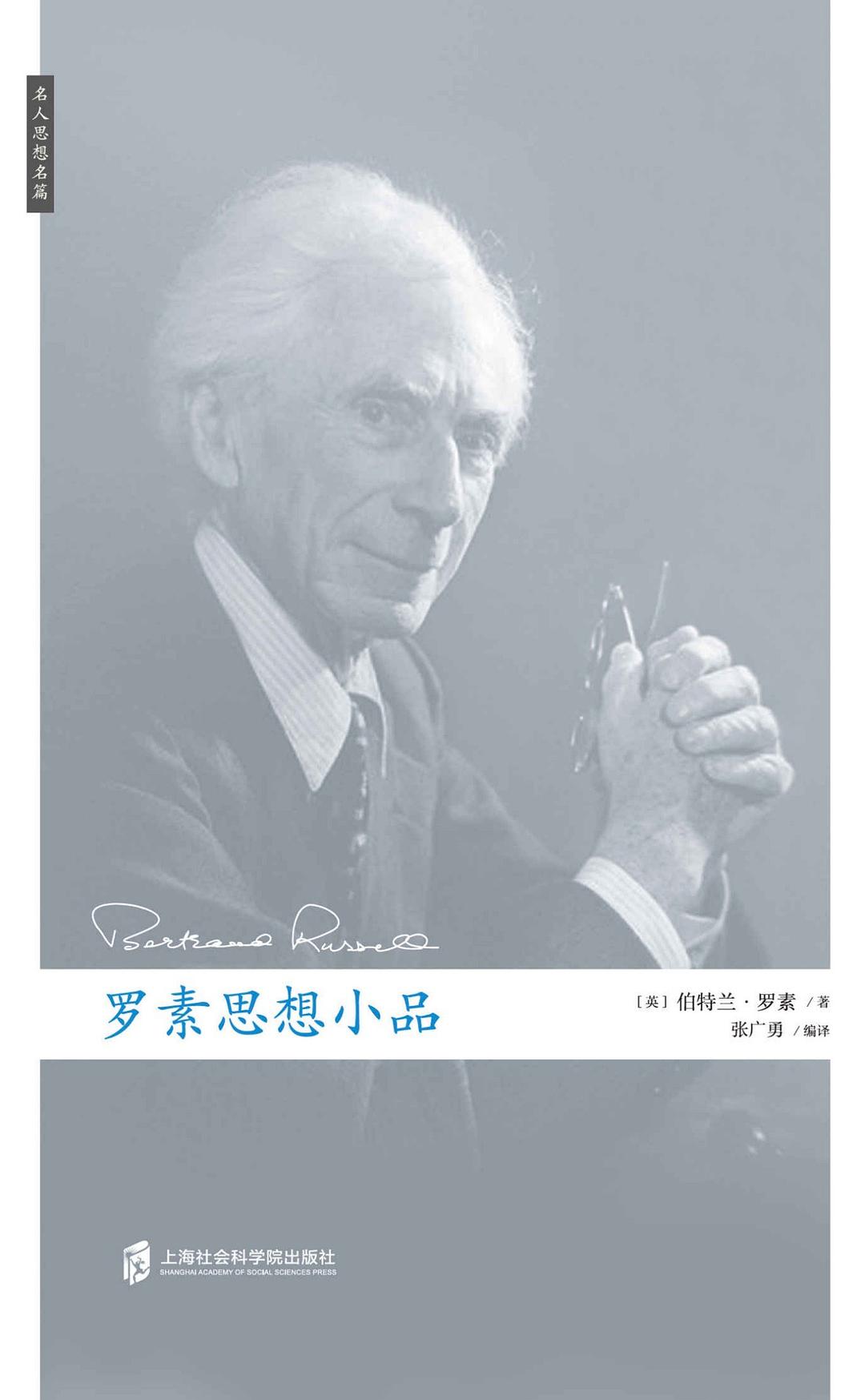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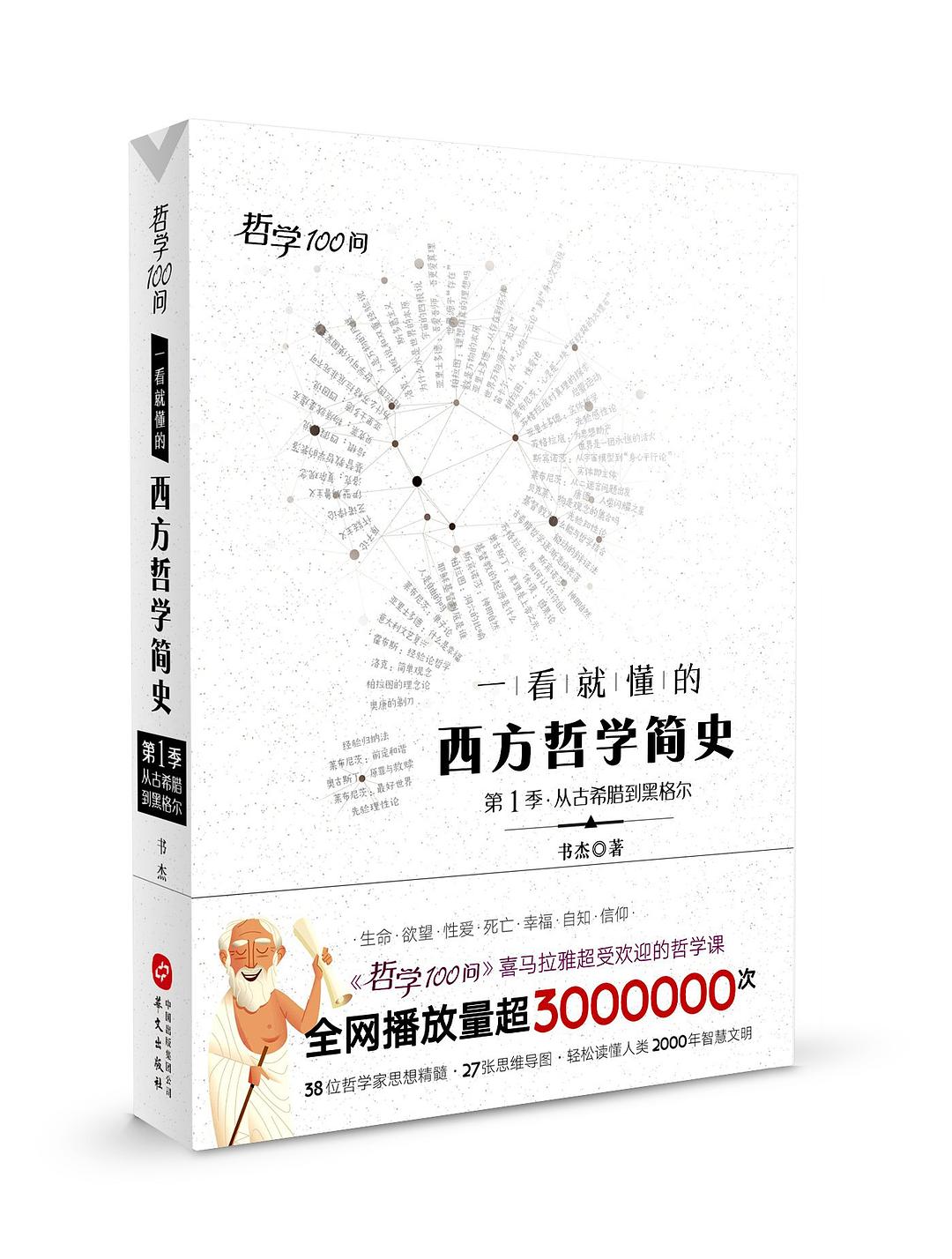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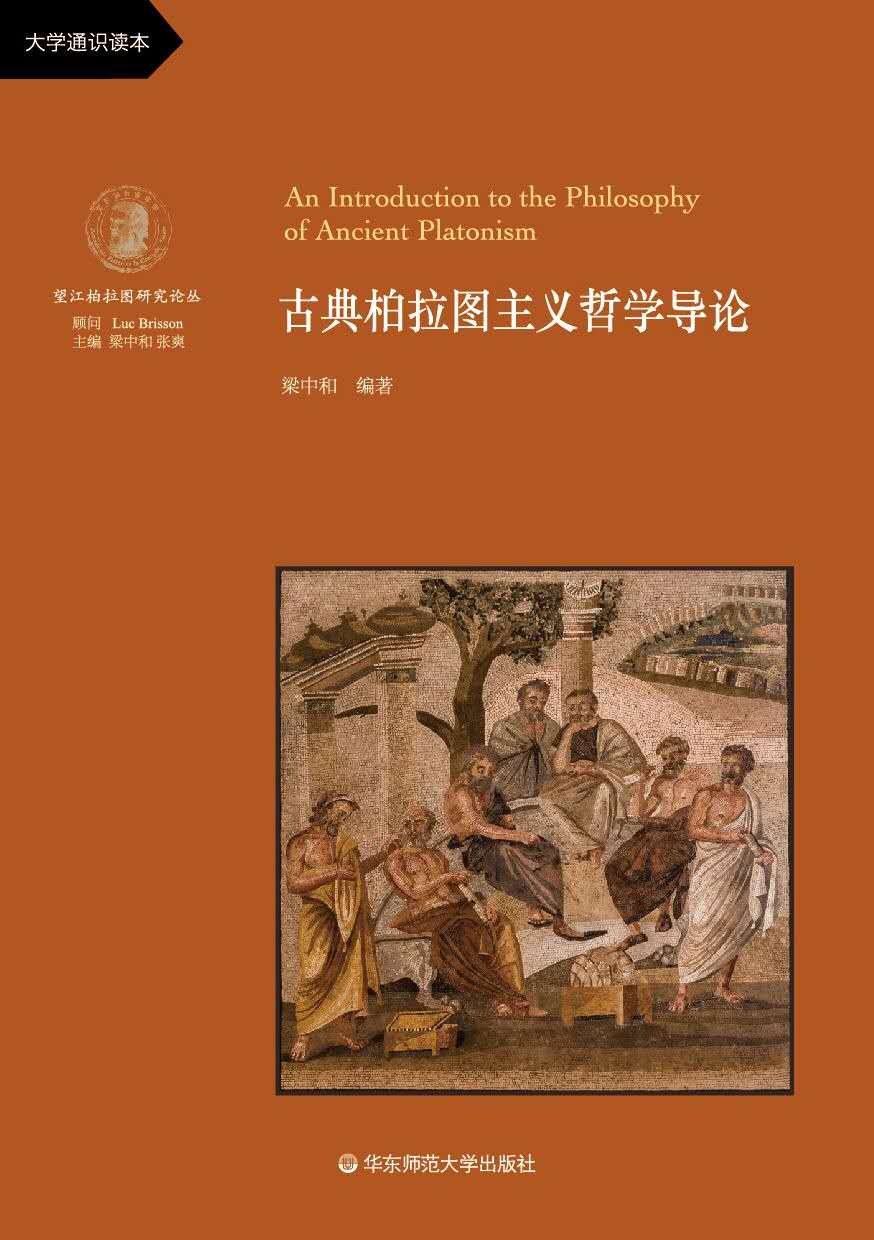

发表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