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身为女性的选择》女性的自我挣扎中的选择
书名:身为女性的选择
1
0

光辉岁月 2023-08-28 18:23:30
突然发现父亲的软弱。这是个隐秘的觉知:随着父亲的年老,他的父权在家庭中慢慢衰退,此消彼长,部分权利慢慢转移到正当壮年的我身上。不论他多色厉内荏,想行使他的权威,但实质上已经无法真正控制我了。
稍微能限制我行为的,是我对他的亲情,对他的爱。可对他的滤镜早就消散了,实质上很多年前就破碎了,对他的爱也是有限度的,甚至岌岌可危。亲情和爱,不意味着要让渡我的生命权。我可以行使在家庭中的权利,也可以不行使,或者另开炉灶,从这个家庭结构中脱离出去,大可不必受制于人,成为父母的傀儡,为他们而活。
当有了这个觉知后,一个无形的重担似乎卸下了。前段时间这么多痛苦只是我的选择。我还可以有另一个选择:为自己而活。为自己而活并不容易。
某天,大概是又一次声嘶力竭之后,我突然意识到,在父母眼里我并非独立的个体,而是一个有生育功能的容器,一个承载着给他们繁衍养老任务、顺从他们指令的工具人。初察觉时,是痛苦的,甚至有自毁的想法——我的存在意义被最亲近的人否定了,活着的意义何在。"我"的意识开始冒头,才发现原来身上有这么多枷锁,才发现过往的自己并没有真正地活着。看似自由,看似自我选择,但要么是把自己的主导权让渡出去,要么是无意识地随波逐流。在内外界的束缚挤压下垂死挣扎,最终还是自暴自弃的妥协。妥协的结果是丢失更多的自我。甚至可以说是亲手把自主权利交了出去。所以常常会厌恶自己,厌恶自己的无能为力。更可怕的是,枷锁常常变成舒服享受的温床,哪怕可以察觉到不对劲,还是在自身的惰性之下一步步沦陷。最终,失去的活的能力,更失去爱自己的能力。我都没法为自己而活,又怎么会爱自己。
如果说对父亲还能无视,甚至对抗。对母亲的情感,却是无能无力的疼痛,既想爱她,又想逃离她,最后变成一把钝刀子,实施漫长的自我凌迟。有时候我能意识到妈妈对我的爱——当她说等我老了没个孩子连流浪狗都不如的时候,我知道她是真心这样认为,真心地为我担忧。这样的爱沉重又心酸。我无法改变她的想法,她也无法改变我的,不知什么时候起,我们无法正常沟通。不同想法的两个人相互折磨,结局要么“同归于尽”,要么有个人妥协。她给了我一个甜蜜的诱惑:只要我听话顺从,就不用一家三口都痛苦,就不用受这些折磨。她希望我成为一个“正常人”,她因为我感觉抬不起头来。她自认平生不作恶,却有了我这样忤逆的女儿。我自认平生不作恶,却成了父母的痛苦来源。有时候忍不住想,我在妈妈的眼里是变成怪物了吗我的存在对她成了一种伤害吗明明我如此努力生活,不想伤害任何人,明明爱她,却无法满足她。有时候想杀死“自己”,有时候自我意识又不甘心。能干脆地决绝地做出选择该多好,痛恨这样反复撕扯的我。
人类的繁衍本能真是可怕,似乎只有结婚生子才是正路,承担生育的女性天然处于弱势。可我不想把这一代的痛苦延续到下一代,为了给我养老而违背本心走入婚姻生孩子。我现在痛恨自己被生下来的“使命”,又怎么想再为了这个目的生育孩子。母亲没在婚姻中得到过好处,还是推动着我走入婚姻。为什么呢?因为她担心我异于常人。母亲这一代的大多数
相关推荐
园丁与木匠
孩子不是无意义的打闹,而是在学习社交互动;孩子不是在简单地玩玩具,而是在探索世界;孩子不是因为无聊才问为什么,而是在寻找答案。那么,当孩子在玩的时候,他们到底在学习什么呢?他们是如何学习的?而对于父母 [美]艾莉森•高普尼克(AlisonGopnik) 2023-03-31 02:28:48孩子如何学习
-出生42分钟,婴儿就能模仿大人的脸部表情;6个月大宝宝就能区分各种语言的不同;3岁孩子能在两分钟内测试5个科学假设……人们一直以来认为孩子的学习是被动的,需要教导,但科学证明学习是孩子与生俱来的本能 [美]艾莉森•高普尼克/[美]安德鲁•梅尔佐夫/[美]帕特里夏•库尔 2023-03-31 02:29:21速效学习辅导法:60招化解父母焦虑
在当今社会,如何学习才是最重要的问题。教育学教授、学习问题专家斋藤孝的畅销书《学会学习》在日本上市仅一个月就销售超过了20000册。这本书介绍了60种简单易行的学习辅导法,可以快速地缓解父母们对孩子学 [日]斋藤孝 2023-03-31 02:29:52给爸爸妈妈的儿童性教育指导书
一本书为中国父母讲明白儿童性教育。本书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委托编写的《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为主要理论框架,给出了儿童性教育的指导标准。帮助父母按照科学、全面的性教育指导理论,对孩子进行专业的性教 明白小学堂 2023-03-31 02:31:28好妈妈就是家庭CEO
在本书中,作者提出了“好妈妈就是家庭CEO”的理念。这种理念不仅将妈妈视为孩子的首席教育官,更将其视为先进教育理念的首席执行官。这一理念的提出打破了妈妈们原有的自我认知,赋予“妈妈”这个角色更为深刻的 熊莹 2023-03-31 02:32:04打破你的学生思维
重新优化后的语句并排版分段:这本书踏实质朴,包含大学生最关心的99个问题,例如不知道自己的优势在哪里、到底要怎样做出选择以及如何规划职业发展方向。这本书鲜活真实,回答者从亲身职场阅历中提供独到见解,拓 北京职慧公益创业发展中心 2023-03-31 02:32:38© 2023-2025 百科书库. All Rights Reserv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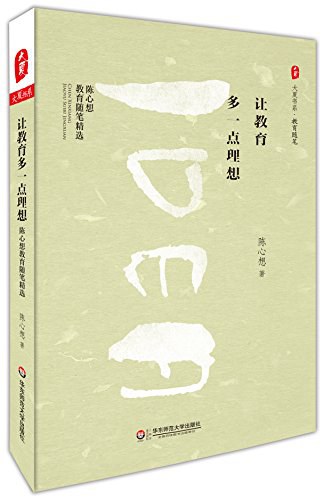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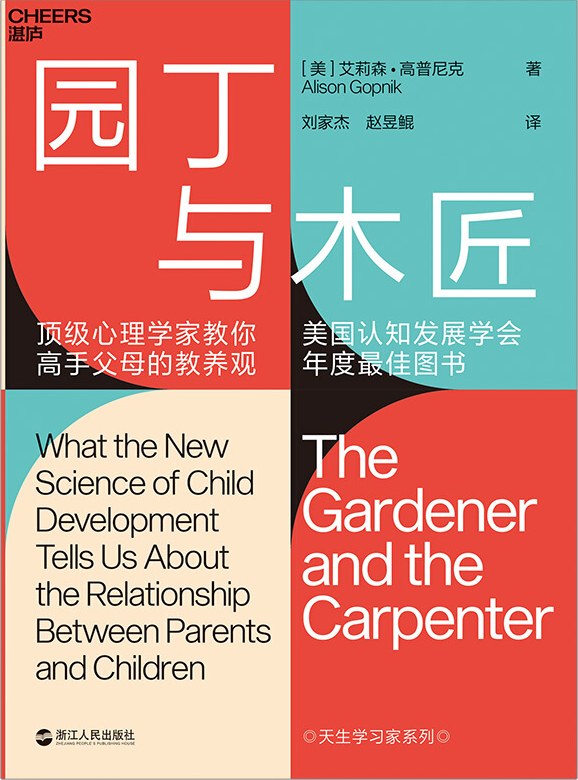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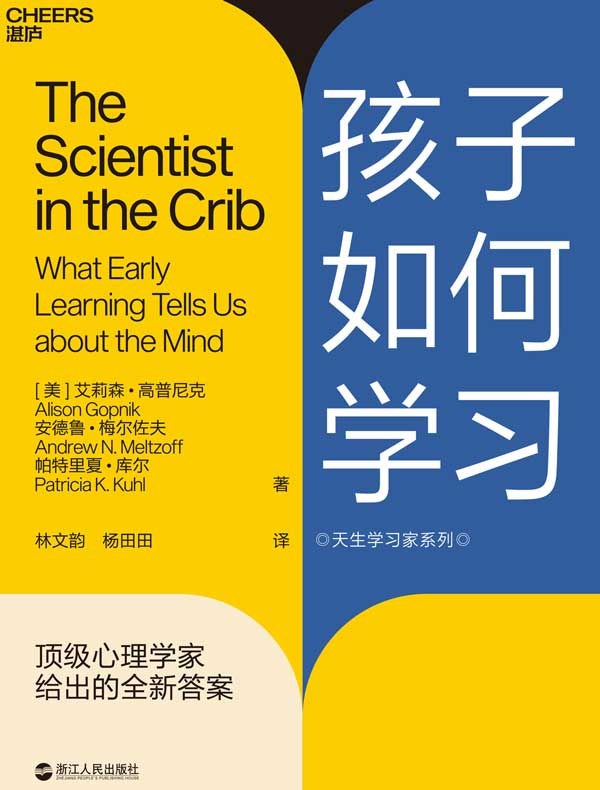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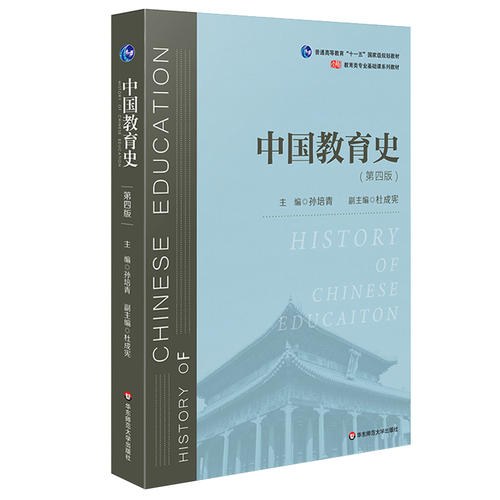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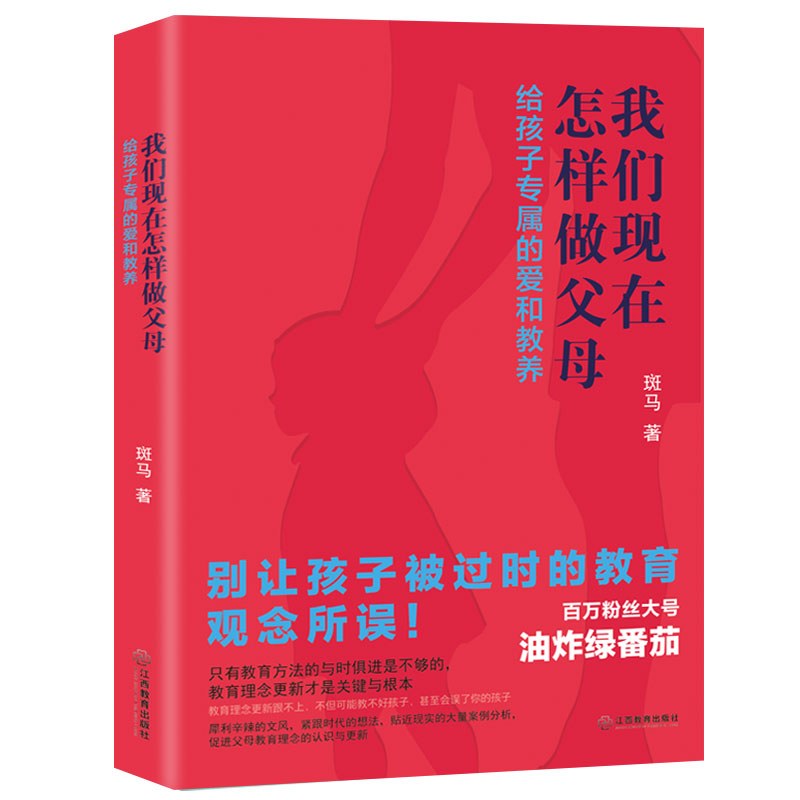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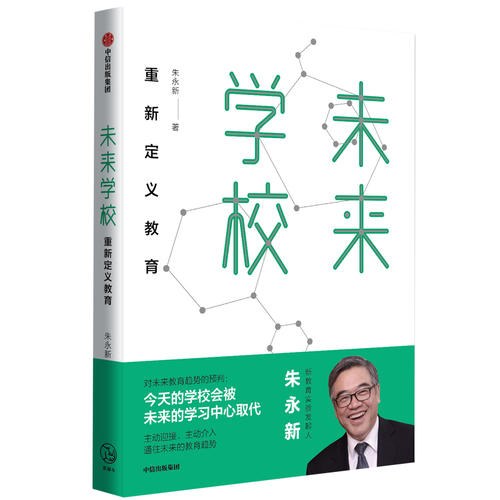

发表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