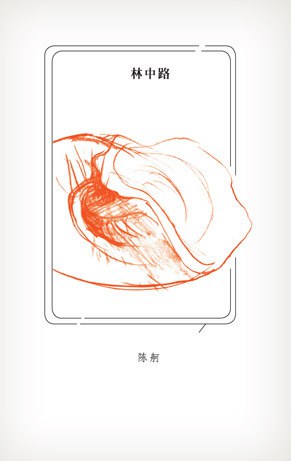
林中路的小笔记:读陈舸飞行
书名:林中路
1
0

聪明小狐狸 2023-07-25 17:43:38
马雁在《质朴诗的未来学——读陈舸诗集二种》中的一句点评引起了我充足的兴趣:“父子悬殊的认识能力与蒲公英的飞行能力之间构成更加悬殊更加戏剧化的对比”。
对于陈舸这首诗,我读出的最重要的东西也是这悬殊的认识能力如何在诗中被唤醒又被运输至现实难以达到的地方。这首诗像是一个封闭容器,在内部对于差异的能量有着最出色的反射能力,而它也是飞行器本身,在诗歌想象力而非现实可以提供的空间里再往前行一段看不清的距离。
“悬殊的认识能力”听上去当然是非常惊人的影响因素,但人是不可能首先在一首诗里感受到这一因素对他们有着多么重大的影响的,而是在生活里——在已经被语言和情感通融了绝大部分不可知、不可说、不可不明白之内容的生活里。
可这一切理解是勉强的、机械的,其弱质性正是它像奇迹一样长存的原因。人一旦开始共同行动,就不得不感受到差异带来的寒冷温度,来自情感、来自记忆。
《飞行》这首诗也是以人和人之间的这种“共同行动”开启的。
“我抱着半岁的儿子/去看风景。”
“抱”的亲密来自父子之间的岁数与力量差异,而不是来自真正的行动和意识上的一致。儿子是半岁的儿子,正因为他年岁之小接近于无,我们才在这里可以宣称他具有邪恶的性质,这判断来自于人对于最初人性的茫然,是十分成立的。当蒲公英展示它飞翔的奇迹的时候,当父亲玩着嘴唇的声音把戏的时候,当一切共同回忆的物质基础消失的时候,孩子的反应都十分一致——“发出清澈的笑声”、“让他手舞足蹈”以及“在阴影里咯咯地笑”。
如果说,诗里的时间跨度长到事物终于走到消亡(“但土坡已经荡然无存”)的话,陪着“我”,那个在这里进行感受的主体一同行走的,是那个怀抱里不知时间和消逝为何物的,非常混沌的生命,同时也是所有生命的起点。即使是这样,这生命迟早也会拥有历史,虽然大部分的历史来自于已经记载好的确凿无疑的“文明史”,“而他也将被一个名字所规定”。
整首诗是在表面上是叙事的,叙事的结局是父子共同在记忆里拥有的小土坡在“机器轰鸣”中不复存在。既然有一个终点,在这里,关于现实的情感记忆也该暂停了,但没有——
“堆积的褐色泥土/让我明白了/夜色中发生的事情/孩子在阴影里咯咯地笑/为看到的新图景”
跟前两次不同,结尾处对于孩子反应的描写并不具有真实的基础,“在阴影里”或许暗示了这一点,这里对着死亡和残忍发出的“笑”是不是在质疑前两次的欢乐也是出于同一种生命的被动和无知而非真实的体验的欢乐,在质疑是不是即使在时间中生命分化出自身,却仍然被起点那可怕的无知牵引,却仍以一种平板的祥和喜气面貌出现。
可是仍然不能够混淆,这里的互动和预测都只存在于那个主要的感受体的想象里——那灰色的想象里,也正是这一节十分清楚地划分出了现实和诗歌不同管辖区的界限。
陈舸的诗集叫《林中路》,在《飞行》一诗中,这条路一半是叙事现实走的,而另一半则是由诗歌想象走完的。
相关推荐
园丁与木匠
孩子不是无意义的打闹,而是在学习社交互动;孩子不是在简单地玩玩具,而是在探索世界;孩子不是因为无聊才问为什么,而是在寻找答案。那么,当孩子在玩的时候,他们到底在学习什么呢?他们是如何学习的?而对于父母 [美]艾莉森•高普尼克(AlisonGopnik) 2023-03-31 02:28:48孩子如何学习
-出生42分钟,婴儿就能模仿大人的脸部表情;6个月大宝宝就能区分各种语言的不同;3岁孩子能在两分钟内测试5个科学假设……人们一直以来认为孩子的学习是被动的,需要教导,但科学证明学习是孩子与生俱来的本能 [美]艾莉森•高普尼克/[美]安德鲁•梅尔佐夫/[美]帕特里夏•库尔 2023-03-31 02:29:21速效学习辅导法:60招化解父母焦虑
在当今社会,如何学习才是最重要的问题。教育学教授、学习问题专家斋藤孝的畅销书《学会学习》在日本上市仅一个月就销售超过了20000册。这本书介绍了60种简单易行的学习辅导法,可以快速地缓解父母们对孩子学 [日]斋藤孝 2023-03-31 02:29:52给爸爸妈妈的儿童性教育指导书
一本书为中国父母讲明白儿童性教育。本书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委托编写的《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为主要理论框架,给出了儿童性教育的指导标准。帮助父母按照科学、全面的性教育指导理论,对孩子进行专业的性教 明白小学堂 2023-03-31 02:31:28好妈妈就是家庭CEO
在本书中,作者提出了“好妈妈就是家庭CEO”的理念。这种理念不仅将妈妈视为孩子的首席教育官,更将其视为先进教育理念的首席执行官。这一理念的提出打破了妈妈们原有的自我认知,赋予“妈妈”这个角色更为深刻的 熊莹 2023-03-31 02:32:04© 2023-2025 百科书库. All Rights Reserv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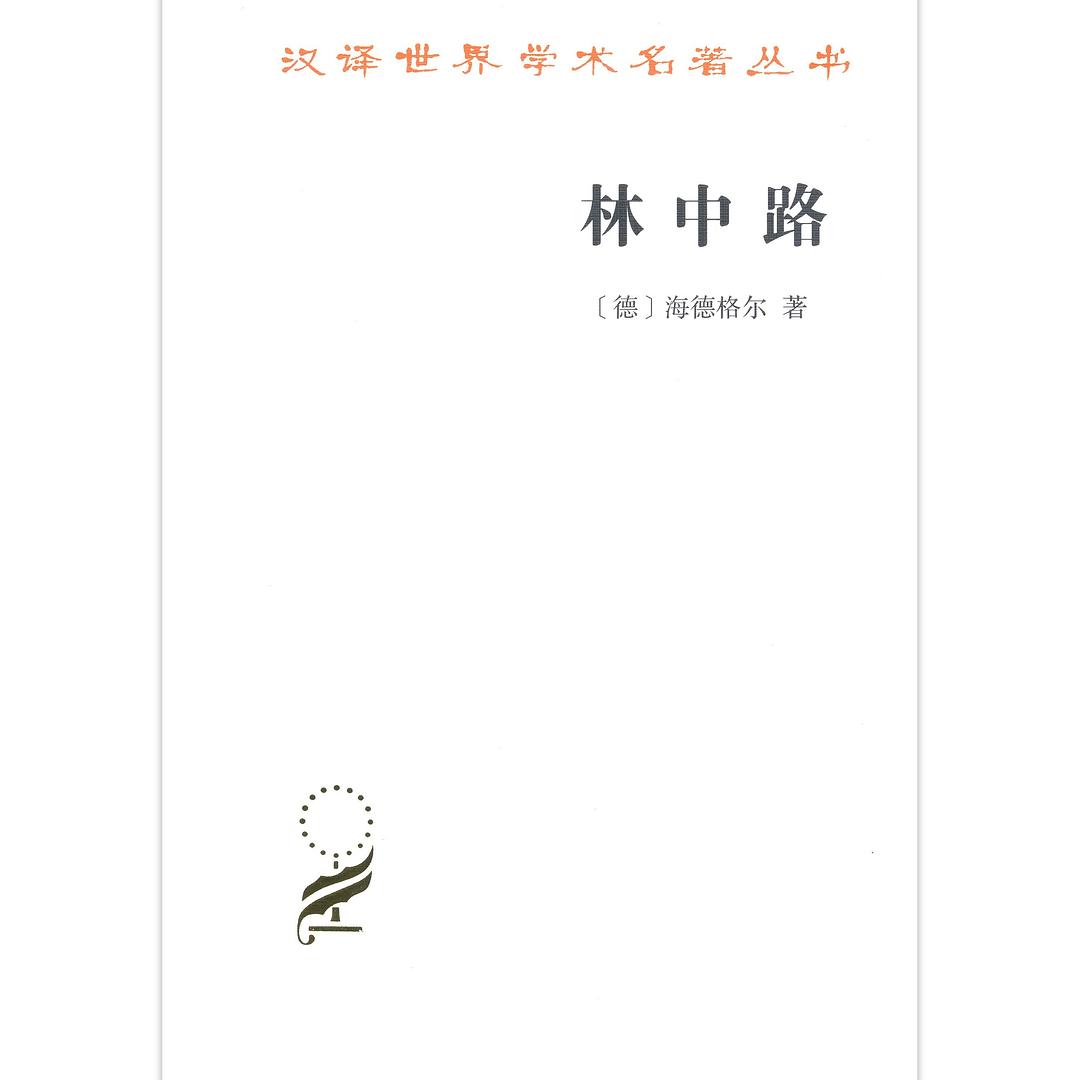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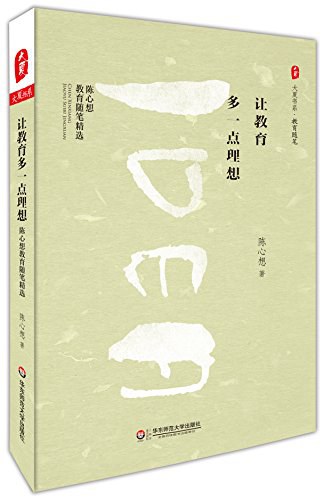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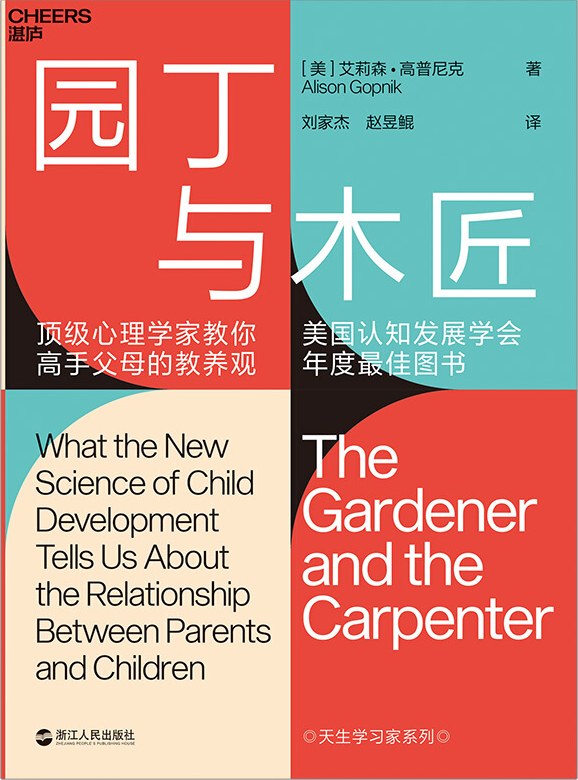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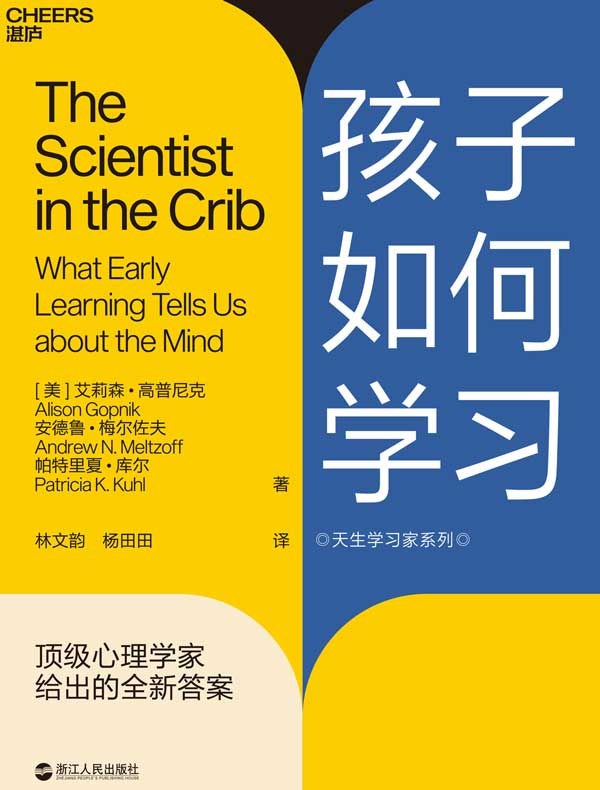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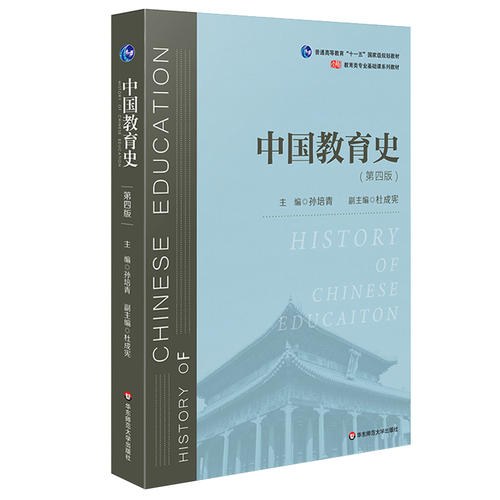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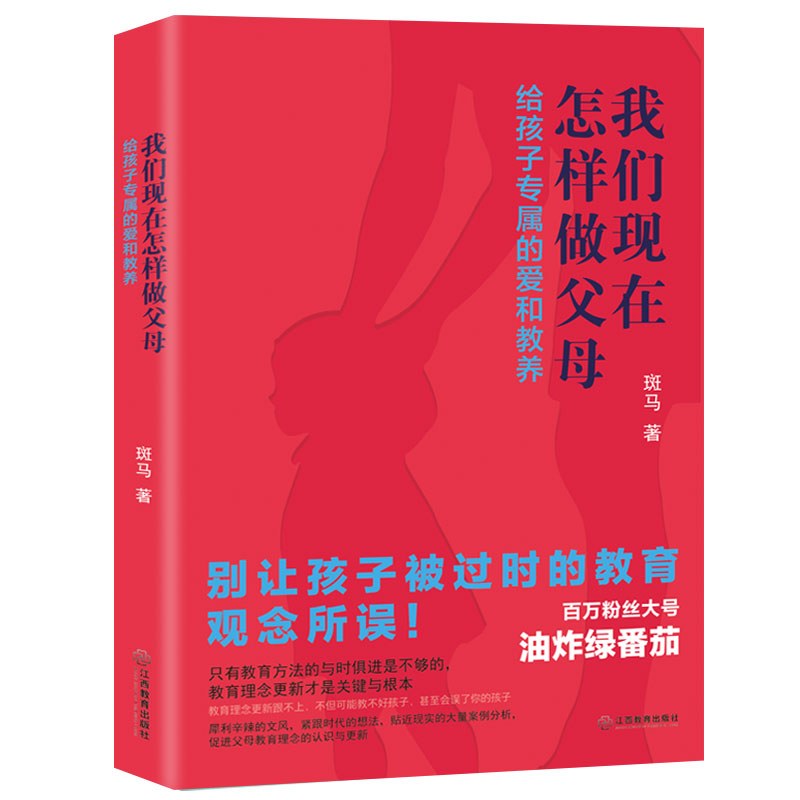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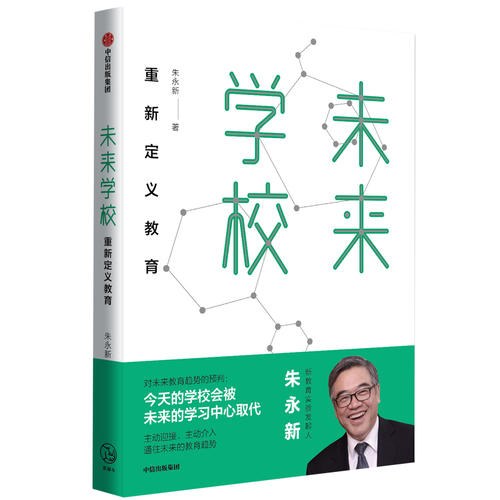
发表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