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再在乎卡夫卡:阅读卡夫卡短篇小说全集感受
书名:卡夫卡短篇小说全集
1
0

神秘之门 2023-04-29 05:00:54
很多年前,我痴迷于卡夫卡,仿佛找到了一个安宁的栖身之所,可以玩弄文字。但是,有些事物无法比较。我再也不能像十几岁时那样充满期望和疏离疑惑的复杂情感。现在,即使失眠,也不会再像以前那样憋气到太阳穴血管剧烈跳动,也没必要在电梯里仔细打磨临时想出的奇异故事和笑话。我记得自己的笑话原则: 爆笑的笑话不是好笑话,24小时之后还能记得的笑话,也不是好笑话。于是,我尽量抹去特点,又让它们有点好笑,让人获得一点点快乐,却不会让人记得。当时的我肯定无法承受此刻的心境,但现在的我也不能打包票能承受那时的痛苦。
美好和痛苦都在我胸膛刻下印记。冬天假期和当时的恋人躺在床上或沙发上时,我总是让她把一只手放在我的胸口,仿佛这样能轻松一些,仍是捂住锁住的门锁,让人轻松一些。脆弱的神经也遇上无尽的压力和困惑叫我总做出一些怪异的举动。记得有一次冬天,我特别想吻一口她的汗水,于是两个人艰难地在雪上奔跑着,结果很快出汗。由于自己这怪异的请求,我不好意思用舌头去舔,只好草草了事。两个人休息时,我问她我总做这些怪异的举动和提这些奇怪的要求,生活中也有许多怪异的习惯,这样会不会很奇怪。其实,我感觉自己和她的关系像一个奇怪的孩子和一位神性的牧师。她不了解我,不能感受我,头脑也不是很聪明,性格也不完美,身体也瘦弱,我一只手就可以把她托起来。但是,她总是表现得很有耐心,仿佛全知天下,不慌不忙,没有什么要做的事,却又一事不落,没有什么渲染或香味,却有种熟悉的味道。她就像大街上的一个陌生人,但是,下一秒如果和她一起去寻死,一点都不会让自己奇怪,一点儿也不会让她奇怪,甚至天空和云彩也不奇怪。我们就像两个互相契合的方块,没有处可以契,并且又无处不契。
她没有读过很多书,也没有什么文采,甚至很少去思考,但我总记得她当时回答我的那几句话。她说,怪人做怪事是不奇怪的,在咖啡厅喝甜咖啡、苦咖啡、抹茶咖啡都让人快乐。或许你不觉得快乐,但其实你是。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一点也不爱她,但我想我们可以度过一生,直到死亡。我不爱她,不是因为不想去爱,不能去爱,或者不愿去爱,而是人不能够给予自己从未拥有过的东西。我没有后来的问题,因为她已经死了。我们本来就是因为寻死而遇上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她死了,而我没有。虽然我有更多的理由去寻死,但我偶尔会和别人提起我种种混乱的思想和做过荒诞的事时,他们都竖起大拇指大笑不止。按道理来说,一起度过了许多年,应该会怀念。但是,我很少回忆,也很少怀念。我很奇怪我自己,但是我记得她说我不奇怪,于是就很少去想了。
我自己用玻璃粘了很多鱼缸,制造了很多景象,养了很多鱼虾,沿着客厅把空间三面包围起来。我每天会打开鱼缸灯,坐在中间一圈一圈地旋转,速度加快,渐渐看不到水草的景象,看不到鱼的颜色,灯光也混到了一起,最终只剩下光亮。然后我开始眩晕,窗外的天空也开始发亮,我分不清阳光和灯光,也分不清吹着我胸膛的到底是窗外的风还是由于旋转产生的旋风。我逐渐松开力气,旋转渐渐停下来。
如果一整夜都没有睡觉,在拂晓时睁开眼,是否算得上是惊醒?
之前有人说过我快乐,但这些年来我感受不到了,以后也不会有快乐。没人会告诉我我快乐了。
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一点也不在乎卡夫卡了,也记不起他的故事。我看到一根圆木在冰面上滚啊滚,一张白纸上出现多少黑点才不算是单调?
相关推荐
园丁与木匠
孩子不是无意义的打闹,而是在学习社交互动;孩子不是在简单地玩玩具,而是在探索世界;孩子不是因为无聊才问为什么,而是在寻找答案。那么,当孩子在玩的时候,他们到底在学习什么呢?他们是如何学习的?而对于父母 [美]艾莉森•高普尼克(AlisonGopnik) 2023-03-31 02:28:48孩子如何学习
-出生42分钟,婴儿就能模仿大人的脸部表情;6个月大宝宝就能区分各种语言的不同;3岁孩子能在两分钟内测试5个科学假设……人们一直以来认为孩子的学习是被动的,需要教导,但科学证明学习是孩子与生俱来的本能 [美]艾莉森•高普尼克/[美]安德鲁•梅尔佐夫/[美]帕特里夏•库尔 2023-03-31 02:29:21速效学习辅导法:60招化解父母焦虑
在当今社会,如何学习才是最重要的问题。教育学教授、学习问题专家斋藤孝的畅销书《学会学习》在日本上市仅一个月就销售超过了20000册。这本书介绍了60种简单易行的学习辅导法,可以快速地缓解父母们对孩子学 [日]斋藤孝 2023-03-31 02:29:52给爸爸妈妈的儿童性教育指导书
一本书为中国父母讲明白儿童性教育。本书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委托编写的《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为主要理论框架,给出了儿童性教育的指导标准。帮助父母按照科学、全面的性教育指导理论,对孩子进行专业的性教 明白小学堂 2023-03-31 02:31:28好妈妈就是家庭CEO
在本书中,作者提出了“好妈妈就是家庭CEO”的理念。这种理念不仅将妈妈视为孩子的首席教育官,更将其视为先进教育理念的首席执行官。这一理念的提出打破了妈妈们原有的自我认知,赋予“妈妈”这个角色更为深刻的 熊莹 2023-03-31 02:32:04打破你的学生思维
重新优化后的语句并排版分段:这本书踏实质朴,包含大学生最关心的99个问题,例如不知道自己的优势在哪里、到底要怎样做出选择以及如何规划职业发展方向。这本书鲜活真实,回答者从亲身职场阅历中提供独到见解,拓 北京职慧公益创业发展中心 2023-03-31 02:32:38© 2023-2025 百科书库. All Rights Reserv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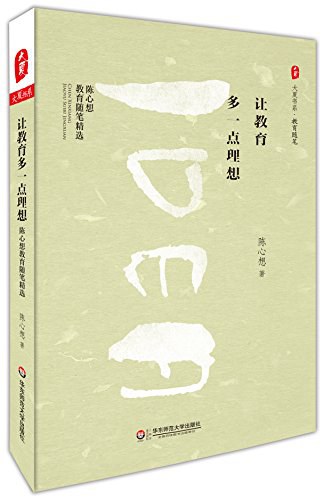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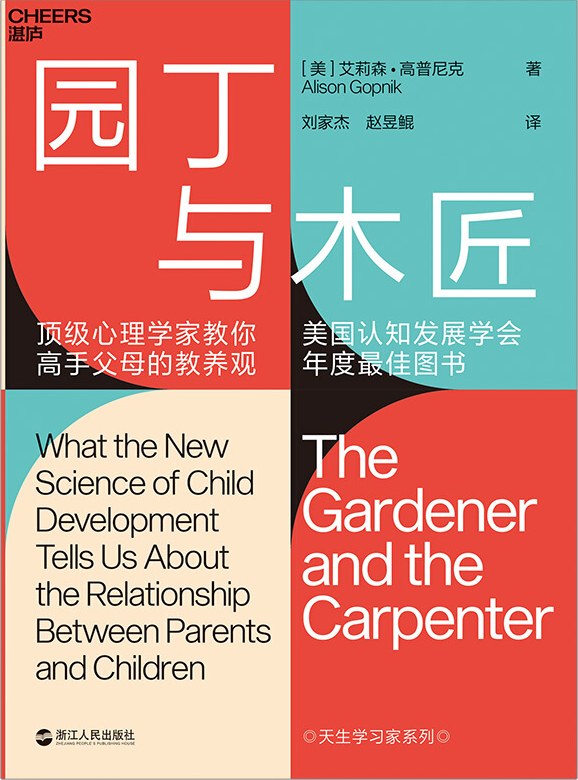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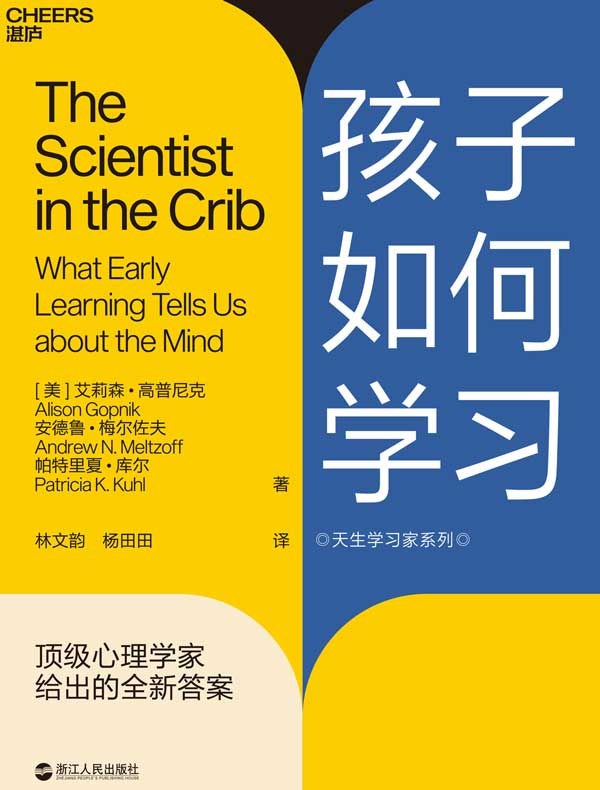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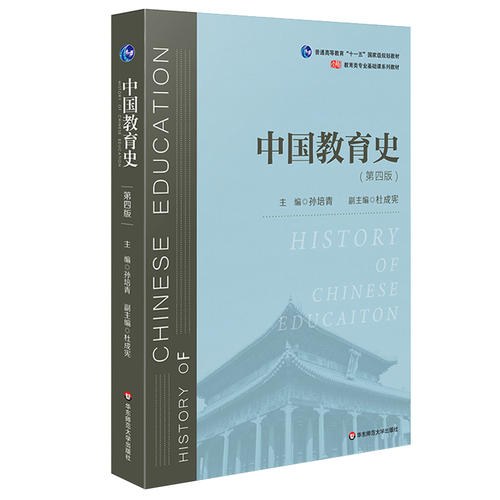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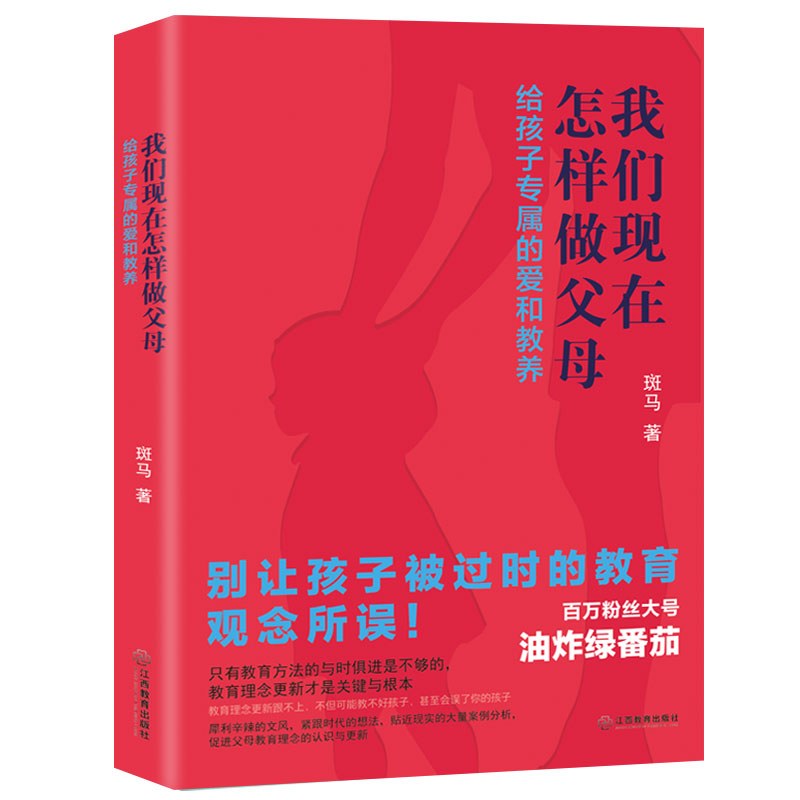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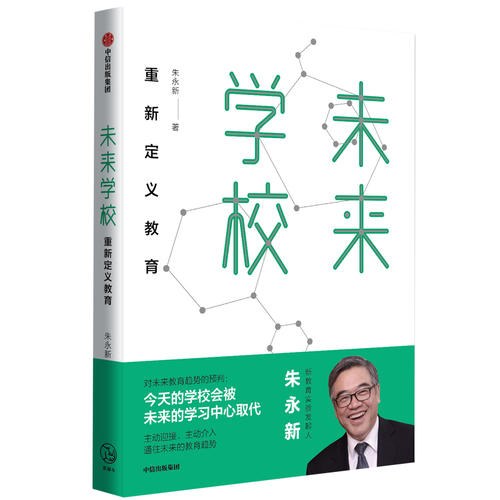

发表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