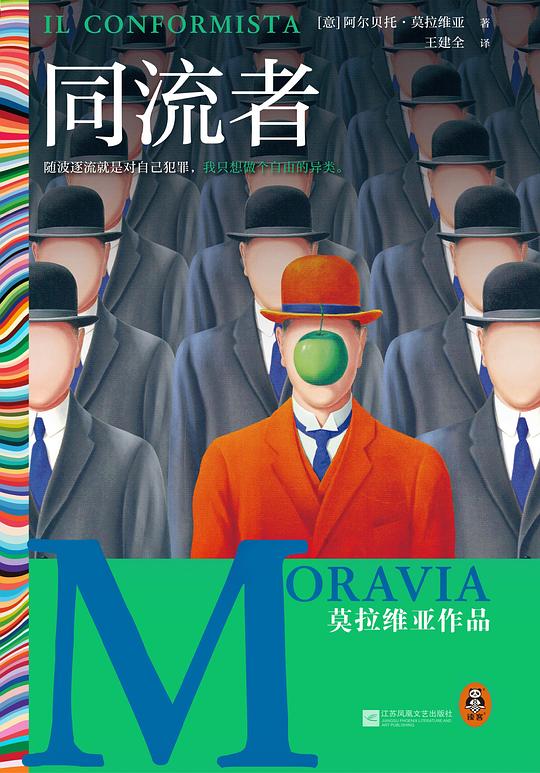
"同流者:共同前行,同步发展"
书名:同流者
1
0

超级英雄 2023-06-12 07:16:23
“我们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失掉了这份天真……这就是正常状态。”
不知道该如何评论这个作家。他的一切发展既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即使他的文笔算不上细腻,整体小说故事水平发挥也不算稳定,但你还是想把这个故事看完,想彻底“窥探”主角的内心所想。
我个人更喜欢他前半章童年部分的描写。愈到后面,不论是情绪刻画还是故事构架上,感觉愈加薄弱。而后期也花了更多的笔墨去描写了周遭场景,估计是为了能从侧面突出情绪心境。但我觉得节奏没有把握好,反而给整个故事有种高开低走之感。
但是,我对他的故事又有着极大的好奇,因为前期的描写让我这个“同流者”太多的感同身受。那种矛盾又固执的自我扭曲。特别是前期以“孩子”的视角背景那种无力感和残忍都十分的真切,一度让我觉得曾经自己内心的那些无法言明都被他一股脑地扒开然后倾泻。所以,因为前章情节我对这个故事是有着主观的偏爱的。
当你在很早期就意识到自己的“格格不入”时,这就像一个诅咒的早熟。因为你没有能力去自洽和理解这种“异类感”,而这也是主角一直自我拉扯的起因,终身选择“同流”包括事业。
最后发现,“正常状态正是这样一种徒劳而艰难的渴望:渴望证实自己被原罪所破坏的一生是正确的,而不是从他遇见利诺第一天起就一直在追求的虚无的假象。”那种空虚的失落,就像是被自己所营造的“稳定感”狠狠地背叛和讽刺。
让我想到了早年看卡伦霍妮《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的想法,那就是每个时代的“正常”都在改变,没有一种能绝对的“正常”。主角那种渴望“正常”成为“同流者”的种种努力,有种可笑的呆滞感,但在这可笑中我看到了曾经那个自我拉扯的自己。
曾经他渴望“正常”结婚生子,最后在这“正常化”的过程中也诞生了“爱”,只是他太关注“正常”,导致他轻视了这种爱的力量感。文中后半部其实已经逐渐展现了他需要着自己的家人们,她们早已不是作为“正常家庭的配角”存在,而是他爱着的的妻子和孩子,他从局外人切实融入其中。
这个让我想到了《世界奇怪物语》里有一个故事,一个丈夫作为商业间谍被抓住后,敌方公司说要把他送到另一个星球,便把他迷晕。等他醒来后,他看着周遭相同的一切,却坚信着“这是个和地球类似的星球”。他觉得这个星球的妻子和孩子太可怜,自己也回不去“地球”,就抱着怜悯之情以“假扮这个星球的自己”和“这个星球的家人们”生活下去。但是他时时刻刻都怀念着自己“地球”的家人,不能“欺骗”自己这就是曾经的“地球”,所以他觉得自己的生活每时每刻都是局外人。
这是个荒诞的故事,而主角马马尔切罗也是带着一丝“荒诞感”的。但他和加缪的“西西弗”之荒诞是不同的,加缪的荒诞是一种反抗,而马尔切罗的荒诞是一种无力。
最后他醒悟了,准确来说是自洽了。“丧失天真是不可避免和正常的。” 这寥寥几个字使他明白了。二十年来他一直执迷于一条错误的道路,而现在他必须坚决地从这条道路上走出来了。貌似正要转好之时,他曾冷眼旁观的战争就这么毁掉了一切,留给他一片死寂。这个结尾让我想到了《单身男子》里那个放弃自杀却死于心脏病的主角,无常的怅然若失。
最后的结局让我哑然,但是又觉得这才是时代洪流下的必然。我很期待接下来作者《鄙视》和《冷漠的人》的故事,即使觉得作者写的故事并不够精湛,但这个作者就是有种魔力让你看下去。
摘文中,他心态最后的改变:“这株野花生长在灌木丛的阴影中,附着在石灰岩上的一小块贫瘠的土地上。它没有试图去限制其他更高、更强壮的植物的生长,也没有认同自己的命运而简单地接受或者拒绝它。在完全无意识和完全自由的情况下,这株植物在种子随意落到一个地方之后就开始生长,直到这一天他的手把它摘下。他心想,生长在黑暗的灌木丛中一块苔藓地上的这孤独的小花,它的命运真是太卑微了,但也是自然而然的。相反,那种自愿的卑微,妄图去徒劳地找到那不可能得到的、虚假的正常状态,这样的做法却只能将骄傲或者爱意折叠并掩藏起来。”
相关推荐
单身男子
电影《单身男子》原著小说由汤姆•福特执导,科林•费尔斯主演。小说讲述了一个单身男人失去挚爱后的二十四小时。《单身男子》是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的代表作,2009年改编为同名电影并获得多项国际大奖。小说充 [美]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 2023-04-19 17:33:59鄙视
了对现代人的爱情困境和婚姻危机的深刻洞察。在《鄙视》中,他揭示了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即夫妻间缺乏彼此理解和尊重,以及爱情破灭后的无能为力和无奈。在他的作品中,深刻的思想和对社会风俗、道德观念的挖掘与揭 [意]阿尔贝托·莫拉维亚 2023-03-22 13:19:05园丁与木匠
孩子不是无意义的打闹,而是在学习社交互动;孩子不是在简单地玩玩具,而是在探索世界;孩子不是因为无聊才问为什么,而是在寻找答案。那么,当孩子在玩的时候,他们到底在学习什么呢?他们是如何学习的?而对于父母 [美]艾莉森•高普尼克(AlisonGopnik) 2023-03-31 02:28:48孩子如何学习
-出生42分钟,婴儿就能模仿大人的脸部表情;6个月大宝宝就能区分各种语言的不同;3岁孩子能在两分钟内测试5个科学假设……人们一直以来认为孩子的学习是被动的,需要教导,但科学证明学习是孩子与生俱来的本能 [美]艾莉森•高普尼克/[美]安德鲁•梅尔佐夫/[美]帕特里夏•库尔 2023-03-31 02:29:21速效学习辅导法:60招化解父母焦虑
在当今社会,如何学习才是最重要的问题。教育学教授、学习问题专家斋藤孝的畅销书《学会学习》在日本上市仅一个月就销售超过了20000册。这本书介绍了60种简单易行的学习辅导法,可以快速地缓解父母们对孩子学 [日]斋藤孝 2023-03-31 02:29:52© 2023-2025 百科书库. All Rights Reserv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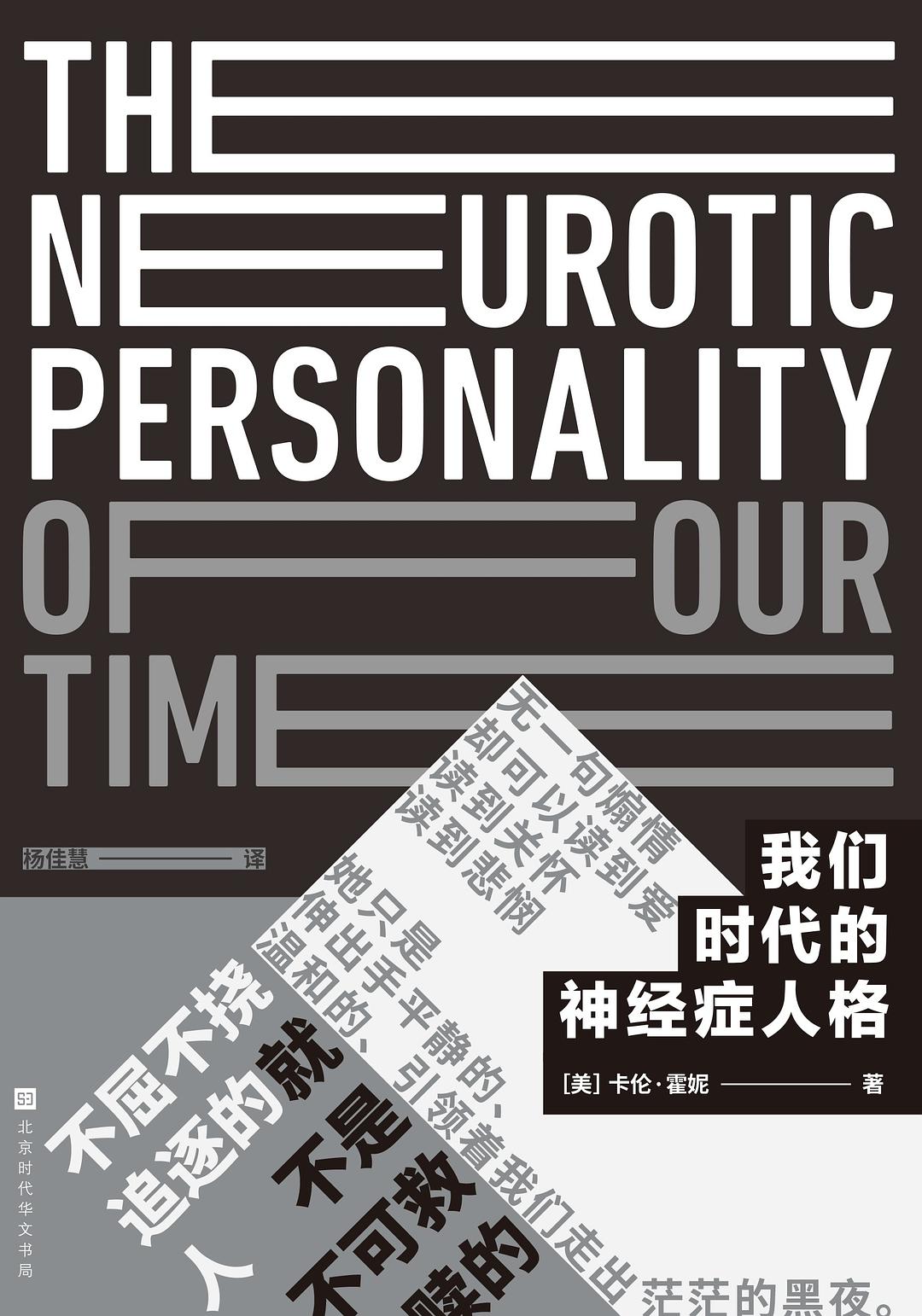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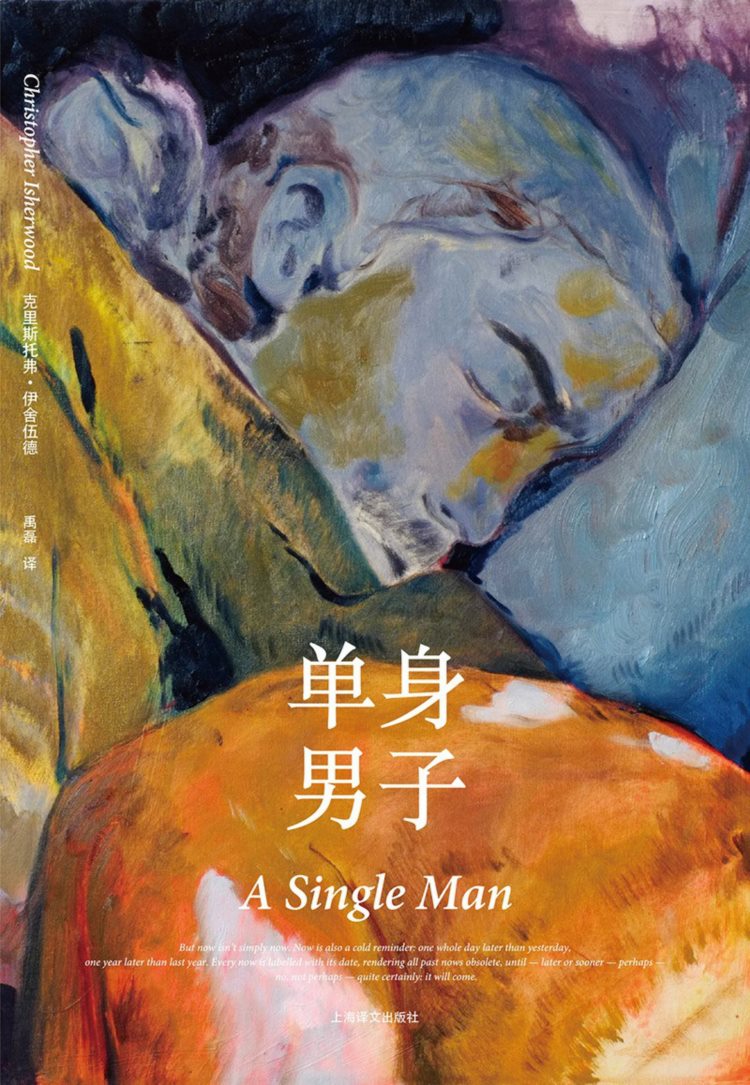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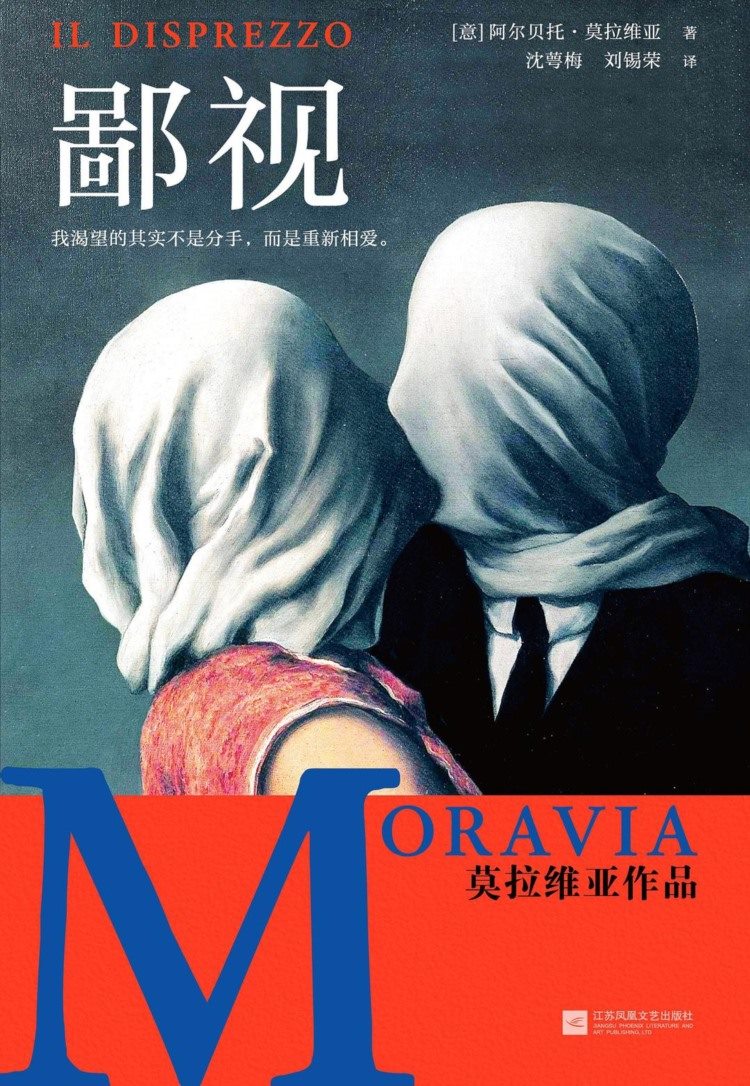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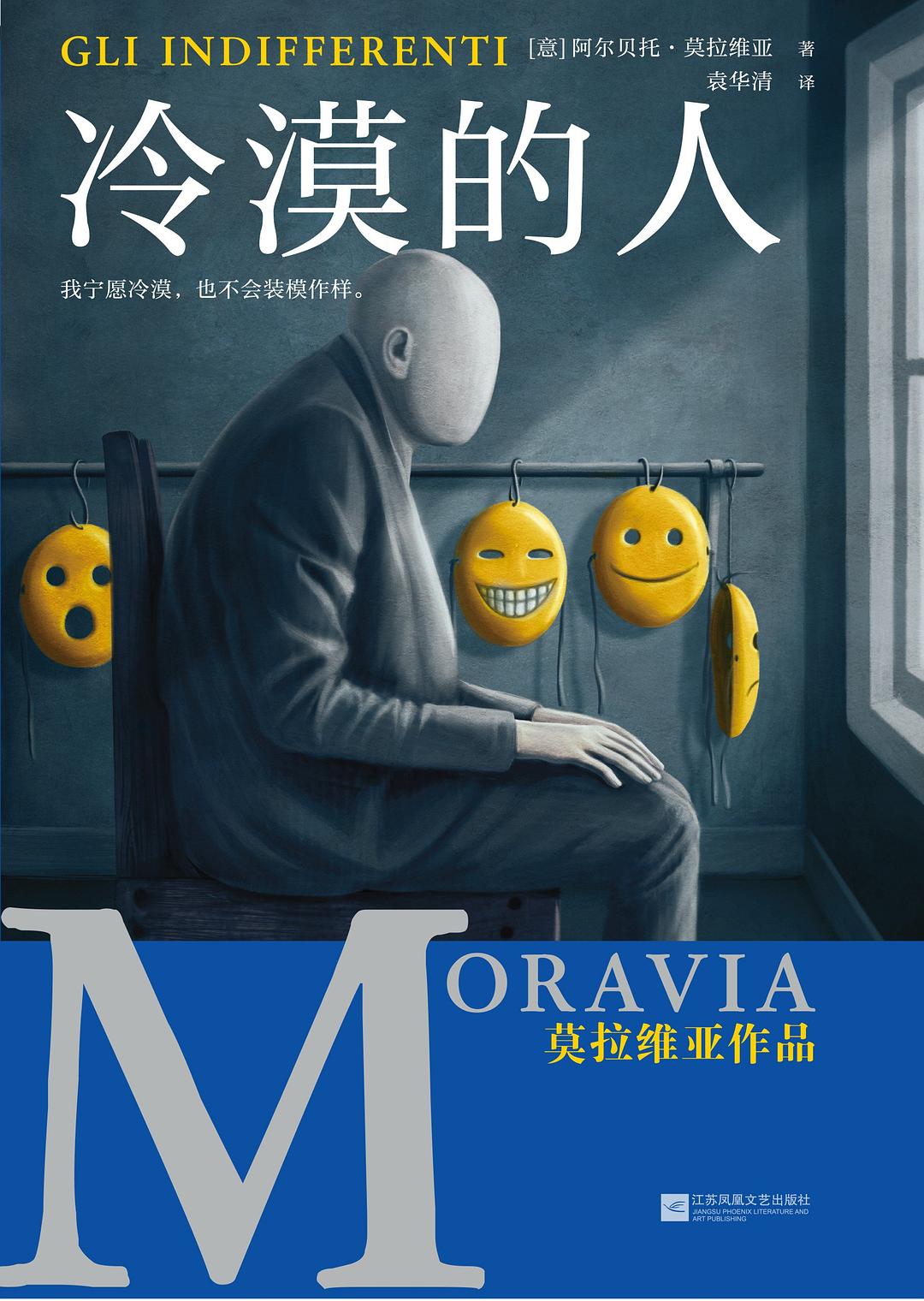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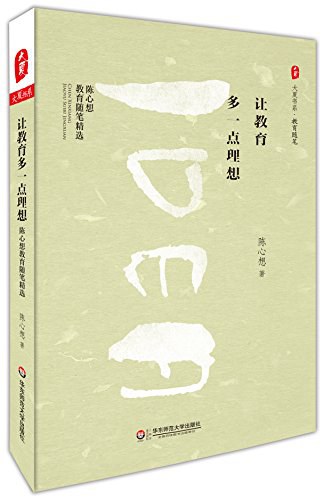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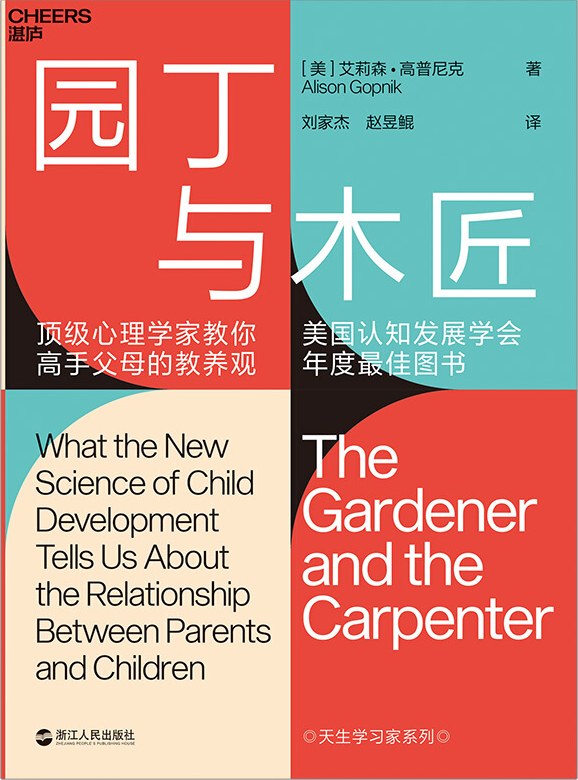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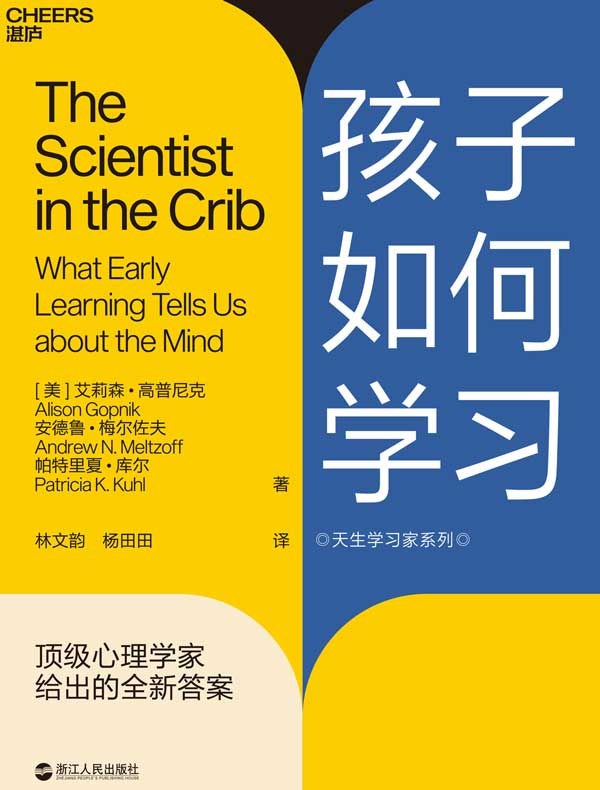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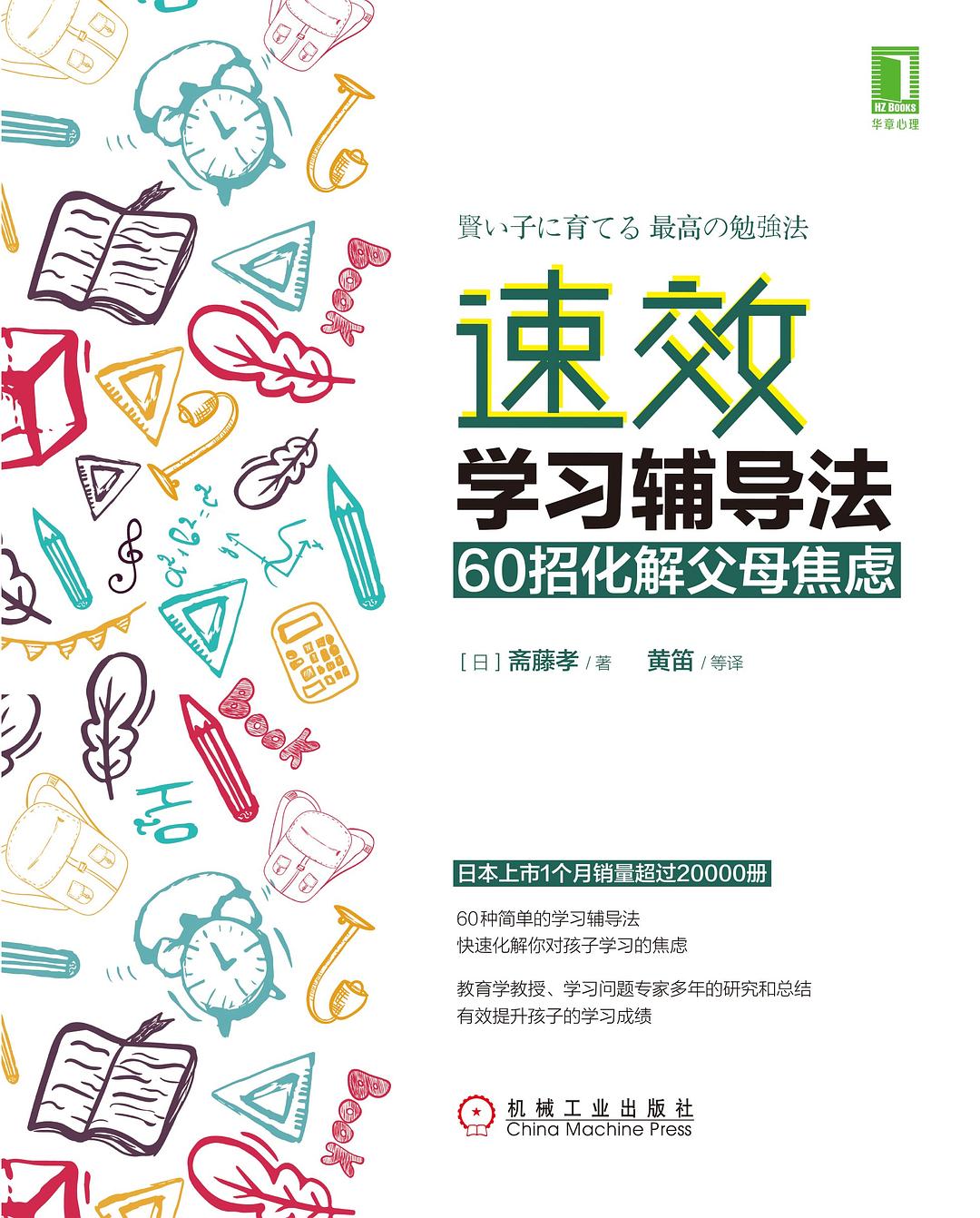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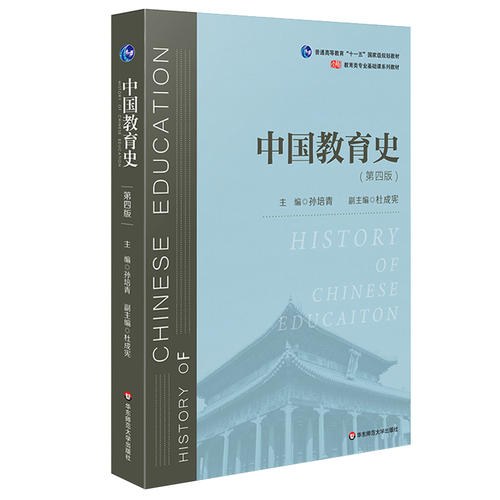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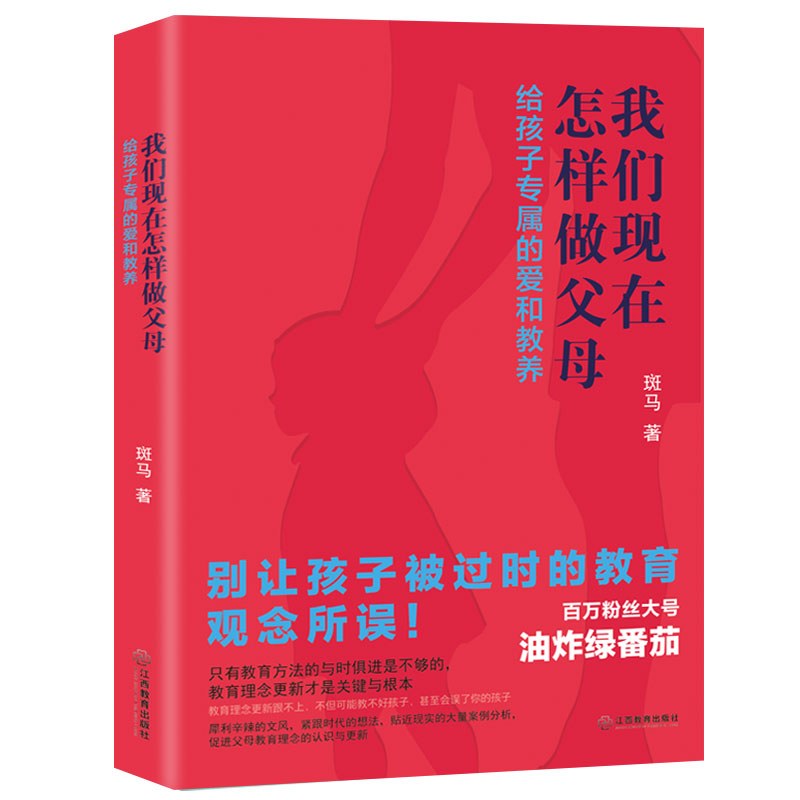
发表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