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帝国屋檐下》“多纳图派的政治思考”
书名:帝国屋檐下
1
0

莎士比亚 2023-10-24 11:20:54
2022年下半年,刚刚读完花威的专著《奥古斯丁早期意志哲学研究》,我就又收到花威的信息说,他的新作《帝国屋檐下:奥古斯丁政治哲学研究》已经完稿。这个写作速度令我非常惊叹。其实,《奥古斯丁早期意志哲学研究》作为花威的博士论文,于2012年就已经完成了初稿,但他又于2013年申请了教育部的课题,不断修订,直到2022年才最终出版。而在2014年,花威又申请了国家社科基金的课题,开始研究奥古斯丁的政教关系思想。他没有像很多人那样,用一个内容申请两个课题,而是在修订前书书稿的同时,着手进行第二项研究。因而,花威对前部书稿的修订和这部新书的撰写,应当在相当长时间内是同时进行的。两本书的出版时间虽然非常接近,但花威都投入了相当长的时间,并分别在华侨大学和岳麓书院开设多门课程,逐渐完成。这恰恰显示出,花威长期以来专心致志地在奥古斯丁研究这一领域辛勤耕耘,从两个很不同但都非常重要的角度同时理解奥古斯丁,相辅相成,形成一幅越来越清晰而全面的奥古斯丁思想形象。现在,他在短时间内拿出这两部书稿,使我回忆起来,他在博士毕业后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其实一直没有出版任何专著,而是如蚂蚁搬家般进行着自己的研究。他在本书后记中说,自己“已经在奥古斯丁研究这条小园香径上徘徊了十四年之久”,一个意气风发的少年已经成为年过不惑的父亲。这两部书的相继出版,恰恰是对十多年比慢功夫的最终收获。
花威在后记里谈到了在北大修我课程的经过,其中许多具体情况我已经不大记得了,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除了修习我开设的《上帝之城》课程之外,花威申请加入我主持的读书班,深度阅读《〈创世记〉字解》。他对保罗思想和外文研究文献的掌握,都让我记忆犹新。后来,花威博士毕业后就到了华侨大学,我几次到厦门的机会,都见到了花威,直接的感觉是,他在如此美丽安逸的南国,充分享受着天伦之乐。后来他又到了岳麓书院,这个我非常熟悉的千年学府。或许正是这种让读书人非常羡慕的生活方式,为花威的研究提供了最丰厚的营养,使他能有今天这样骄人的成绩。研究奥古斯丁的著作中偶尔跳出的唐宋诗词,正是这种状态的反映,并成就了花威笔端的节律与韵味。
花威这两部书的研究主题,我都很感兴趣并有所涉猎。我最早关注奥古斯丁,其实就是从自由意志进入的,也写过相关论文,开过相关课程,但深感这个问题过于重大,而自己短时间内很难取得真正的突破,所以就搁下了,不敢写太多的东西。读了花威的《奥古斯丁早期意志哲学研究》之后,虽然对他的具体结论尚有保留意见,但对于他勇于独辟蹊径,在国内外众多成说之外提出新说的做法,是非常敬佩的。并且也正是花威的这项研究,以及他对奥古斯丁诠释《罗马书》早期著作的翻译,使我澄清了许多疑惑,激发我再次思考奥古斯丁对自由意志问题的讨论。
花威著《奥古斯丁早期意志哲学研究》
而花威这本书中讨论的政治哲学,则是我在《心灵秩序与世界历史:奥古斯丁对西方古典文明的终结》中曾着力处理的,但他和我的写作方式和角度都很不同。拙著的思路,是希望从思想史的古今之变出发,从奥古斯丁的哲学整体来看他的历史哲学与政治哲学。其中虽然不可避免地会关注历史背景,但在这方面并没有特别用力,以致还有一些错误。至于奥古斯丁政治哲学,则亦多有沿着我对奥古斯丁的理解,发挥出奥古斯丁并未直接讲过的内容。但花威此书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将奥古斯丁的政治哲学放在罗马帝国和早期基督教历史背景之下,做非常严谨和细密的历史与文献分析,因而充分展示其哲学、神学思考与历史考据和演绎相结合的功夫。花威一再强调,奥古斯丁并非一个书斋里的哲学家,他是希波主教,在大公教会并不占优势的北非宗教格局中,他要处理教会内外的诸多事务,更要与罗马帝国官员发生各种各样的交往,特别是在公元410年罗马城陷落之际,又必须将宗教与帝国事务交织在一起来思考。而正是这些纷繁的事务,才成就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奥古斯丁。如果他没有在公元391年戏剧性地进入希波教会,并被强行留下,而是如他一开始所愿的那样,与若干同道一起进行哲学沉思,不仅奥古斯丁将会走完全不同的道路,基督教历史也很可能会改写。花威没有满足于单线条地呈现奥古斯丁的思想体系,而是将他放在如此复杂的政教历史当中来看待,看上去线索有些多,是因为奥古斯丁的生活时代本来就有如此多的线索,他就是在如此复杂的情境之下,完成他的哲学思考的。
花威利用国外许多新的研究成果,对多纳图派分裂做了尽可能详细的梳理。我们读到全书最后,才会理解花威的总体考虑,因为多纳图派分裂,正是理解奥古斯丁政治哲学的要害。关注奥古斯丁的国内学者或多或少对多纳图派这个奥古斯丁长期与之斗争的基督教异端,会有一些了解,但对于多纳图派的主张究竟是什么,他们究竟是如何形成的,与奥古斯丁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大多数人不会花太多时间来了解。毕竟,奥古斯丁的敌人太多了,他一生都在与各种对手辩论,甚至可以说,正是与这些派别的辩论,才激发他深入思考许多特定的问题,使他完成其思想体系中的某些方面。
早期的摩尼教、中期的多纳图派、晚期的佩拉鸠派,是奥古斯丁一生最重要的三大对手,但三者对奥古斯丁的意义是不同的。摩尼教是灵知运动中的一个派别,并且是奥古斯丁早年加入的教派,但灵知主义被判为异端,在奥古斯丁之前许久已经发生了,奥古斯丁与他们的斗争虽然亦有在哲学上澄清一神教、三位一体等重要教义的意义,但摩尼教对大公教会的实质威胁已经式微,奥古斯丁与他们的辩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告别早年的自己;晚年与佩拉鸠派的斗争,主要是在原罪、自由意志、恩典等神学问题上澄清他的理论立场。早晚这两场大的辩论,更多是在理论和教义上的。但中期的多纳图派非常不同,它除了在理论上也提出一些挑战之外,更多是威胁到了大公教会在北非的地位。奥古斯丁在面对他们的时候,主要考虑的是如何以最恰当的方式化解政教危机,而面对多纳图派的思考与实践,正是奥古斯丁完成其政治哲学的关键环节,且有着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
奥古斯丁皈依
多纳图派分裂是一个有着重大政治影响的事件,它所涉及的不仅是基督教中不同教派之间的争端,更是刚刚基督教化的罗马帝国宗教宽容政策的深刻调整,而奥古斯丁在面对多纳图派分裂时摸索出来的方式,更成为基督教会应对宗教分裂的重要历史和理论资源。等到宗教改革之后,这个事件再次成为人们热衷讨论的话题。多纳图派成为一些新兴教派的模仿对象,奥古斯丁处理多纳图派的做法则成为宗教宽容争论的重要理论资源。在十六、十七世纪的欧洲,如何处理宗教争端无疑是最重要的政治问题之一,奥古斯丁思想的现代意义不仅体现在他成为路德和笛卡尔思想的来源,同时在于他是宗教宽容双方共同诉诸的理论权威。花威以多纳图派争论进入奥古斯丁的政治哲学,有着深刻的洞察力和敏锐的历史关切。
罗马在对众多民族的征服中,将各种宗教崇拜的神祇纳入自己的万神殿,同时要求被征服者也要礼敬自己的皇帝,因而发展出一套相当成熟的宗教宽容政策。犹太教和基督教由于其不拜偶像的禁令,拒绝礼敬罗马皇帝像,这成为早期基督教与罗马帝国发生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即便如此,罗马帝国与基督教的关系逐渐磨合,在《米兰敕令》中将基督教纳入宗教宽容的范围,仍然以相当高明的政治智慧平衡着帝国内的政教关系,虽然其后也偶有像朱利安这样迫害基督教的皇帝,和基督教暴力攻击异教的事情发生。多纳图派分裂,将这种并非常态的冲突推到了极端,对罗马帝国的宗教宽容提出了严峻挑战。多纳图派分裂始于对戴克里先迫教中上交《圣经》、圣器的基督徒的排斥,虽然在策略上也会借助于帝国的政治力量,但倾向于拒绝帝国对宗教事务的干涉,其游荡派则以各种极端的暴力行为威胁着社会秩序。多纳图派的兴起和壮大,导致北非基督教会的严重分裂。而奥古斯丁则在与多纳图派长期的近身交手中,不断调整着其对待异端的策略。按照花威的研究,奥古斯丁起初是主张以辩论和劝说等和平方式为主的,但面对多纳图派的强硬态度,特别是游荡派的极端暴力行为,不得不改变策略,使罗马帝国采取一定的宗教强制政策,成功使很多多纳图派信徒回归到大公教会。在调整其实践策略的同时,奥古斯丁也进行着理论上的总结。他深信,任何人的信仰只能出自内心,没有人可以被强制改变信仰,这是宗教宽容思想的理论基础。但在实践中,一定程度的强制会使某些人有机会接触宗教真理,从而导致其内心的改变,并且,面对如游荡派那样的暴力异端,没有必要的强制手段,大公教会又确实无能为力。所以,奥古斯丁越来越倾向于借助帝国的政治介入,强行使多纳图派信徒改变信仰,虽然始终坚持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而罗马帝国对北非宗教问题的政治介入,始终未能达到一个理想的均衡状态。虽然大公教会最终在更大范围内取得了强势,但未能彻底征服北非。北非后来被伊斯兰化,也和多纳图派分裂未能获得完满的解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多纳图派分裂以及奥古斯丁在其中的态度变化,展现的更实质问题是:宗教宽容究竟意味着什么?希腊罗马古典宗教本来就是多神教,而且本就有从异族引入神祇的历史,所以,罗马万神殿中神谱的变化不会从根本上改变罗马的政教格局和宗教形态,只要各民族人民认可罗马的政治形态。到君士坦丁之时,罗马帝国的神谱已经和古典时期非常不同了。有着如此多元的宗教格局,罗马在维护其政治统一的前提下,宽容各种形态的宗教,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但一神教的引入在根本上改变了这一状况。一神教的信仰本就拒斥多元,与罗马帝国的这种宗教格局格格不入。君士坦丁既是基督徒又是帝国大祭司的双重身份,只能是一种过渡形态。多纳图派虽然极端,但它将这种宗教特质最鲜明地展示了出来。从奥古斯丁对古典宗教的批判可知,他前期之所以认可宗教宽容,并不是因为他认可多元宗教格局的存在,他始终坚信基督教是唯一正确的宗教,并希望它能击败和取代异教;在与诸多异端的争论中,他也毫不妥协,只是他希望人们都能以和平的方式进入信仰,因为只有内心认可的信仰才是真正的信仰。他后来之所以认可帝国政治的介入,也是因为,只要人们有了真正的信仰,究竟是通过强制手段间接获得的,还是如他一般通过自己的摸索认信的,并无本质区别。当大公教会强大起来之后,教会对异教和异端越来越严厉的态度,正是这一思路的进一步发展。
奥古斯丁与异教徒争论
但在十六世纪宗教改革之后,多纳图派争论再次成为讨论的焦点。各种新教教派之所以脱离大公教会,并不是因为它们主张宗教多元,而是因为教义上的分歧,至于对自己宗教是唯一正确宗教的认信,它们丝毫不弱于大公教会。因而,奥古斯丁当年面临的问题和种种尝试,在这时又重新被提了出来。比如在英国,宗教宽容与否的争论,在都铎和斯图亚特两个王朝都伴随着最核心的政治斗争。在这场争论最精彩的一幕,洛克以《论宽容书》诠释了光荣革命之后英国的宗教格局后不久,普鲁斯特就对洛克发起了旷日持久的往复争论,直到洛克去世。普鲁斯特所援引的正是奥古斯丁对待多纳图派的态度。无论洛克还是普鲁斯特都非常清楚,只有出自内心的认信才有意义,但洛克由此推出,任何外在的宗教强制都是不该有的,普鲁斯特认为其间存在逻辑错误。在他看来,虽然很多时候宗教强制不能使人皈依真正的信仰,但某些外在强制有可能使人们关注从未关注的内容,由此就会真正产生内心的变化。如果可能通过外在强制间接使人走上真正的信仰,又怎能完全否定宗教强制呢?普鲁斯特的这一推理确实比洛克更加严密,洛克虽然写了远超过《论宽容书》十倍的篇幅来反驳,但大多数冗长论述并无足够的说服力,而普鲁斯特的宗教态度背后,正是奥古斯丁经过艰苦实践得出的结论。洛克所能找到的不同于奥古斯丁和普鲁斯特的一点是:宗教强制的前提是,必须清楚什么是唯一正确的真宗教。奥古斯丁在面对诸多异端的时候,当然毫不讳言他对唯一宗教的认可;面对洛克的质疑,普鲁斯特也同样坦然承认:当然,英国国教就是唯一正确的真宗教,而作为英国国教的信徒,难道洛克没有同样的信念吗?洛克只能不无尴尬地回应,他确实也认可英国国教,但出于政治现实的考虑,为了使英国和欧洲不要再次陷入宗教战争当中,诸多教派的信徒只能将这种认信保留在自己内心深处,而不能将自己的信仰强加到别人身上,包括国王和教士在内。这才是现代英美宗教宽容思想不同于古罗马的实质:它并不认可万神殿中的每一个神,而是面对教派多元的现实,在承认只有唯一一种正确信仰的前提下,将这种判断和选择完全交给每个人的内心。
洛克
洛克的模式,似乎使世界宗教格局走出了奥古斯丁式的困局,欧洲文明在经过宗教改革和宗教战争的阵痛之后,终于彻底走出了中世纪。但这并不意味着,奥古斯丁的多纳图派问题就彻底消失了。洛克和普鲁斯特争论的,只是新教教派之间的关系,二人不仅完全排斥了伊斯兰教等非基督教,甚至都没有将天主教作为宽容的对象。各新教教派之间的诸多共同理念,是洛克主义得以成立的前提。但在数百年后的今天,当世界宗教版图吸纳了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信仰体系,当如同游荡派那样的情形出现在宗教多元的世界,当许多宗教信仰与暴力、恐怖直接绑定的时候,奥古斯丁式的难题便再次严峻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而这一点,正是花威如此细密地研究多纳图派分裂的现实意义。
在花了两章的篇幅详细讨论多纳图派争论之后,花威才进入传统的政治哲学领域,即奥古斯丁对政教关系的讨论和对罗马帝国的态度。这种独具心裁的章节安排,展示了作者未曾明言的思想关切:多纳图派,并不只是奥古斯丁所面对的诸多异端之一而已,奥古斯丁在此一争论中的实践与思考,正是理解他的政治哲学的要害。从《圣经》开始,基督教思想家就已不像希腊政治哲学家那样,将政体问题作为中心关注,而是将政教关系作为终生讨论的核心问题。如何看待帝国与教会关系,在上帝之下如何看待尘世统治的合法性,如何面对异族的入侵与罗马的陷落,以及如何评价罗马的历史地位,都从属于这一根本问题。在对这些问题的深入讨论中,花威非常清晰地得出了他的卓见:罗马虽然属于地上之城,却并非魔鬼之城,虽然奥古斯丁并不认可第三座城,但罗马这样的尘世政治仍然在一定限度内有其积极意义。
我非常欣赏花威这种清晰和明确,特别是相对于拙著《心灵秩序与世界历史》而言。我在此书的写作过程中,一直坚定地认为,奥古斯丁将罗马当作地上之城,但地上之城就是魔鬼之城,因而罗马只能是魔鬼之城,因为如果不是上帝之城就是魔鬼之城,不可能存在第三座城。由于一直将第三座城之说当作批评的靶子,所以我特别强调奥古斯丁对罗马的否定,尤其是相对于优西比乌和奥罗修斯而言。但在全书完稿之后,我却越来越感到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比如,一个基督徒皇帝,当然是罗马帝国的首领,而如果罗马帝国就是魔鬼之城,难道这个基督徒皇帝也会是魔鬼之城的领袖吗?那他岂不就成了魔鬼或其代言人?奥古斯丁对基督徒皇帝的讨论,明确否定了这种可能。
吴飞著《心灵秩序与世界历史:奥古斯丁对西方古典文明的终结》增订本
于是在拙著即将出版之际,我就写了《地上之城与魔鬼之城:奥古斯丁政治哲学中的一对张力》一文来调整自己的判断。其中得出的结论是,无论上帝之城之善还是魔鬼之城之恶,都是就心灵秩序而言的,尘世中的地上之城当然不是上帝之城,因为它不存在于心灵秩序层面。一方面,地上之城并不能完全代表魔鬼之城的恶;但另一方面,不属于上帝之城的,归根到底还是会进入魔鬼之城,因为并不存在第三个城。我以前过度强调了后一个方面,而忽略了前一个方面。正是由于这两方面之间的张力,在地上之城与魔鬼之城的中间地带,才会有基督徒皇帝。地上之城与魔鬼之城的差异,其实是基督教政治哲学中一个非常根本,但又不常被注意到的问题。这个问题发展到但丁的《神曲》中,地狱就是魔鬼之城,但诸如佛罗伦萨这样堕落了的地上之城,当然不能等同于地狱,因为它虽然在源源不断为地狱输送着众多的公民,却仍然可以培养出不少天堂的居民。这正是奥古斯丁思想中的差异的进一步发展。而这种差异,是奥古斯丁本人并未明确讲出来的,却贯穿于他最根本的政治哲学思考当中。我在修订《心灵秩序与世界历史》时,只是将《地上之城与魔鬼之城》一文作为附录,而全书的主体内容既经成形,也就难以做太大调整。而从花威的写作中看,他并未直接受到我后来思路的影响,而是自己独立发现了罗马作为地上之城与魔鬼之城的差别,并在此书全面贯彻了这一点。这一点,弥补了我的研究中的一个缺憾。
但丁
总之,花威此项研究清晰地呈现出来,奥古斯丁开启了以政教关系为中心的政治哲学传统,以区别于以城邦政体为中心的古典政治哲学,和以个体自然权利为中心的现代政治哲学。希腊罗马对政体问题的讨论虽然在中世纪教会和国家制度中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留,但已经不再作为政治哲学的第一问题。正是思路上的这一重大转变,才产生了许多新的政治哲学问题,也塑造了中世纪欧洲的基本格局。等到政体问题在马基雅维利、博丹、霍布斯等近代思想家笔下重新被发现之后,大家已经是在新的欧洲格局之下,再来讨论这些问题了。此时,政教关系已经不再像中世纪那样作为第一位的政治问题,但它始终伴随着最重要的政治哲学争论乃至战争,伴随着现代人对自然权利的思考,使人们不得不回忆起一千多年前的北非与罗马。
·END·
本文首发于《澎湃新闻·上海书评》
相关推荐
神曲
但丁(DanteAlighieri,1265—1321)是意大利最伟大的诗人之一,被誉为西方文学史上与荷马、莎士比亚齐名的巨匠。他的杰作《神曲》代表了中世纪文学的最高成就,耗时十多年完成。2021年是 【意】但丁/DanteAlighieri 2023-04-19 14:15:18萤火谷的梦想家
艾莉森•麦吉出生于1960年,是美国《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同时也是大都会州立大学创意写作课的教授。她的作品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并出版,也曾被提名普利策奖,并获得苏斯博士奖金奖、克里斯托弗图书奖、美国 [美]艾莉森•麦吉/[美]克里斯托弗•丹尼斯/绘 2023-03-27 16:50:25© 2023-2025 百科书库. All Rights Reserv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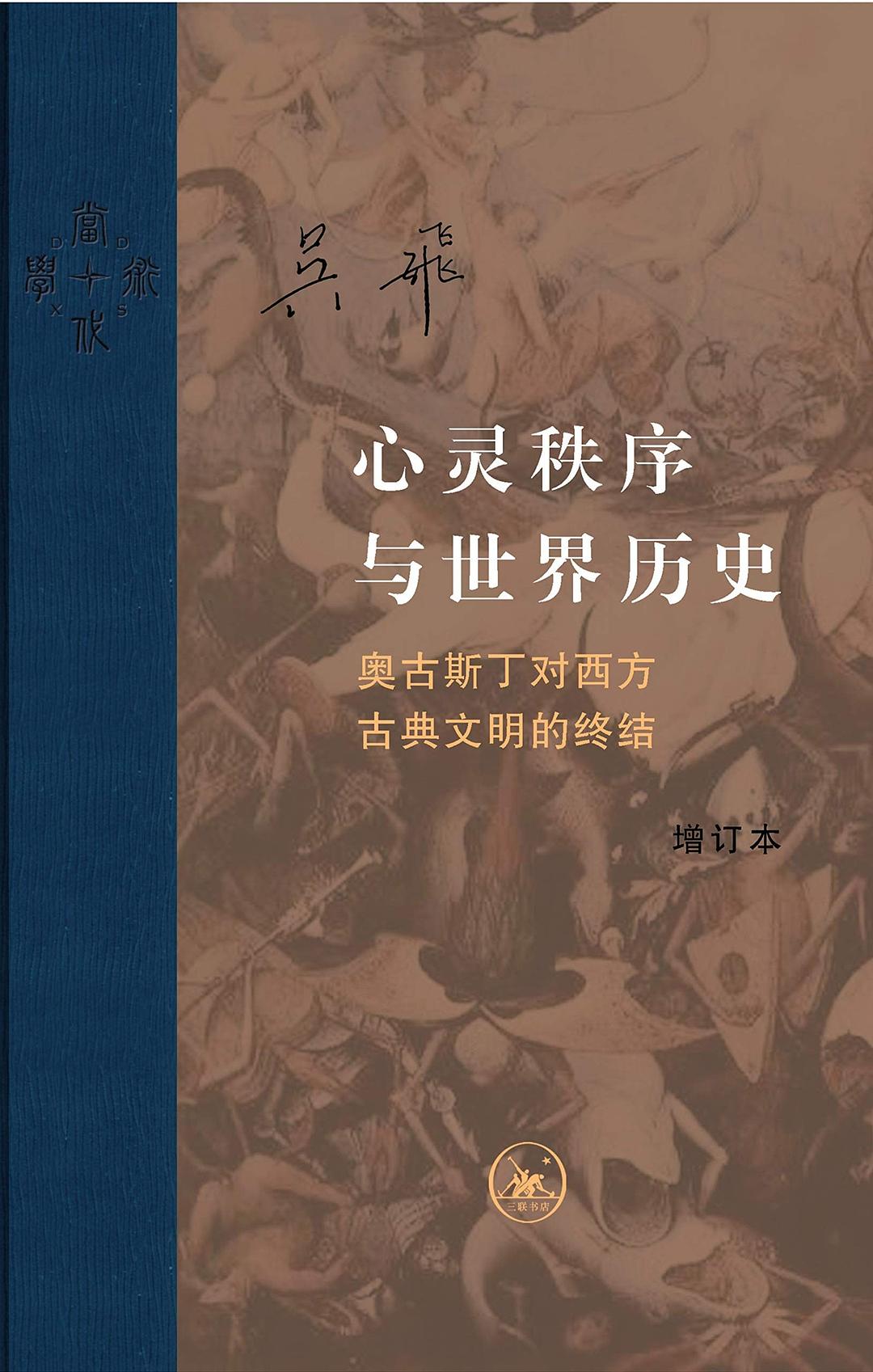








发表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