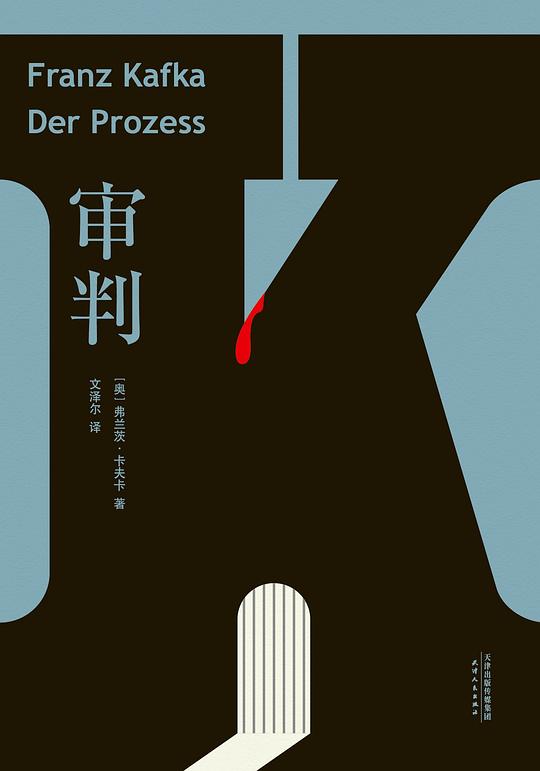
审判迷雾重重
书名:审判
1
0

神经质小狮子 2023-10-09 16:31:49
写于2022年12月22日,在噩梦开始之前。
看完《审判》后我陷入长久的思绪空白,不知道该想些什么,也不知道该有什么样的感受。直到终于能下笔的时候也只有一句话:在严密的作恶的系统里没有答案。
小说讲述了主人公K陷入的一场无妄之灾,一场没有开始也没有结尾的审判。这场审判经历了调查、逮捕、庭审,看似流程完备与现代文明中的审判别无二致,可事实上这些都不存在,它只是系统完成的一次猎杀。
没有答案,作恶的系统严密到将“恶”切割成无数细碎的片段,以至于作恶的人都不曾察觉。正是因为系统将完整的“恶”分割地如此细碎,在系统中的人只需要完成“份内的工作”就可以完成作恶的一环,而系统的每个组成成员所完成的工作甚至不足以被给予道德上的评价,因为它是如此微小而难以被分辨。这么细碎的恶,一方面不被作恶的人所察觉,他们可以用无数正当的理由毫无感觉地继续下去而不至于使系统难以维持运作;另一方面,在他们所有人共同完成的巨大的邪恶面前,每个人单独的恶显得不足指摘,比如私吞被逮捕的人的财物的看守,他们道德上的污渍小得实在不足以和整个系统的恶相抗衡。
然而这种被严密分割的恶使系统的每个成员都并非不可替代,不需要任何特殊技能或品质就可以成为系统的一环,以至于看完小说后没有任何一个人的脸是鲜活的,即使有外貌描写也无法想象到一张具体的脸,他们都不像是人而是某个精密仪器的最小零部件,每个人都是配角,都像是画布上可有可无的一笔,但谁都没想过,如果去掉他们,系统就不复存在。当然,作恶的系统不会留给系统最底端的人反思的权利,反思几乎是一种特权。
最后一位射杀翻越柏林墙逃亡者的士兵在柏林墙倒塌后受到审判,如果东德射杀翻墙的逃亡者是在作恶的话,那这个小士兵就是作恶的最小一环,他只是听从命令,而他的行为在当时甚至是合法的。这样的审判在当下是明显有争议的,可就在这时几乎是相同的审判重现了历史:就在这个月,2022年12月,德国的法庭宣布了一位现年97岁的老人IrmeardFurchner在一万多起谋杀罪中成立从犯,因为这位老人曾在18岁时担任纳粹的一个集中营的秘书,处理文书工作。对这位老人的审判结果无法让人理解和接受的地方在于,不仅是在案发后近八十年对作恶链条最底端的一人作出惩罚,也在于虽然纳粹系统的恶是显而易见的,但仅仅从事文书这项具有完全替代性的(即不是仅有这个人才能完成的独创性行为)、甚至在当下可能会被机器取代的(即完全没有个人意志)、完全中性的(写文书很难有道德评价)工作是难以分辨其中多大程度是一种作恶的行为的。
与此同时,像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那样,作恶之人无法察觉自己是施害的一方,自然无法察觉自己也是受害的一方,是可能被作恶的系统随机选中的下一个人。可这些面目相似的人又太像是系统的工具,他们在那个零件被固定着的位置一动不动又不能移动,以至于他们有时又仿佛站在受害者一方,说着“我理解你”“我也没办法”,但他们永远不可能跨过哪怕最微小的权力的天堑来到系统的对面。就像是K在预审法庭遇到的清洁工,他像是一个普通人那样谈话,可转身,他就可以隐身在权力的系统里,在系统里过着一旦有日程安排就要清空房间的寄生生活。
没有答案,作恶的系统不提供任何答案,这是巨大的、足以吞噬人的权力。从看守和官员闯进K的家开始,K就在不断提问:问自己被逮捕的原因是什么,没有答案;问他们是谁,没有答案;问自己应该什么时候出现在法院,没有答案;问应当如何解决官司,没有答案。系统用权力构建了细密的网,系统内部不提供任何答案,只是“好心地奉劝”,将被害者碾压成他们需要的形状。仅是寻找一个问题的答案,就会消耗被害者的大量精力,哪怕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只是系统内部的人几秒之间就能回答的一句话。小说里的系统和审判涉及的法律系统在戴岑豪斯看来并不是一个法律体系,因为它既没有法律的确定性,K至死都没有被告知自己涉案的案由;也没有保障权利的方式,即使K可以聘请律师,但律师和法庭的运作都是不透明的,没有任何程序正义可言;在没有答案的系统中更不存在在法律框架内取得权利的可能性,这个系统没有答案,也没有提供答案的意图,本身也不遵循任何能被系统外的人所得知的规则。
系统没有答案,吞噬掉人提问和思考的能力和空间。小说中大量提到了K在面对任意变化、无法预料的新变化时的思考和质疑,他原本为适应突如其来的审判做了应对的设想,在面对预审法庭的法官时他可以用他对秩序和权利的固有理解为自己的案件争取,乐观地认为自己的案件不会牵扯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可随着他一次次得不到答案,只能依靠自己寻找一声声指向不明的回音时,他失去了寻求答案的欲望,他为了应对官司、为了试图看清这个系统的运作而筋疲力尽,不断奔走在一个个说不通道理的人之间,不再抱有得到答案的希望。直到一年后K被杀死的那一刻,他仍没有得到哪怕一个问题的答案,他也不需要得到答案了,他的案件以失去生命的方式被了结。甚至在看小说的过程中,系统不会给人问出“为什么”“凭什么”的机会,只能看着自己无力地被系统摆布。
看到K的死亡时,我想问的是“他疼吗”。疼是对重创的反应,疼是突然醒来意识到自己的存在,疼是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可当刀刺进K的身体里时,我甚至认为他已经感受不到疼痛了,他只有眩晕和彻底昏睡,头上悬着的刀终于还是落下了。厄运平等地追随着被系统操控的每个人,恐惧侵吞了回归正常生活的可能性。一个与无法被统计数字的老人在半天之间形神俱灭,而系统却可以自由切换官方叙事的语境,调侃致命的灾难。厄运终会降临,我甚至不敢祈求自己和爱的人被放过,不能有任何侥幸认为可以逃过劫难。系统随意地绞杀,被害对象身份是不确定的,因为系统的权力大到没有被撼动的可能,它不在意被害人的身份,K是个体面的银行襄理也无济于事;它不在意被害人的情感,没有给离去的人说再见和正式告别的机会;恨意只能伴随恐惧被淹没,个人的情绪没有宣泄的出口,因为在系统的暴力的作用对象是集体的时候个人是无法被凸显的,只能眼看着生活被摧毁却拿不回一点尊严。系统或许有改变的时刻,但等不来那一天的人们永远不会得到道歉(因为承认错误会使系统失去权力的合法性)。
没有答案,在严密的作恶的系统里没有答案。《审判》的真实感带来的恐惧仍然无法抹去,它也没有提供答案。如果真的能从系统外找到自己的出口,我想还是要回到爱和反思。爱是勇者之识,意识到系统的恶随机降临也无法逃脱,更让我能面对能把人拉入深渊的恐惧。因为知道了没有那么多来日方长,才能为具体的关系赋予更多意义、有勇气说出自己的爱、过自己真正想要过的生活。反思也是如此,反思让我们知晓身上的伤从何而来,知晓我们作为系统的集体灾难的批量产品幸存下来的意义。另外,书写也是答案,是思考的载体,是抗争系统正确集体记忆的方式,在每天的生存中交付一部分自己来对抗遗忘和麻木,带着不安全感一点一点把自己交给世界保管,与他人有更强的联结感,去爱或远或近的人与世界,找到答案。
相关推荐
萤火谷的梦想家
艾莉森•麦吉出生于1960年,是美国《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同时也是大都会州立大学创意写作课的教授。她的作品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并出版,也曾被提名普利策奖,并获得苏斯博士奖金奖、克里斯托弗图书奖、美国 [美]艾莉森•麦吉/[美]克里斯托弗•丹尼斯/绘 2023-03-27 16:50:25鬼马女神捕1·绝密卧底(上)
腹黑凤凰vs毒舌鸡妖——蓝翎:“小姬,跟我去人界吧!”姬十四:“干吗?让人宰了我做小鸡炖蘑菇吗?”蓝翎:“不啊,让妖怪宰了你做小鸡炖蘑菇更气派。”凤凰蓝翎和鸡妖姬十四生活在无忧无虑的灵界。他们的故乡叫 郝天晓 2023-04-17 00:22:47© 2023-2025 百科书库. All Rights Reserv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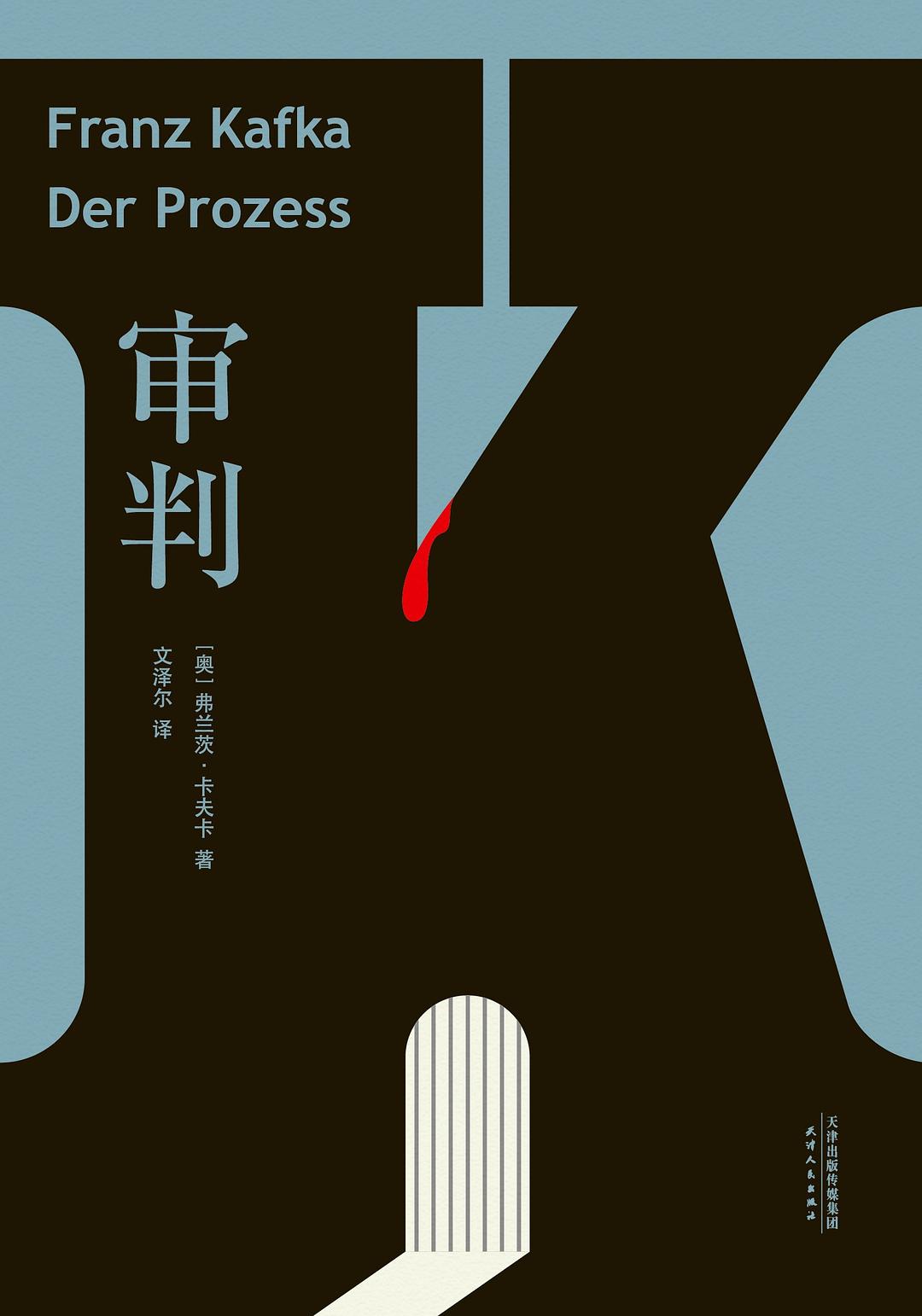









发表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