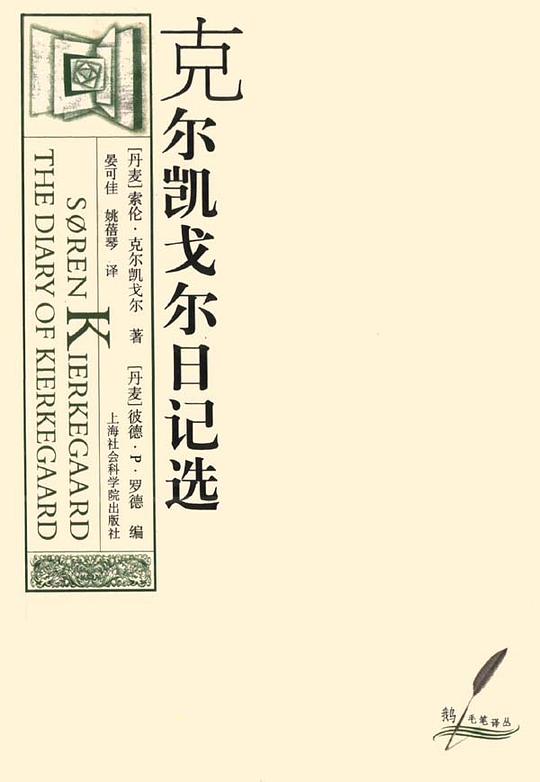
"克尔凯戈尔日记选:黑暗后的一束光"
书名:克尔凯戈尔日记选
1
0

红牛能量 2023-09-22 14:37:15
黑暗后面,那一束光隐藏。江介。
“人们可以趁莴笋心还没有长成就把它吃掉的;不过它那极其鲜嫩而又卷曲的菜心和它的菜叶到底是大不相同的。在精神世界里情况也完全相同。人们终身忙碌,其结果只是:个人绝少能够长成一颗心;另一方面,那些实际已经长出一颗心来的思想家、诗人或宗教徒却根本不能和大众打成一片,倒不是因为他们不善与人相处,而是因为他们的职业要求他们独自一人潜心工作,要求他们保持某种与世隔绝的状态,追求关于其自身的知识。”
这段话出自于丹麦哲学家索伦﹒克尔凯戈尔的《克尔凯戈尔日记选》。这本小书白色封面,极为素雅,晏可德、姚蓓琴翻译,一九九二年三月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特别适合一个人安静的时候用心阅读。它能使人反省自身,思考肉体与精神的双重关系。这时候,“个人”就犹如一眼深井,不断地像下面挖掘,再向下面一些,直至挖出来一眼清泉。这本小书篇幅并不很长,每页却洋溢着醍醐灌顶般箴言名句的智慧灼人。可以这么说,是一本随着阅历增加使人越读越厚的书。
与克尔凯戈尔那些厚重、晦涩、逻辑性强的专著比较起来,这本日记却显得如此朴素、真挚、动心。有时候像是他一个人喃喃自语,写满并分析自己的痛苦与挣扎。有时候像是在向对手直书与痛斥。有时候又像是以高屋建瓴的位置分析并宣扬自己的学说与见解。日记记载的一些事件,在旁人看来是微不足道的,因为哲学家的身份与敏感的心灵相互交织。因而文字熔铸感性与理性于一炉。“和她的情绪、观感、片段的思想火花结合在一起,总能激发出来特别的效果”——一以贯之的是哲学家与神学家克尔凯戈尔这个双重身份。作为读者的我们,有时候不免与克尔凯戈尔共情那些日常事件所激发出来的心灵感悟。有时候能搞清楚他的哲学主要一些观点的阐释与生成时的来龙去脉。有时候又跳跃式地穿梭于克尔凯戈尔不同哲学观点的丛林中。关于克尔凯戈尔的日记与著作的关系,译者有特别生动的概括:“克尔凯戈尔的日记和他的大量著述有着一种特别的联系,两者分别形成了他的思想的历时性的一面和共时性的一面。日记里的思想往往是片段的、格言式的甚至是跳跃而不顾及逻辑推演的;著述里的同样思想则显得比较系统、比较完整,具有一种比较精巧的表现形式。日记往往是他观念的准备和训练;而他的著作则是他的思想的完成和定型。日记里的克尔凯戈尔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呼之欲出,而著作里的克尔凯戈尔则是一幅古典式的肖像画。”
作为个体生存,在人世间必然有各种需求,包括满足肉体与精神上两方面的“欲望”。伴随着欲望的出现,必然就出现了痛苦。而克尔凯戈尔正面并且积极地承认并且面对了各种“痛苦”。他说:“往往是微不足道的捉弄令生活痛苦异常。我将乐意盯着怒号的狂风,热血沸腾,奋力前行;但是只要一阵和风吹来,将一颗纤尘吹进我的眼睛,就令我烦恼,竟至于裹足不前了。”“正如一个伤员渴望拆掉缠绕在身上的绷带一样,我那健全的精神渴望赶去我肉体的羸弱;正如一个得胜的将军,当他的坐骑挨了一粒子弹时,便大呼大嚷着要换一匹新马一样——哦,但愿我的得胜的健全的精神一样勇敢地呼唤:给我换匹新马,给我一个全新的肉体。”克尔凯戈尔对于痛苦的正面认同,并且像轭绳一样紧紧地勒进自己的肩膀上。
为什么克尔凯戈尔有一种直面认同这种“痛苦”的意识呢?在我看来,这与他的“基督教徒”的自我认同感是密切相关的。克尔凯戈尔的清醒之处,在于自己生活时代,他已经意识到:“基督教”已经过于僵化和程式化,完全背离了“基督教”的原教旨,掉入一种世俗化的死胡同。所以他才痛批那个时代社会下的“基督教”的各种教会、教父、牧师。对于教主、牧师的质疑,斥责他们“掌握行政大权”,同时也斥责他们沦为卖弄口舌之徒,不仅动摇了基督教的根基,甚至“我一向以为,一切认为教士应和大学讲师一模一样的想法会由此(esipso)招致基督教的灭绝”。克尔凯戈尔甚至说过:“教授是人间最乖谬的蠢货,因为他代表这一个企图通过反思而穷尽那远远高过反思东西的满脑袋古怪念头的人。”
他认为对于基督教徒而言,直达殿堂的有真伪两条道路——“一种是承受痛苦;另一种是修学毕业当个教授,专门讲授别人的痛苦。前者是踩出一条道;后者是在道边上晃悠(为此,边上晃悠一语可用作所有讲座和讲座一传道的代名词,而边上晃悠可能是以沉沦告终。)”对克尔凯戈尔而言,基督教的质朴性不是指的鼓吹知识、鼓吹人人都能成为一个天才等,而是指的是灵魂安贫乐道、先求上帝的国。他直言道:“基督教倾向于使任何事物趋于实现,成为一种现实的存在,这种现实的存在是唯一和它真正相关的中介。除了身体力行之外是没有其他任何方法可以拥有它的,除了启发和唤醒众人以外是没有其他任何方法可以拥有它的,除了启发和唤醒众人以外是没有任何方式可以把它拿来相互交流的。”正因为如此,克尔凯戈尔被他的同时代人指责为离经叛道,因为他动了教会的实际利益。
从某种程度而言,克尔凯戈尔的痛苦恰恰是同时代人对他的攻讦和不理解,而他恰恰维护了“基督教的”纯洁性,即是“身体力行性”,这样,由要你“信仰”,变成“我要信仰”,从内至外的一种个体精神生活需要性,“生活在凡俗即意味着要做一个基督徒”。
克尔凯戈尔认为,真正要抵达“基督教”的最高层次的“永恒之境”只有一种途径——“厌世”,“那能达到厌世的人或者说那在上帝的帮助下能坚持这一思想的人,即正是上帝以他的爱而使他达到这一点的人,在基督教的意义上,已经经受住了生活的考验,已经变得成熟而进入永恒之境。”这样看来,真正能够抵达到“信仰大道”的绝非有捷径可走,一定要经受一番脱胎换骨的锤炼与蜕变,而这种蜕变无疑是由量到质累积的,由“厌世”这扇“窄门”方可登堂入室。正因为“厌世”,这种决绝的境遇,个体以义无反顾地舍弃所有,对于“基督”抱有永不背叛、永远隐忍的态度,“然而他是爱、无限的爱,但是只有你濒临于死,他才能够爱你;那痛苦的折磨乃是出乎怜悯、出乎把永恒的痛苦转化为暂时的痛苦的怜悯。”为了这种“痛苦的怜悯”,所有痛苦的隐忍都是积极向上的,而不是消极向下的,构成一种不断“量”的累积,只有这种“量”的累积达到一种极限的时候才会获得基督真正的爱。对于“基督徒”来说,这就是一个诞生“信仰”的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由克尔凯戈尔的这种观点,我们深受益处,其实不仅是“基督教徒”,推而广之,现代社会中的每一个独立个体都应该以这种方式夯实和抵达自己的“真正的信仰”。有时候我常常想,一个真正严肃、虔诚、崇高的个体面对自己想抵达的理想彼岸,这种理想中的“信仰”本就含有宗教色彩,甚至可以说是殊途同归。根据克尔凯戈尔的观点的启示,我们完全有可能相信,自由宗教阶段才是最佳的生活方式。因为只有达到宗教阶段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说明他必然不满足于自己浑浑噩噩的现实生活,不满足于肮脏浑浊的现实,而是返回到自己孤独个体的丰富的内心和灵魂之中来,无条件的服从“上帝”的召唤。当然这种“上帝”是一种精神至高点的高度精神化的浓缩,可以看成道家中的“道”、佛教中的“涅槃”、希腊哲学中的“逻各斯”等等,其实就是一种抵达“真理”的过程。即使是信奉艺术也不例外,也可以视之众教徒眼中的“基督”。我们必然要经历各种蒙昧的过程,由重物质趋向重精神,由重经验趋向超经验,由怀疑趋向笃信,由此岸趋向彼岸,最后甚至达到“厌世”这扇窄门,犹如鲤鱼跳龙门,如果跃过去,前面是一束耀眼的光芒,而身后是无边无际的黑暗……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境地就意味着决绝地遵从信仰召唤之路,而这种“厌世”反而成为信仰之路的一个先决条件,一条必经之路。
在《致死的疾病》中,克尔凯戈尔认为,“致死的疾病”,也就是厌世,必将导致两种结果,一种是死亡;另一种直接催生的就是“信仰”,成为一名真正的“基督教徒”。由此可知,“信仰”并不是廉价唾手可得的,而是珍贵至极,意味着一种“冒险”。
正是因为这种“冒险”,类似于在两座高山之间走钢索的行为,是一种舍弃所有义无反顾的行为,区别开来众多的伪教徒与少得可怜的真教徒,方彰显出来“信仰”的稀缺性与检验性。“无立足境,是方干净”,唯有彻底放空,才意味着然后的“持守”。同时正因为这种“冒险”属性,同时说明了追求“信仰”——不是一种物理反应,而是一种化学反应。
孤独地坐在黑暗中,台灯投下昏暗的光区,将我的身影分割在白色墙壁上,映成好几部分。而这本《克尔凯戈尔日记选》就静静地躺在书桌上。掩卷长思,好像自己的身体也沦落进这漫天的黑暗之中。隐藏在黑暗后面的那一束光,微如豆火,每一个个体在孤独无助的时候都能洞若观火。为了最终这点人间珍贵的“簇火”,一切痛苦都是有价值的,最终有了“重”的分量,惟有萃取这巨大的、无数的重量,获取到那一点点之轻——“信仰”,才使得人类保持灵性与精神的纯粹性,而免于归之于兽类。同时,正因为人世间的种种痛苦,我们才能植根于大地,并且在地面上踽踽而行,避免了自己像一种氢气球一样,没有任何铅坠,会堕入虚无的境地,最终消失在天空中……
孤独的境地,反而更能内省并理性地反观自己,于是这种“孤独”也成为一种成为“自由”向上攀登的一种最有效途径。克尔凯戈尔说:“衡量一个人的标准是:在多长的时间里,以及在怎样的层次上他能够甘于寂寞,无需得到他人的理解。能够毕生忍受孤独的人,能够在孤独中决定永恒之意义的人,距离孩提时代以及代表人类动物性的社会最远。”当我自己觉得孤独、绝望之时,正是这句话给予我最后的慰藉,植根于现实,并且热爱现实中那个承受各方压力与痛苦的自己,“年复一年,我继续当着作家,为了理想而承受着来自内心的痛苦”,依然努力,就是为了最终走上前去,获得最后一点“隐藏在黑暗后面的那一束光”,尽管它看上去那么微弱,但是对于前行者来说是珍贵至极,像是一只搀扶羸弱行人的温暖之手伸过来……
二零二三年九月十九日。
相关推荐
哲学的底色
作者的目标是让本书变得容易理解,读者只需轻松阅读即可获益。真、善、美、自由、公平、正义是人类追求的主题,也是哲学的根本意义。在本书中,作者采用通俗易懂的叙事方式,让哲学思想逃脱晦涩难懂的语言,使读者可 [美]莫提默·艾德勒 2023-03-25 16:12:16美学权力
【编辑推荐】1.作者在哲学家从认识论和形而上学等不同的面向对“美学”进行理论奠基时,看到了“接受理论”或者“艺术理论”的困境。她指出纯粹理论化的不足,并对抵制“美学”彻底抽象化做出了努力。2.作者圣吉 [法]巴尔迪纳·圣吉宏 2023-05-26 02:56:51康德《实践理性批判》句读
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是他哲学体系中的重要部分之一,于1788年出版。相比于前一部作品《纯粹理性批判》的任务是研究人类认识力先天要素之规定,本作则关注于理性实践中的先天原理,考察其可行性、范围和限制。 邓晓芒 2023-03-25 16:13:27游世与自然生活:庄子评传
庄子是战国中期伟大的思想家,他所关心的许多问题仍存在于当代,他的思考仍启迪着今人。颜世安教授以隐者传统和道家思想为背景,以郭象所注三十三篇本《庄子》为依据,博采庄子研究众家之长,从全新角度解说庄子,阐 颜世安 2023-05-26 02:39:07古典柏拉图主义哲学导论
:这本书对于柏拉图主义哲学史进行了全面的梳理,时间跨度长达九百年,涵盖了从学园开始到晚期新柏拉图主义的整个历程。书中详细研究了代表性人物的主要观点和彼此的思想联系,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柏拉图主义哲学的全 梁中和编著/梁中和 2023-03-25 16:14:25如果我们错了呢?
用有意思的知识,验证有价值的思维方式。《如果我们错了呢?》是美国知名哲学思维畅销作家查克•克洛斯特曼挑战传统文学、文化与科学知识的上乘之作。这本书被《出版人周刊》、《科克斯书评》等13家媒体评选为年度 [美]查克•克洛斯特曼 2023-04-10 20:30:38© 2023-2025 百科书库. All Rights Reserv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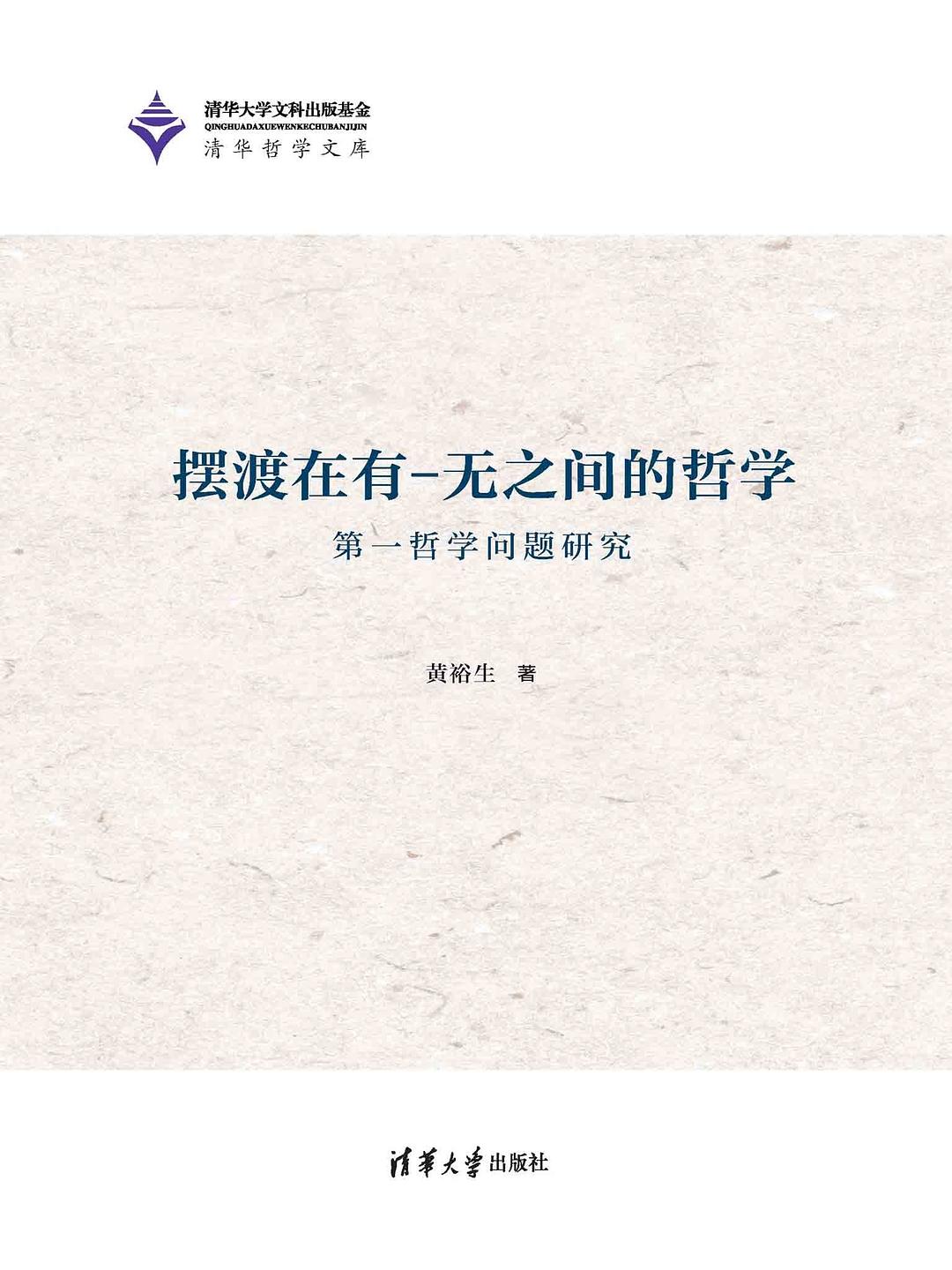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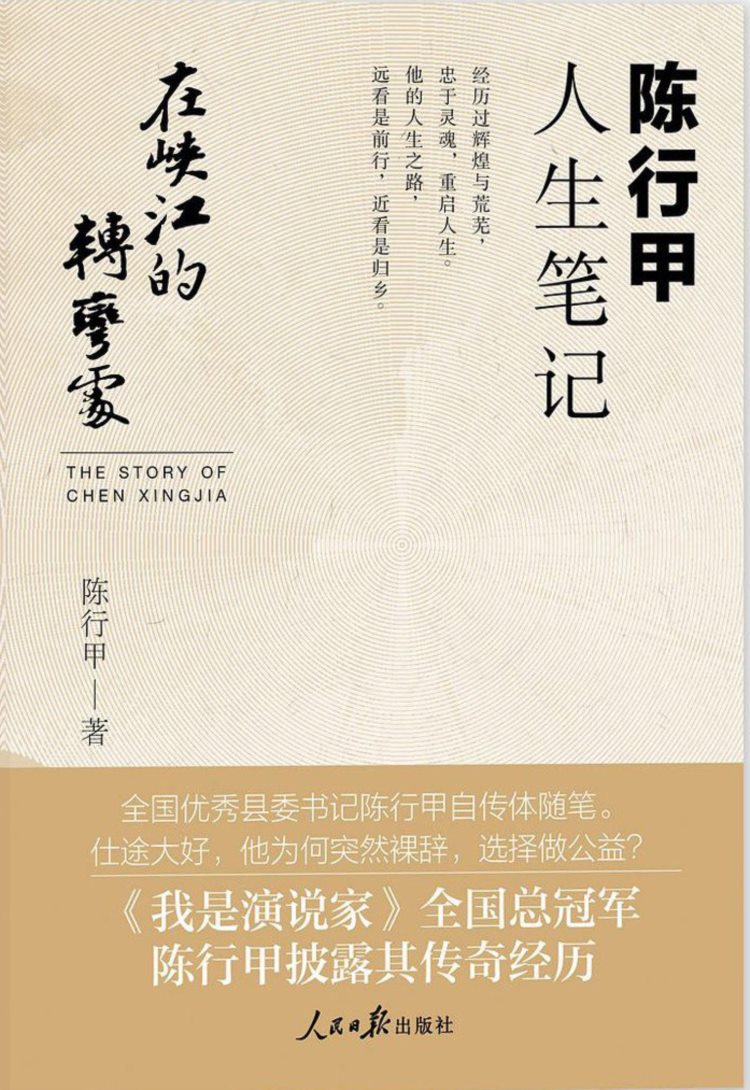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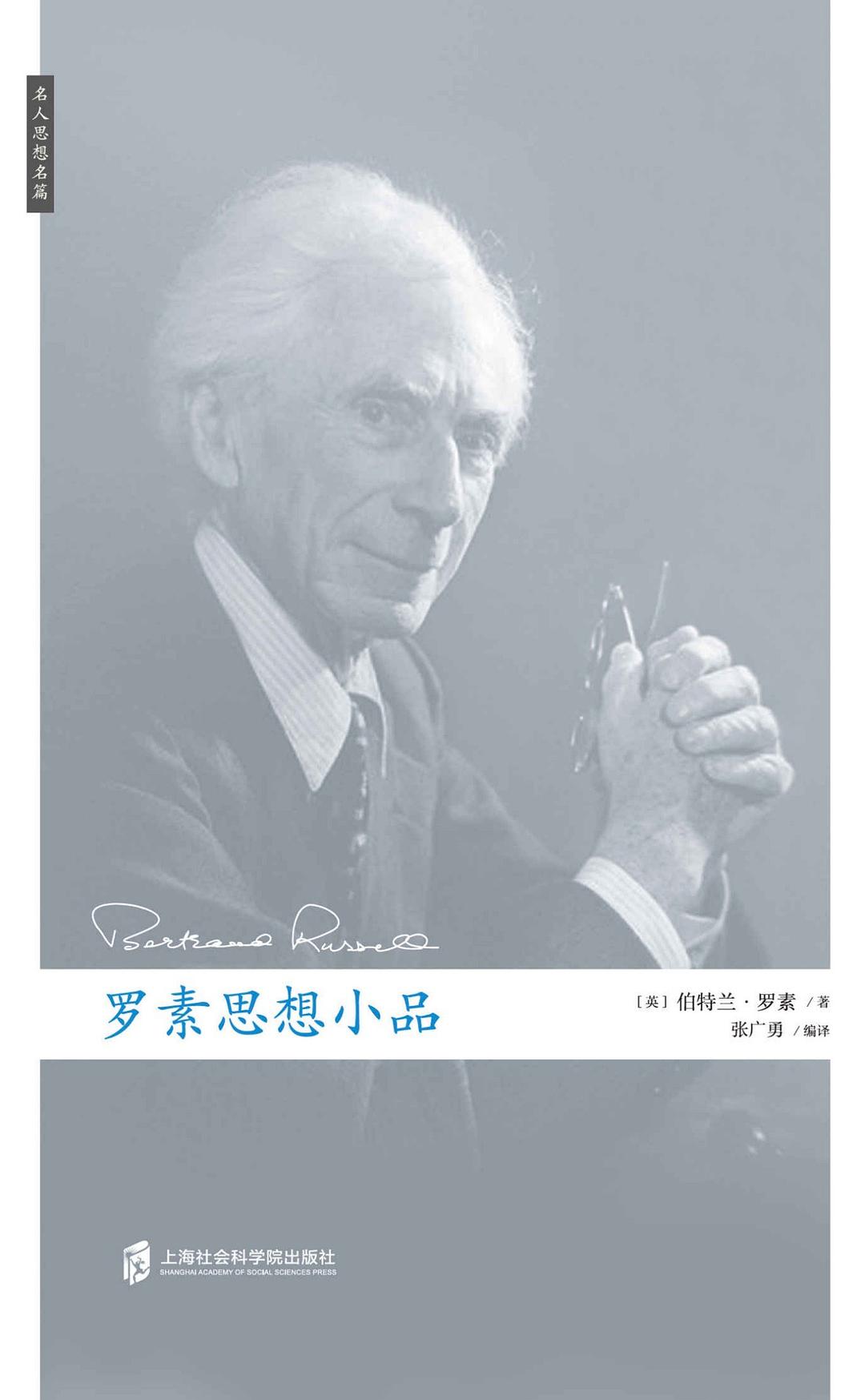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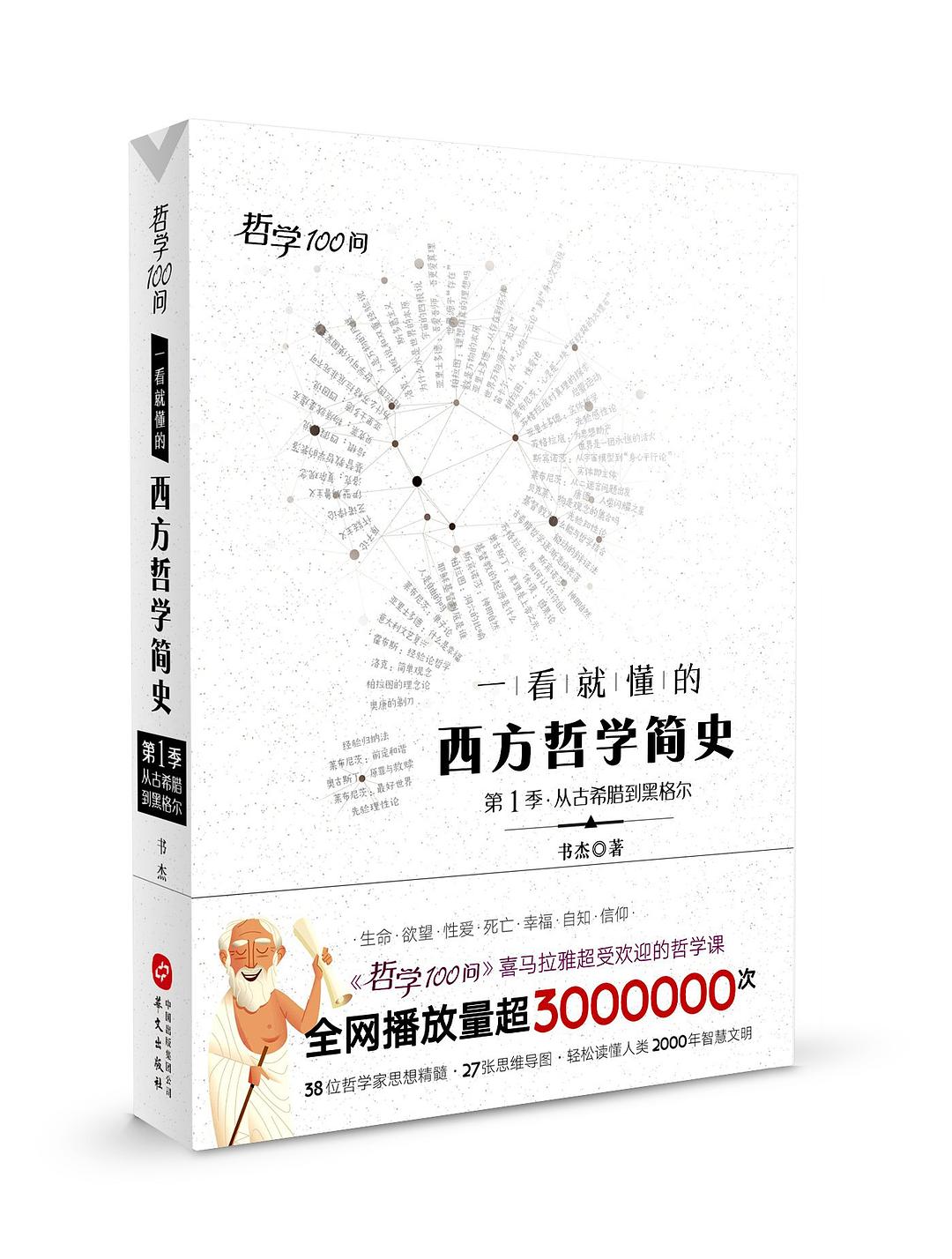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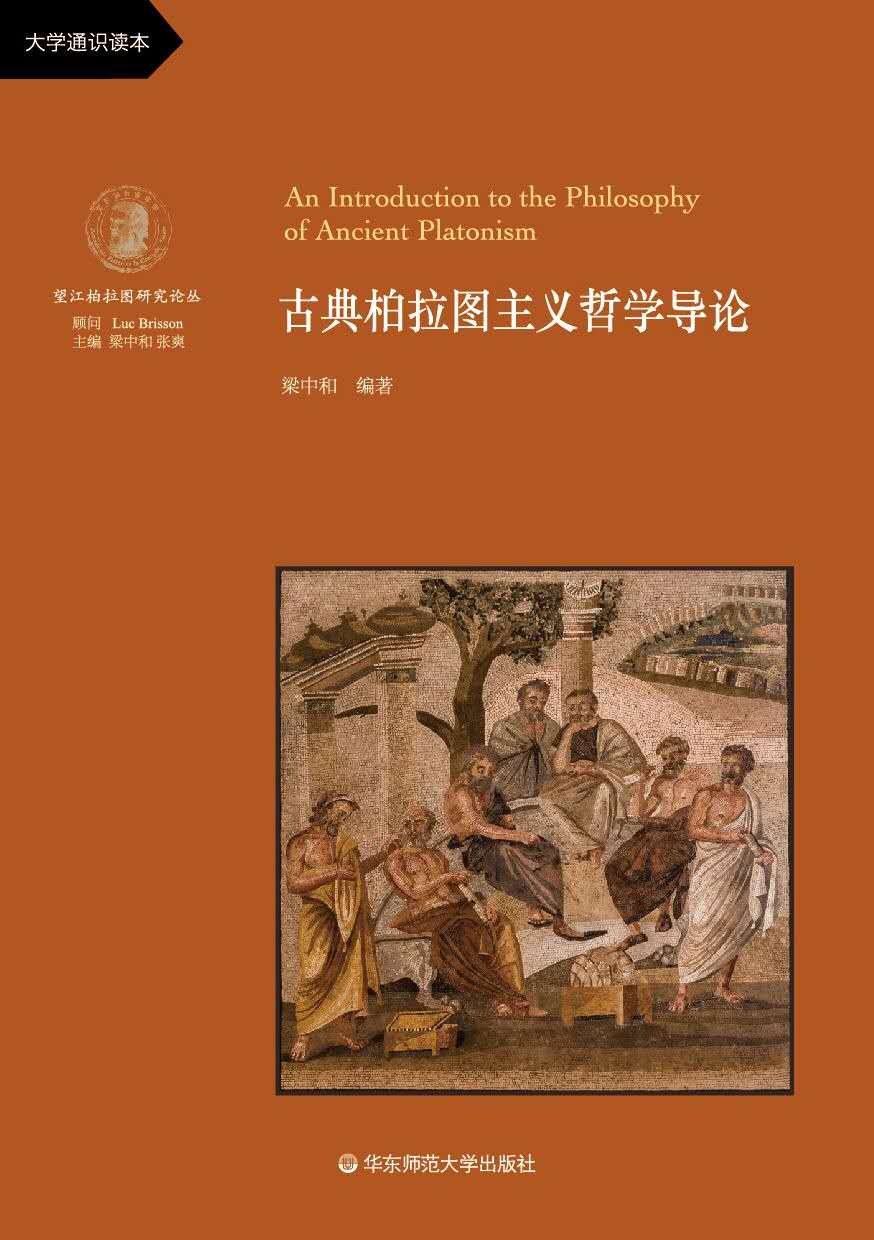

发表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