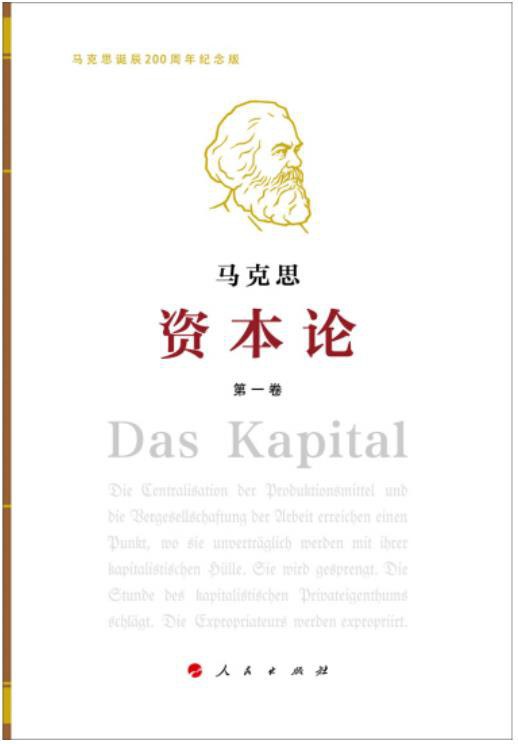
资本论第3卷:虚拟资本与资本主义自我消亡的哲学思考
书名:资本论
1
0

胡说八道 2023-09-13 23:21:44
内容提要
资本主义的信用关系系统,是资产阶级在经济物相化空间中巧妙运用的一种彻头彻尾的经济欺诈和合法的公开掠夺。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最奇特的我-他自反性劳动异化,也是资本(生息资本)拜物教的最高伪境。当产业资本家通过虚拟的信用关系直接占有非其私人所有的巨大社会资本时,就会掌握剥削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巨大资本力量,在一定意义上,这种社会化的资本可以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这就为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提供了缓冲空间。资产阶级在信用关系中创立的股份公司,是一种以虚拟资本的方式出现的生产资料社会占有,但这预示了一个可能的前景,即私有制向“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过渡,这正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客观历史趋势。
关键词
《资本论》;信用关系;虚拟资本;股份公司;自由人联合体
作者简介
张一兵(1956-),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哲学系博士生导师(江苏南京210023)。
文章来源
《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年第1期。
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视角,深刻地剖析了作为资产阶级经济物相化空间中以信用关系建构起来的虚拟资本的历史作用。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的信用关系是生息资本复杂的升级方式。它从剩余价值分配的异化形式,畸变为可以客观集聚巨大社会资本力量的虚拟资本关系,以异化的信用关系伪境之上的股份公司形式,缓解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对抗性矛盾,也为走向自由人联合体的新社会奠定了现实的可能性。
一、信用:资本拜物教的存在方式
在《资本论》第3卷的最后,马克思明确提出了资本主义经济物相化空间的神秘性问题。他说:“在论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甚至商品生产的最简单的范畴时,在论述商品和货币时,我们已经指出了一种神秘性质,它把在生产中由财富的各种物质要素充当承担者的社会关系,变成这些物本身的属性(商品),并且更直截了当地把生产关系本身变成物(货币)。一切已经有商品生产和货币流通的社会形式,都有这种颠倒。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和在构成其占统治地位的范畴,构成其起决定作用的生产关系的资本那里,这种着了魔的颠倒的世界就会更厉害得多地发展起来。”[1]这正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揭示的带有神秘性质的经济定在之上的商品、货币和资本三大拜物教。马克思在此指出,经济拜物教的本质是将经济物相化中的对象化劳动倒置为物,人与人的关系颠倒地呈现为经济事物之间关系的事物化物像,这种经济负熵质被直接误认成这些经济定在本身的自然属性,这就是物化观念的发生。在这个意义上,物化误认是整个经济拜物教的本质。更重要的是,马克思在这里指出,无论是商品中价值关系颠倒为货币,还是生产条件作为颠倒为物性对象的资本关系,都生成着资本主义经济物相化空间中特有的着了魔的颠倒世界。从马克思始于《伦敦笔记》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第三次经济学研究的全部过程,我们看到了资本主义这个着了魔的颠倒世界的历史发生和复杂的赋型过程。不过,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真的让我们直接遭遇一种“更厉害得多地发展起来”的着了魔的颠倒世界,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生息资本异化之上建立起来的整个信用关系伪境。如果说资本主义的生息资本“是一切颠倒错乱形式之母”[2],那么经济物相化空间中出现的信用关系场境则是资本拜物教更高级的存在方式。这也是一直到今天还横行于世的资产阶级经济物相化空间中最神奇的金融海市蜃楼。遗憾的是,马克思这一极其重要的理论论述却长期被忽视。
早在刚刚开始进行第三次经济学研究的时候,马克思在《伦敦笔记》中遭遇的就是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的信用和通货理论。我们看到马克思的摘录中有一段对当时现实生活场境的描述:“现在上市公司在我们的社会经济中占重要地位。我们在由上市公司创办的学校和学院接受教育。我们通过在一家银行开户来开始积极的生活。我们通过保险公司为我们的生命和财产投保。”[3]这是仍然发生在今天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中的情景。这里的上市公司,已经是在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上市、通过发行股票募集社会财富的股份制的联合社会资本;在银行开户和在保险公司投保,则是通过存贷款、支票、汇票和保单等获得利息和保险金的钱生钱的“积极生活”。
马克思最早在1844年的《穆勒笔记》中讨论资产阶级经济构式中的信用问题,并在《布鲁塞尔笔记》和《曼彻斯特笔记》中比较具体地分析信用关系之上的金融关系,比如银行债券和股票发行等经济活动,而在1847年的《居利希笔记》中,马克思看到荷兰和英国证券交易所和股份公司的历史发生。在同期发表的《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一文中,马克思第一次直接指出,“信用制度和投机等等引起的冲突在北美比任何地方都更为尖锐”[4]。而在《伦敦笔记》的前期摘录中,他深知这一新生的资本主义信用体系是经济学物相化空间中最具欺骗性的幻象,所以他很快就通过发现被遮蔽起来的货币—通货理论与劳动价值论的内在关联,走向自己的剩余价值理论。然而,一直到《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思想实验,马克思也只是在一般理论逻辑中涉及生息资本的异化问题,而没有回到信用与通货理论以及资本主义经济现实中金融问题的深入思考上来。也许马克思意识到,只有在彻底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科学透视全部资产阶级经济物相化运动机制之后,才可能真正破解资本主义的信用关系这一特殊经济负熵定在的幻象和伪境的本质。所以,一直到面对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才第一次正面讨论了在资本主义经济物相化空间中已经成为重要经济领域的信用(金融)实践和复杂的通货理论。
在《资本论》第3卷第25—36章,马克思对信用关系场境中出现的虚拟资本关系伪境在资本主义经济生产、流通和分配关系中的最新变化,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并形成了完整的批判性思考。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信用关系系统,是资产阶级在经济物相化空间中巧妙运用的一种彻头彻尾的经济欺诈和合法的公开掠夺。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最奇特的我-他自反性劳动异化,也是资本(生息资本)拜物教的最高伪境。在《1863—1867年经济学手稿》中的《资本论》第3卷的初稿中,这一部分内容是在第5章第5节开始讨论的。[5]马克思使用了“信用、虚拟资本”的标题,这一标题在《1882—1883年经济学手稿》中直接成为《资本论》第3卷第25章的章标题。[6]马克思还专门补充说,这是要思考“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的主题。在恩格斯整理出版的《资本论》第3卷中,这一主题成了第27章的标题。
《资本论》第3卷第25章的标题用了醒目的“信用和虚拟资本”。这里的“虚拟资本”概念是全新的科学概念。它并非指资本关系的虚无性和虚假性,而是特指资本关系在资产阶级信用关系构序伪境获得的生息资本的升级形式。马克思这里的“虚拟资本”概念有可能受到西斯蒙第相近观点的影响。[7]哈维认为,马克思的虚拟资本概念“给了货币资本的拜物教性质一个更为形象可感的形状和形式”[8]。这种看似虚拟的信用资本关系,却可以客观地集聚起巨大的社会资本力量。如果资本是一种被遮蔽的社会关系,那么在信用关系场境中,这种从生息资本脱型和转换而来的空手套白狼的复杂关系场境,从一开始就处于一种虚拟的他性占有状态之中。这是一整套在虚拟资本关系伪境中塑形和构序起来的新型经济负熵定在。马克思说,这个作为生息资本的“货币资本的相当大的一部分也必然只是虚拟的,也就是说,完全像价值符号一样,只是价值的权利证书”[9]。早在《伦敦笔记》中,马克思就摘录过这样的说法:“债券、汇票和本票不是货币的一部分;它们是债务的证据。”[10]这个虚拟资本,是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现象学构境才能透视的不是它自身状态的伪在场,这是起点上的神秘性。可以说,这是资本拜物教在生息资本之上生成的全新异化形态的观念映照。
马克思说,与讨论生息资本中的简化公式G-G'不同,资本主义经济物相化中生成的信用制度,正是建立在将G-G'中的生息货币关系转换为一种可以定期支付的交换凭证或者票据的流通领域之中。一方面,这个流通领域不是商品与货币的直接交换,而是这种交换凭证(票据)的虚拟流通;二是这个票据不再是前资本主义社会钱庄中也可能存在的点对点的线性债务关系的借据,而是一种由资产阶级国家银行操控的复杂运作系统中的信用货币。[11]这个信用货币并非仅仅指英磅和美元等货币本体,而且指持有这些货币及其衍生产品的凭证。在一定意义上,这是私人所有的实有货币之上的虚拟信用关系场境中占有金钱的证据。马克思告诉我们,“银行家资本的最大部分纯粹是虚拟的,是由债权(汇票),国债券(它代表过去的资本)和股票(对未来收益的支取凭证)构成的”[12]。它们“只是在法律上有权索取这个资本应该获得的一部分剩余价值”的凭证。然而,“随着生息资本和信用制度的发展,一切资本好像都会增加一倍,有时甚至增加两倍,因为有各种方式使同一资本,甚至同一债权在各种不同的人手里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出现。这种‘货币资本’的最大部分纯粹是虚拟的”[13]。也就是说,信用资本关系是一种虚拟的资本关系伪境,其本质仍然是榨取剩余价值的一种虚幻的神秘方式。这里的神秘性在于,虚拟关系场境中倍增的剩余价值从何而来?马克思指出,银行的有价证券和股票,虚拟资本的“这些所有权证书——不仅是国债券,而且是股票——的价值的独立运动,加深了这样一种假象,好像除了它们能够有权索取的资本或权益之外,它们还形成现实资本”[14]。整个信用体系及其后续复杂的衍生产品,塑形和构序起一个全新的虚拟资本关系场境,它是由利率、汇率和股市等看不见的新型非商品证券交换市场赋型起的资本运作的全新经济定在负熵构式,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畸形筑模形态。哈维说,资本主义信用货币资本的“自我增殖过程的拜物教外观如何采取了虚拟资本这种特定形式,将自己隐藏在神秘中,即使它在债券、有价证券和其他市场中再真实不过了”[15]。这当然会成为马克思高度关注的经济领域。因为,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由此也发生了重要的改变,仿佛在这个新的资本主义经济物相化场境中资本家并不直接剥削工人。马克思说,作为这种新型资本场境关系的人格化的银行家成了“货币资本的总管理人”[16],以后还会有作为股票证券交易关系场境的人格化的证券商。似乎他们面对的大多为资本所有者,而非工人。在这里,即在这种新型的信用关系体系构序出来的经济定在中,作为剩余价值转化形式的利息也仅仅是现成剩余价值的分配吗?这是马克思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到这里,我们看见马克思都是在纯粹经济学的实证话语中描述资本主义信用制度。可是,如果我们没有遗忘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所揭露的货币的本质,即商品交换中被客观抽象出来的事物化颠倒的对象化劳动的异化,以及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中已经揭示的作为这种信用关系的前提的G-G'(生息资本伪境)是资本拜物教的完成,那么问题的实质就会是:如果说商品价值关系是劳动交换关系的客观抽象,而货币是这种抽象的反向事物化和异化,那么作为资本主义信用体系基础的票据则是这种经济物相化空间中事物化和异化的结果,即一般财富所有权的证据。这里发生的全部资本主义信用制度,正是资本主义经济物相化空间中虚拟资本伪境塑形和构序的最新事物化和异化层面,并且,这种资本主义经济信用关系场境所特有的劳动异化关系的海市蜃楼性质就昭然若揭。这是我们接下来讨论信用关系伪境,甚至是今天批判性地研究当代资本主义金融资本关系的正确构境方向。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36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28页。
[3]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IV/7,Text,Berlin:DietzVerlag,1983,S.141.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335页。
[5]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II/4.2,Text,Berlin:DietzVerlag,1992,S.469-646.
[6]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II/14,Text,Berlin:AkademieVerlag,2003,S.240.
[7]在《布鲁塞尔笔记》中,马克思摘录了西斯蒙第这样的说法:金融领域中出现的“这些虚构的资本家,这些资本家是由交往产生的”(cescapitalistesfictifs,cescapitalistesenfantésparl’association)。参见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IV/3,Berlin:AkademieVerlag,1998,S.189。
[8]〔美〕大卫·哈维:《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第2卷,谢富胜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第181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75页。
[10]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IV/8,Text,Berlin:DietzVerlag,1986,S.161.
[1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50-451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32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33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29页。
[15]〔美〕大卫·哈维:《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第2卷,谢富胜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第253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53页。
二、信用关系生成资本主义经济物相化活动新的虚拟基础
作为资产阶级“货币资本的总管理人”,银行家手里管理的主要不是他自己的财富,也不是哪一个私人资本家的财富,而是一种在虚拟的信用关系场境集聚起来的真实社会资本。这使虚拟的信用资本关系神奇地转换为现实的资本力量。请注意,在信用关系伪境中生成的虚拟资本的神奇作用就在这里,虽然信用货币资本是虚拟关系场境,可它却可以聚集起客观的社会资本力量。这是马克思所指认的那个虚拟资本最重要的经济负熵定在的本质。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敏锐地发现,这也会生成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获得新的生存空间这一重要条件。为什么这么说?一方面,这种经济物相化中虚拟的信用关系场境,由于一部分交易根本不再使用货币,就使得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中“流通费用减少”,流通的速度也得以加快。“由于信用,流通或商品形态变化的各个阶段,进而资本形态变化的各个阶段加快了,整个再生产过程因而也加快了”[1],这必然使资本主义的生产总过程获得新的积极因素。另一方面,这种经济物相化中的虚拟资本关系也聚集起真实的社会资本,或者叫资产阶级“自在的共有资本”[2]。之所以马克思将其指认为资产阶级“自在的共有资本”,是因为这种资产阶级以社会占有的方式聚集资本的生成,是通过信用市场关系自发集中起来的。马克思在分析银行通过信用关系汇集的货币时讲到,“一切阶级的货币积蓄和暂时不用的货币,都会存入银行。小的金额是不能单独作为货币资本发挥作用的,但它们结合成为巨额,就形成一个货币力量”[3]。这里的货币资本显然不仅仅是一般的“作为资本的货币”,而是特指银行通过特殊的虚拟信用关系集聚和转化而来的巨额社会资本,这里的货币力量也不是从交换工具异化成“世俗上帝”的货币权力,而是可以超出个人占有的个别资本的力量的巨大G-G'社会资本的支配力量。而当产业资本家通过虚拟的信用关系,直接占有了并非他自己私人所有的巨大社会资本时,就会掌握剥削工人的全新的巨大资本力量,在一定的意义上,这种社会化的资本客观上可以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这就为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提供了缓冲空间。
马克思指出,发生在银行中的“贷放(这里我们只考察真正的商业信用)是通过票据的贴现——使票据在到期以前转化成货币——来进行的,是通过不同形式的贷款,即以个人信用为基础的直接贷款,以有息证券、国债券、各种股票作抵押的贷款,特别是以提单、栈单及其他各种证明商品所有权的凭证作抵押的贷款来进行的,是通过存款透支等等来进行的”[4]。在这里,我们的脑海里再次浮现马克思在《伦敦笔记》中遭遇的情形。在《伦敦笔记》的第1—6笔记本中,几乎全部都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关于货币信用和通货理论的讨论。这一大堆令人眼花缭乱的银行业专用术语会让人陷入严重的认知障碍。通俗地讲,这里无非是说,当资产阶级银行通过并不发生在真实商品流通和生产过程中的虚拟信用关系,将大量货币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就会有资本家通过信用关系场境中的贷放(借钱),在完成一系列复杂的信用关系后,可以在存款透支的信用关系场境中“占有异己的资本”,用大量不是自己的、作为资本的货币重新真实地投入到扩大规模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当他获得新的本不属于自己的巨额剩余价值之后,再支付给银行贷款利息,而银行则通过存款利息支付给资本的实际所有者,这是银行信用(生息)资本的G-G'假象背后的剩余价值再分配的异化关系真相。只是,这种信用关系中的经济剥削关系和深层的劳动异化,被更加繁复的信用关系塑形和构序伪境所遮蔽。马克思指出,这是发生在资产阶级国家层面上的一种资本信用投机和欺诈。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是无法从事这种大规模信用投机的,因为他们没有可以作为抵押担保的各种“有息证券”“国债券”“股票”“提单”和“栈单”,银行信用关系的资本贷放只是富人的投机游戏。马克思指出,这种投机游戏之所以是一种欺诈,因为它直接违背了资产阶级平等交换的原则,信用制度助长了“买空卖空和投机交易”[5]。对此,马克思十分气愤地说:“随着信用事业的发展,像伦敦那样的大的集中的货币市场就兴起了。这类货币市场,同时还是进行这种证券交易的中心。银行家把公众的货币资本大量交给这伙商人去支配,因此,这帮赌棍就繁殖起来。”[6]在信用贷放中,借贷资本家“自己根本没有资本,他们自然就在得到支付手段的同时也得到资本,因为他们没有付出等价物就得到了价值”[7],这个价值就是信用关系场境中的虚拟价值。在商品交换关系中客观抽象出来的价值是实在的社会定在,它通过事物化颠倒和异化为货币;而在这里支撑信用货币的则是一种并不实在的虚拟价值关系,它正是虚拟资本的生成基础。在这个意义上,连劳动异化关系都成了虚拟场境,这使得资本主义经济物相化空间中的劳动异化变得更加难以捉摸。哈维仔细分析过这种资本主义信用关系场境中从虚拟价值到虚拟资本的过渡[8]。资本家利用虚拟的信用资本获得了本不属于自己的巨额剩余价值,这就是冒险的金融“赌棍们”可耻的信用投机和欺诈。在《伦敦笔记》中,马克思摘录了相近的观点,“高利敲诈,即为银行、保险和其他目的而设立的公司违反法律,拥有自己的工业产品,却没有提供等价物”[9],“银行系统是这样运作的:不动产的名义价值已经提高,成千上万的人被引导投机,如果没有银行贷款的便利,他们永远不会这样被引诱”[10]。这种空手套白狼的目的,还是凭空获得剥削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更大资本力量。在聚集社会资本剥削工人剩余价值这一点上,资产阶级信用关系场境中的虚拟资本并不是虚拟的,而是货真价实的残酷经济剥削。这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物相化中信用关系场境的意识形态伪境的本质。
马克思强调,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津津乐道的信用制度,的确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获得了一种新的生存空间,或者说,“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就是建立在这个运动的基础上的”[11]。甚至,资产阶级信用制度会成为“促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到它所能达到的最高和最后形式的动力”[12]。这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发展进程的最新判断,也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科学认识新的构境层,《资本论》第3卷第27章的标题就是“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资本主义“信用制度固有的二重性质是:一方面,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用剥削他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并且使剥削社会财富的少数人的人数越来越减少;另一方面,造成转到一种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马克思的定性分析是双重的。一是认定资本主义的信用制度是一种建立在虚拟资本关系伪境中的赌博欺诈制度。资本主义信用关系的本质是,通过银行和股份公司等虚拟资本的方式,把不属于自己的财富转换为剥削剩余价值的手段,这种信用关系的实质是合法的赌博和公开的欺诈。对于资产阶级国家银行中的借贷资本来说,仿佛“赌博已经取代劳动,表现为夺取资本财产的本来的方法,并且也取代了直接的暴力”[13]。从信用货币交易获得财富的假象,好像发财可以脱离对雇佣劳动的直接关系,这就像赌场中碰运气的赌棍,只是这种欺诈性的虚拟资本越来越集聚在少数金融贵族手中。马克思后面专门讨论了这个新生的金融贵族。二是断言,资本主义的信用制度也是自身消亡和走向新的社会解放的过渡,其中最重要的证据就是股份公司的出现。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94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13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53-454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54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47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79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83页。
[8]哈维指出:“一名生产者用一件尚未出售的商品作为抵押来获取信用。他在实际的出售发生之前就取得了与这件商品等价的货币。这些货币随后可以被用来购买新鲜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然而,贷方持有一张票据,它的价值是以一件尚未出售的商品为后盾的。这张票据可以被描述为虚拟价值。任何种类的商业信用都会创造这些虚拟价值。这张票据(以汇票为主)倘若开始作为信用货币来流通,就成了流通的虚拟价值。信用货币(它总是具有虚拟的、想象的成分)与直接受货币商品约束的‘实际’货币之间由此就打开了一道缺口(《资本论》第3卷,第573-574页)。这些信用货币倘若作为资本被借出去,就成了虚拟资本。”参见〔美〕大卫·哈维:《资本的限度》,张寅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421页。
[9]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IV/8,Text,Berlin:DietzVerlag,1986,S.164.
[10]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IV/8,Text,Berlin:DietzVerlag,1986,S.167.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93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85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00、541页。
三、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物相化新形态的股份公司
在德文中,“Aktiengesellschaften”的原意为“股票社
相关推荐
萤火谷的梦想家
艾莉森•麦吉出生于1960年,是美国《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同时也是大都会州立大学创意写作课的教授。她的作品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并出版,也曾被提名普利策奖,并获得苏斯博士奖金奖、克里斯托弗图书奖、美国 [美]艾莉森•麦吉/[美]克里斯托弗•丹尼斯/绘 2023-03-27 16:50:25鬼马女神捕1·绝密卧底(上)
腹黑凤凰vs毒舌鸡妖——蓝翎:“小姬,跟我去人界吧!”姬十四:“干吗?让人宰了我做小鸡炖蘑菇吗?”蓝翎:“不啊,让妖怪宰了你做小鸡炖蘑菇更气派。”凤凰蓝翎和鸡妖姬十四生活在无忧无虑的灵界。他们的故乡叫 郝天晓 2023-04-17 00:22:47© 2023-2025 百科书库. All Rights Reserved.












发表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