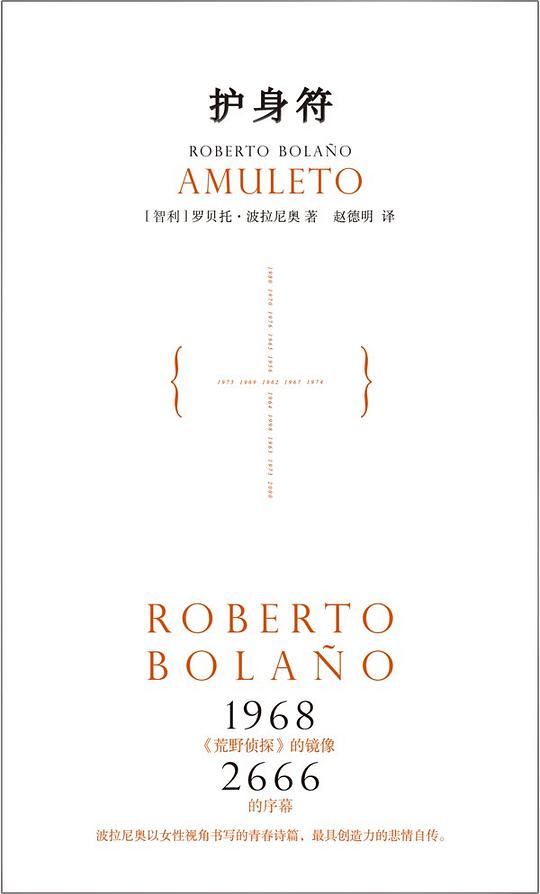
护身符:历史分娩
书名:护身符
1
0

沸腾的水 2023-07-29 02:48:39
与此同时,历史大声喊叫着它即将分娩,医生们则低声宣布我得了贫血症。我纳闷:怎么会因为贫血就给我动手术呢?
我费了好大力气才说出这么一句话:“大夫,我要有儿子了吗?”医生们戴着强盗面具似的口罩从上面望着我,回答说:“没有!”与此同时,担架车飞快地在一条蜿蜒如体外循环的血管一样的通道里跑动。
我问医生们:“我真的没有儿子吗?我不是怀孕了吗?”他们瞅瞅我,又说:“没有,夫人,我们只是送您去参加历史的分娩仪式。”我说:“大夫,干吗跑这么快?我头晕!”医生们仍然用回答弥留之际病人的那种单调乏味的口气回答道:“因为历史的分娩时刻不容等待,因为要是咱们迟到了,那您就什么也看不到了,只剩下废墟和烟雾、一片空空荡荡的景色,就算您每天晚上跟随您那些诗人朋友喝得烂醉,也将永远孤独一人。”我说:“那咱们就快跑吧!麻醉效果到达我的头部,如同奇特的琼浆涌上心头,于是我(暂时)不提问了。
我注视着天花板,耳边只有担架车胶皮轮的晃动声、别的患者低沉的叫声、别的接受麻醉药注射的病人的嘟囔声(这是我想出来的);最后,我感到了一种轻微的热乎乎的舒适感缓缓地从冰凉的骨骼里爬升上来。
一进手术室,我的视力模糊起来,感觉疲劳,视力下降,眼前一片黑暗,接着一道光亮打破了碎片,接着,风把尘埃带进一片虚无中,或者带进墨西哥城里。
相关推荐
逆天的冒险
我们是天生的冒险家,对冒险的爱从不会离开我们,直到我们迈入垂老之年。”博莱索写道。他认为,“胆小的老头子,在他们的兴趣当中,冒险应该是绝灭了的。”这也是为什么诗人们偏爱冒险,而法律通常是老年人制定的原 (南非)威廉·博莱索 2023-04-10 05:12:26艺术与观念(上册)
《艺术与观念》这本书深入探讨了不同历史时期和社会背景下的艺术观念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作者通过对自史前文化、古希腊—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以及现当代欧洲和北美等地的文化事件和艺术形式进行描述和分析,展 [美]威廉·弗莱明/[美]玛丽·马里安 2023-12-07 07:03:40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
谭其骧(1911年2月25日—1992年8月28日),字季龙、笔名禾子,是浙江嘉兴嘉善人,中国历史地理学家,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科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谭其骧于1930年毕业于暨南大学历史系,随后在 谭其骧 2023-12-07 04:11:41© 2023-2025 百科书库. All Rights Reserv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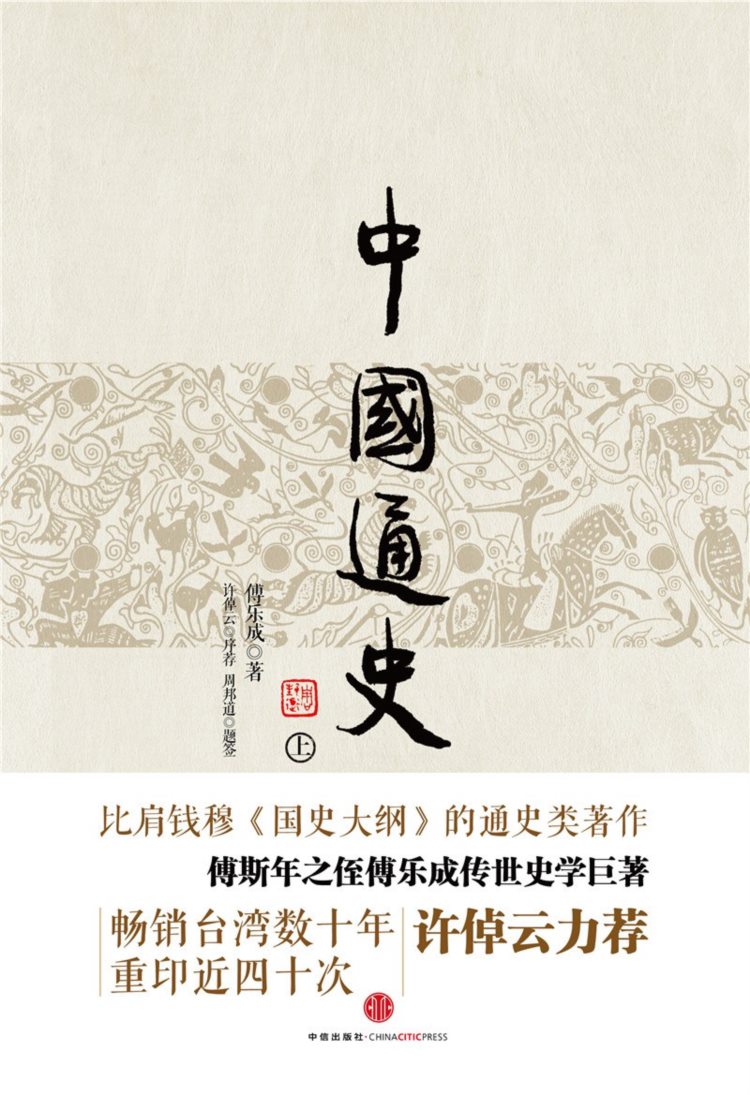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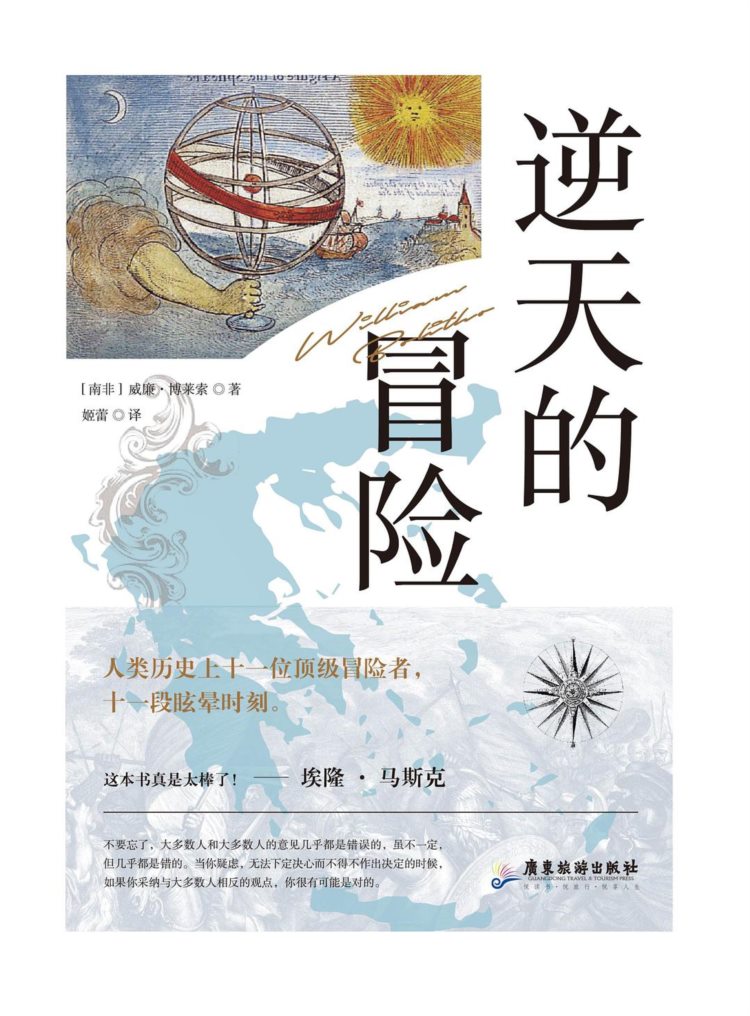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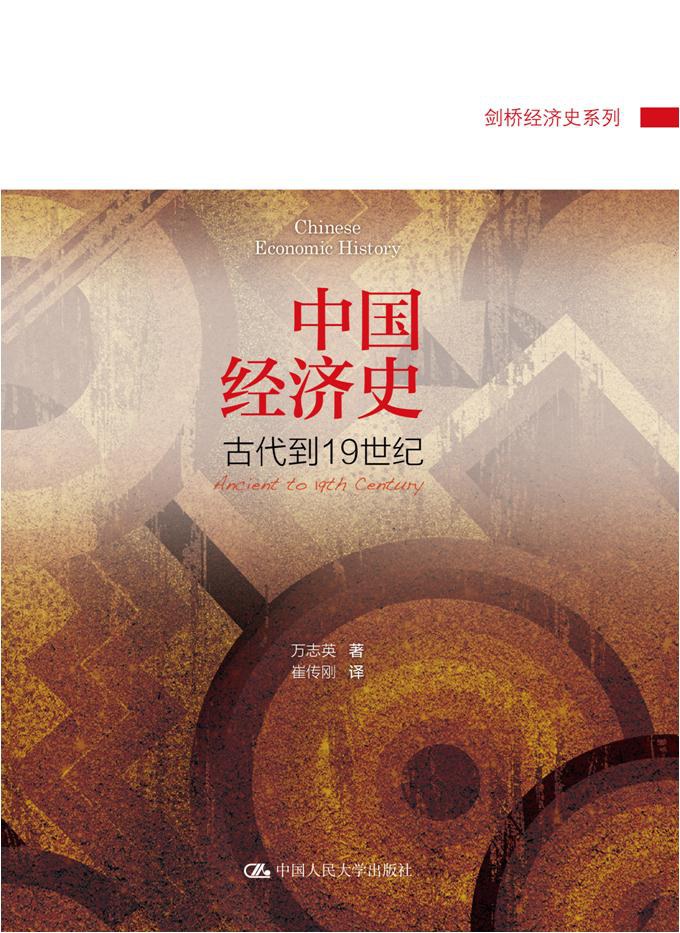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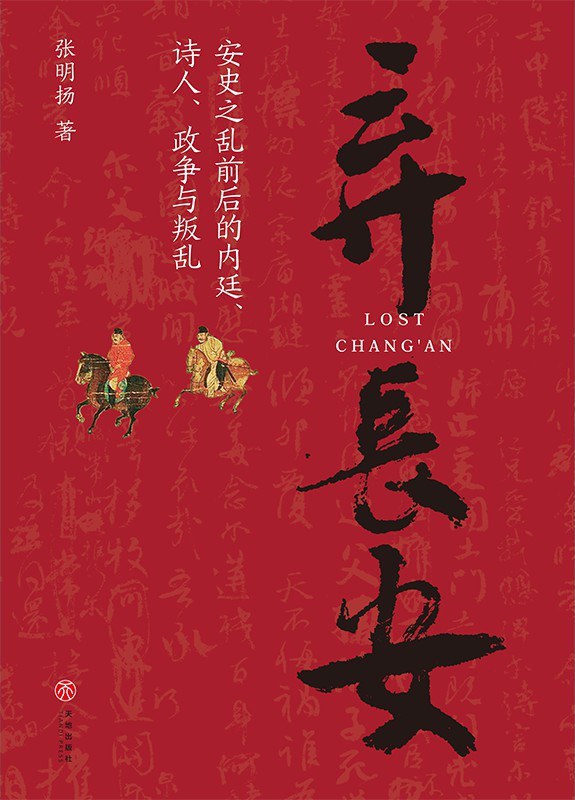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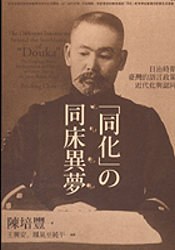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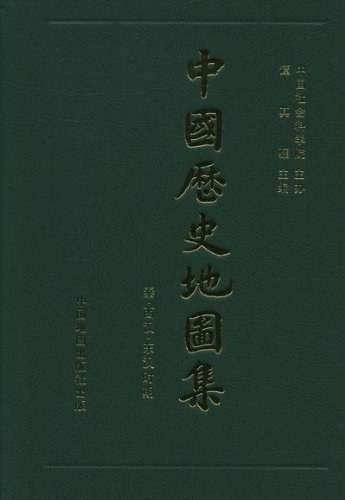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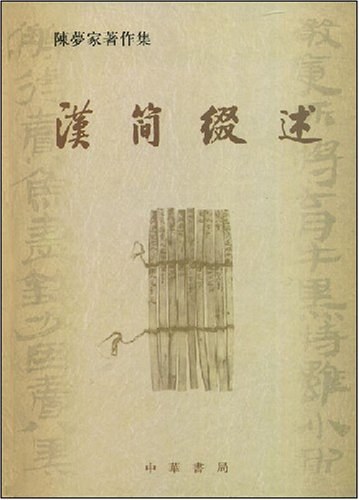
发表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