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额尔古纳河右岸》额尔古纳右岸:口述史小说之独特威力!
书名:额尔古纳河右岸
1
0

小肥羊 2023-07-11 00:33:35
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和余华的《活着》有着非常相似的结构。它们都是一个年长的人讲述自己一生的故事。这个年长的人主要讲述他年轻时候的故事,这些故事非常丰富,占据了书籍很大的篇幅。而越往后故事越简略,直到最后变成了几句话的粗线条描述。而且在后期的故事中,往往伴随着许多人物的死亡,长辈、同辈,甚至晚辈的死亡都被着重讲述。
这与人的回忆是相符的,年轻时总会拥有许多印象深刻的经历。这些经历塑造了人格,而越往后这样的经历便越少。随之而来的便是曾经朝夕相处的人们一个个地离去,最后孑然一身。这便是人生都会有的经历,活得越久这样的经历便越多。
当然本书与《活着》还是有些不同之处。《活着》中的“我”并不是故事讲述者福贵本人,而是一个“民间歌谣收集者”。这个收集者遇到了福贵,听他讲述自己一生的故事。而本书中并没有这样一个角色。但我们其实可以从文中许多地方看出这个隐藏叙事者的存在。鄂温克女人“我”并不是主动将自己的故事讲出的,而是在隐藏叙事者的循循诱导下才愿意一点点把故事讲出来。隐藏叙事者带走了鄂温克女人的故事,再将它呈现给读者(中间可能有不少润色)。这才是这个故事原本的叙事逻辑。
我们不妨将这一类小说称为“口述史小说”。口述史是一个历史学的概念,不少社科都有使用这一概念。“口述史以历史重建为目,建基于对过去事件亲历者的采访,更强调访谈对象的平民性、边缘性。”本书的叙事角度与口述史有很强的相似性。而且作者本人也有像学者那般进行调查研究。在本书的跋中迟子建提到,自己在鄂温克人聚居地调查过一段时间,又花了三个多月阅读鄂温克族的资料。这其实已经有不少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味道了。
这让我想起一部人类学著作《妮萨》,这是一部讲述博茨瓦纳昆族女人的民族志。在许多方面,它其实比《活着》更像本书,尽管它们属于不同的两个学科。《妮萨》中的叙述者“妮萨”是一名年长的昆族妇女。在作者到昆族聚居地调查时,妮萨总是喋喋不休地缠着作者,之后作者才决定将妮萨的故事写成一部民族志。这本书里同样有许多普通妇女该有的经历,出生、成长、玩耍、性意识觉醒、结婚、生子、孩子的成长以及死亡。
当然人类学家要比小说家更“诚实”一些。他们做的是讲述故事,挖掘真相,文学的润色是不允许的(至少是不能过分修饰的)。在这方面,《妮萨》比本书要粗糙许多。但我们很容易体会到两本书的相通之处,那些经历、那些情感,那些欢乐与苦闷都在不断地重复。我们很容易看到相同的东西,也会为同样的内容而感动。
文学毕竟允许虚构。本书中的鄂温克女人“我”不是一个具体的人,她与故事中的其他人物共同构成了整个鄂温克族群的生活史。但《妮萨》也未尝不是如此,“妮萨”并未叙述者的本名,她的故事也远远不止关乎她个人,也是关于一个族群的故事。拿掉那些表面的区别,拿掉学科的隔阂,拿掉地域与种族的区别,拿掉叙述方式的不同,拿掉真实与虚构的区分,还剩下的是什么?是一个原原本本的普通人的一生,是我们习以为常,时常忽略的那些真实情感。
从这个方面来说,我大约只是喜欢这份情感,喜欢这份本初的动力。无论是本书还是《妮萨》,都能带给我这般感受,尽管它们与我非常遥远。我不曾,也不可能拥有她们的经历,可这份直抵心底的触动却终究难以忘记。
相关推荐
妮萨
1969年,玛乔丽带着她的丈夫前往非洲喀拉哈里沙漠研究昆人。这是一项跨学科的田野研究,持续了约20个月。在这段时间里,玛乔丽学习了昆人语言,融入了当地的文化。她与能说会道的昆人女性妮萨交谈,并获得她讲 [美]玛乔丽·肖斯塔克 2023-04-10 15:38:35男人有风险,相爱需谨慎
这是一本针对女性的必读快意恋爱书。作者文字麻辣,生猛娇俏,不仅让许多无病呻吟的爱情文字打退堂鼓,更是快刀斩乱麻,毫不留情地揭露各种爱情假象和虚妄,迫使读者直面淋漓的现实。只有勇敢地清醒头脑,敢于迎接挑 曾雅娴 2023-03-29 18:46:56国际超模的极简瘦身课
这是一本为中国女孩撰写的“易瘦体质”培养指南,作者是一名国际超模李霄雪。李霄雪曾与纽约排名第二的模特经纪公司EliteModelManagement签约,在国际模特界打拼了10年,之后她决定回到中国成 李霄雪 2023-03-31 06:29:24我有一杯酒,可以慰风尘
祝愿你的岁月平静无波澜,同时也希望我的余生不会有太多的悲欢。这里介绍的是关东野客的又一力作,它名为《我有一杯酒,可以慰风尘》,共涵盖13个故事。这些故事或许会让你感到孤独和温暖,也或许会涌起遗憾和美好 关东野客 2023-03-29 19:34:53即使生命如尘,仍愿岁月如歌
优化后:想要走向自信、尊严的人生,女性可以从工作、家庭、生活等方面入手。本书将通过作者及身边朋友的经验告诉读者,一个女人是否能够实现美好的生活,决定性因素并不在于她的经济状况,而在于她有无勇气不委屈、 晚秋 2023-03-31 07:15:04我们的性
《我们的性》,现在是它的第7版,生物、社会心理、行为和文化诸多方面以对个人有意义的方式,对性做出了全面、学术观点鲜明的介绍。我们非常高兴读者对本书前几版一直反应热烈且热心;这些反应激励着我们为你们的学 [美]罗伯特·克鲁克斯(RobertCrooks)/[美]卡拉·鲍尔(KarlaBaur) 2023-05-05 06:31:19© 2023-2025 百科书库. All Rights Reserv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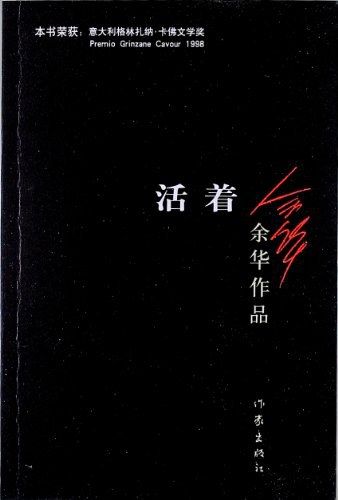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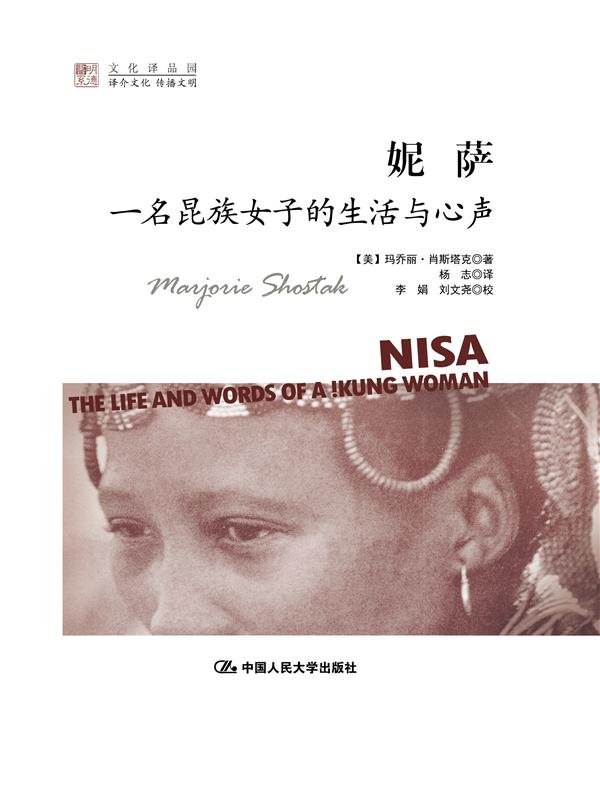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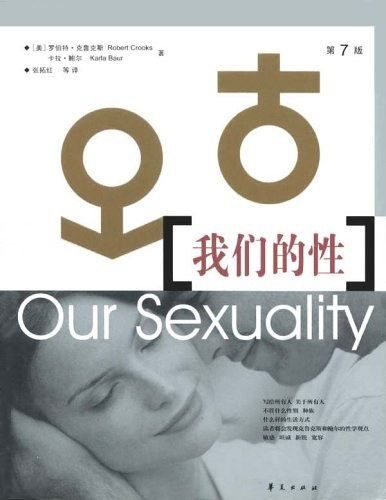
发表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