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哥本哈根的守夜人》哥本哈根守夜人:普通人也能成英雄!
书名:哥本哈根的守夜人
1
0

星星之火 2023-07-08 04:31:36
虽说作者几次强调想写一本“单薄”的小书,但克尔凯郭尔从1813-1855度过的一生,这本书还是很难啃。它高密度地展示了克尔凯郭尔独孤的勇气和为(他所信奉的)真理献祭的决心。在我的同桌的印象里,克尔凯郭尔是位作家;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位哲学家;在读这本书的印象里,他是宗教作家。了解这一点也许比了解他的身世、感情、研究生涯更为首要。
他以野鹅与家鹅为喻,指出基督徒与剩下的人之间的区别(尽管他说这不适用于基督教)。家鹅见到野鹅飞过,会扑腾翅膀一段距离,作出短暂的行动。克尔凯郭尔认为某种程度上家鹅知道飞行意味着什么。但如果有一只野鹅,试图教化家鹅飞行,只会遭到厌倦和嘲笑,最后也沦落为家鹅。这是一个“成为”的问题。家鹅不会成为野鹅,但野鹅会成为家鹅。所以,他告诫野鹅们保护自己、保持警惕,如果不能赢得个体的转变,更不要让它在自己身上发生。“一旦发现家鹅开始控制你的力量,撤退、撤退吧,与野鹅群一起离开!”
这是作者选择的、克尔凯郭尔的两份遗言之一。确切地说,这并非克尔凯郭尔生命最后的话语,而是他在去世两年前“有先见之明的”对人生意义的阐释(即野鹅的象征),“使自己祭物的意义变得清晰”。后者对应“一小撮香料”。被献祭的人成为那一小撮香料,它被抑制,很难被辨认或判断出来,“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啊!”但厨师确切地知道它为何能以及如何影响了整体的味道。香料内心会理解,自己的痛苦又多么蒙福。
“你这个普通人!”作者引用了克尔凯郭尔论战中的绝笔(但因他突然生病,没有被发表,作者为此感到可悲)再一次替他解释,他就住在街上,和我们一样。他没获得任何重要性,不属于任何阶级的利己主义,“如果我属于任何地方的话,我必须属于你,你这个普通人。”
尽管这段话的原意也是为了布道——从普通人上升至无限的高度——但选择展示它与作者的立场形成鲜明且引我好奇的对比。作者本人对克尔凯郭尔的情感流露在字里行间(哪怕对一本较为学术的著作来说),他是他的信徒:
如果我如此轻率地承认我是克尔凯郭尔的爱戴者,我会让人知道,这就是我所爱的克尔凯郭尔——不是放荡绝望的年轻人,不是归来的浪子,不是不幸的情人,不是创造各种假名的天才,而是完全不适合应付这个世界的脆弱之人……他在那里没有人能伸出手来救他……除非我崇敬他……而只有当我看到他有勇气作为真理的见证人去世时,我才开始崇敬他。
当然,他都是,但更是作者给出的至高赞美。抱歉的是,在作者对克尔凯郭尔的爱的布道下,我也难苟同。最直接影响我判断的是“不幸的情人”,他与蕾琪娜的婚约与毁约。他认为她是他的唯一所爱,却提醒她他的忧郁伤人(在作者看来,这种自我压抑的爱很可怜,但也请求大家的同情)。他认为自己将她捧的高高的,创造了她的光,赞美她,并且她接受了这份赞美。当蕾琪娜再次与别人结婚,与克尔凯郭尔偶遇时,后者感到她的目光在请求他的允许。
克尔凯郭尔最直接的渴望是诚实,这一点无法反驳。从替被叫衰的丹麦语声辩到认为自己的存在使前未婚妻的人生更突出,他对自己的天才属性(体现出的是优越感)是诚实的。因为情变,他重写了《或此或彼》,用自己的爱情悲剧将这本停留在伦理层面的书变得更完整,里面这两句还是打动了我:
我开始写一个新的故事,标题是有罪/无罪它自然会包含一些震撼世界的东西(就是这种感觉!),因为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我在自己身上体验到的诗意,比从所有浪漫文学作品里体验到的加起来还要多。
作者在此解释了“诗人”这个词的意思,最初是创造者。作者认为在丹麦语中,将柏拉图称为诗人也是正常的,诗人不一定要写诗,这个词汇代表的是多样性、自发性和创造性。克尔凯郭尔的审美作品中当然有诗意,他使哲学也过于诗意,甚至在“我们最不期待的地方”宗教话语中也有浓烈的诗意。
如果是这样,以“诗人”为眼,就更好理解这位以许多假名出版书籍,作为自己分裂的线索、作为自己各种可能性的化身的维克多、沉默的约翰尼斯、维吉利乌斯·豪夫尼恩斯(
相关推荐
哲学的底色
作者的目标是让本书变得容易理解,读者只需轻松阅读即可获益。真、善、美、自由、公平、正义是人类追求的主题,也是哲学的根本意义。在本书中,作者采用通俗易懂的叙事方式,让哲学思想逃脱晦涩难懂的语言,使读者可 [美]莫提默·艾德勒 2023-03-25 16:12:16美学权力
【编辑推荐】1.作者在哲学家从认识论和形而上学等不同的面向对“美学”进行理论奠基时,看到了“接受理论”或者“艺术理论”的困境。她指出纯粹理论化的不足,并对抵制“美学”彻底抽象化做出了努力。2.作者圣吉 [法]巴尔迪纳·圣吉宏 2023-05-26 02:56:51康德《实践理性批判》句读
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是他哲学体系中的重要部分之一,于1788年出版。相比于前一部作品《纯粹理性批判》的任务是研究人类认识力先天要素之规定,本作则关注于理性实践中的先天原理,考察其可行性、范围和限制。 邓晓芒 2023-03-25 16:13:27游世与自然生活:庄子评传
庄子是战国中期伟大的思想家,他所关心的许多问题仍存在于当代,他的思考仍启迪着今人。颜世安教授以隐者传统和道家思想为背景,以郭象所注三十三篇本《庄子》为依据,博采庄子研究众家之长,从全新角度解说庄子,阐 颜世安 2023-05-26 02:39:07古典柏拉图主义哲学导论
:这本书对于柏拉图主义哲学史进行了全面的梳理,时间跨度长达九百年,涵盖了从学园开始到晚期新柏拉图主义的整个历程。书中详细研究了代表性人物的主要观点和彼此的思想联系,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柏拉图主义哲学的全 梁中和编著/梁中和 2023-03-25 16:14:25如果我们错了呢?
用有意思的知识,验证有价值的思维方式。《如果我们错了呢?》是美国知名哲学思维畅销作家查克•克洛斯特曼挑战传统文学、文化与科学知识的上乘之作。这本书被《出版人周刊》、《科克斯书评》等13家媒体评选为年度 [美]查克•克洛斯特曼 2023-04-10 20:30:38© 2023-2025 百科书库. All Rights Reserv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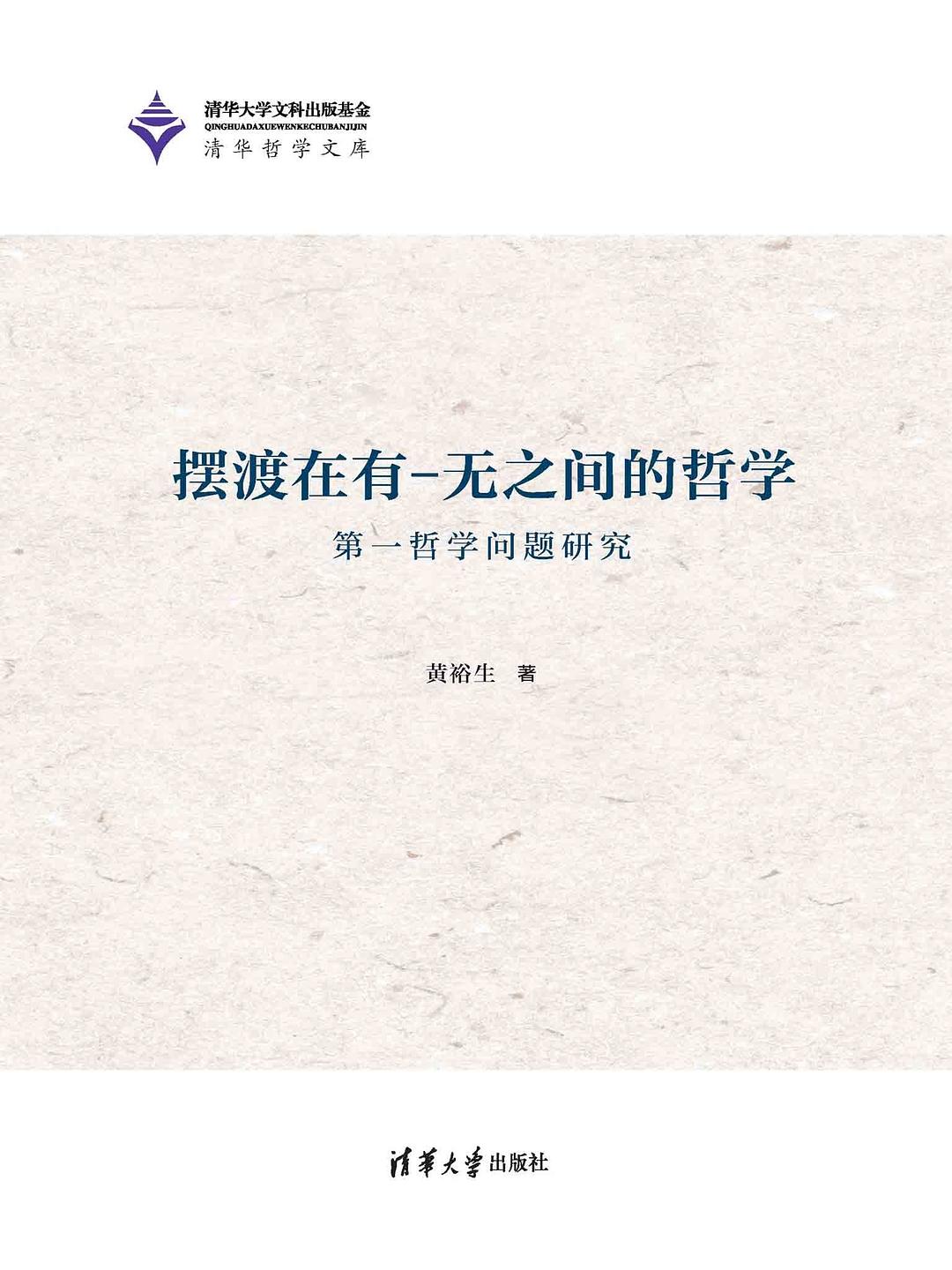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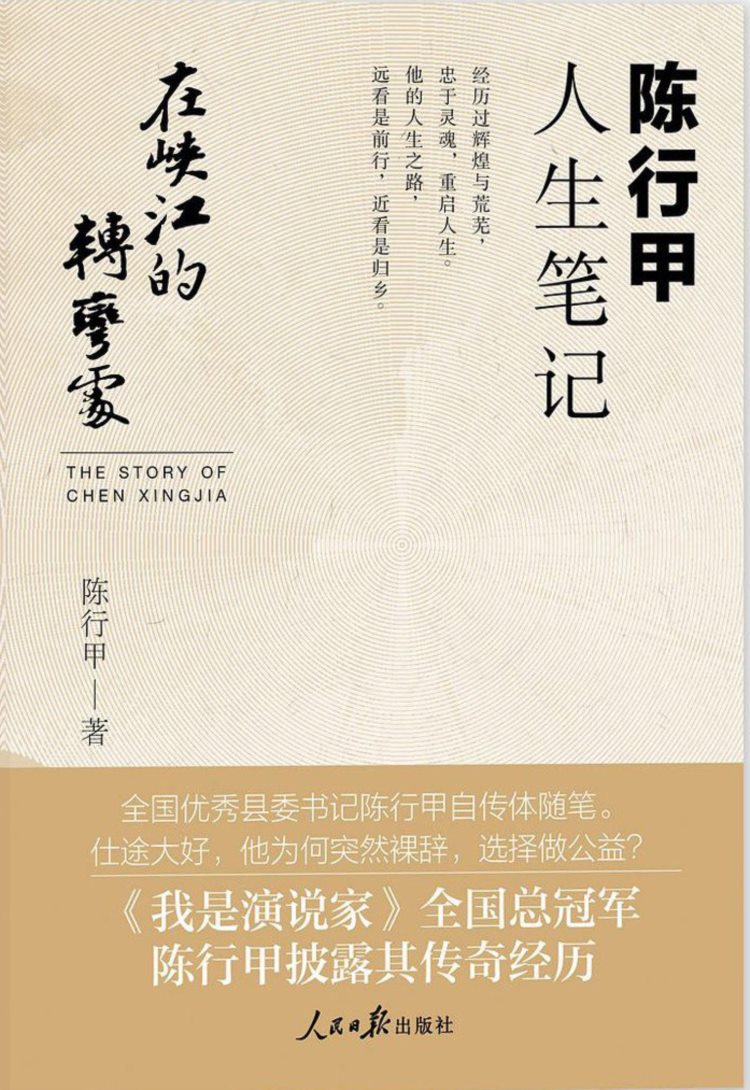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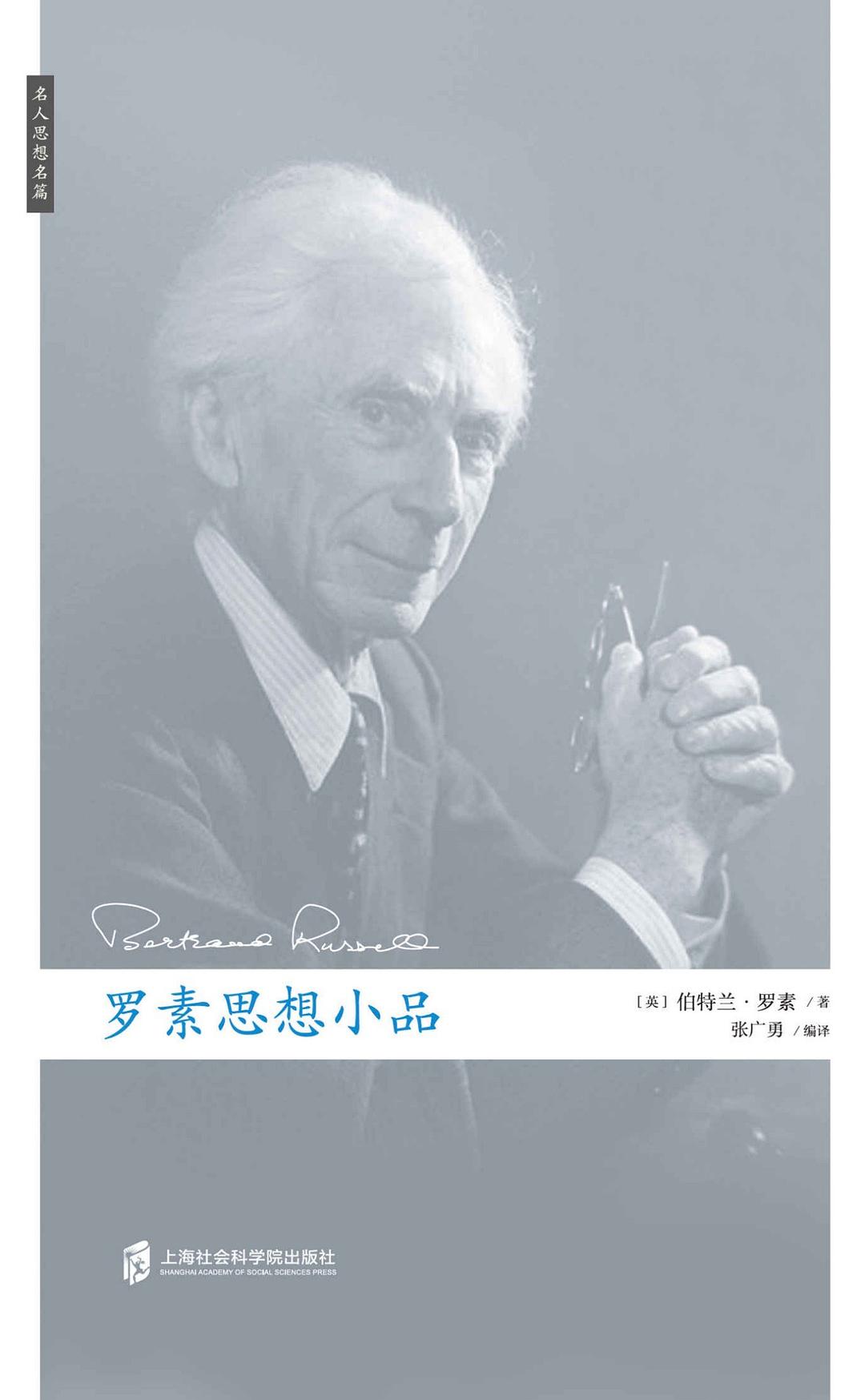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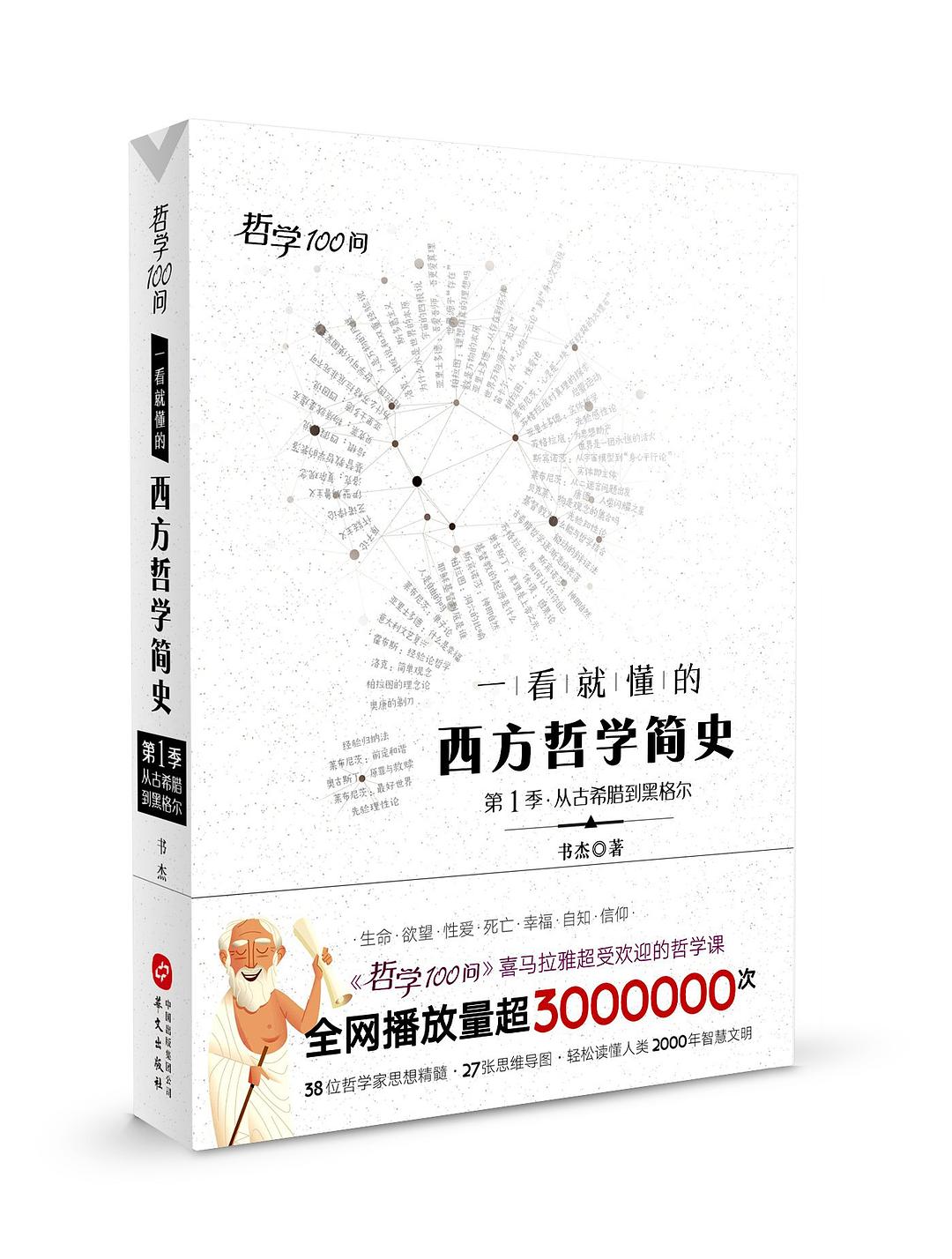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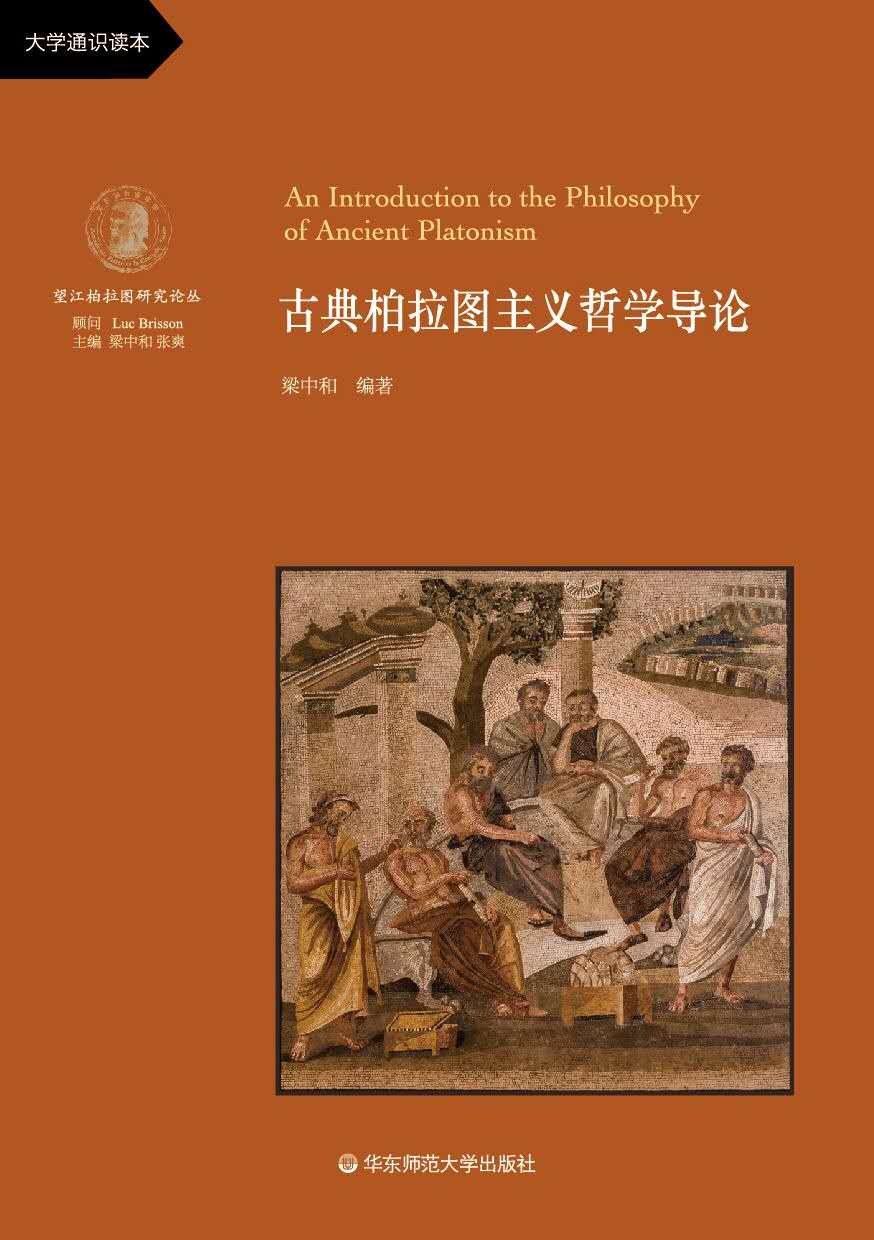

发表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