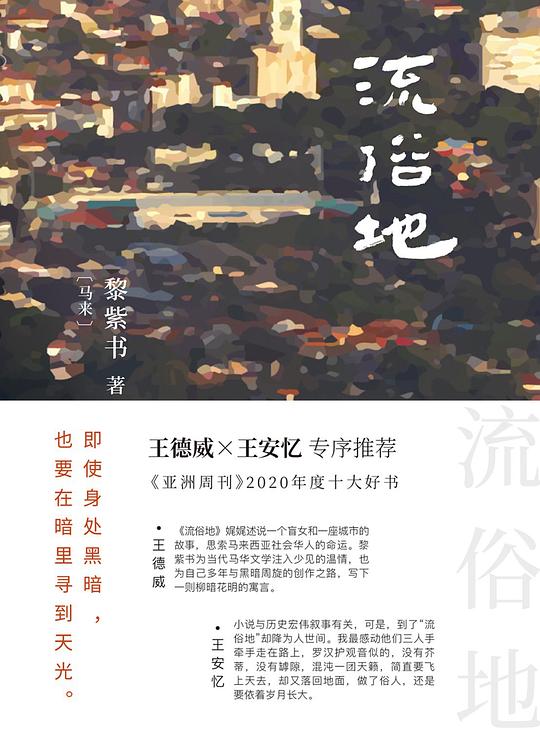
《流俗地》追求流行文化的圣地
书名:流俗地
1
0

皮卡丘 2023-07-03 02:17:31
《流俗地》的结构从容精巧。非线性叙事,首尾两章之间铺了一张巨大的群像网。时空与视角来回切换,闪转腾挪,穿插起各人的故事。银霞、细辉、拉祖、莲珠、马票嫂、婵娟、大辉、蕙兰、银霞的母亲梁金妹、细辉的母亲何门方氏、顾老师、老古、巴布、拿督冯...
叙述富有耐心。白描居多,宛如涓涓细流。有人只用一句话写的一个动作,她会用一段话来写。但很奇怪,我丝毫不觉得拖沓,反而乐意顺着她的文字慢慢去描摹那个画面。顺便说一句,她笔下的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给到我一种既亲近又异质的新鲜感,某些地方相似到甚至感觉就在身边。
语言沉稳扎实。尤其是文中的各种修辞,乍看陌生,并不打眼,但细想居然有种毛骨悚然的贴切。举重若轻的技法里,是南洋的风土人情、马华社会的历史变迁以及锡都平民区内多族群、语言混杂的“楼上楼”众生相。
既没有故作其事,也没有空泛炫技,围绕的皆是底层老百姓的平凡生活,市井小民的俗事俗务。
黎紫书曾言:“不炫技”比“炫技”更考验我们的修为啊。如她所说,《流俗地》看起来朴素,但底下却融合了各种技巧与心机。
她是真的会讲故事的。
我发现,我是真的喜欢古银霞这个人物,还有细辉、拉祖。直到往事不断被挖掘,我看到作者讲银霞的过去、众人的过去,某个瞬间,竟生出一种“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感觉。
一开始,我也以为她是“从往昔的阴郁浓重和暗黑黏腻中走出来,站到了南洋的赤道阳光和蕉风椰雨下”,但看至后半,并不是这样的。
生命的底色,终是悲凉。没有忸怩夸大痛苦,不去刻意回避丑陋。当然,她不愿吝啬温暖希望,她最终给了盲女银霞一个有光的归处。她说这也是她希望以此给老家的同胞一个期许:即使环境再恶劣,仍能怀抱希望活下去。
——————————
“最要命的还是长篇小说几乎不给作者设限,它的空间大得让作者产生自由的错觉,以为自己宽裕得有资格对文字任意挥霍,甚至偶尔偏离正途岔开了去亦无妨。要在这种状况下保持高度自觉和克制,做到对每一个字斤斤计较,毫不松懈,这对写作者的个人修为毋宁是十分苛刻严竣的考验。”
“相比其他文体,一部长篇小说,十万字百万字,那么个洋洋洒洒,作者步履艰难有时,得意忘形有时,他什么时候拮据什么时候挥字如土,读者中自有明眼人可一目了然。作为文学读者,我可要比作为创作者更为资深,或许也更敏感,每每读到这些或者太过或者不足的尴尬处,便觉得如鲠在喉,仿似瞥见了作者身上那华美衣裳上掩盖不了的破洞和补丁,不免也要为他尴尬一把。”
“要书写真实,便不能把真实从现实世界里一五一十地照搬过来,因为真实一旦由文字去承载,需要以读感去体察,它的质地便会产生变化,多半流于枯燥乏味。在这个事情上,“虚构”有它重要而积极的意义,它在文字里将那已经变质的真实修改和调整过来,让小说读起来更接近真实。于是,在编造出来的语言中,读者反而听到了真正的锡都腔调;在非线性的时间形态和不断跳跃的插敘藏闪之中,小说反而更逼真地呈现出现实生活本来的姿态面貌。”
“说到底,马华作者如我,终究是长久以来在贫瘠艰难的环境中挣扎求存的。既为野生,势必发展出野蛮的生存法则,文学亦然,在自我完成的过程中,唯有一点不动摇地遇神杀神,见佛杀佛,力求狂放而已。我不学无术,既被同侪称作素人,便顺势以素人自居,在小说创作的路上多以幻想自修,再连结生活中各种看似毫不相干的观察与体悟,自行发展出一套不见得有根有据的信念来。在我这儿,向来文无定法,不过是每个小说各具风姿特质,便也有各自不同的需求──有时需要的是获取,有时需要的是放弃。真到需要时,为了成全小说的完整性,就连“故事”这基础(可能也是初级)的层面也并非不可以削薄或丢舍。”
相关推荐
逆天的冒险
我们是天生的冒险家,对冒险的爱从不会离开我们,直到我们迈入垂老之年。”博莱索写道。他认为,“胆小的老头子,在他们的兴趣当中,冒险应该是绝灭了的。”这也是为什么诗人们偏爱冒险,而法律通常是老年人制定的原 (南非)威廉·博莱索 2023-04-10 05:12:26© 2023-2025 百科书库. All Rights Reserv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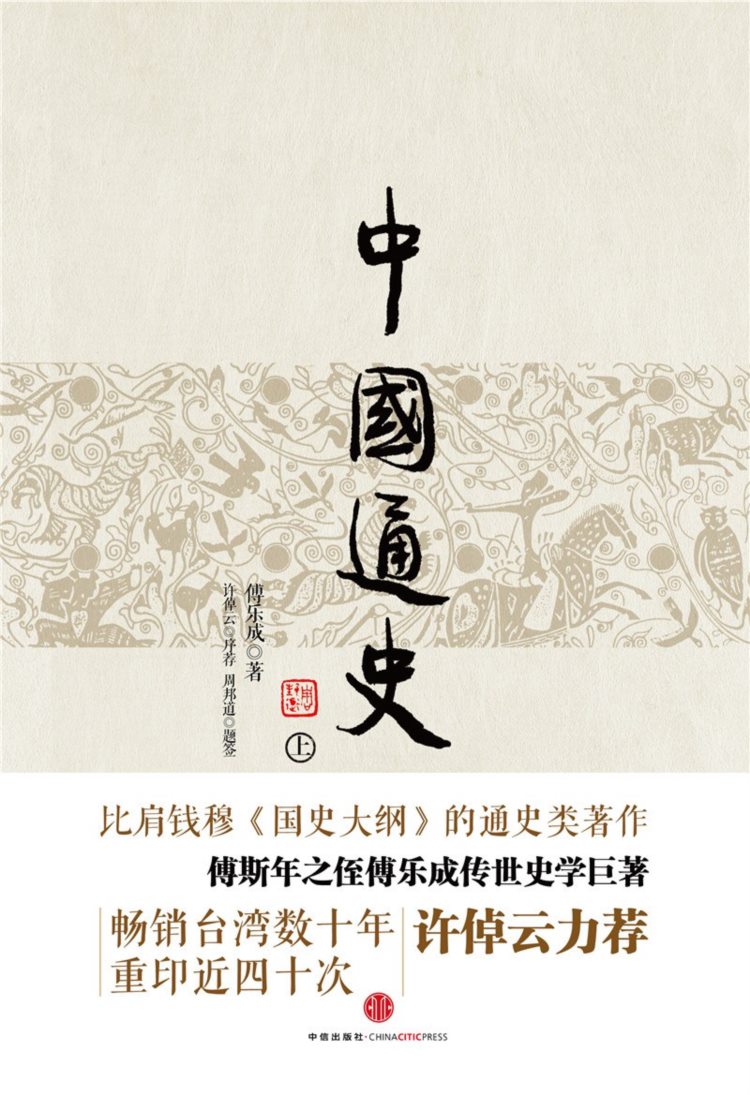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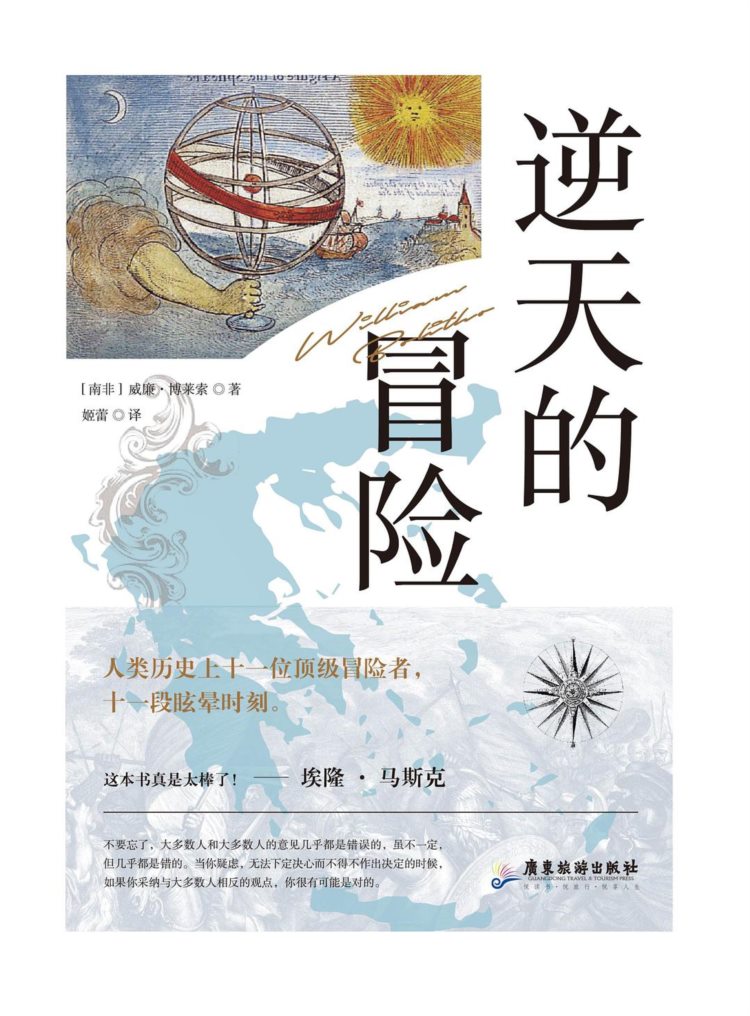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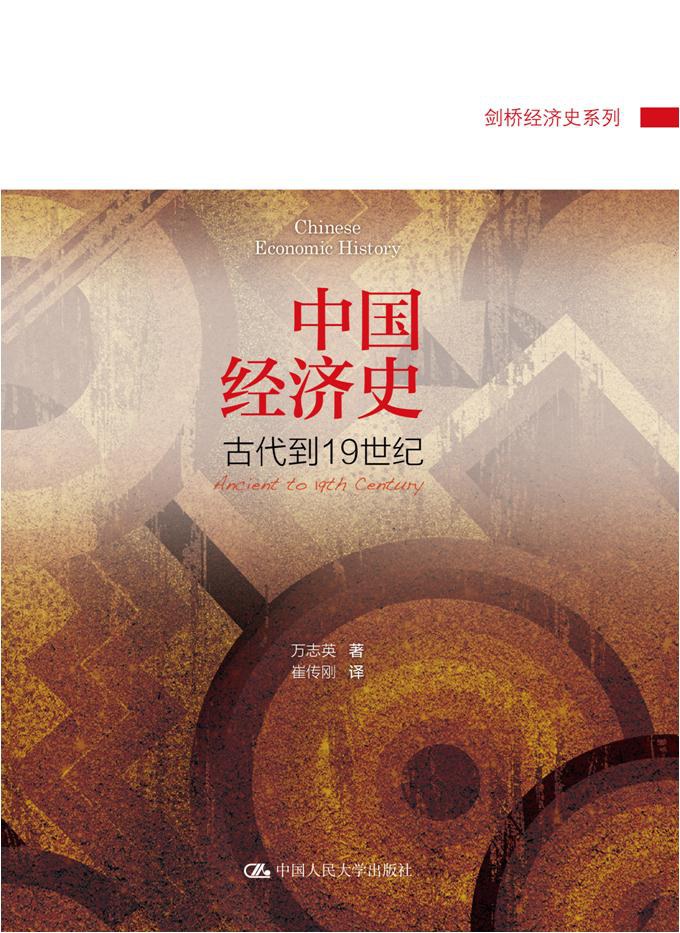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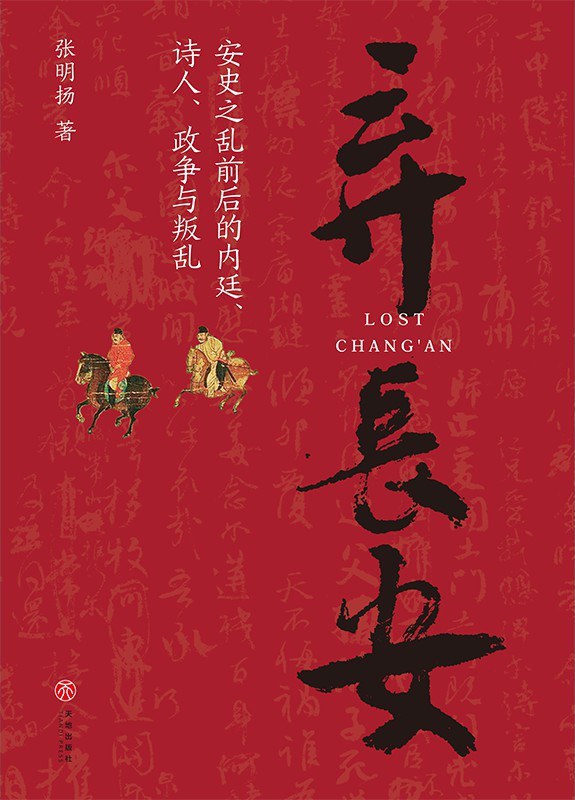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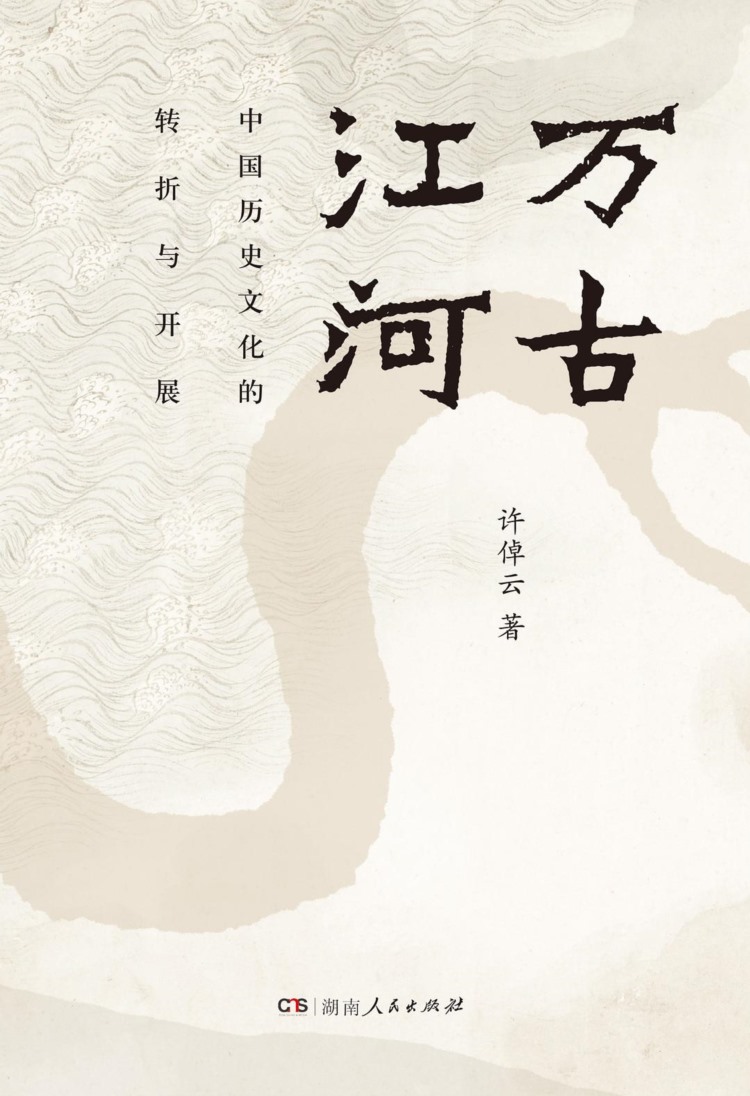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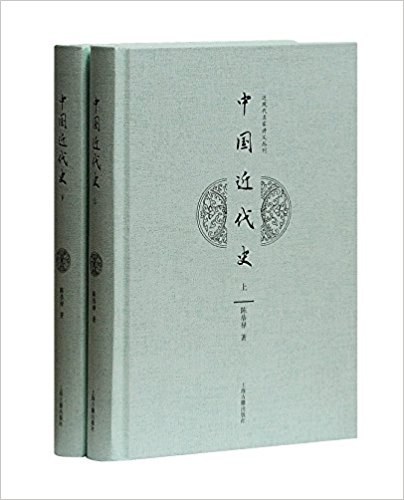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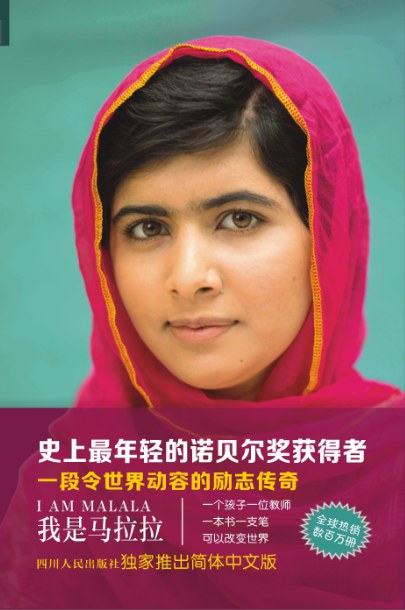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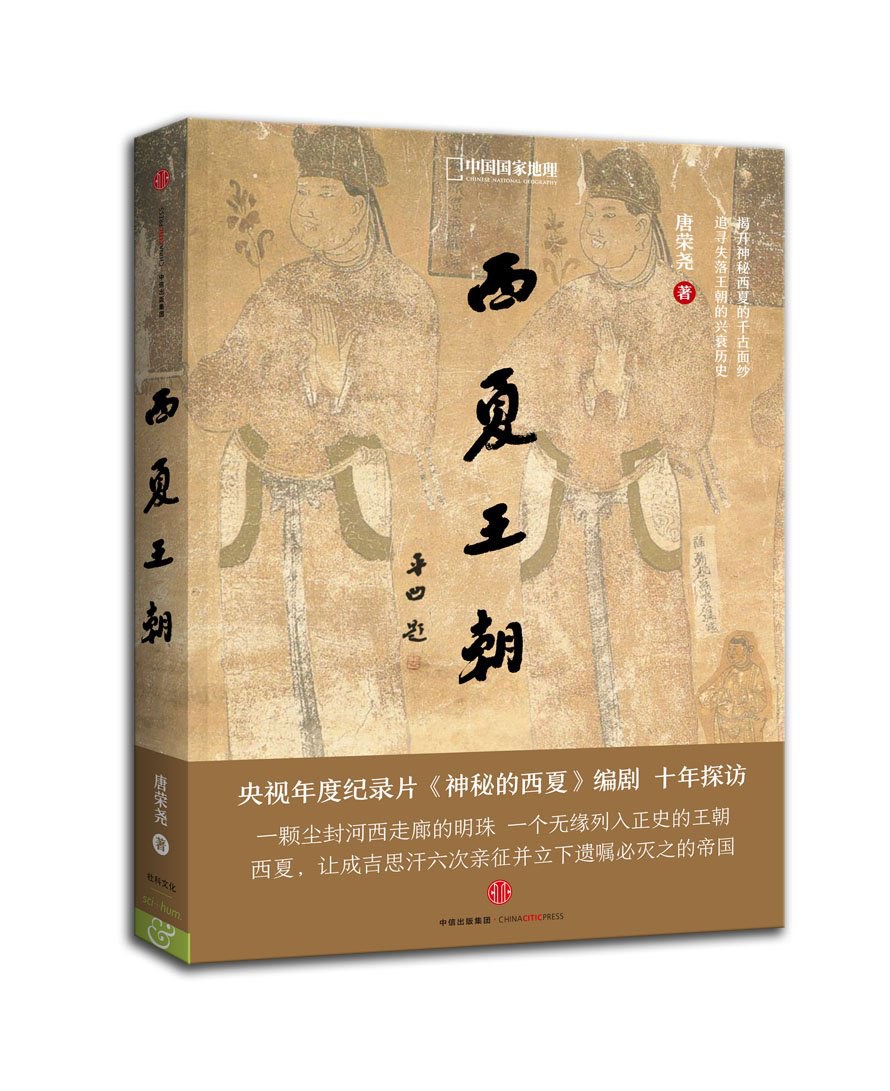
发表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