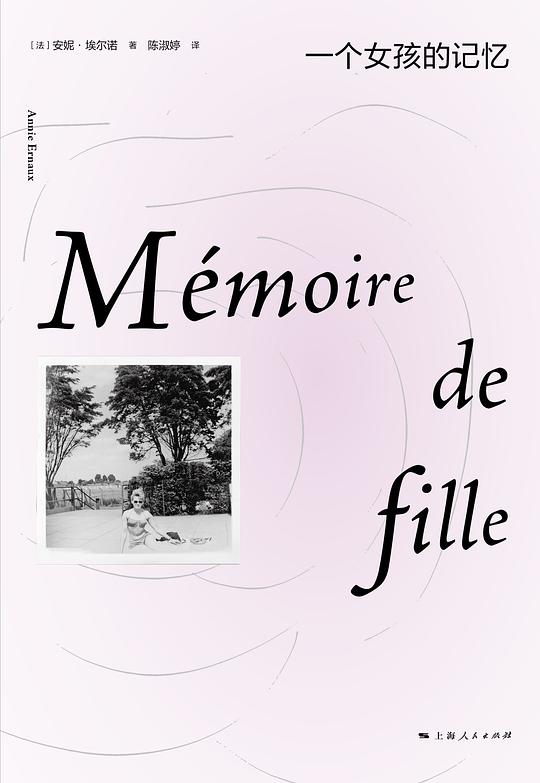
《一个女孩的记忆》女孩记忆:书写与和解
书名:一个女孩的记忆
1
0

春天大转变 2023-07-02 02:30:30
当男人用写作来掩饰他们的出轨、嫖娼和入赘时(《窄门》《悉达多》《斯通纳》),女人在用写作审视个体记忆的真实性以及加之于其身的哲学思潮、社会环境的变迁。耻辱的初夜,困顿的青春,欲望驱使的突围,友谊的戛然而止,丰富的心理描绘与精简的故事情节,兼具个性与共性,是私史也是集体记忆;书写与遗忘,自我与他者,从“我也想忘记”到“我都忘记了”,从“沉溺在别人的世界里”到“没有男性,我们自娱自乐”,是给予波伏娃、萨特等存在主义先驱的回答,也是对几十年女性主义运动成绩的戳章。
这就是埃尔诺的《一个女孩的记忆》。
我承认,当我在书店里打开这本书的时候,几乎一瞬间就陷进去了。它非常符合我对自传式文学的期待。对于一个有深厚哲学功底的写作者来说,写作不仅仅是故事情节的“显现”,它事关叙述者的“在场”或“旁观”,事关被叙述者的“他者”化,以及二者之间的“主体间性”。而且毫无疑问地,当这个命题被放到女性主义文学中时,其重要性被大大地强化了:如何避免女性在叙事中被客体化,如何处理叙事的真实性,如何谈论女性解放运动的历时性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和解读,这些都是女性主义文学、女性私人记忆的写作乃至metoo中每一次的女性话语表达中不可避免的问题。
“我乱七八糟地记下了所有细节。仿佛因为这种日期的日复一日,写作让我可以轻而易举地直接回到那个夏天……由于画面、文字的涌入,写作需要不断延伸…它不断溢出我。我越写越感觉自己写的不贴切……我不愿意因形式而痛苦。五十页后,我又停笔了。”—埃尔诺,《一个女孩的记忆》
同是法国人,埃尔诺的思辨毫无疑问地受到了波伏娃和萨特的影响,而其写作手法又带有莫迪亚诺和加缪的风格。莫迪亚诺擅长写作主人公的自我追寻,通过零散的物件引出碎片化的回忆,朦胧而又神秘。埃尔诺的写作则大幅度弱化了其中的神秘感,因其明确地属于自传式写作,叙述者并非不能准确进行回忆,因而相较于莫迪亚诺浓重的后现代风格,埃尔诺更强调主体由于时间的跨度而带来的不同。她明确地以1968年女性解放运动为时间锚点来叙述其1958年的经历,虽然对比了不同时期的思潮对这段经历的不同看法,但是在叙述中特别地“抛弃积累多年的各种阐释,不进行任何加工”。这便是她的写作尽可能完成的“在场”。
“我是否应该这样写,在五月革命的十年前,我勇敢无畏,是捍卫性自由的先锋…因而我应该用一种轻松愉悦的写作笔调…或者立足于1958年法国社会的观点认为女孩的行为举止是女孩全部价值的体现,说这个女孩太过无知、天真幼稚、可怜可恨,自己应该承担所有责任。或者写作视角应该在1958和2014年之间不断转换。”—埃尔诺,《一个女孩的记忆》
埃尔诺擅长构筑那个似真似假的1958年的时空。除旧物件外,她恰到好处地援引了大量当时流行的文艺作品,以展现当时的社会氛围。阅读本书时容易想到同样是使用了大量隐喻的《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想到哲学、文学与女性命运之间的关联。事实上,法国人的记忆并不会形成阅读上的障碍。作者反复区分的1958年和1968年,正恰巧相当于处女情结、月经羞耻泛滥的十年前与今日。这种女性的共同记忆,使得本书有了跨民族的感染力。
“这种耻辱是历史性的,十年后才出现我的身体我做主的口号。纵观历史,十年白驹过隙,但是十年对于生命之初而言,是一段漫长的岁月。”—埃尔诺,《一个女孩的记忆》
应当说,埃尔诺更加幸运,女人也会因为性爱走入哲学。主客体之辩让人学会冷静旁观,哲理性写作则帮助人实现自我疗愈,这是许多女性的共同经验。其哲学归宿也往往不是纯粹的独断与先验,而是伴随着女性主义运动的飞速发展,呈现出多元、多变的趋势。埃尔诺的片段式写作,难道不也是一种时代的必然吗?
如果这不是诺奖级的作品,那我也不知道什么能算是了。
相关推荐
萤火谷的梦想家
艾莉森•麦吉出生于1960年,是美国《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同时也是大都会州立大学创意写作课的教授。她的作品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并出版,也曾被提名普利策奖,并获得苏斯博士奖金奖、克里斯托弗图书奖、美国 [美]艾莉森•麦吉/[美]克里斯托弗•丹尼斯/绘 2023-03-27 16:50:25© 2023-2025 百科书库. All Rights Reserv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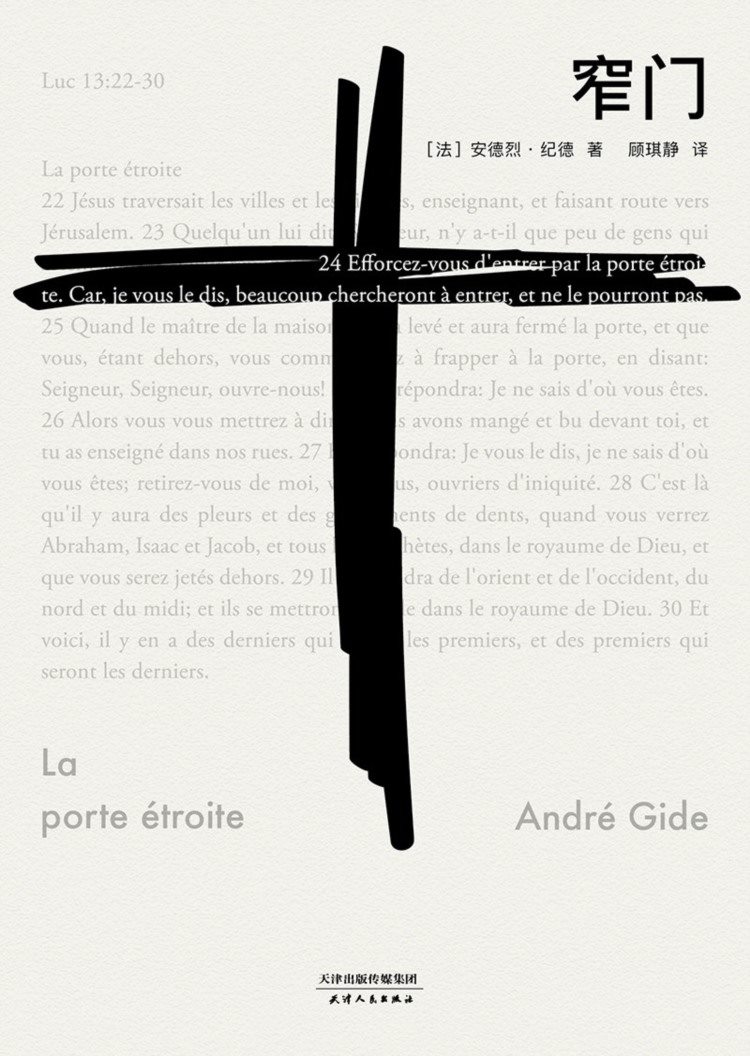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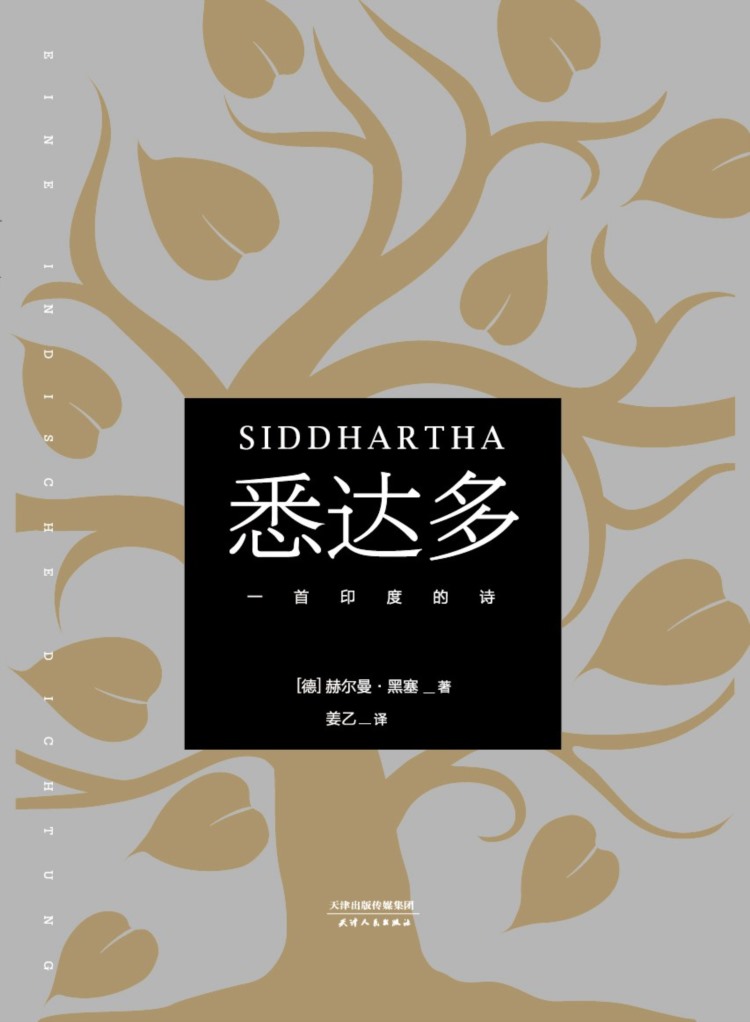








发表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