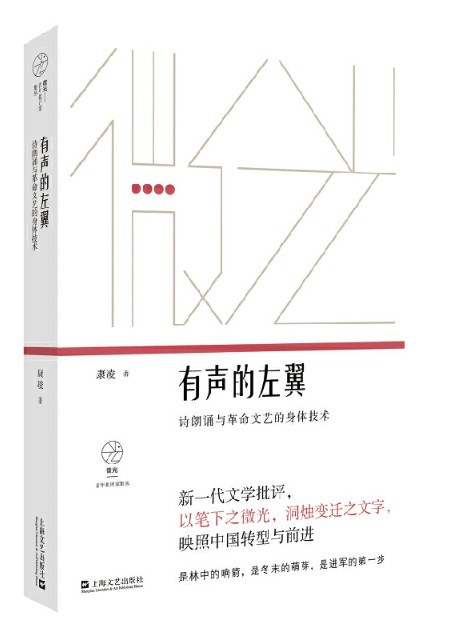
有声的左翼:诗贯穿感官经验·中介技术·革命动员
书名:有声的左翼
1
0

快乐大本营 2023-06-29 23:37:33
麦克卢汉的一句“媒介即讯息”道尽了文学研究中的内容偏向。一方面,文字文字作为无言的载体自身可能也成为一种遮蔽,使得后人忽略掉历史情境中的复杂张力。在研究文艺的过程中,文本虽然重要,却不是唯一重要的因素。许多文艺实践的形式重点在于绕过文本性存在,探究媒介形式如何将大众的意志与个人的观感相互勾连在一起。
康凌这本小书选择了一个十分巧妙的切入点。他以1930年代中国诗歌会的诗朗诵实践为例,探究特定历史条件下,左翼诗人们如何突破鸳鸯蝴蝶派、新月派、新感觉派笔下的风花雪月。在特定的关于诗歌、关于身体、关于声音的知识论基础上,借由对诗歌音响结构和节奏模式的设计与经营,创制出一种身体技术。这种技术能够在诗朗诵的实践中捕捉、动员大众的身体经验,召唤、组织铭刻于大众身体经验上的感官记忆与情感认同。(P28)
声音实践的引入,意味着扭转固有的内容偏见。对内容的崇拜实际上忽视了语言作为一种媒介的不透明性,将诗歌简化为单纯的语义信息(P22)。实际上,声音视角使得诗歌在三个维度上在历史中被打开。
第一,时间性的转换。中国新诗的发展不单纯是对西方语法的寻章摘句,它面对的是中国特殊的社会情境。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要求民族历史意识在时间性上有一个深刻的转折。诗人们要求在历史的遗骸中实现翻转与创造,从个体高涨的“我”到集体构筑的“我们”。诗歌在这样一个历史时刻不是对现实的映照,而是成为革命进程的中介物。它在见证人民大众饱受剥削与压迫痛苦的同时不断生成全新的意识形态,激励、动员、鼓舞大众,并且参与到政治解放进程当中。
第二,物质性的经营。谈到“声音”,康凌将其分为象征与实指两个层面。所谓象征,“声音”作为一种修辞可指代主体的崛起与政治的觉醒。具体来看,与“新史学”类似,工人、农民、底层士兵、破产市民等主题开始被创作。先前被压抑的、沉默的声音被诗歌赋予可视、可听、可感的形式,与集体主体相伴而生的是政治觉悟。抵抗外侮、坚决抗日成为当时主旋律。然而,声音不仅作为象征存在于文艺中,它同时也是一种特殊的感官展演。以诗朗诵为例,它是一种作为听觉经验与声音现象的诗。与作为书写文本与阅读对象的诗不一样。(阅读文本更多是小型沙龙乃至个人的实践活动,而诗朗诵面对的是公共的、匿名的、集体的人声展演)。诗朗诵特有的物质性结构导致其拥有三种特点:(一)直接的感动性,相比文字更加具象化,音调的慷慨激昂在效果上更易感动人;(二)大众的普及性,面对不识文字的大众,诗朗诵可以通过从耳朵灌注的方式实行文化教育;(三)集团的鼓励性,听觉传播比视觉传播所受限制要小得多,在范围上能够影响更多的人。通过诗朗诵的技术特性,可以看到诗歌在实践运作过程中,意义的生成并不在文本、语义、结构之间,而处于声音传达的时空场中。
第三,音响节奏的连接。左翼诗朗诵的目的在于动员民众投身民族主义事业。文本讯息往往需要通过诗歌中的音响效果、节奏样式(格律、韵脚、重音、重复等)来中介。在这里,音响节奏不仅是诗歌内部的形式特征,它还将政治、社会与身体全部勾连起来。换言之,诗歌节奏的设计要从劳动、经验、身体出发,用音响节奏召唤出集体的、政治的身体形式与感官共鸣。
从这个意义上看,革命文化的动员并非只是对革命主题的苦心孤诣。革命文化的动员是在身与心、体与脑、理与情关系中达到平衡。思想的动员要回归到身体的认同当中去,文本的溯源要回归到历史的传播网络中去。因此,对民间文艺形式的运用不能简单地以“旧瓶装新酒”来概括。知识分子、大众、歌谣形式与新旧思想间的内容差异可能只是最表层的。而从身体记忆与感官经验中发掘出的可通约的集体属性,使得传统劳作被转换为革命动员。大众不断进行自我觉醒并不断进行自我形塑。在这样的运作过程中,有关“民间形式”的讨论话题始终处于漫长的传统与急切的革命之间。对这一切的讨论,我们不得不回归到身体记忆与感官经验。
相关推荐
逆天的冒险
我们是天生的冒险家,对冒险的爱从不会离开我们,直到我们迈入垂老之年。”博莱索写道。他认为,“胆小的老头子,在他们的兴趣当中,冒险应该是绝灭了的。”这也是为什么诗人们偏爱冒险,而法律通常是老年人制定的原 (南非)威廉·博莱索 2023-04-10 05:12:26艺术与观念(上册)
《艺术与观念》这本书深入探讨了不同历史时期和社会背景下的艺术观念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作者通过对自史前文化、古希腊—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以及现当代欧洲和北美等地的文化事件和艺术形式进行描述和分析,展 [美]威廉·弗莱明/[美]玛丽·马里安 2023-12-07 07:03:40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
谭其骧(1911年2月25日—1992年8月28日),字季龙、笔名禾子,是浙江嘉兴嘉善人,中国历史地理学家,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科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谭其骧于1930年毕业于暨南大学历史系,随后在 谭其骧 2023-12-07 04:11:41© 2023-2025 百科书库. All Rights Reserv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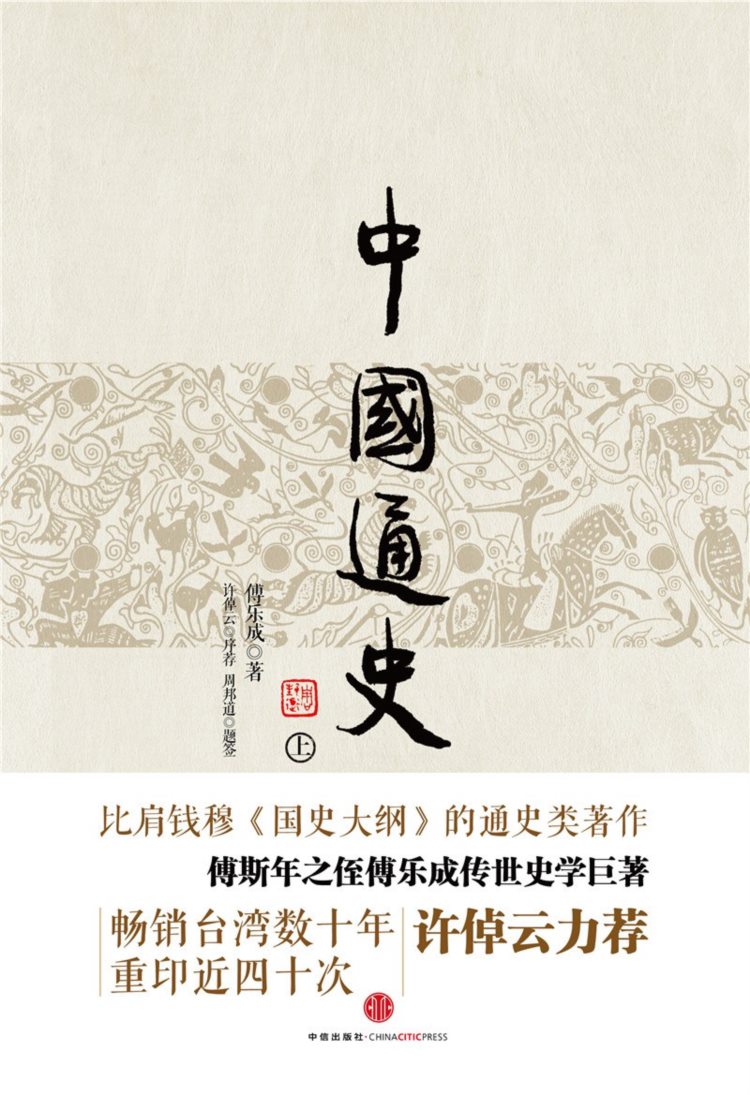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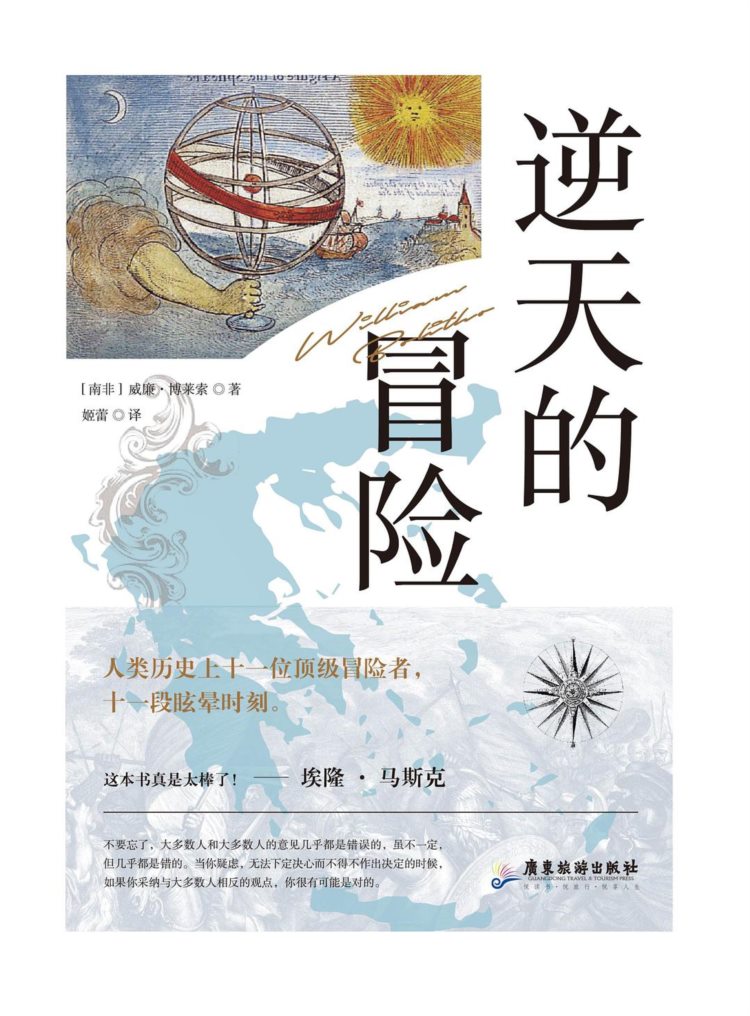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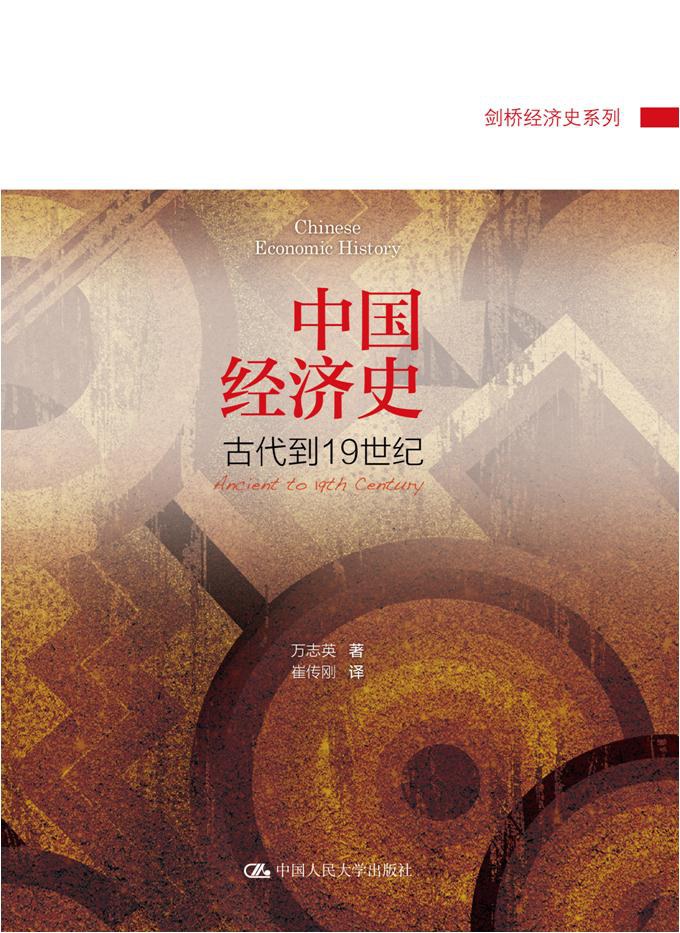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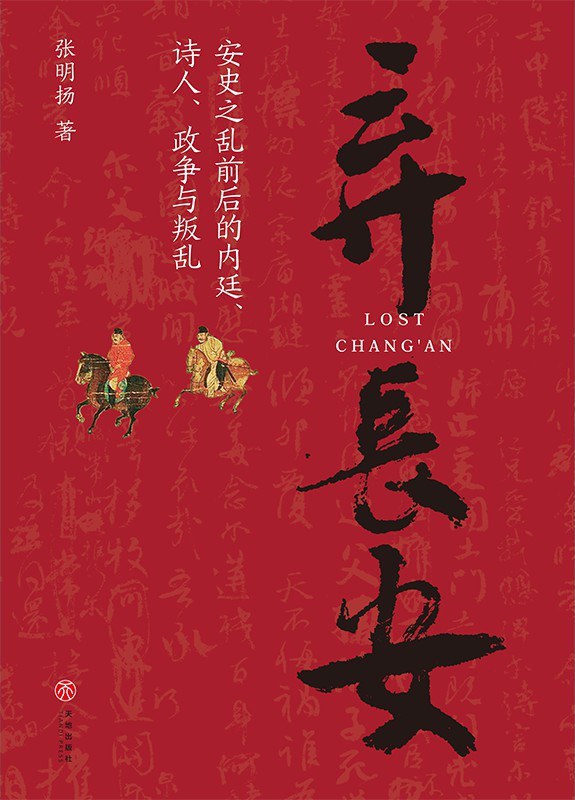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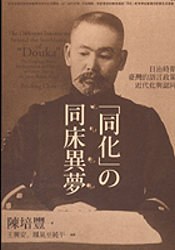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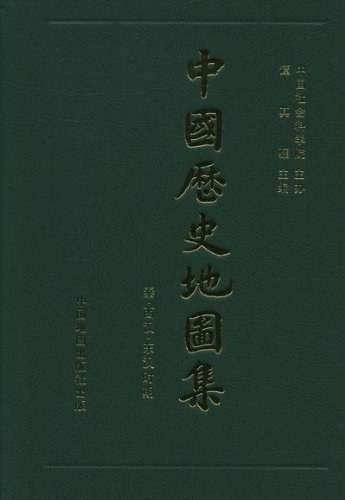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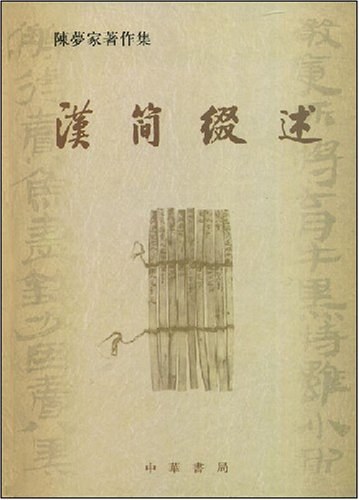
发表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