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帆集刷新行雨迷弈
书名:云帆集
1
0

心情好 2023-06-23 22:05:25
此前读商伟先生的《题写名胜》。便觉得别具会心,是另一个维度的好看的文学史。去国多年的商伟先生是林庚先生的弟子,文笔竟然也似其师,平实中见有诗意。在海外熏染这些年后,视野和角度又颇具新鲜。如此二美并备,写出来的书自然好看。《题写名胜》在体量上虽然是小册子,然而却别见天地。一路山明水秀游走下来,只觉会心处原来真不在远。
最近又得他的新书《云帆集》,述学论诗忆旧怀人。果然又是云烟帆影之新境界矣。拿到手上,先读最末回忆林庚和袁行霈两位尊长的长文,也觉风华遍被。尤其是回忆袁行霈先生的长文很值一读:“一次聊天,不知说到什么话题——好像是提到了俄国的哪位作家。袁先生正好起身去接电话了。杨先生顺口评论说:你的袁老师没有俄国情结。我听了愕然,怎么会呢。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尤其是读文科的大学生,当年都多少经历过俄苏文化的洗礼。连我这位六零后,还赶上了一个余波:在文革期间,谁没偷著读过俄国小说,听过俄苏歌曲。但转念一想,杨先生的话还真的有些道理。平常聊天,袁先生也会谈到俄苏文学,但喜欢俄苏文学不等于有俄国情结。在袁先生的大学时代,全国上下以集体组织的方式,大张旗鼓地学习俄苏文化,难免引人反感。记得先生自己说过,他向来是闲云野鹤的逍遥派,对任何有组织的,一边倒的活动都没太大的兴趣。可以想见,在那些群情激昂的狂热场面中,先生会显得多么落落寡合,要不就是心不在焉。多少有一些反感和抵触。当然,以先生的性格,我想恐怕也很难认同俄国文学中常见的自我戏剧化的倾向和斯拉夫气质。这或许也是一个原因。先生喜欢读巴尔扎克的小说,早在1986年就购进了十卷本的《巴尔扎克选集》,在书架上一字排开,而且很快通读了一遍。这让我有些惊讶,因为巴尔扎克离唐诗宋词未免太远了,趣味也完全不同。但先生读得津津有味,他喜欢巴尔扎克对人世的透彻观察,也喜欢傅雷的译笔。正值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傅雷家书》走红,人手一册。有一次闲聊,先生说他也读了,《傅雷家书》先生很有见地,但又补充了一句说:不过,我可受不了家书的那个腔调。这样的意见,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但我明白先生的意思。”
读完这几段文字,才恍然了悟难怪袁先生这么喜欢淵明诗,一连编写出三本专著来酬答其意。这三本书我得其二。以前读陶诗,用的就是袁行霈先生的注释本,详尽完备。尤其好玩儿的是收罗了一堆后人和陶的诗作,尽管绝大部分的作品都很干枯无聊,即便才高学厚东坡居士的《和陶诗》,尽管他老人家颇为自得,以为“不负淵明”,但读来依然质木无味,诗由兴而起,缘情而生。“唱和”的念头一有,再高明的技巧也就只是技巧了吧。
说到学人们对淵明诗之欣赏,更想到年辈稍长于袁先生的冰茧庵繆公彦威。读他的《冰茧庵论学书札》,时时有耽读陶诗的辞句,如致刘操南札:“多年饱历沧桑,静观世变,更喜读《庄子》,陶诗。昔苏东坡少读范滂传,晚和淵明诗。此或亦中国士人必经之途径歟。”
又如与张志岳札:“年岁老迈,涉世亦深。读陶淵明集更深有体会。竊以为在中国古代士人中,淵明兼综儒道,寓愤激入世之壮怀于冲夷淡泊之中,在真风告退,大偽斯兴之世实为最高之修养。”
又如与程千帆札:“鉞少读史书,慕顾亭林之为人,有激
相关推荐
萤火谷的梦想家
艾莉森•麦吉出生于1960年,是美国《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同时也是大都会州立大学创意写作课的教授。她的作品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并出版,也曾被提名普利策奖,并获得苏斯博士奖金奖、克里斯托弗图书奖、美国 [美]艾莉森•麦吉/[美]克里斯托弗•丹尼斯/绘 2023-03-27 16:50:25鬼马女神捕1·绝密卧底(上)
腹黑凤凰vs毒舌鸡妖——蓝翎:“小姬,跟我去人界吧!”姬十四:“干吗?让人宰了我做小鸡炖蘑菇吗?”蓝翎:“不啊,让妖怪宰了你做小鸡炖蘑菇更气派。”凤凰蓝翎和鸡妖姬十四生活在无忧无虑的灵界。他们的故乡叫 郝天晓 2023-04-17 00:22:47© 2023-2025 百科书库. All Rights Reserv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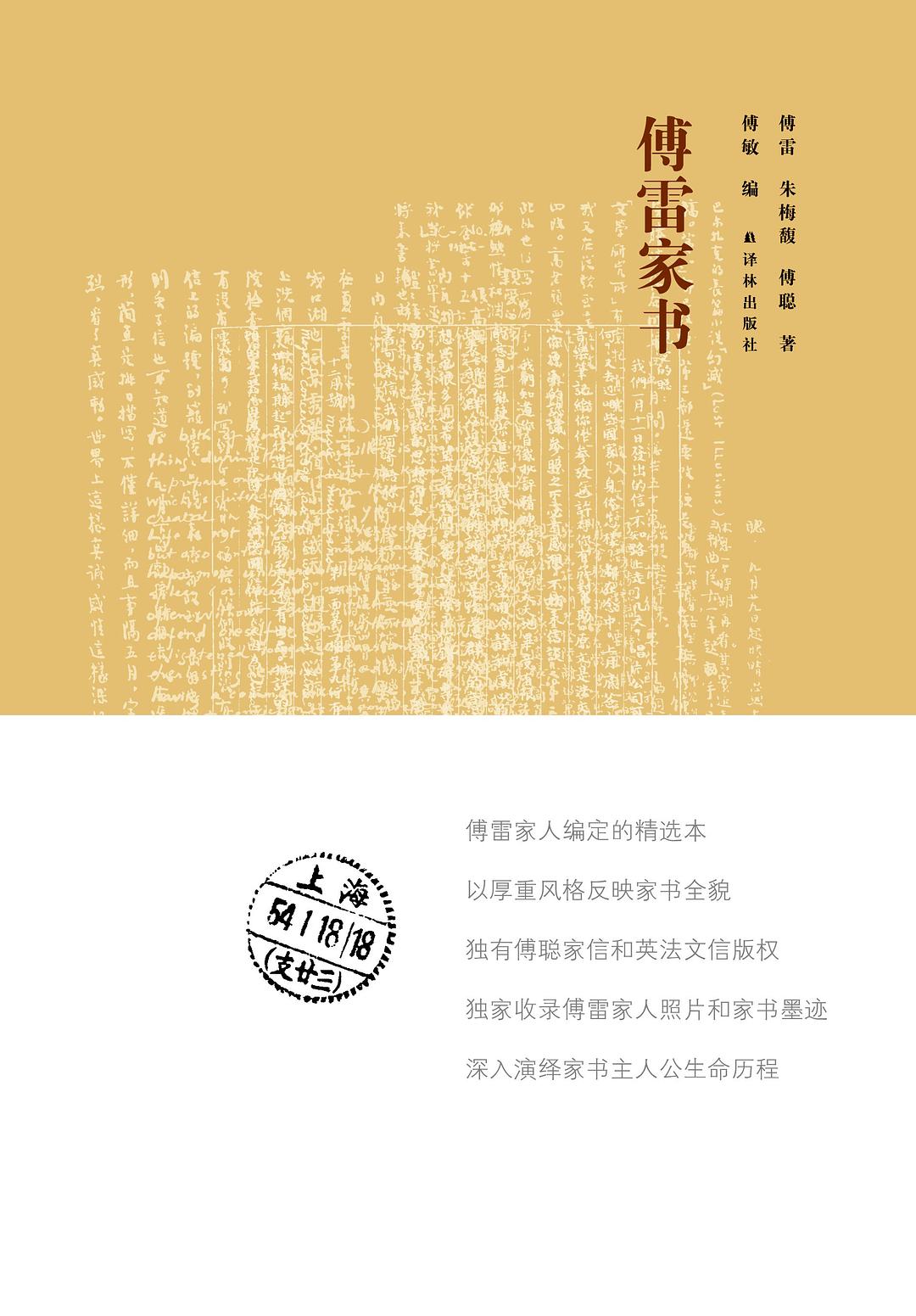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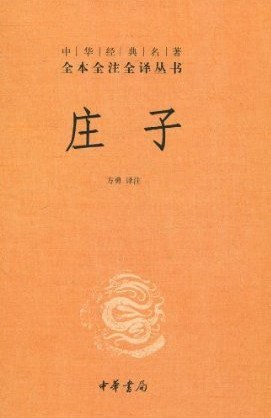








发表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