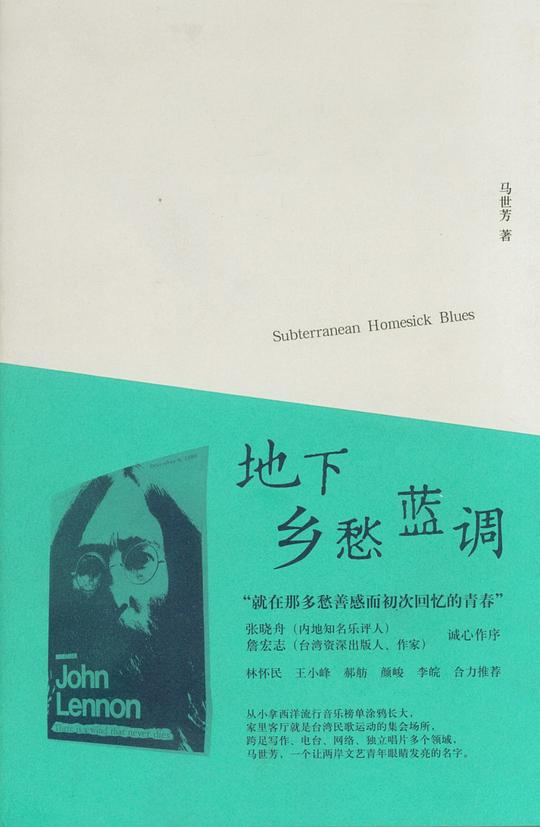
《地下乡愁蓝调》乡愁是给没有家的人
书名:地下乡愁蓝调
1
0

毛毛虫 2024-01-07 21:54:52
二刷后的随手记录:
古老的中国没有乡愁,乡愁是给没有家的人,少年的中国也不要乡愁,乡愁是给不回家的人。这是马世芳的音乐青春的记录,也记录了一个他未曾赶上的时代。原本以为这只是一本个人符号的随笔集,却意外地唤起了我自己被遗忘的青春记忆。这并不奇怪,因为摇滚乐就是现代人共同的青春与乡愁。而我也是一个精神上没有家的人。
我还记得第一次听到Bob Dylan的歌是从《Blowing in the wind》开始的,当时很难接受他破破烂烂的嗓音。但几年后,我被《Like a rolling stone》的歌词深深地打动了,因为我曾经就是那个自带优越感的高傲公主,流浪异乡,失去一切,迷茫幻灭,一次次打碎自我,然后重新开始。青春就是要在路上挥霍,成为一个真正的现代人和成年人。
Lou Reed的《Perfect Day》在音乐响起时,逝去的记忆如同幽灵一样瞬间复活。我最早是在高中同学中小范围传播的一张名为《穿过骨头抚摸你》的音乐精选集中听到这首歌的。在大学的时候,又在电影《猜火车》的配乐中再次听到。当时,我对现代音乐缺乏欣赏能力,只有一些主观感性的认识。但Lou Reed那无所谓中充满绝望的唱腔和猜火车那毫无选择的片段承载了我19岁时的孤独、抑郁和躁动。因此,这首歌在一段时间内成为了我单曲循环,并成为某篇日志的配乐。后来,那些日志消失在赛博空间,猜火车的情节被彻底遗忘,精选集的名字也抛在脑后。与此同时,还有那些永远笼罩在阴霾中的日子,一起被彻底遗失了。
我正式开始听摇滚乐是从Nirvana的不插电现场版《Where did you sleep last night》开始的,这首歌是第一代民歌手从监狱中找到的Leadbelly的翻唱。简洁低沉的吉他扫弦,副歌中突然爆发的呐喊,黑暗到不好意思和别人讲的歌词,录音中著名的叹息声等等,让我感受到了追求本真的lo-fi美学。当时,我把Nirvana的专辑都听了个遍,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或许没有深入理解,但Nirvana的音乐审美多多少少还是一直在影响着我。我不喜欢过于精致的制作,而是更欣赏追求本真的音乐。在我不自觉地挖掘民歌的路上,对唱腔的喜好也渐渐形成了。Nirvana是我和许多人的摇滚启蒙乐队。
The Doors这个乐队对我来说是一个音乐上的分水岭。他们高水准的乐手、灵动的Blues律动、迷幻、叙事性的歌词和性感的唱腔完美地融合在一起,真的太难得了。甚至,我是先听了The Doors,然后才偶然听到汪峰被称为中国的Jim Morrison,他的音乐也是人文叙事歌词加上迷幻布鲁斯风格,于是我开始听汪峰早期专辑《花火》。
胡德夫的《匆匆》,像山间的溪流一样奔放的钢琴和感人至深的吟唱让我深深地记住了这个名字。从他那里开始了解台湾的民歌,然后在前两年通过一位朋友的博士论文整体了解了同时期的大陆音乐。《牛背上的小孩》,《美丽岛》和《少年中国》这些歌让我在成年后的最脆弱时刻落泪。父母和祖辈无法述说的故事和心中凝结的情感开始涌动,变得通畅柔软。音乐就是有这种力量。
Ozzy Osbourne的《Goodbye to Romance》,经典的金属柔情。每隔几年我都会翻出来听一听,喜欢专辑中Rhoads的吉他,干净、清晰、激昂,生者如此追求。人生中总会与一些情绪和个人的浪漫告别,然后才能想起这首歌。我们总是要与虚妄的情绪和个人的浪漫告别,然后朝着更激荡、更广阔的天地奔赴,让生命融入永恒的浪漫。
以上就是我会补充记录下来。
相关推荐
国际超模的极简瘦身课
这是一本为中国女孩撰写的“易瘦体质”培养指南,作者是一名国际超模李霄雪。李霄雪曾与纽约排名第二的模特经纪公司EliteModelManagement签约,在国际模特界打拼了10年,之后她决定回到中国成 李霄雪 2023-03-31 06:29:24我有一杯酒,可以慰风尘
祝愿你的岁月平静无波澜,同时也希望我的余生不会有太多的悲欢。这里介绍的是关东野客的又一力作,它名为《我有一杯酒,可以慰风尘》,共涵盖13个故事。这些故事或许会让你感到孤独和温暖,也或许会涌起遗憾和美好 关东野客 2023-03-29 19:34:53即使生命如尘,仍愿岁月如歌
优化后:想要走向自信、尊严的人生,女性可以从工作、家庭、生活等方面入手。本书将通过作者及身边朋友的经验告诉读者,一个女人是否能够实现美好的生活,决定性因素并不在于她的经济状况,而在于她有无勇气不委屈、 晚秋 2023-03-31 07:15:04我们的性
《我们的性》,现在是它的第7版,生物、社会心理、行为和文化诸多方面以对个人有意义的方式,对性做出了全面、学术观点鲜明的介绍。我们非常高兴读者对本书前几版一直反应热烈且热心;这些反应激励着我们为你们的学 [美]罗伯特·克鲁克斯(RobertCrooks)/[美]卡拉·鲍尔(KarlaBaur) 2023-05-05 06:31:19抱歉,这么晚才找到你
在漫长的岁月中,你是否曾经深爱过一个人?他是否还在你身边,或者已经消失在人海中?他曾陪着你粗茶淡饭,还是一起骑马喝酒走四方?你的爱情,又是怎样的模样呢?乔诗伟用温暖的笔触为你带来了25个温馨的故事,每 乔诗伟 2023-04-01 17:46:31© 2023-2025 百科书库. All Rights Reserv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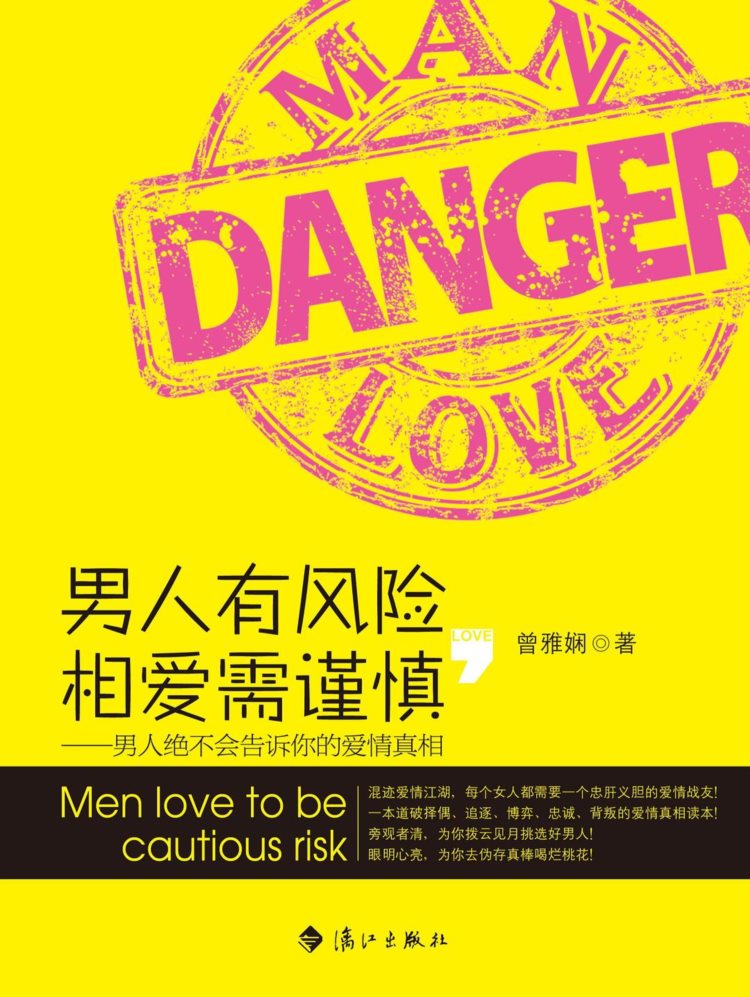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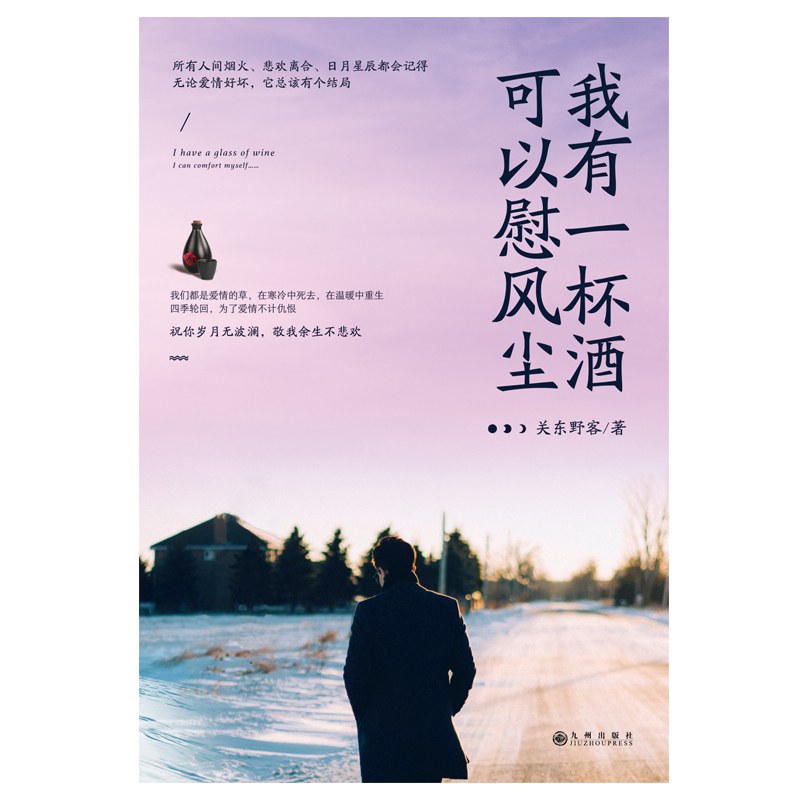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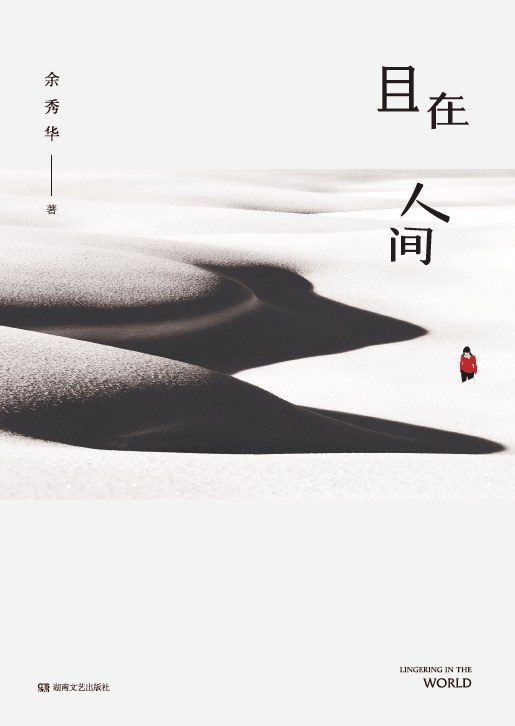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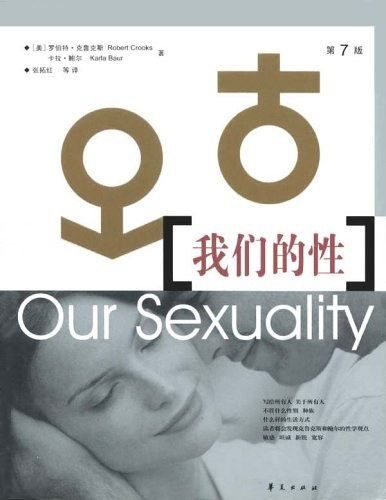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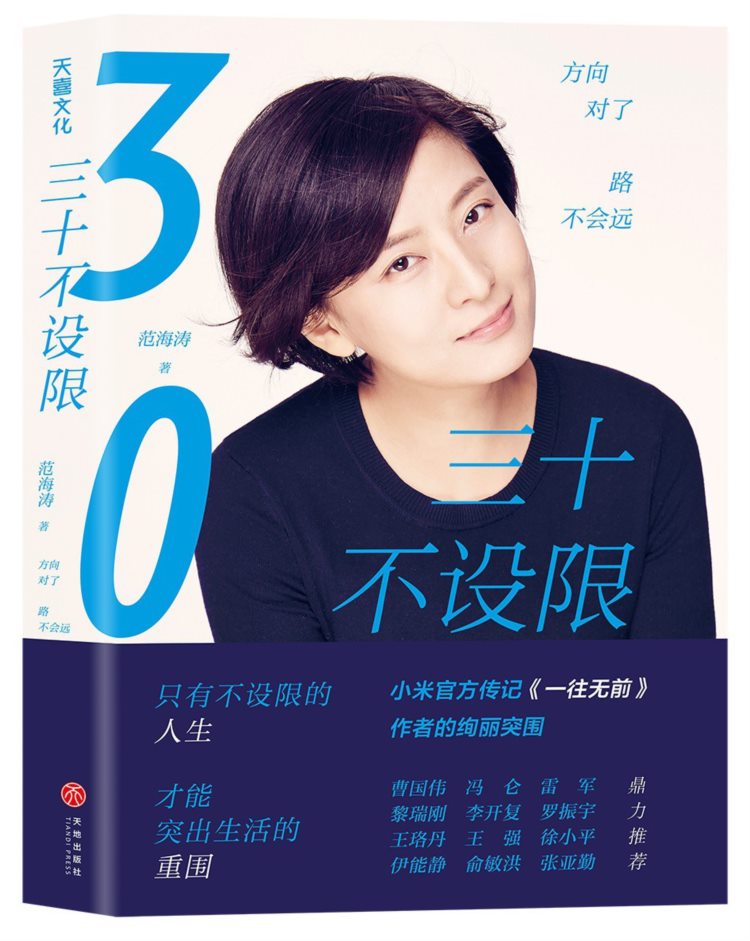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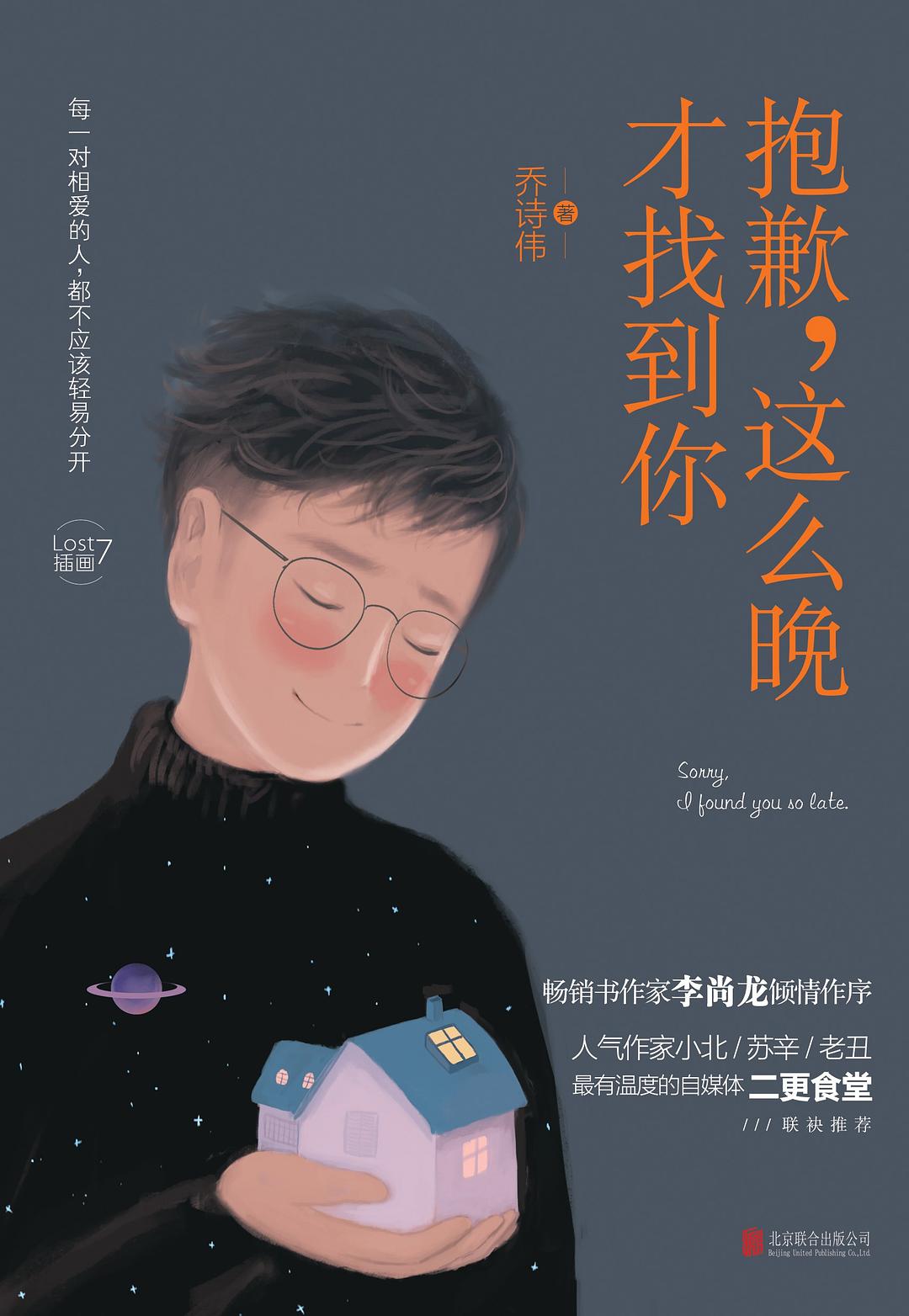
发表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