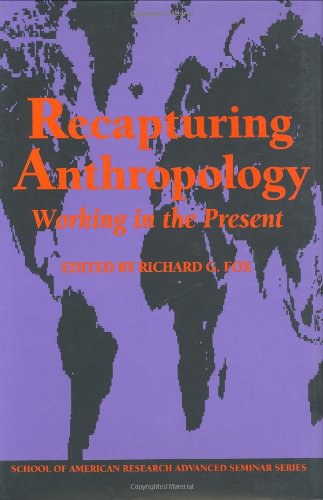
《Recapturing Anthropology》突破文化束缚:庶民发声的途径
1
0

大长今 2023-10-15 01:02:01
1.在Clifford等人的《写作文化》中,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分歧和鸿沟并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此外,还存在一些群体同时具有主体和客体的性质。因此,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划分可能是虚构的,不真实的。这种划分本质上包含着权力的不平等,主体几乎总是站在白人男性的视角上。在这种语境下,一些身份多元、超越边界的群体,例如女权主义学者、跨性别者、移民等,在研究中被忽视,或者他们本身就是研究者时,无法通过白人男性所设定的自我与他者、主体与客体的标准来进行定义和审视。
2.阿布鲁格(AbuLughod)对"文化"进行了解构,可能根本就不存在一种被称为"文化"或"共同体"的东西,或者即使存在,也是推动形成立场性的因素,决定一个人在社会坐标系中的位置。但是这种位置的存在是建立在结构性的基础上的,必然假设有更高层次的力量在决定它。这种力量可以是一种潜在的权力/霸权力量。因此,关注个体的日常经验有助于人类学家摒弃或者说不再将经验完全融入到既定的文化框架中,用一套固定的理论,透过有色眼镜审视他者。在这一点上,阿布鲁格和赛义德所说的制度化的东方/中东也是一致的。
3.总体而言,拉尔(LAL)还强调人类学家应该关注社会的权力结构,而不是试图将它们融入先入为主的文化观念中。人类学家应该远离"文化"的本质化同质化,转而关注个体在社会中的生活经验和能动性。个体应该被从悬浮的理念、隐匿的权力话语中剥离出来,为自己代言。再看《纱遮的情感》(Veiled Sentiments),斯皮瓦克(Spivak)提出的"庶民无法发声"的悲观论调在拉尔这个"halfie"的写作中得到缓解。拉尔成功做到了在写作中"连接过去和现在"、"连接自我与他者"、"连接手头上的研究与变化万千的世界"。
相关推荐
国际超模的极简瘦身课
这是一本为中国女孩撰写的“易瘦体质”培养指南,作者是一名国际超模李霄雪。李霄雪曾与纽约排名第二的模特经纪公司EliteModelManagement签约,在国际模特界打拼了10年,之后她决定回到中国成 李霄雪 2023-03-31 06:29:24我有一杯酒,可以慰风尘
祝愿你的岁月平静无波澜,同时也希望我的余生不会有太多的悲欢。这里介绍的是关东野客的又一力作,它名为《我有一杯酒,可以慰风尘》,共涵盖13个故事。这些故事或许会让你感到孤独和温暖,也或许会涌起遗憾和美好 关东野客 2023-03-29 19:34:53即使生命如尘,仍愿岁月如歌
优化后:想要走向自信、尊严的人生,女性可以从工作、家庭、生活等方面入手。本书将通过作者及身边朋友的经验告诉读者,一个女人是否能够实现美好的生活,决定性因素并不在于她的经济状况,而在于她有无勇气不委屈、 晚秋 2023-03-31 07:15:04我们的性
《我们的性》,现在是它的第7版,生物、社会心理、行为和文化诸多方面以对个人有意义的方式,对性做出了全面、学术观点鲜明的介绍。我们非常高兴读者对本书前几版一直反应热烈且热心;这些反应激励着我们为你们的学 [美]罗伯特·克鲁克斯(RobertCrooks)/[美]卡拉·鲍尔(KarlaBaur) 2023-05-05 06:31:19抱歉,这么晚才找到你
在漫长的岁月中,你是否曾经深爱过一个人?他是否还在你身边,或者已经消失在人海中?他曾陪着你粗茶淡饭,还是一起骑马喝酒走四方?你的爱情,又是怎样的模样呢?乔诗伟用温暖的笔触为你带来了25个温馨的故事,每 乔诗伟 2023-04-01 17:46:31© 2023-2025 百科书库. All Rights Reserv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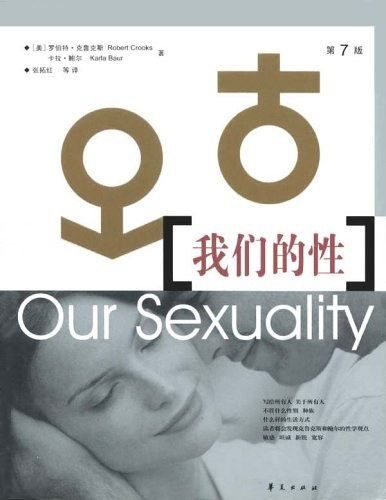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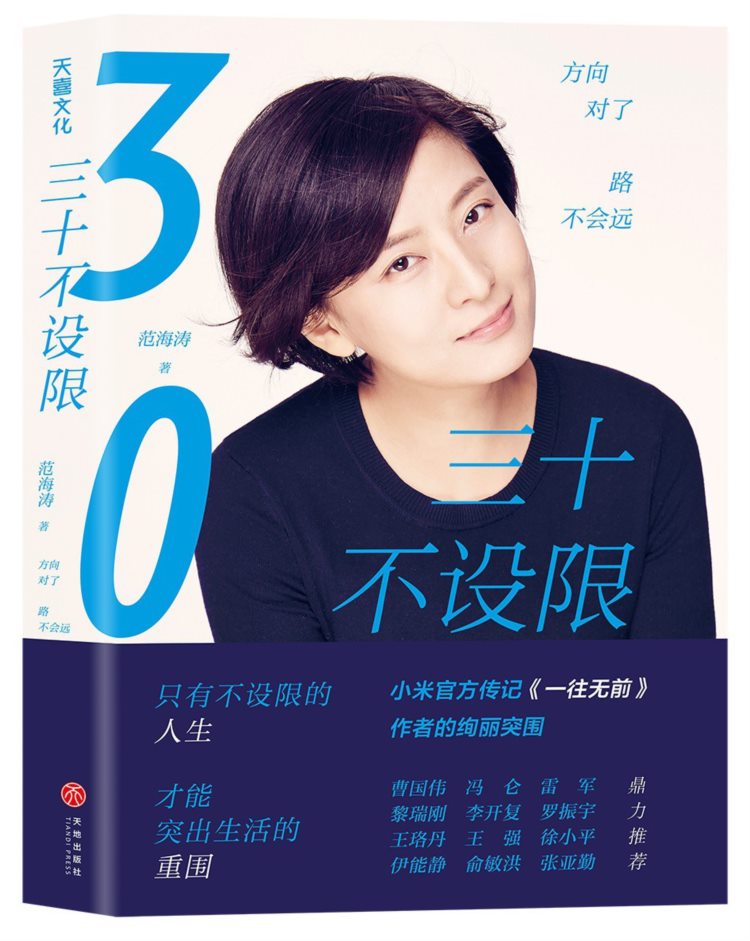



发表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