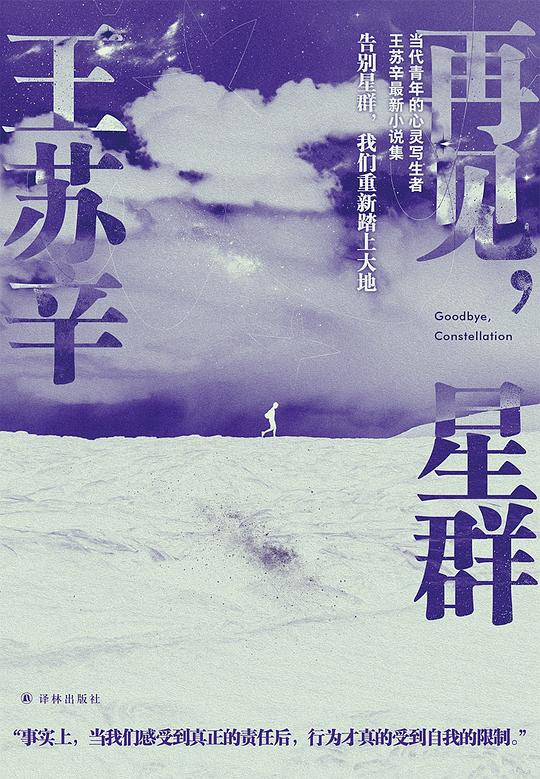
《再见,星群》再见星群:21岁与30岁之间的成长与告别
书名:再见,星群
1
0

冰雪女孩 2023-10-03 01:47:50
算起来,写作已超过了十年。站在现在年纪的当口回望,已经忘记二十一岁那年的状态。于是,二十一岁只是一个虚指,指代所有被迅速过掉难以回望的时光。
或许大部分写作者都是如此,除了最初燃起写作雄心和真正下笔之时,其后总有一段迅速被遗忘的写作时光。为何被遗忘无非是那年的心境并未与起初写作时差别太多,或者说,在漫长的写作时光中,也许除了那最初的心志,就剩下写出代表作的那些光阴被记忆镌刻下来。
也或者说,除了这两截刻骨铭心的写作记忆,大部分写作的生活,往往伴随着枯索、忧闷。有时候内心波澜万丈,大部分时候却像挤牙膏似的在写。每每遇到难题,还会质疑自己。尤其这过程中,自身的生长又不断提醒着人,前面的写作必须被推翻了——这个过程,在年轻的时候总是经常发生。就好比此刻的我,回忆八九个月前的自己,知道那已经和现在大有不同——也只有这样剧烈的转折能够被写作者深切记忆。
而那些因为附着在更平常的生长之日中,反复被遗忘。却又在某些剧烈变化的时刻,突然又被忆起。恍然发现,也许并非是那么平淡的时光。
这个过程,在写作的十多年来,反复在生活中交锋着,而精神世界更像溢出的一小块飞地,写不出来的暂时深埋心底,作为提醒,写得出来的,作为果实,拿出来,有机会在不同的阅读者面前摊开。这些过程,都是幸福的。
如今,再回到虚指的“二十一岁”,我能够想到的更多是物质层面——还在找工作,或刚刚走向社会,没有收入,投稿又总是被退。这样熟悉的经历,或许每个写作者都无比熟悉。现在看起来只是必经的一段路,当时却往往觉得举步维艰。仔细想想,人年轻时最亲密的朋友,有的往往因为互相借过钱产生了友情(甚至爱情)。
但也就是那样一段现在看起来很普通的岁月,默默锻炼着最初的心智,起码在面对基本困难时不会觉得忧心。这些细节,也都为其后度过写作难关积累了经验。因为写作面对的内心磋磨只会更多而不会少,因此这些生活的困难都作为辅料先于写作本身验证着自己的心,比如一个人是否有坚持做事的能量。因为写作就是一种“做事”。
但创作总是和别的事情不太一样,因为常常没有回报。不像大考,即使失败,再付出些努力,也很可能有机会。写作不同,这是一项常常没有回报的工作。技术的锻炼虽然可以通过日积月累的理解抵达一定的水平,面对不同的题材是不是能有深度的理解能力却非常难说。
有时候头脑走在前面,笔却跟不上。有时候笔在前面,文字却像被力气连缀起来似的。这样或多或少失败的经验也都渐渐影响着写作本身的实现。即使在进入创作成熟期后,这一现实也仍旧频繁出现,阻碍着写作者作品成熟度的实现。
于我而言,转折点在2015年写的短篇小说《白夜照相馆》。写完这篇小说后,突然觉得自己有一种枯竭感。仿佛依凭叙事直觉建构故事的自己在逐渐消失,而新的自我似乎还没有被我再次发掘。于是,2016年3月,我开始着手书写另一个对我来说十分重要的中篇小说《在平原》。女美术教师与男高中生之间从备考到更深入的交谈,混入七天的高山写生之旅。显性的故事被取消,隐性的故事则是每一次对话的跃迁。《在平原》完成后,同名小说集,和另一本全新命名的小说集《象人渡》相继出版,虽然阅读者回应并不多,但当时的写作形式确实也并不可能要求更多回应。
直到2020年初,我们都知道的变故开始。我突然发现,自己看世界的眼光一下子跟着环境发生变化了。2019年下半年到2022年上半年,我写下八个与以往内在不同的中短篇小说。这是一些内在并无一致性的“他人”各自参与和串联起来的命运和人生。描述不同的普通人各自性情的光彩,让它们汇集成一片广袤的精神世界,是这一阶段的愿望。为此,这八个小说需要一个整体的命名,我叫它们《再见,星群》。编辑给出的文字描述是相符的——“告别星群般混沌的力量,告别虚浮麻木的日常、混沌的思索、踌躇与躁动,我们的双脚重新踏上大地”。于我而言,这是一部关于普通人用身心走出自己的“远大前程”的故事。
在物质和阶级重新占据人的头脑的现在,有这样一群人在平等、坦诚地与这个世界交流,故事里的人在很长一段时间也鼓励着我,帮助我成为更好的人。我想把这些故事带给一切可能的阅读者,找到我的线性的朋友们。这个过程中,我重新感受到在那个虚指的二十一岁,我所感受过的一些体验。当年未被发现和认识的,突然都清晰起来。以至于有时候我会想,也许一个写作者最重要的时光,是他完全不知道如何做如何写的那段时光,正是那些沉默、激烈、难以清晰触摸的言辞,日日敲击过内心,待有一天有机会掏出来,才发现自己也有能把一些所感安放的能力。
尽管在理论架构的强悍力量下,文学表达有时候显得如此不堪一击,甚至我都不知道在更深层次的思考竞争中,小说写作在我这样程度的人身上,是否还有些新的机会,但更重要的是,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事情。所以我决定不再想了。只在接下来的生活中好好把这件事做好,成为一个真正合格、优秀的文学写作者。
2022春
相关推荐
萤火谷的梦想家
艾莉森•麦吉出生于1960年,是美国《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同时也是大都会州立大学创意写作课的教授。她的作品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并出版,也曾被提名普利策奖,并获得苏斯博士奖金奖、克里斯托弗图书奖、美国 [美]艾莉森•麦吉/[美]克里斯托弗•丹尼斯/绘 2023-03-27 16:50:25© 2023-2025 百科书库. All Rights Reserv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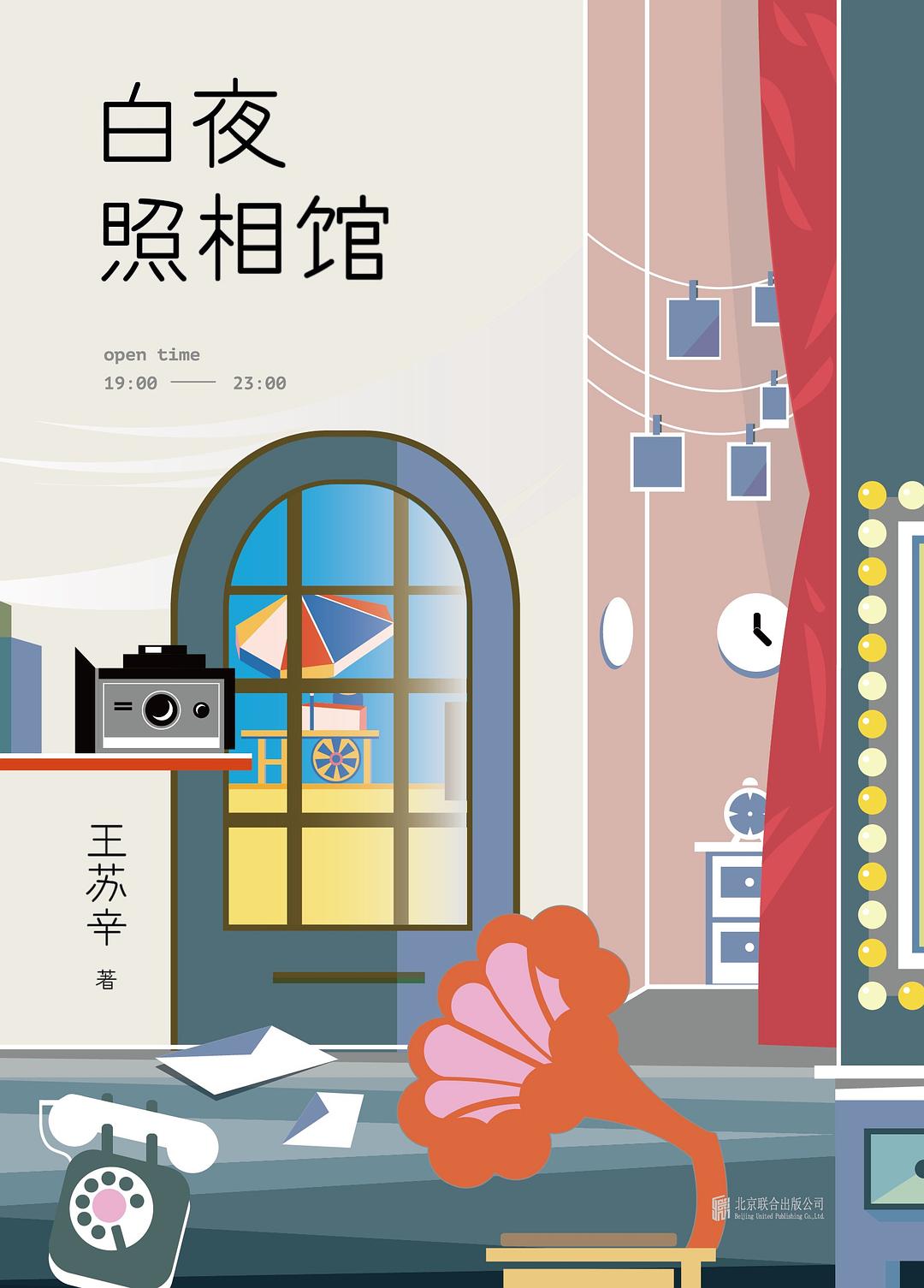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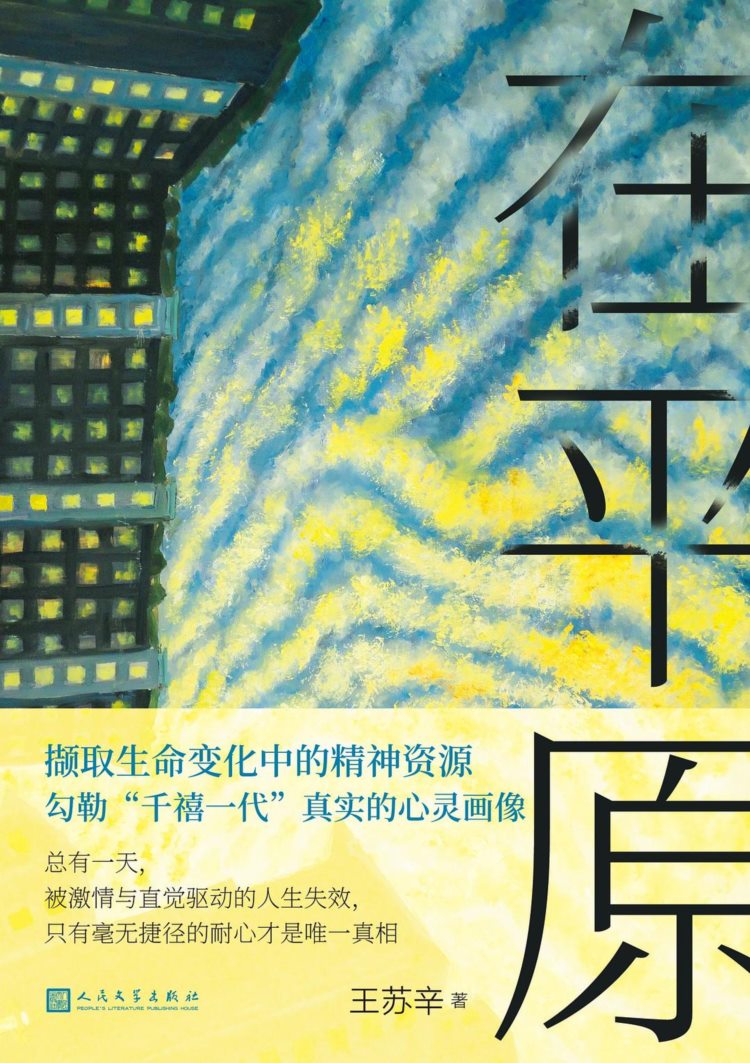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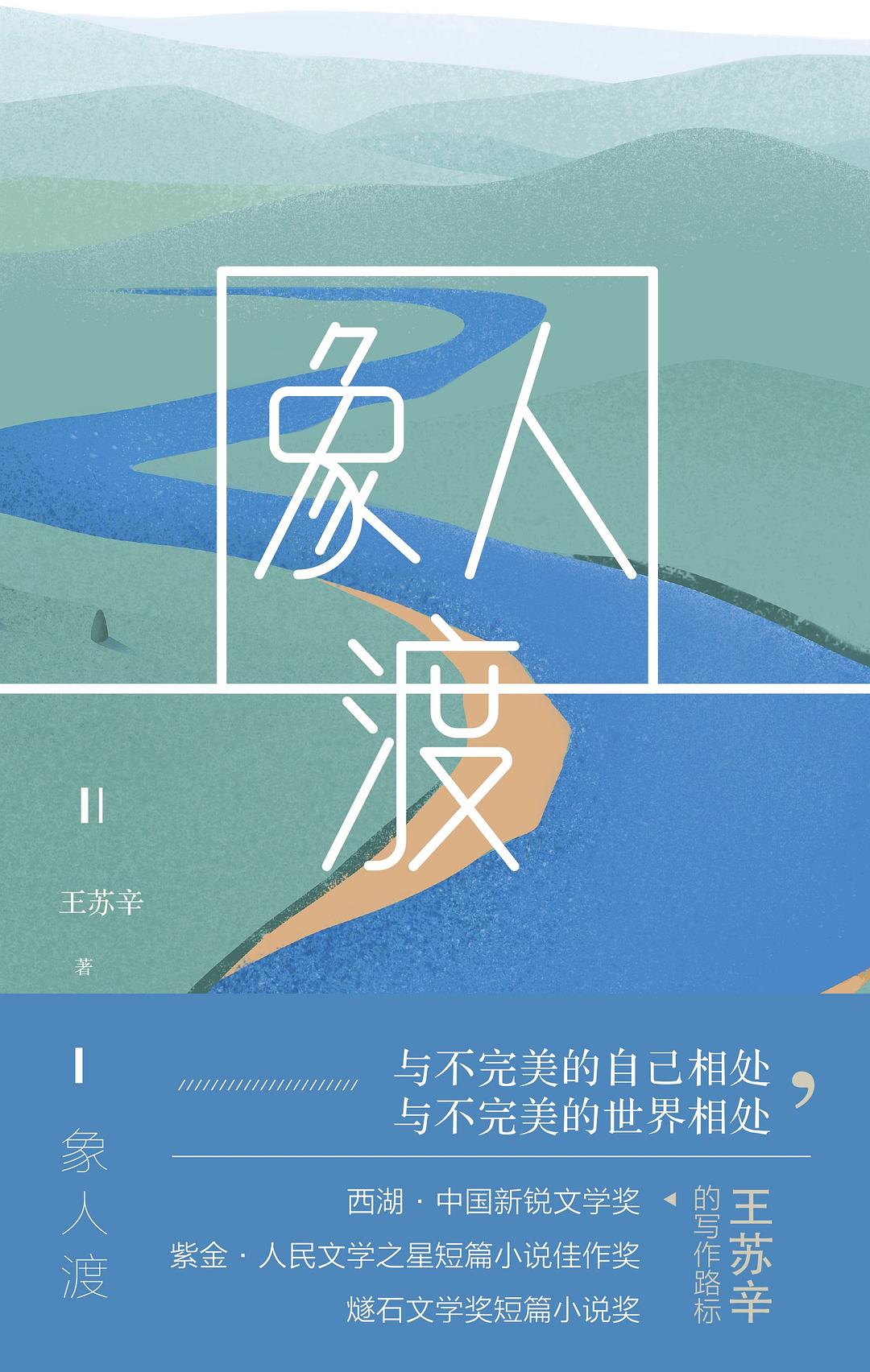







发表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