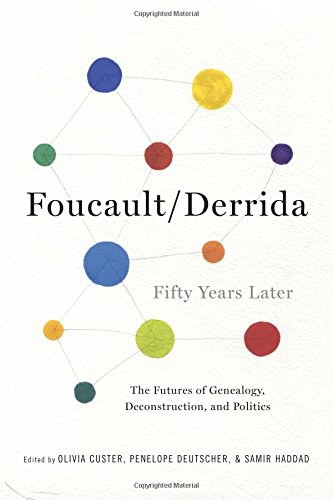
《Foucault/Derrida Fifty Years Later》"Foucault/Derrida 50年后:疯狂史中的述行性矛盾与浪漫主义姿态"

优雅小天鹅 2023-10-02 00:17:59
Amy Allen著,何啸风译。
1.德里达对《疯狂史》的批判
本文讨论德里达对福柯《疯狂史》的批判,重点是德里达提出的方法论问题。德里达的批判非常复杂和微妙,但我认为,德里达对《疯狂史》的方法论有两种重要的解读。
第一种解读是“沉默的考古学”,这种解读颠覆了福柯的主张,即《疯狂史》书写的是疯狂本身的历史,而不是用理性语言描写的疯狂史。德里达认为这是“整个方案中最为疯狂的部分”,因为方案必须完全摒弃理性的语言,但考古学必然要使用理性的语言去书写。此外,福柯似乎要对历史进行审判,但德里达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预审和裁决在选择字词时已经不断强调这种过错。尽管德里达没有使用“述行性矛盾”这个词,但他显然暗示了某种述行性矛盾:由于福柯动用了他实质上反对的理性语言,因此其述行性言辞违背了批判的实质。
我们要暂停一下来解释为什么德里达认为我们无法逃脱历史的有罪性。他认为理性是一种总体性结构,是“无法逾越的、独一无二的、至高无上的伟大”,我们无法摆脱理性的宏大结构,即使要书写沉默的考古学也必须借助于理性来反抗理性、质疑理性,“对理性的革命只能在理性中进行”。因此,在德里达看来,“理性的历史”这一概念对《疯狂史》来说是无意义的,因为历史从来都是一个合理性的概念。
福柯本人深知书写疯狂史的困难。在《疯狂史》序言中,他意识到了他的方案中存在的述行性矛盾。德里达引用了他的这句话:“力图捉住疯狂的原初状态必然属于一个将其捕捉了的世界。”因此,书写疯狂史是对囚禁着疯狂却无法恢复其原初状态的历史的整体进行结构性研究。这表明福柯书写的是疯狂作为历史对象的话语/非话语实践的历史整体。
德里达对《疯狂史》方法论的第二种解读是“逻各斯的不和”。福柯意识到书写疯狂史的困难,因此他在序言结尾说,应该保持“无助的相对性”。德里达认为福柯的话语“无法依赖某种理性或逻各斯的绝对性”,“拒绝在理性句法中被说出”。在这里,德里达勾勒出第二种方案的轮廓,即找到一种语言,能超越疯狂和理性的鸿沟,找到两者断裂的转折点。
2.哈贝马斯对《疯狂史》的批判
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对福柯的批判范围更广,涵盖了《疯狂史》以及其晚期作品(不包括关于伦理学的作品)。但我关注的是他对福柯早期考古学作品的批判,因为在这个批判中,我们看到了他与德里达的共同之处。哈贝马斯提出了两种方法论解读《疯狂史》(比德里达更简洁、紧凑),他认为福柯从浪漫主义的角度考虑了这个问题,尽管后来放弃了这个主题。福柯认为,在疯狂的各种表象背后,还存在一种需要揭示的本质。与德里达一样,哈贝马斯首先把《疯狂史》的目的看作是书写疯狂本身的历史,让本质的经验开口说话。然而,他也注意到福柯承认任务的不可能性,因为我们只能用理性的语言来表达疯狂的真相。在注意到这一点后,哈贝马斯也走向德里达所说的第二种方法论,即探索疯狂与理性分道扬镳的起点,从中揭示出无法言说的东西。
与德里达一样,哈贝马斯认为,福柯早期作品的目的是对理性进行彻底批判。他认为这种批判是用一种人文科学的历史写作方式展开的。他关心的问题是,这种写作方式是否成功地完成了对理性的彻底批判,而又没有陷入自我关涉研究的困境。因为历史学家必须在理性视野内进行研究活动,所以哈贝马斯对福柯的关键批判是他早期作品中的方法论问题,即如何清晰描述理性与疯狂之间复杂关系的问题。换句话说,关键的方法论问题是如何以一种人文科学的历史写作方式书写“对理性的彻底批判”的目标。尽管哈贝马斯的批判范围更广,但他与德里达的方法论考量是一致的。从这个共同点出发,他们批判了福柯对现代性的抽象否定以及对理性的彻底批判存在的矛盾。然而,假如福柯的目标不是对理性的彻底批判,那么他们的批判就是错位的。在证明这一点之前,我先以简单的方式总结他们对福柯的批判的三个关键点。
第一,他们都认为福柯的目标是对理性的彻底批判或对理性的革命。这是一个重要的共同点,为其他两个共同点奠定了基础。
第二,他们都认为福柯存在述行性矛盾(德里达没有明确提到这一点,但可以概括为这个词),因为我们只能用理性的工具完成对理性的彻底批判。这意味着福柯重复了他想批判的疯狂的排他性态度,并且陷入了解决不了的悖论或两难境地。
第三,他们都认为福柯逃离述行性矛盾的唯一途径是一种浪漫主义态度。换句话说,他们认为唯一的方式是让疯狂自己开口说话,因为这样做可以让疯狂保持野生、原始的状态,而不被理性限制。然而,这是一种浪漫主义态度,最终是一种形而上学态度。因此,德里达和哈贝马斯认为,福柯陷入了两难境地:如果福柯用理性工具来讲述疯狂的历史,那么他就陷入了述行性矛盾。如果福柯想逃离述行性矛盾,那么他只能采取浪漫主义、形而上学的态度。
3.理性的超越性与内在性
德里达和哈贝马斯为何在对福柯的批判中一致他们似乎都担心福柯的方法论的不可行性,特别是福柯试图书写某种理性历史时,会产生许多矛盾和两难。我认为,这是因为他们预设了理性的超越性。这种超越性是德里达所说的“无法逾越的、独一无二的、至高无上的伟大”,或者哈贝马斯所说的“绝对因素”、“普遍有效性的超越性”,它“消除了时间和空间”。显然,他们对这种“绝对因素”的理解是不同的。我认为他们对理性的超越性的解释是不同的。而且,在晚期作品中,德里达并未坚持这种“无法逾越的、独一无二的、至高无上的伟大”。比如,在《无赖》(2003)第2部分,他说理性在根本上是历史性的,从而十分接近福柯的计划。在《法律的力量》(1989)中,他说解构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谱系学的。因为他在学术生涯早期就关注形而上学历史,所以想要全面理解他的理性概念,必须考虑到他思想变迁的复杂过程。然而,在我看来,他的晚期作品强调理性的历史性,与《我思与疯狂史》的批判完全不同。德里达在《无赖》中指出,理性的超越层面与有条件者、可计算者、力量、法律的悖论性交织在一起。这种超越性与哈贝马斯所说的超越性不同:从特定的语境中产生,但超越该语境。然而,他们都提供了一种方式,将超越性作为某种程度上超越理性的环节,某种理性内部的无条件性。
把超越性作为理性的无条件环节,这种观念不同于规范的超越性,但二者有密切的关系。例如,哈贝马斯认为,理性的超越性源自理性的有效性,而理性的有效性赋予理性一种约束力。反过来,在构成人们日常交往的生活世界的规范性背景下,这种约束力又是至关重要的。类似地,在《无赖》中,德里达说:
解构(如果存在这样的东西)我的眼中首先仍然是一种无条件的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明确地以未来启蒙的名义,不放弃所有条件、假设、约定和前提的合理的方式来悬置,以无条件地批判所有条件,其中包括关键理念的那种条件。
相关推荐
逆天的冒险
我们是天生的冒险家,对冒险的爱从不会离开我们,直到我们迈入垂老之年。”博莱索写道。他认为,“胆小的老头子,在他们的兴趣当中,冒险应该是绝灭了的。”这也是为什么诗人们偏爱冒险,而法律通常是老年人制定的原 (南非)威廉·博莱索 2023-04-10 05:12:26笔误:文学大师的秘密生活
爱伦·坡小时候曾在一个墓地里上学?马克·吐温曾当着维多利亚女王大谈放屁,是怎么回事?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在派对上双手趴在地上,像狗一样大叫又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认为,作家应该是正襟危坐着写书的人,但《笔 (美国)罗伯特·施耐肯伯格 2023-04-10 10:13:49© 2023-2025 百科书库. All Rights Reserv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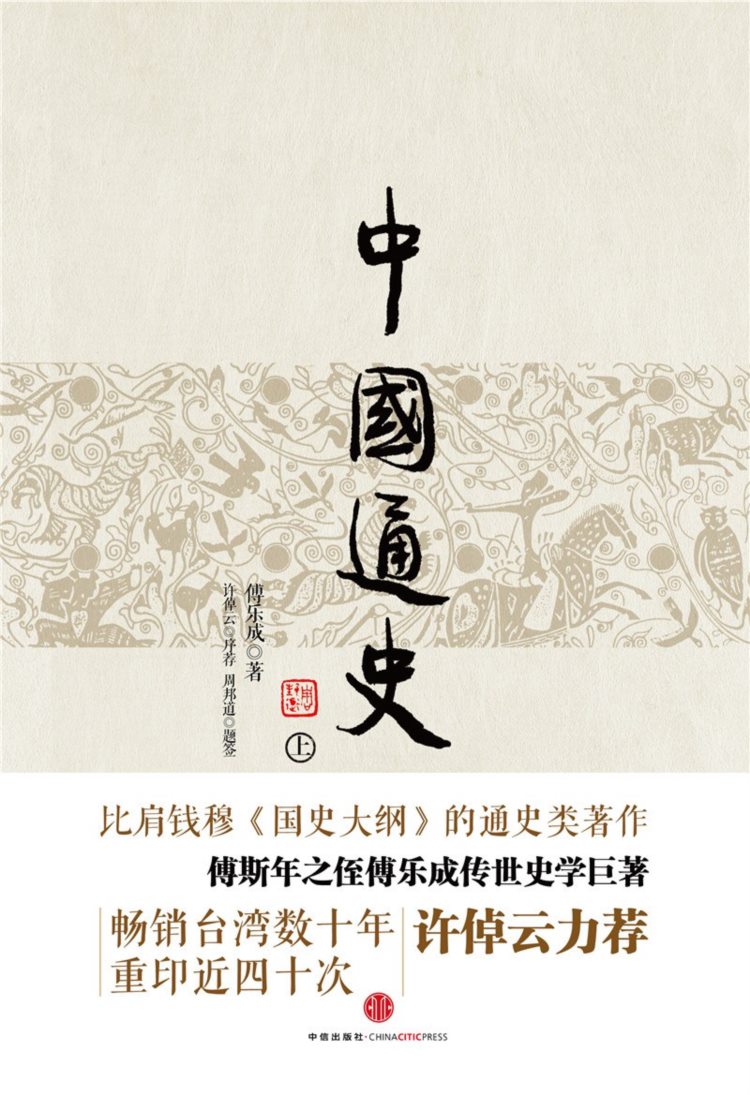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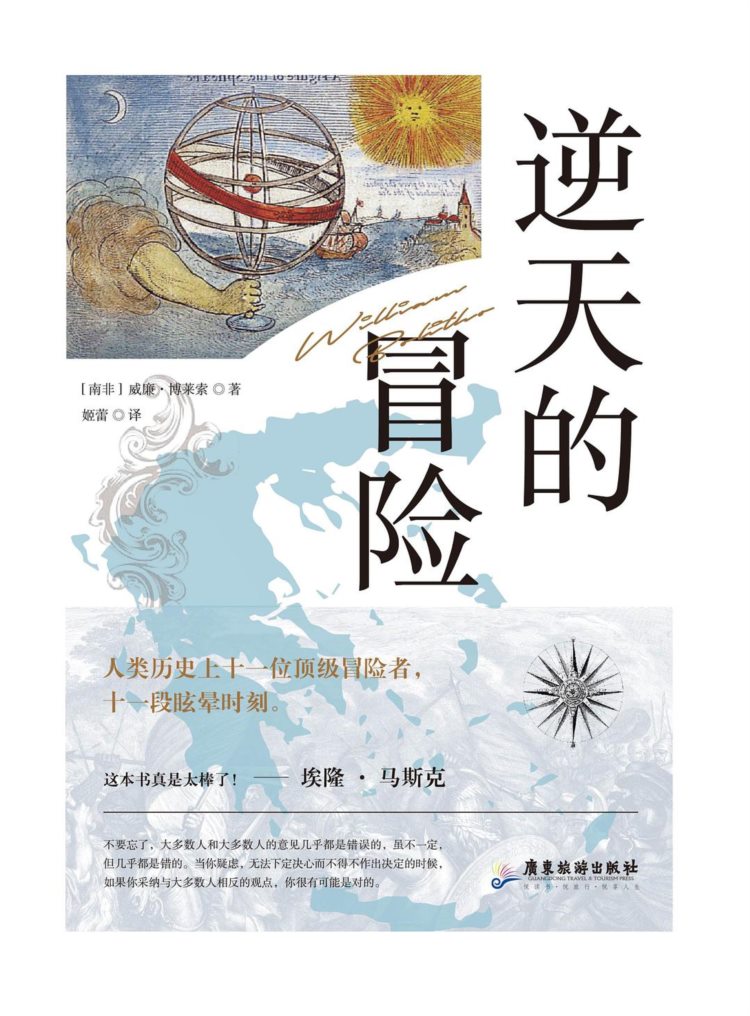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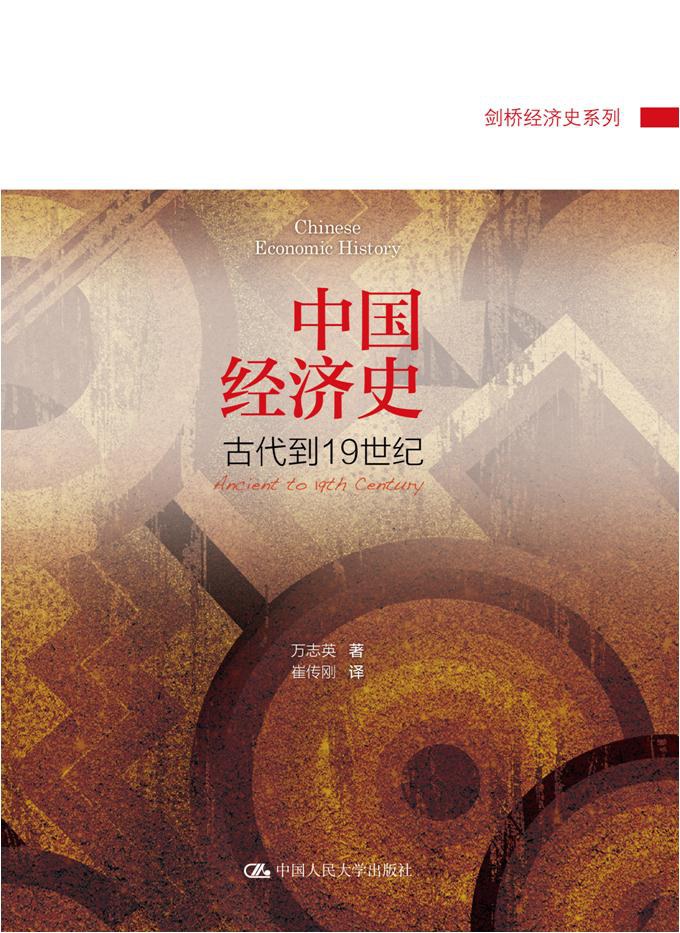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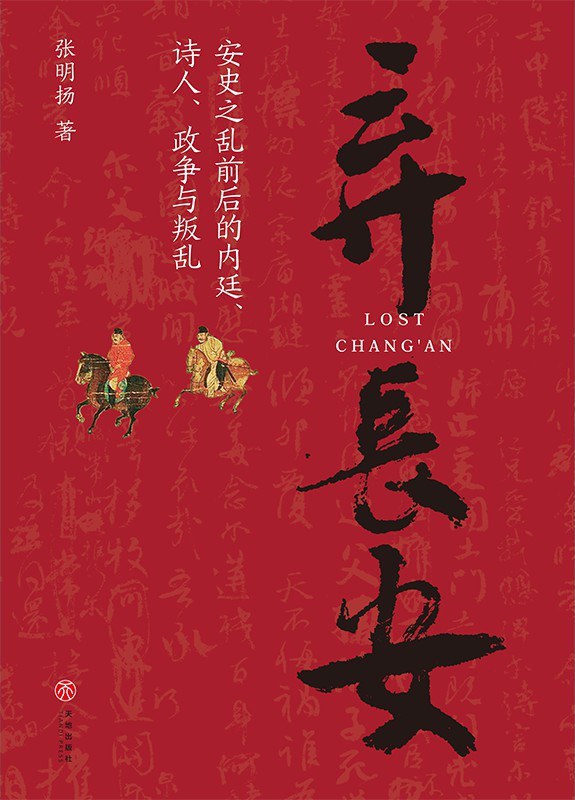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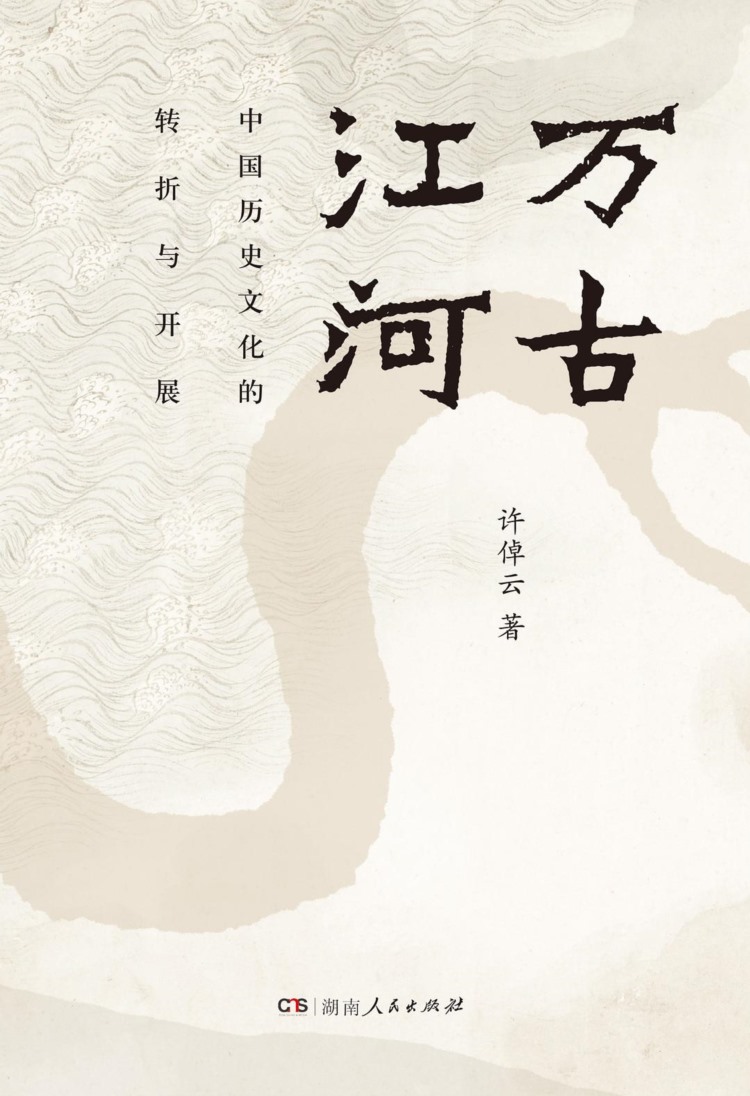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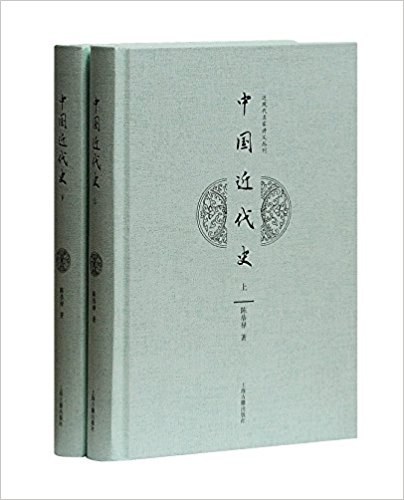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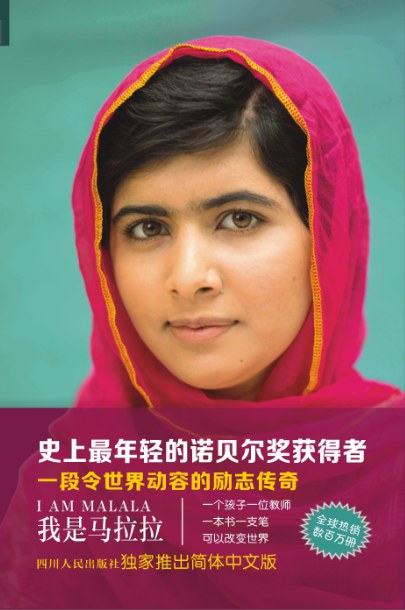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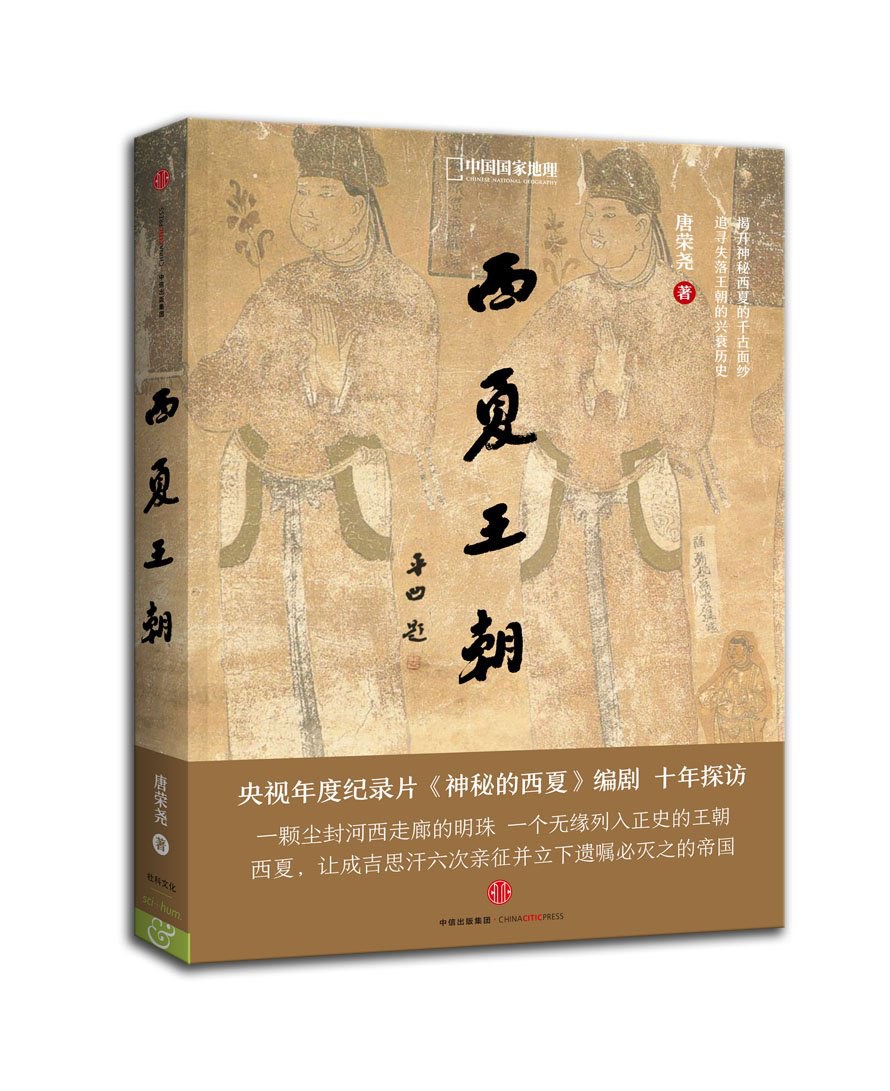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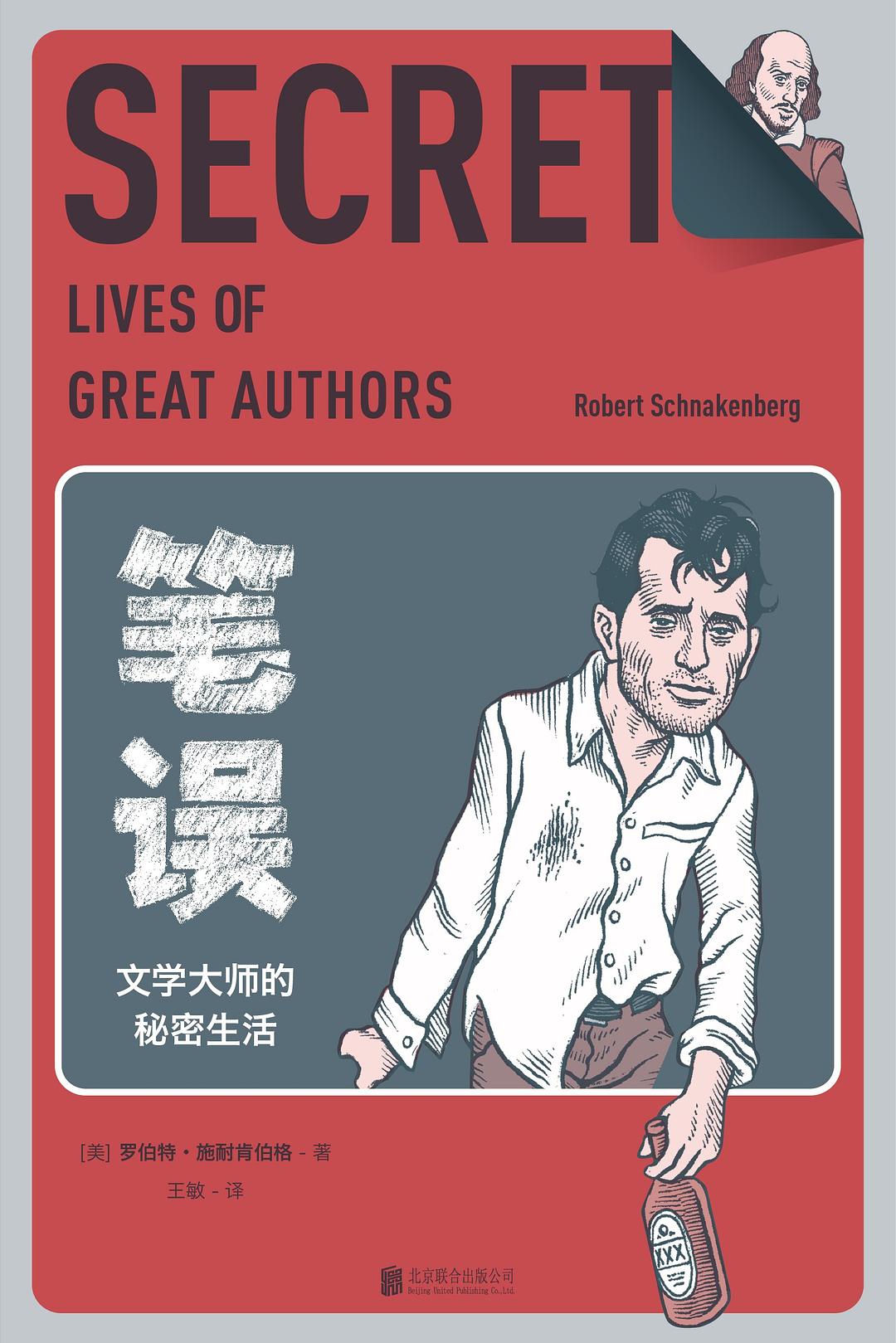
发表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