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小说解构初读
书名:福
1
0

朗读者 2023-09-28 22:19:19
从前没有读过库切。前几日和亲爱的朋友瓜瓜在图书馆逛的时候他说到了这本,然后我就拿起来看了,看了两页只觉得整个人都陷进去了,然后就一连串好几个晚自习读完了。其实这本书不厚,翻译得也很精彩,只是很多细节我没想明白。
最后,我再也划不动了。我的双手起了水泡,后背灼热,全身酸痛。
一开始我并没有读懂这篇小说想说什么,只觉得最后的梦境和第三章的重章有一种经历过多精神失常的美,大抵还是出于我没有读过后现代主义的窘迫罢。我姑且这么想着,然后我读了译者后记,就想把手探向更深处。
无奈高中还没毕业,讲话也不通畅,说得不好之处请见谅了。
秩序解构
男权和女权秩序的解构是我是个单身女子。我父亲是法国人,为了躲避在佛兰德遭受的迫害跑到了英国,他的本名是波顿,但是被别人说走了样就成了巴顿。我母亲是英国人。我意外登上了小岛,却没有被普遍认知里的男权所蹂躏,我和岛主克鲁索之间保持着良好的秩序,但是感觉这种秩序有一些反常,因为在这样一个寂寞了如此多年的老男人心中没有一点对女人的感觉,这是作者以“我”之视角展开叙述时自己内心也在挣扎和斗争的东西。这里应该蕴含着第一个点,男女秩序的解构。
同时作为一个与鲁滨逊等同的形象,她并没有按照惯例去积极扩张大英帝国的殖民秩序,去建立鲁滨逊那样的世界。她作为一个殖民者能够做的事情是接受被殖民者男性的指挥。
我会留下我的梯田和墙,这些就足够了,而且绰绰有余。
其实这里算是一面镜子。库切处在南非,曾经的英国殖民地。而二战之后是殖民主义从全世界消退的过程,他就诞生于这样的时代。他应该见到了殖民秩序的出走和本土秩序对外来侵略的抵制。无论是有声的无声的,有形的无形的,有目的有组织的亦或者暗流涌动的。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是在尝试留下自己的梯田和墙维持自己本土的秩序。
我得以逃出之时,岛上顽固派克鲁索(代表原本的秩序)离开了原有的土地直接呜呼一命,死在了海上。黑奴星期五虽然得以离开,但是他只是从一种秩序到另一种秩序中去。从在岛上听人说挖就挖,听人说给女士唱歌就唱歌。他唯一能做的斗争是一直吹那六个音的笛子,去找寻那些原本的记忆。到了英伦岛上也没有自由之身,需要每天伏案在写字台上写字母o,我还逼着他第二天要学写字母a。其实这也象征着我们全世界都被这样一种语言文字所拴住,这是殖民主义留下来的枷锁,我们必须被迫承认这样一种语言是更有所谓价值和实用性的。
而我在尝试驯化星期五写字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过程中,总是感到不耐烦的,我总是感到有星期五这样的存在拖累了我的生活,使我的人生戴上了脚镣。我在思考这一段是否是尝试想说明殖民主义后期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动使殖民主义的形式从血腥的直接掠夺变成了更为隐形的资本输出的方式的这一段历史,这样的过程中想抛弃原始的劳动方式,因为有了机器生产的推广。离开了耕作离开了挖地离开了修筑梯田取而代之的是带上假发穿上长袍不是跳起原始部落的舞蹈而是被囚禁在写字台前书写。这是一种新型的奴役,从原本小岛上惟命是从到另一个小岛上现代生活的牢笼,也揭露了殖民主义的新方式。即使有了自由契约也没有真正的自由,算是一种讽刺吧。
对于女儿的形象,我的拙见是,英国方面对一些殖民地不再进行管辖后,前殖民地的依赖性仍然存在的问题。因此女儿不断地登门拜访,因为她的思想里告诉她,这个人就是自己的母亲。他还为此哭泣,为此穷追不舍。“母亲”无奈只能“亲吻”她,向其提供相应的援助等。(不过这个说法挺立不住脚的,看个乐呵就好了)
作者用了很多角度来讲同一件事情,比如星期五被割掉舌头的事情,船长讲了几遍,我讲了几遍,作家福讲了几遍,他自己却没讲,话语权被剥夺了。
小岛上的故事,我讲了一遍,我说“最后我再也划不动了。”克鲁索说巴伊亚只不过是巴西森林边缘的小岛。船上的人却建议我说我不是一个女探险家,而是克鲁索的妻子。福用他自己的方式讲了一遍这个故事。通过多个角度的叙事,作者是不是想说明历史在不同人的笔下书写的方式是不同的呢作为殖民者当然不会刻意去刻画过多自己丑恶的历史,作为被殖民者当然会尽力去夸张那样的伤痛来获得一些民族凝聚力。
最后一段我偏向认为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在看这件事。作者似乎采用了一种“荒唐”的逻辑,星期五没有舌头,他的嘴却张开了:
从里面缓缓流出一道细流,没有气息,不受任何阻碍地流了出来。这细流流过他的全身,流向了我,流过了船舱,流过整艘船的残骸,冲刷着悬崖和小岛的两岸,朝着南方和北方,流向世界的尽头。
那道涓涓细流是柔软的,又是冰冷冷的,黝黑的,似乎永远流不尽,它拍打着我的眼帘,拍打着我的面庞。
合上书本,我的心还沉在库切的世界里,海浪也在无声地拍打着我的面庞。
相关推荐
逆天的冒险
我们是天生的冒险家,对冒险的爱从不会离开我们,直到我们迈入垂老之年。”博莱索写道。他认为,“胆小的老头子,在他们的兴趣当中,冒险应该是绝灭了的。”这也是为什么诗人们偏爱冒险,而法律通常是老年人制定的原 (南非)威廉·博莱索 2023-04-10 05:12:26艺术与观念(上册)
《艺术与观念》这本书深入探讨了不同历史时期和社会背景下的艺术观念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作者通过对自史前文化、古希腊—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以及现当代欧洲和北美等地的文化事件和艺术形式进行描述和分析,展 [美]威廉·弗莱明/[美]玛丽·马里安 2023-12-07 07:03:40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
谭其骧(1911年2月25日—1992年8月28日),字季龙、笔名禾子,是浙江嘉兴嘉善人,中国历史地理学家,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科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谭其骧于1930年毕业于暨南大学历史系,随后在 谭其骧 2023-12-07 04:11:41© 2023-2025 百科书库. All Rights Reserv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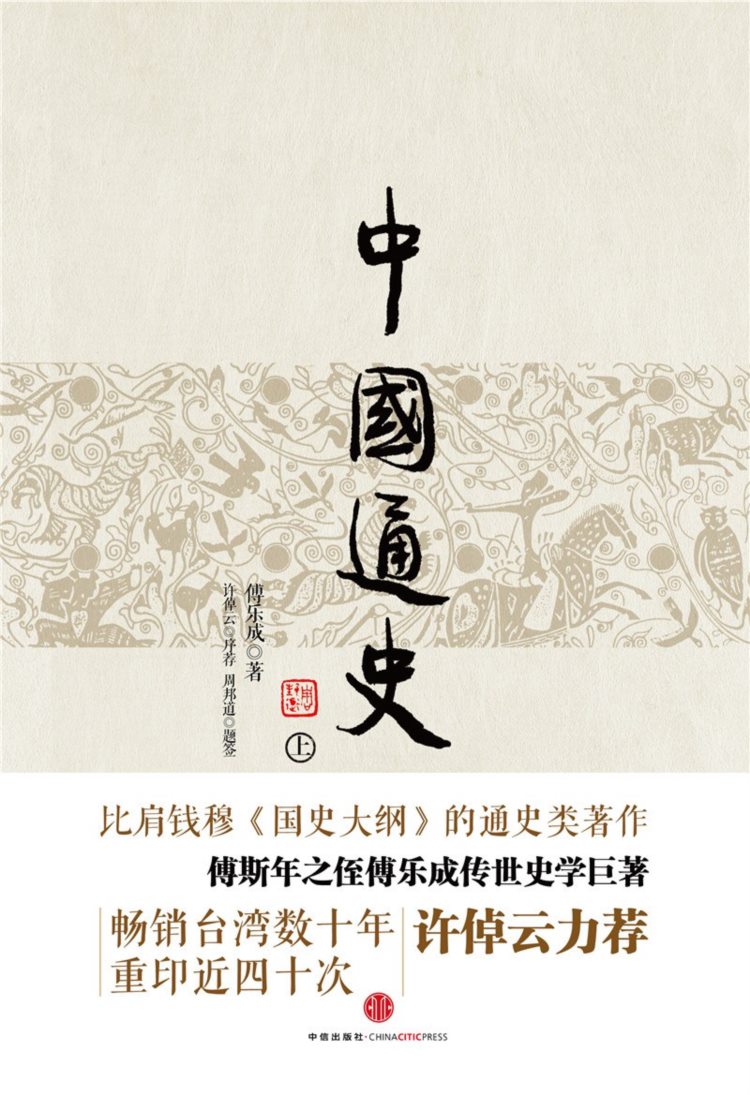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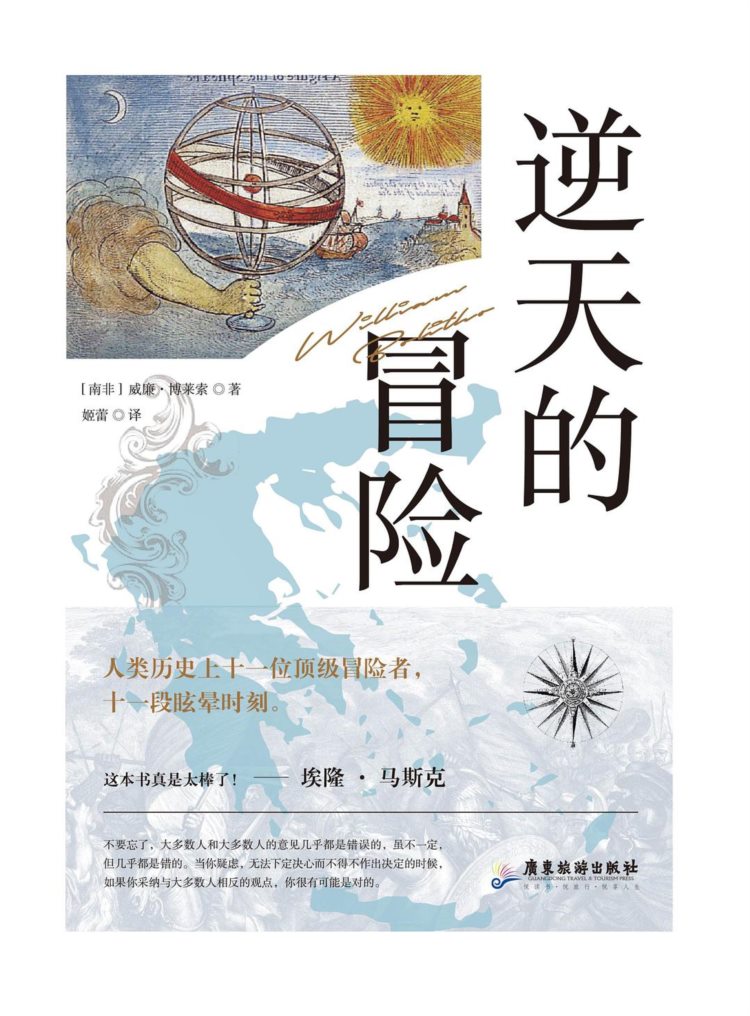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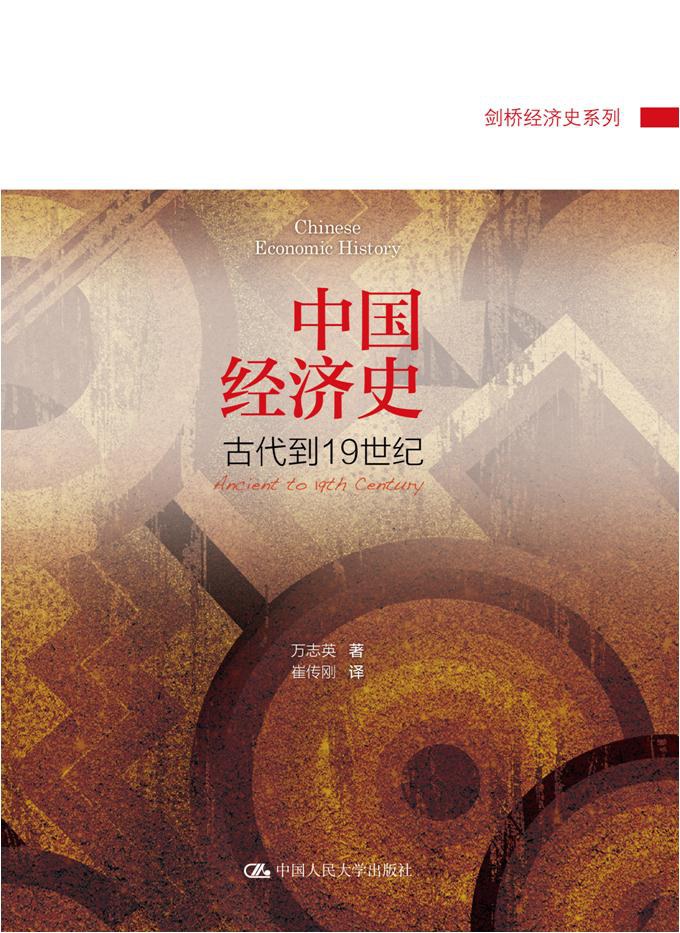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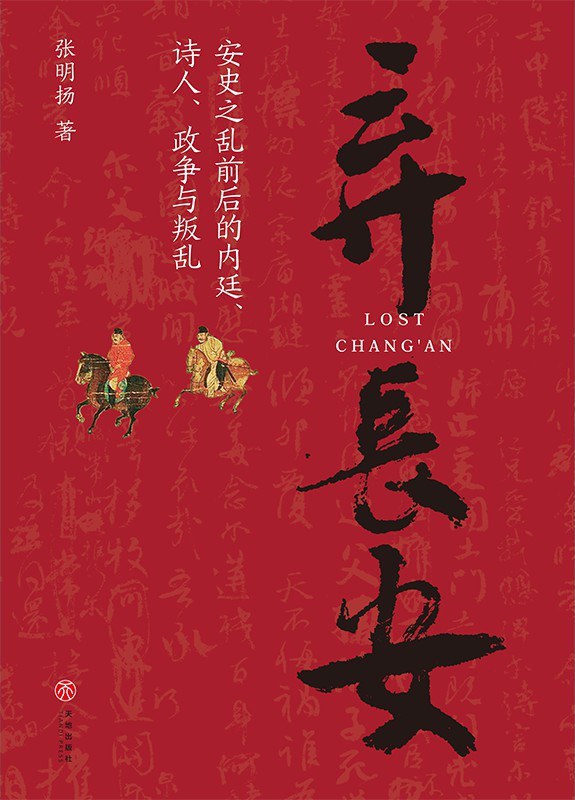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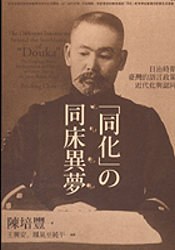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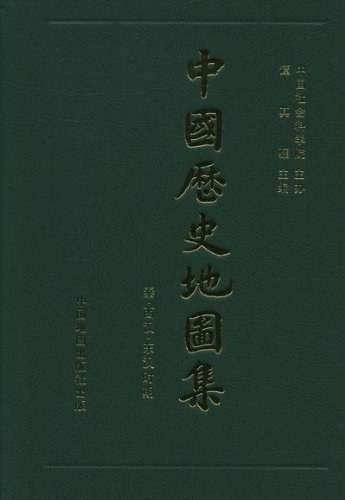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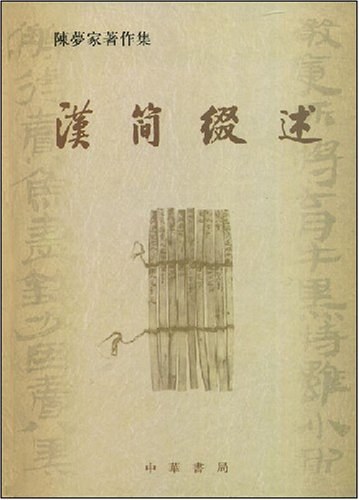
发表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