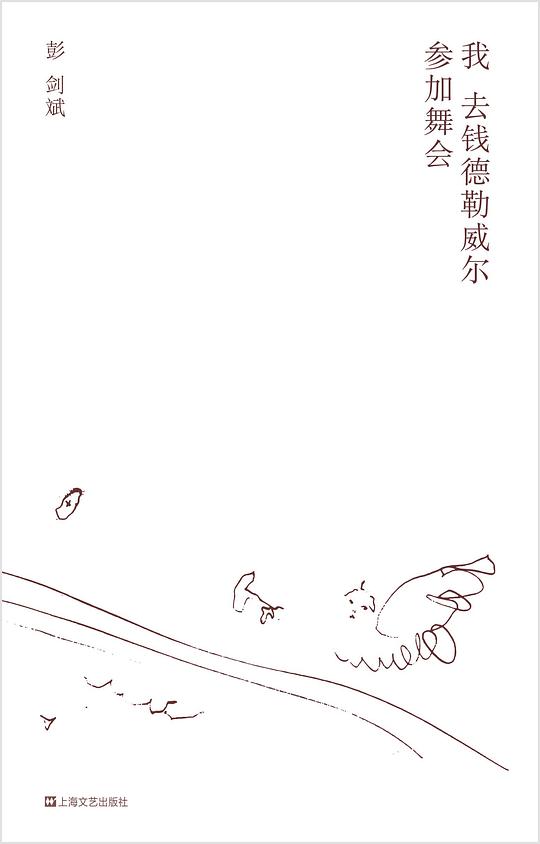
《我去钱德勒威尔参加舞会》继月快评:机器·人
书名:我去钱德勒威尔参加舞会
1
0

开讲啦 2023-05-05 12:00:27
虽然《继月》在描写宁静田园和疯狂幻想之间形成了对比,但令我印象深刻的却是小说中出现的三次“机器人”:
“继月跟个机器人似的洗完红薯、茄子和辣椒。”
“她的男人也是,像个机器人,专挑重活来干。”
“她耐着性子,仔细地——像个机器人——把所有要洗的东西都洗干净了。”
这个词的出现在充满自然主义的描绘中显得格格不入。这些机器人般的存在就像继月箩筐里那两只熟透的烂桃子,她拿不定主意,自己不想吃,喂给猪还怕噎死它们。它们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机关,带来情绪上的波动,与平稳的氛围不协调,如同“刚才看到两个红薯沉下去,她心里被揪了一下似的。”
然而,随之而来的烦恼和不安反而消除了机械式劳作的外在形象,物品的内心波动打破了机器人的外壳,并展现了继月的某种人性。即便这种内部幻想充满了暴力和死亡,透露出继月眼中(想象中)乡人的嫉妒和觊觎,以及相邻地区的仇恨和争吵,还有乡村生活的危险和脆弱。
这种想象也许在一定程度上是真实的,但其中也存在夸大的幻想成分,因为她的水井是村里的男人砌成的,并通过挖坑埋管引来蓄积的水;她家附近的鱼塘也是村民们加固填平的,乡里人不仅有仇恨,也有协作。继月家的土地是被围着的,她的大门是“她从外面锁上的”,她的迫害妄想症随着与男人不断地机械式劳作而扩大,同时也对外封闭得紧紧的,就像一个机器拒绝“人”的存在。
在结尾幻想高潮的部分,彭剑斌再次使用了叙事视角上的硬切,由继月和“她”的第三人称转变为“我的”和“我男人”的第一人称。这让读者更能感同身受到继月而在外部旁观中,她始终像一个机器一样地劳作。
相关推荐
萤火谷的梦想家
艾莉森•麦吉出生于1960年,是美国《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同时也是大都会州立大学创意写作课的教授。她的作品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并出版,也曾被提名普利策奖,并获得苏斯博士奖金奖、克里斯托弗图书奖、美国 [美]艾莉森•麦吉/[美]克里斯托弗•丹尼斯/绘 2023-03-27 16:50:25鬼马女神捕1·绝密卧底(上)
腹黑凤凰vs毒舌鸡妖——蓝翎:“小姬,跟我去人界吧!”姬十四:“干吗?让人宰了我做小鸡炖蘑菇吗?”蓝翎:“不啊,让妖怪宰了你做小鸡炖蘑菇更气派。”凤凰蓝翎和鸡妖姬十四生活在无忧无虑的灵界。他们的故乡叫 郝天晓 2023-04-17 00:22:47© 2023-2025 百科书库. All Rights Reserved.












发表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