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夜樱与四季:变与不变
书名:夜樱与四季
1
0

狂野小蛮妻 2023-09-08 16:21:51
8月19日,《夜樱与四季》新书分享会举办在上海举办。作者张玲玲以及责编张诗扬现场对谈。以下为经整理后对谈内容。 张诗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变与不变——张玲玲小说集《夜樱与四季》新书分享会”,我是上海文艺社的编辑张诗扬,也是本书的责编,是今天活动的主持人。请允许我向大家介绍这本书的作者张玲玲。 张玲玲是一位出生于1986年的江苏籍小说家,今天我们分享的这本《夜樱与四季》是她第二本小说集。这本书自从今年四月出版以来已经入选过七个含金量很高的文学榜单,包括中华读书报月度好书榜、2023刀锋图书夏季榜等。其中《中华读书报》对于本书的评价是,“虽然只是她的第二本小说集,却显示出作者相当从容的文字把控能力”,“写的是与时代同步的故事和人物,却并无这个时代很多文学作品易见的浮躁和刻意,张玲玲的写作经由这本小说集朝着更清晰的路径而去。”在我看来,这不仅是对于一个青年小说家的相当高的评价,而且也是相当中肯、客观的评价。 虽然我做编辑从业十余年,但之前一直在北京工作,这还是我第一次参加上海书展,想问问玲玲之前参加过上海书展吗?有没有什么深刻的印象的故事和大家分享一下。 张玲玲:我记得上海书展是从2004年开始的,国际书展是从2011年开始的,迄今大概有十八、十九届了,我之前读过新闻,据说有的读者收集过全部的门票。 我第一次参加书展是在2017年前后,刚入职公司的第二还是第三天,我被派来看书展。当时已经是最后几天,现场七零八落的,我绕过那些纸板、木条等等,找到了那个版权人,也非常凑巧,后来她成为了我《夜樱与四季》这本书首发式的嘉宾。 2019年出第一本书时,因为出版时间问题,未能赶上;20、21、22我也没出新作,无法参与,只知道21年的活动有所延期,22年规模较大。所以作为三年疫情后的第一个书展,加之首次采取电子票等措施,总体感觉是人极多,票极难抢,让你一度联想起上海国际电影节的盛景。甚至会让你产生一种错觉:阅读的黄金时代已经到来了。第二,这是我第一次以作者的身份参加书展,从读者到作者是一次重要的转换,是一个从客体到主体的转换,就像你是女性,一个被书写者,开始执笔,去叙述自身的故事一样。 张诗扬:那咱们两个人今天真的是“菜鸟搭档”,我是第一次作为编辑参加书展,你是第一次作为作者参加书展。 我之前没有在上海生活过,我在上海旅游时就会一直很注意展览中心地标,因为有很美丽的金顶,我有一个很喜欢玩的电子游戏叫《最后生还者》,那个游戏里面要想解密就要去找各种有金顶的建筑,进到那里面就会触发事件。当时我看到上海展览中心的金顶,就很想能进去,我觉得这里面可以触发很有意思的事情。今天终于从一个观看者的角度走到这个金顶下面。那么我们看一看今天的分享会能触发什么东西。 我首先大致介绍一下这本书,《夜樱与四季》是一本小说集,里面收录了七个体量差不多长的小说,最长的一篇是四万字,其他的是差不多在两万字左右,一共十五万字,是张玲玲第二本小说集。主要书写的是2010-2020年代之间,和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很接近的一些故事。 它的一个特点在于主要是描写在形形色色不同城市和纬度之间行走的漂泊者,就好像我原来在北方,然后现在到南方,会出现纬度的变化,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事情,可能你今天在北京工作,下一刻就在广东工作。 这本书尤其吸引我的地方是它非常丰沛的女性情感,能够感受到充满生命力的女性情感,它会扑面而来,这是张玲玲情感的体现。但是与这个情感相对应的是她很理智、冷静的部分,这本书不是讨论爱情,讨论的是情和爱的话题,讨论的是情和爱这样的东西在经历时间时必然会面对残酷的检验过程。也许我们今天很相爱,三个月后怎么样?三年后怎么样?我对你的爱,你对我的情,三十年后怎么样?这必然会有一个消散的过程。 这个书的名字叫《夜樱与四季》,取的是这本书篇头和篇尾的两个篇名,这本书的打头篇叫《夜樱》,尾篇叫《四季歌》。评论家黄德海在评论本书时说:“最后这本书会有一点点像散落一地的樱花,是一本离散之书。”这个离散是怎么造成的,其实就是时间造成的。 张玲玲自己描述这本书时讲过一段很美的话,我在此复述一遍,她说:“它是空间之书,也是时间之书;是自我之书,也是他者之书;是真实之书,也是虚幻之书;是希望之书,也是失望之书。”大家由此可以看到她的语言中是非常美而且具有哲学性的。现在我想问一下,这本书里你为什么选择去书写2010-2020年这个当下的时间段?在构思的时候是怎么考虑的? 张玲玲:第一本小说集《嫉妒》写的是1997-2017之间的故事,当时我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写作存在这样的特性,亦即习惯于将故事的时间拉到最近。譬如小说集的最后一篇完稿于2019年3月,故事时间已经写到了2018年;新的小说集也一样,最后一篇完稿于2022年4月,故事时间写到了2020年夏,也就是疫情中部。 为什么这么去写?从很多层面来说,太近的经验一般都不建议纳入写作,因为一切尚未定型,经验还需沉淀后使用。我很明白这点,但我还是这么做了。一开始是种无意识的选择,但隔了几年之后,你仍然采取相似的叙述策略,甚至不想、不愿去修正,那可能说明这跟你的主题之间存在着莫大的关系。因为从许多层面来说,第二本书其实是对第一本书的修正,如语言、调性、结构、笔法等等,但某些部分还是固执地保存下来了,所以我也不禁问自己,为什么? 小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从最广义的层面来说,我们或许可以说,它是一个故事,经典的故事结构包括了起承转合,合即结局。但我最大感受是,很多时候,我能给的仅是一个阶段性结局,只是故事在这里,必须要收场了,落下了,但人物的结局还远未到来。譬如《嫉妒》(收录于小说集《嫉妒》)的最后,许静仪遇到了顾睿,俩人开始热恋,但对于自己的历史,她说“什么也没发生”,这可能会对将来留下一定隐患;譬如《似是故人来》(收录于小说集《嫉妒》)里,姜洁和伍家豪在深圳大吵一架后,断联了一段时间,在回不回广东之间莫衷一是。收拾行李的晚上,姜洁忽然打来电话,先读了些战争史料,说了一些姚子青的事,然后才说,她忘不了他,最后又说,天地那么大,总容得下一对自私而不道德的男女苟活,是不是?家豪笑了,没做回答,那个故事即终结在此。 好吧,浪漫爱情小说的结局总是将两人在一起作为结局,无论是告白、婚姻或是长期同居,但我们都知道,爱情的变故如此之多,人的变化如此之快,关系几乎随时都在逆转。谁能说,当代生活里,在一起或是婚姻就是故事的终局?它仅仅是一个开始。故事仍在行进。 我的想象和阅读经验可以帮我处理比我个人生命更久远的时间,或者做一些关系和人的推演。但我更在意此刻和长期的真实观察。也就说是,以我个人视角、个体经验所展开的对当代的持续性观察,我很好奇人物在面对这些当代的变动时,又会做出何种选择?我经常不时问自己:17年之后的许静仪和谷雪她们到底如何了?那对自嘲为自私而不道德的男女,其关系又持续了多久?如果在一起,又会面临何种问题?如何分开,又遇到了什么样的人呢?又是几年过去了,你进入了青中年,有了更多复杂的体验,你的人物也顺理成章地进入了新的时间,新的阶段,面对新的问题。这种疑问构成了许多篇目的动力。它不同于写续篇。这是抽出来的生命体验。他们和你同行。 我的人物很多都保持着对历史的强烈关注,我想这是我自己的一种投射。我不认为对于所有人来说,历史和过去是必要性的,对于普通人或者多数人来说,历史无足轻重,过去的业已过去。在我们的中式哲学里,遗忘和往前看是比追溯更普遍的生存法则。也许因为我们的苦难史和创伤史太长,也许因为历史和记忆频频被纂改、伪造,也许还有别的。总之,这绝非多数人的选择。 但我自己很难接受这样的处境。身处浮岛,看不清前后路,这令我恐慌。我想知道今天为什么是今天,此刻又何以变成此刻,我想知道时间带来了什么又改变或摧毁了什么。所以必须一次次看向过去,深究每一个错误,并从中发现可用的部分。我必须看向过去,如此才能对将来形成某种参照。我必须书写这十年,二十年,因为这是我亲历的时间;我必须书写,否则此刻就会迅速滑过,消散,被历史化或什么也留不下来。我渴望书写的不仅是外部的景观,还有人之内部,不止于轮廓,还有蕴藏在心的部分,恐惧、希望和失意。我记得世纪末的情绪,也记得世纪初的情绪,记得那些朦胧、热切的希望,记得那些希望如何慢慢变冷,变得伤感。然后又是新的希望,新的毁坏。有时候构成所谓时代感的,正是这些东西:情绪。 张诗扬:我觉得刚才玲玲讲的一个意思非常好,两个人在一起,这看起来是一个结局,但其实只是一个开始——两人在一起之后又能怎样。我觉得从文本外部来看的话,张玲玲有两个特点,第一是现实主义,其次是关注对近距离当下的书写。但刚才你解释为什么要这么写的时候,让我觉得更加理解了你。因为你要展开的是对当代的阶段性观察。 你刚才说到第一本书《嫉妒》与《夜樱与四季》的不同是,前者主要是书写的青年时代的故事,我借此也想问您一个比较私人的问题。我和玲玲是21年认识的,所以我们两人是在35岁之后才相互认识的同龄人,我不是很了解你的青年时代,所以你能讲一讲你二十多岁时候的事情吗?也就是《夜樱与四季》这本书里所涉及到的2010-2020年之间你过着怎样的生活。 张玲玲:说起10到20年,正好是我人生最重要的十年。我大学学的是汉语言文学,本来应该08年毕业,结果因为羽毛球挂科,且屡考不中,不得不延期了一年。那段时间其他人都在准备考公、考研或是找工作,我却闲散在那,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当时的男友便帮忙在报社找了拉广告的工作,但前提是必须离开上海去杭州。我便去了。在广告部我主要负责发传真和打电话。后来有天读了胡舒立和程益中的报道,心想,这才是我要做的事情。 我在他们身上看见的是这个时代罕缺的理想主义特质,我看见了写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强力地作用于现实。这对一个年轻人来说是有着强烈的吸引力的。但内部转岗并不容易,尤其是从非采编岗到采编。我不好意思和主编说我想写稿,能写稿,因为事实上你就是不会。我买了些新闻写作书开始自学,但没有实践,也无章法,学得乱七八糟的。当时财经记者什么专业都有:公共卫生管理、海洋物理、财务会计等等,还有轧钢专业,我对行业门槛就有些摸不准。后来社里搞征文大赛,我就去了,得了三等奖。拿奖时,副总编问我有什么心愿,我就说我想去采编,他就开了口,把我调了过去。尽管大部分时间是负责整理录音或是写生活类副刊,但内心很振奋。有了正式写稿的机会就更高兴了。2010年到2012年是我最快乐的阶段,因为一直在路上,一直在做报道。我只是没想到这个阶段会持续地那么短,没有想到自己赶上的,已经是纸媒最后的黄金时代。13年之后,情况开始发生改变,危机是全方位的,有内部也有外部的原因。报社做了许多尝试,以谋求转型,其一就包括投资及开设影视公司。我就这样离开了采编,在集团内部做了一个编剧。此时已是2016年。 编剧这活儿我干得很烂,但时间还算充沛。我发表了第一个小说,但仍然没想过自己可以通过写作生活。17年之后,我回到了上海,开始做版权,之后的三年,基本维持着相同的节奏,也即,白天上班,晚上写稿。直到2020年7月辞职,开始了全职写作的生活。 张诗扬:张玲玲是一个对写作这件事怀有热望的人,在《夜樱与四季》的后记中她曾经写到:“很难说清为什么小说对我有着持续不绝的吸引,我对小说的兴趣和期望远大于我对自己人生的兴趣和期望。”这本书我们在6月21日夏至日那天开过一个首发式,在首发式上,你坚定地判断自己不是文艺青年,写的也不是文艺青年的小说,也提及在做新闻的时候被告知,做工业品比做理想品更重要的,因为理想品是不着边际的,但是工业品是一个有迹可循的东西。她说这个观点影响了她之后的职业生涯和小说写作,我觉得你可以顺着刚才的这个问题讲一讲,你可以谈一谈你的新闻生涯对你的影响吗? 张玲玲:新闻生涯对我有很多影响,但在写作方面,可能也没我们以为的那么大。我们常常从工作履历谈起,因为那是解释自己或他人最简便的方式。你无法解释自己,能拿出的,很多时候只有履历。我现在已经彻底失业了,所以有些忘了找工作或是工作时期的艰难,忘记了很长时间里面,工作曾是自己人生里最重要的构成。你一无所有,唯有工作。我经常看着这样一个女性:漂在异地,无根无据,她急切地想寻找一个抓手,但抬眼望去,要么是工作,要么是感情,而感情往往表现为婚姻、家庭或是长期同居关系。后者在今天被否定的次数更多,所以更多时候,工作成了我们的首选。你做了,但仍有强烈的缺失感。你仍然要不断追问自己是谁,喜欢什么,要做什么。这个问题极其难以回答。这些追问甚至会动摇你的生存信念和人生信念,但如果不看清,我们都不过是一份职业、一段情感,一个人或者观念的附庸而已。 至于为什么说我不是一个文艺青年,我倒不是不爱读书,但兴趣就集中在小说领域,其他方面,如音乐、绘画、艺术等都懂得较少。文青应该包括着更广泛的文艺兴趣吧? 张诗扬:而且你是中文系的呀。 张玲玲:读中文系也并不说明就热爱文艺。上学第一天,你会发现班上只有四个男生,四个男生都告诉你,他们不喜欢文学,他们是第一志愿落选后被调剂过来的。班上很多人都是因为调剂才来到了中文系,文学是他们的次选乃至末选。第二个,尽管如此,中文系还是有许多才女,她们都很会读,很会写,你很容易就能看清自己是没有才华的类型,这导致大学时期的写作尝试基本是偷偷摸摸进行的;第三,当时盛行一时的论坛写作或是地下写作群体我都没参与或是接触过。我没有参与过文青生活。 文艺青年最大特质应该是浪漫吧?但今天的生活是反浪漫主义而推实用主义的。我们谈论情感价值,探讨某种关系有益而另一种关系无益时,其实背后已经包括了一套理性的、实用的、商品化的考量。我觉得今天很多人都在或者尝试用这套方式思考,或出于风险规避,或出于其他。这是一套通行的思维模式。浪漫反而是特异的。我本质上仍然想写的是当代的普遍性。我笔下的女孩可能很多都支持或认同这样的思维模式,她们拒绝认定自己是非理性、不实际的,但她们却陷在某些痛苦里无法自拔,并以这样的痛苦为耻。小说作者会喜欢这样的反差:你以为自己是一个实用主义者时,内心却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你口口声声号称自己是一个文艺青年,但最喜欢的事情却是赚钱,我想这种内外反差及冲突或许比声称什么更为重要。 张诗扬:我再问你一个比较私人的问题。你刚才讲到了自己之前的工作经历,一开始在新闻业工作,之后进了影视业,大家也知道在过去一些年影视业有多疯,热钱有多多,直白来讲,你并不是没有见过钱,也不是没有经历过实用主义的思考,但是现在你是辞职出来做全职写作。所谓全职写作就是没有工作单位,没有体制,就靠稿费。作为图书编辑,我是很知道纯文学职业写作的个中冷暖的。那么你为什么要做出这个选择?这个选择之后,生活给你带来的报偿或者代价是什么? 张玲玲:如果我说,除了写之外,想不出其他生存方式呢?你可以工作、结婚、生育,你可以和其他人一样,做着事情,但你仍然感觉不到自己活着。 我很难谈论所谓牺牲和代价。任何事情都有其代价。我被愿望引到此地,无非如此。或许我周围人付出更多。一个家庭里面出现一个作者并不什么好事,很长时间里,她一无所出,精力都在另一个世界,哪怕真的有天写出什么,家里的受益也很有限。我有时的自我隔绝,也是一种保护。至于报偿,我觉得我比之前高兴了很多。写作本身就让我极为愉悦,极其感激。这个愿望持续了那么长时间,今天终于可以去一点点实现了。 张诗扬:现在咱们来回到一下本次活动的题目。今天我们活动的题目是“我们的变与不变”,这个题目是张玲玲拟的,可不可以请你解一下题,你认为何者为“变”,何者为“不变”? 张玲玲:我觉得我没取好标题……我到早了,提前了两个小时,便坐在柱子旁边看书,有书展读者经过,默念了一下标题,立马落荒而逃。我忍不住思考这个标题确实没起好,没什么吸引力,也不知道你想说什么。 我们先说变化吧。流行说法是,人心不变。但是其实人是在变化的。人会被物质性的东西改变,却以为天然如此。今天在书展,我买了本二手书,叫做《感悟婚变》,出版于2000年,我翻了翻,觉得很有趣,于是买了下来。这里有大量的离异女性访谈,今天去阅读,你会发现大家的心态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维系不再成为一个重要目标,婚姻失败也不再被视为人生失败了。这个看法是过时的、守旧的,但在当时,却一度如此盛行。 以我相对熟悉的女性写作领域好了,我们再看古典通俗小说,或者民国迄今的一些文本,或者一些十八十九世纪的小说,已很难产生共鸣,我们很难想象,我们的生存目标或人生意义会以一个男性、一段婚姻为参照系。这或许构成了我们当代的写作动力。如果经典文本已说出了我们的全部,创造有何必要?我们写了又写,无非是我们仍不满足,我们仍感到倍感愤怒。我们的心灵仍然饥渴而焦灼,准备说出什么,说我们读到的、被写出的还不够,永远不够:不够深、不够确切、不够复杂。人的心灵就像宇宙边界一样,它会膨胀,变化。它是一点点被塑造、被发现的。 不变的或许是某一个人,在很长时间内,不会发生太大变化。我们喜欢顿悟时刻,喜欢人因启示而改,实际上若非重大变故,仍然不会有根底性改变。我小说里写的是你自以为顿悟的时刻,《洄游》的小马就是如此,结尾他似乎存在着一种转变的可能,但他其实没有什么改变。包括在《奥德赛之妻》里面,戏剧导演萧鼐在妻子生病之前,一直在频频出轨,妻子生病之后,他循规蹈矩了一段时间,但新的可能性出现,他还是会重返旧路。许多小说的结尾都昭示着人在历经了重大事件后,仍无可挽回地倒向旧路。启示并未发生。 张诗扬:你之前在首发式上也谈到,流动现代性是你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而且你进一步指出,这种流变并不光是外部的,比如从北京到上海的变动,也是内部的,是和自我对峙的时刻,是自我被否定的时刻。《夜樱与四季》这本书的后记中有一段话很有意思,我看了之后愣了半天,她写的是:“实际上,我应该写一个故事,关于一个作者跑来跑去,寻找自己的根系和主题,一个人跑来跑去,寻找自己的定居之地,但我没能完成,写不出因为这不完全真实,真实就是她和她都失败了,就像今天的讲述一样。”这种对过去自我的否定,这种“她和她的失败”,在你看来具体指的是什么? 张玲玲:所谓否定,我原先以为这是一个自我发现,后来前段时间重读约翰·威廉斯的《奥古斯都》时,发现了类似的句子: 人是多么自相矛盾的动物,自己拒绝或抛弃的偏偏至为珍惜!选择以战争为职业的士兵,打仗的时候渴望和平,太平无事的时候又渴望短兵交接与混乱的喋血战场;奴隶希望摆脱他未曾选择的奴役,凭借勤奋而赎买了自由,却依附了一个比旧主人更冷酷苛刻的主顾;抛弃情妇的爱人,在他终生不泯的幻梦中想象着她的完美。 这里已经进入了小说的第三章节,写作的威廉斯,和做如下思考的奥古斯都,都已步入人生的晚年,但我很年轻时就有了这样的启悟,是从自己、周围人身上观察得来的。发现愿望会被另一个愿望替代,认清自己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 所谓的“她和她”,第一个“她”指的是过去的我,第二个“她”就是写小说的我,就是写后记的我,我理解诗扬当时说,“写个后记,谈谈过去几年”,其实希望看见的是一个故事,但是当时我没写出来,我仍然在说理、说理、说理,整个后记的书写过程成了我过去几年的写作甚至人生的隐喻,也即,一封书信没有抵达目的,它在中途就已经偏移。成功,如果我们以广义的定义,就是你实现了预期,所谓失败,也就是我们没有完成目的,甚至在中途,发现标的也散佚。 编辑:余梓宏 (原文链接:https://appimg.allcitysz.com/template/displayTemplatev1/dist/index.html#/newsDetail/797569/83?isShare=true)
相关推荐
萤火谷的梦想家
艾莉森•麦吉出生于1960年,是美国《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同时也是大都会州立大学创意写作课的教授。她的作品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并出版,也曾被提名普利策奖,并获得苏斯博士奖金奖、克里斯托弗图书奖、美国 [美]艾莉森•麦吉/[美]克里斯托弗•丹尼斯/绘 2023-03-27 16:50:25鬼马女神捕1·绝密卧底(上)
腹黑凤凰vs毒舌鸡妖——蓝翎:“小姬,跟我去人界吧!”姬十四:“干吗?让人宰了我做小鸡炖蘑菇吗?”蓝翎:“不啊,让妖怪宰了你做小鸡炖蘑菇更气派。”凤凰蓝翎和鸡妖姬十四生活在无忧无虑的灵界。他们的故乡叫 郝天晓 2023-04-17 00:22:47© 2023-2025 百科书库. All Rights Reserv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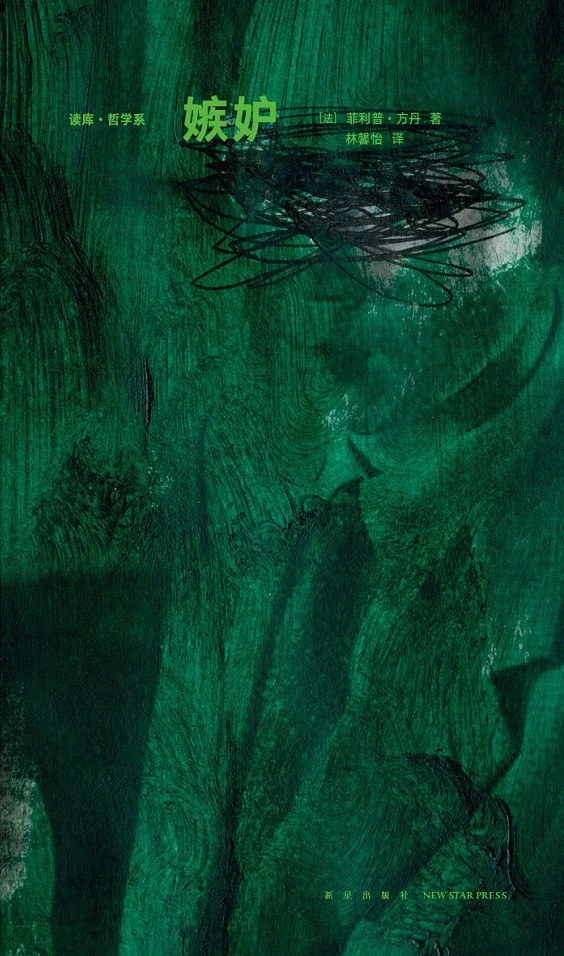









发表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