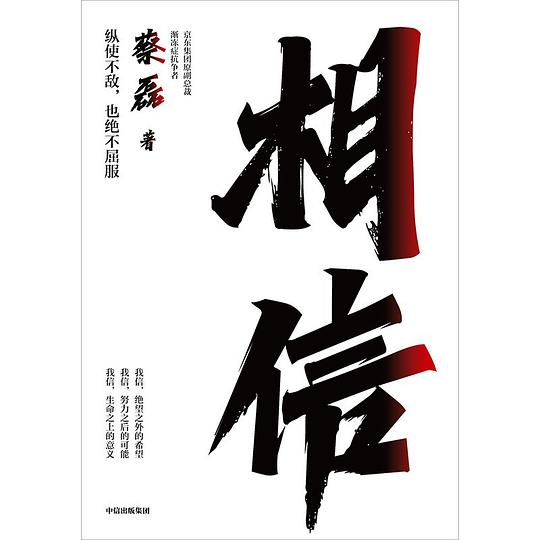
《相信》西西弗斯的信念:脚踩祥云
书名:相信
1
0

神秘之门 2023-08-31 22:54:18
1. 其实我很少看站内推荐作品,因为那会让自己感觉太low了。这本《相信》的名字也不算很吸引人,直到我看到了介绍中“京东总裁”+“渐冻症”+“创业”,这真正吸引了我。而字数也没有很多,我打开了它,然后放出了一个“脚踩祥云的西西弗斯”。
2. 从我短暂的临床试验职业生涯来看,罕见病绝对是临床试验设计中属于皇冠上的明珠,一切都是因为——罕见!因为罕见,患者甚至在死亡前可能都不清楚自己患病的原因;因为罕见,多数临床医生往往一辈子都亲眼见不到某种疾病的病例,或者说是见到但是没有办法给ta下诊断;因为罕见,多数病例虽然症状七七八八,却不得不归为同一类,而这造成了这些疾病的流行病学极其难明确;因为罕见,所以从药企的角度判断,研发药物从研发到上市再到专利期过期的时间内的利润空间极低;因为罕见,在临床试验设计时候没有办法做安慰剂对照,只能从以往的数据库中找到零星几个;因为罕见,所以就算到了患者死亡,ta也许都在进行各种的土方或者偏方的治疗,可能会加快他们的死亡;因为罕见,ta们可能从患病开始就要经历“拒绝”和“埋怨”的阶段到最后(不要啊!为什么偏偏是我呢)因为罕见……
3. 看到了蔡磊的这个故事,我想起了最近我们正在设计的一款药物的开发策略。药物机制是线粒体DNA,也就是只要是线粒体基因疾病,就可能有效,而我们针对的适应症选择了早衰。早衰是一种在罕见病中很“常见”的疾病,部分患者的疾病分形也很清晰:线粒体基因变异。另外,国外也已经开发了一个相同靶点的药物。可以说,由于有这么多信息,实际这个药物开发难度还算降低了不少,但就算这样,我们面对的实际设计困难还是很大。比如,所有的罕见病药物都是以最终的生存率不过类似于渐冻症,患者不是患病后就迅速死亡,而是慢慢地成为一个“老人”,这里面可能有个缓慢和加速发病的阶段。用什么来作为疗效的判定标准最合适非常难定义。
4. 国内的政策也不够重视,并未对罕见病的药物研发有很好的推动作用,比如2018年版的罕见病指南只有118种罕见病,那对于想研发这个目录之外的罕见病,岂不是难上加难了吗这点上蔡磊的作用真实可信,而且也确实需要这样的人多多出面才可以。我在6月苏州的DIA年会上因为要设计罕见病药物,真的遇到了另外一个“蔡磊”:魏云舒,一个罕见病患儿的妈妈,罕见病患者联盟的发起人之一。她的故事让我相信:这个世界,是由人的信念驱动的。而且,我觉得,当时如果我看过这本蔡磊的书的话,我不光会与魏云舒交流经验,而且一定会去现场找蔡磊,因为我知道:他一定会在现场为自己的基金、为自己管线结果的发表、为找到新的靶点而激情演说。
5. 我不清楚自己在“面对疾风吧”时是否能够和蔡磊有相同的心境,但从同龄的我的过去来看,也许我会和他做相同的事吧。换一个角度来想,我是不是可以从现在做起假设自己就是某个罕见病患者或者罕见病患者家属呢这种向死而生的思考,可能才是决定人生高度的时刻吧。我不知道康德、海德格尔、凯廓尔和加缪是不是也是在这种时刻才意识到人生意义的,但我清楚陈天桥、张朝阳、霍金以及《相信》书中的各个渐冻症患者,都是因为这一刻改变了自己的人生。从此或至暗仇视或从容赴死,世界再无彩虹,只剩黑白。
6. 作为斗战胜佛,孙悟空其实最初只是个顽劣童子,直到被压在五行山下五百年,他才知道自己的晦暗,自己空有拆天之力,也无法挣脱身上的小小五指,只是因为那个
相关推荐
基金
这本书用编年史的方式呈现了中国基金业2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它分为九章,以关键事件为节点,描述了从基金业制度建设、改革开放到创新探索等方面的发展历史。作者采访了很多关键人物,为读者提供了更多的事件背景和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2023-03-23 23:24:36货币从哪里来?
货币对我们的生活、金融稳定和货币政策的效果都至关重要。但是,普通人对货币是如何被创造和分配的、中央银行是否能精准调控货币供应量以及商业银行在货币创造中的作用还存在很多疑问和争议。本书以“货币是如何被创 [英]乔希·瑞安-柯林斯/[英]理查德·沃纳/[英]安德鲁·杰克逊/[英]托尼·格里纳姆 2023-03-22 15:12:51股市趋势技术分析(原书第10版)
中国平安的顶尖翻译团队为我们带来了史上最佳的中文译本。近70年来,《股市趋势技术分析》一直是技术分析领域中的佼佼者。1948年首版问世,现在已经更新到第10版,仍然是技术分析领域最重要的原创著作。本书 罗伯特D.爱德华兹/约翰·迈吉/W.H.C.巴塞蒂 2023-03-22 22:49:12赢得输家的游戏
你想战胜市场吗?你想击败85%的投资者吗?你想财富最大化吗?对于那些希望在股市中长期获利的投资者来说,本书是一本值得信赖的指南。被“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称为“迄今为止关于投资策略和投资管理的最 (美) 查尔斯•埃利斯(CharlesD.Ellis) 2023-04-02 01:27:30投资最重要的三个问题
许多投资者把投资看作一项手艺或技能,他们认为经过良好的训练、付出足够的努力、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之后,便能成为优秀的投资者。然而,在肯•费雪的这本经典投资畅销书中,投资大师以自己近四十年的投资经验 肯•费雪/劳拉•霍夫曼斯/珍妮弗•周 2023-04-02 01:28:47营销管理(第16版)
《营销管理》(第16版)是世界领先的营销学权威之一,由西北大学凯洛格管理学院国际市场营销杰出教授(荣誉教授)菲利普·科特勒编写而成。这本书已经连续畅销全球55年,被翻译成了20多种语言,被誉为“营销圣 菲利普·科特勒/凯文•莱恩•凯勒/亚历山大·切尔内夫 2023-03-24 03:11:35© 2023-2025 百科书库. All Rights Reserv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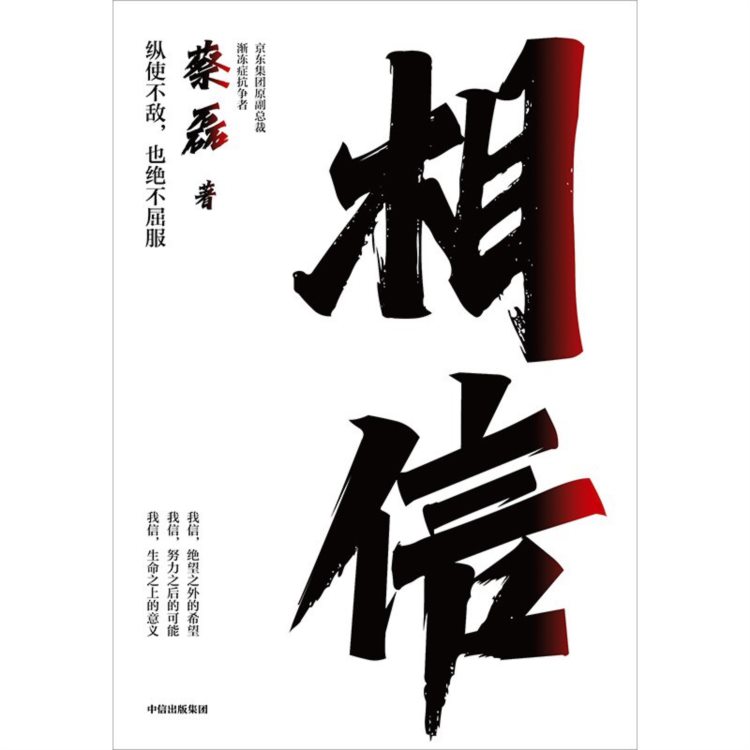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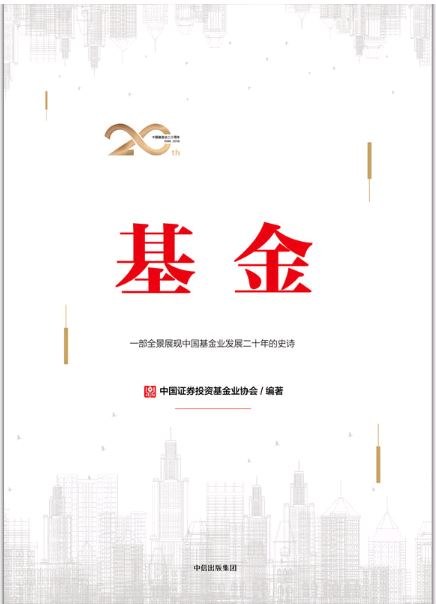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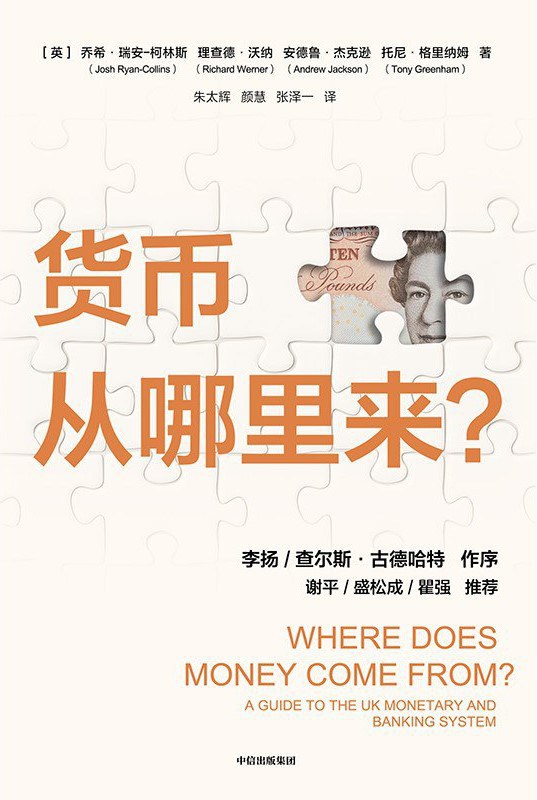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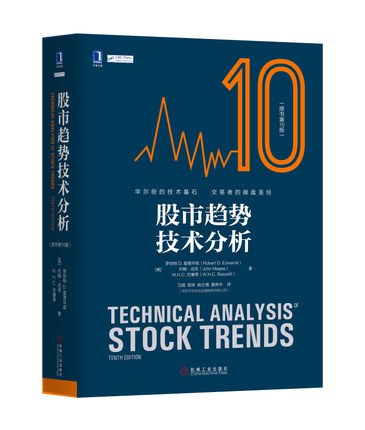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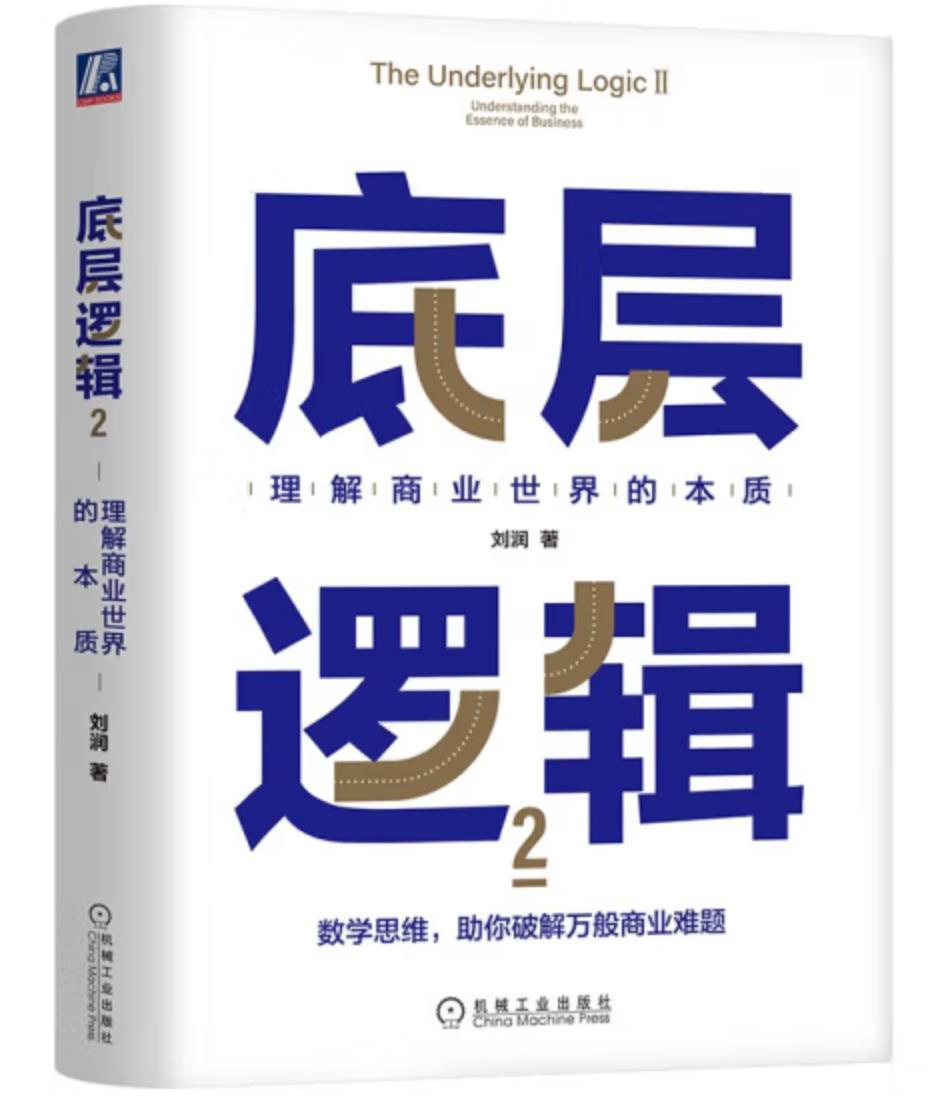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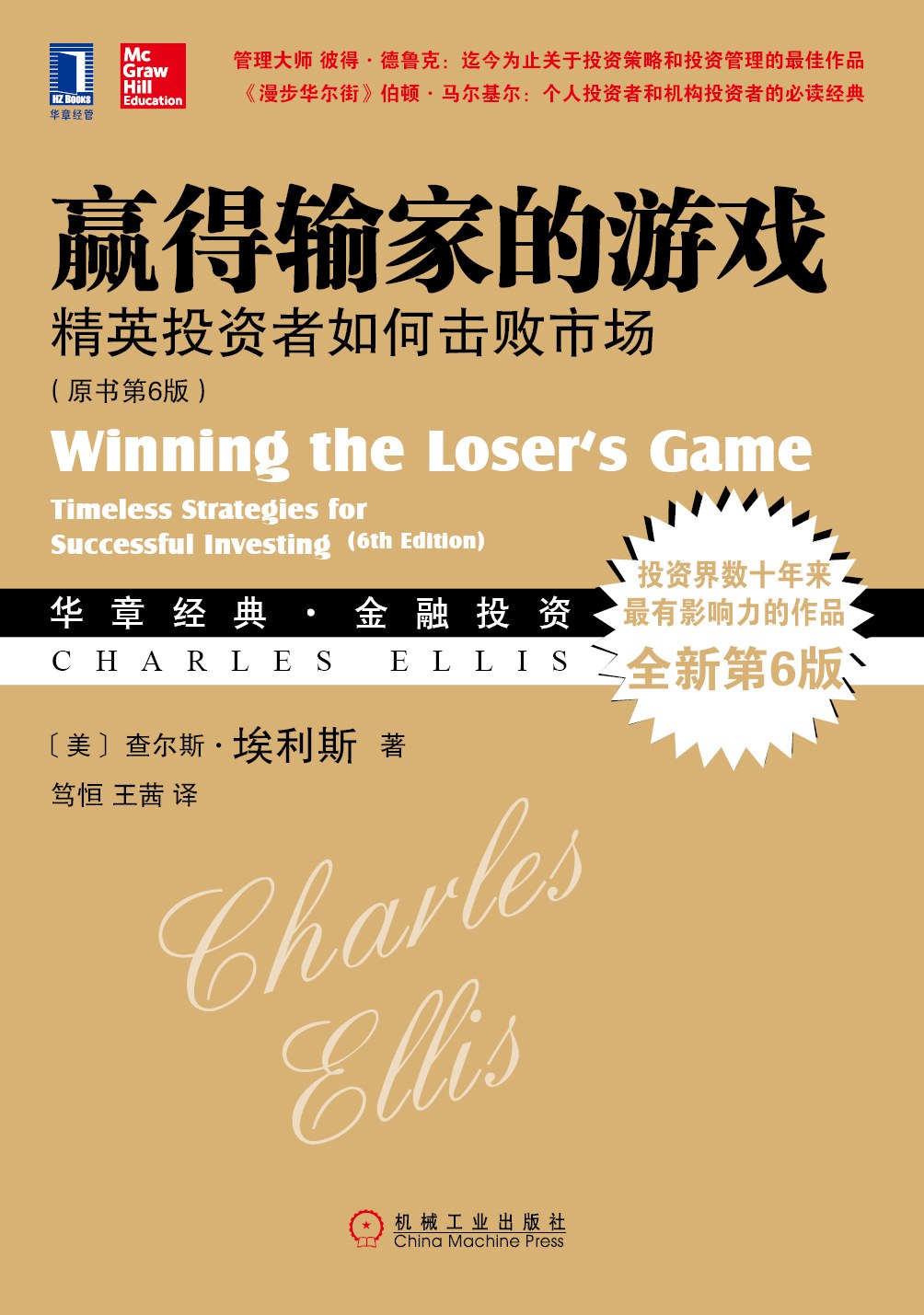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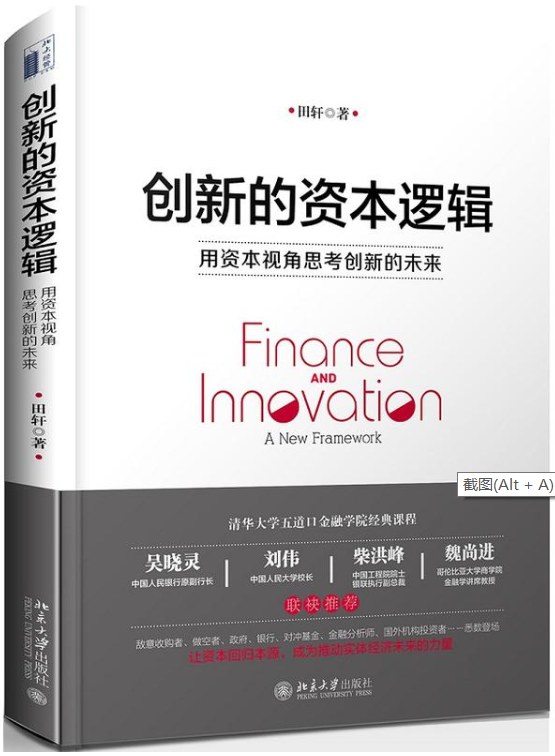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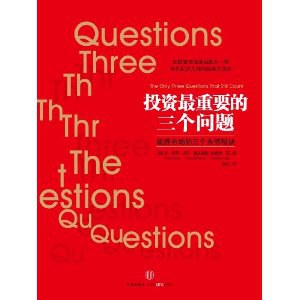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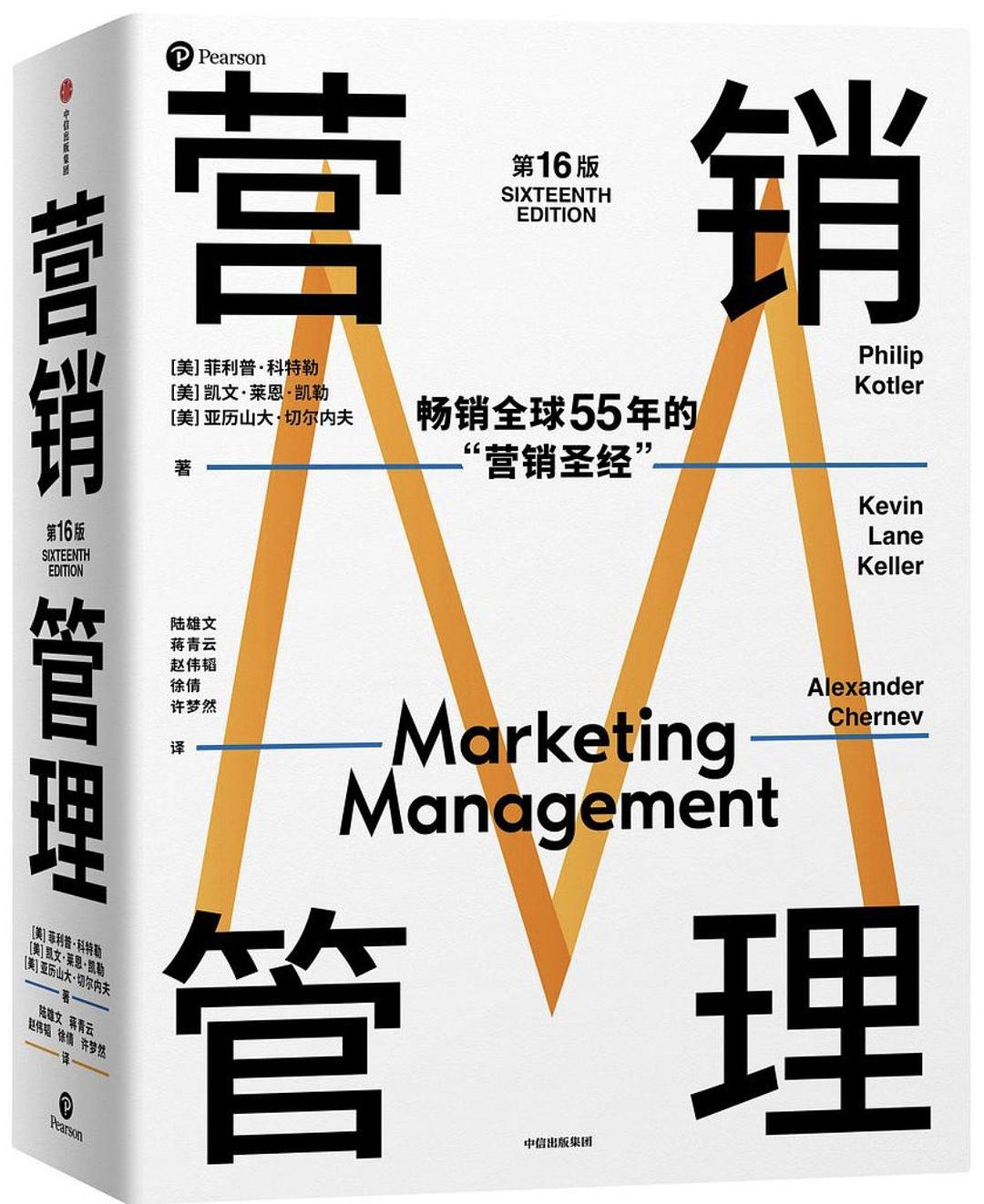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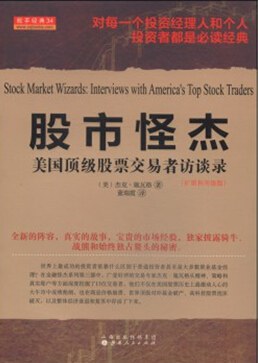
发表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