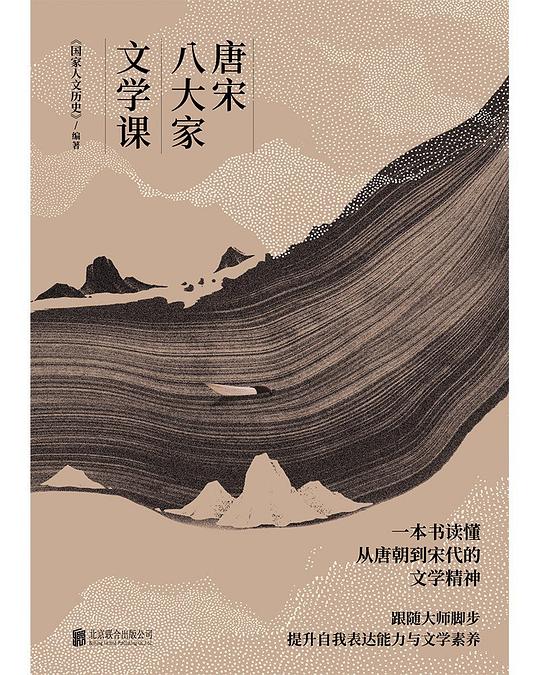
《唐宋八大家文学课》黄儋唐宋八家文学,问你平生黄州惠州惠丰儋州成就
书名:唐宋八大家文学课
1
0

霍比特人 2023-08-27 08:59:47
李思达在《唐宋八大家文学课》这本书中关于“苏轼”的部分介绍道:苏轼酷爱夜游,在黄州有两次赤壁夜游,而到了江西又同儿子一起乘月色泛舟夜游石钟山写下《石钟山记》。此时的苏轼已经摆脱了黄州时的迷茫和痛苦,昔日文章中的道家意境早已消散,取而代之又是儒家“格物致知”之意了。
绍圣四年(1097),朝廷对元祐党人再度进行了整肃,贬于内地的被统统发配到了岭南,而早在岭南的苏轼也就只能漂洋过海,责授琼州昌化军安置。
如此巨大的人生打击,不可能不触及苏轼的人生观。他渡大庾岭“鬼门关”时,思想发生了巨变:“一念失垢污,身心洞清净。浩然天地间,惟我独也正”(《过大庾岭》)。正是在惠州、儋州六年的流放,苏轼埋葬了过去的垢污,真正以“游于自然”“忘情物我”的态度新生,此等精神境界,可以说是佛家的“心无挂碍”,也可以说是道家的“轻去就脱生死",还可以说是儒家“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真正从痛苦中脱胎换骨,融释儒道为一体的苏轼,对人生有了新的感悟,而他此时期所写的各类小品文,往往都是寥寥几句,就能让人咀嚼再三,感悟良多。贬居惠州时,苏轼曾信步出游松风亭,有所感悟,顺手写下了113字的《记游松风亭》。挂钩之鱼乃苏轼最喜譬喻之一,从小到大每当焦虑之时他便会想到此语。
然而到了今天,他已找出降服自己心中焦虑的良法--“当恁么时也不妨熟歇”。人生宛如负重远行,功名利禄犹如远处的亭台楼阁,若是一味盯着此处焦虑“如何得到”,那便是“进则死敌,退则死法”的绝境,换个活法。元符二年(1099),苏轼已经被贬到海南,上元夜再度夜游,成就一篇短小隽永的《书上元夜游》。苏轼依然获得了“放杖而笑”的快乐。这种快乐既非《超然台记》的故作欢乐,亦非《前赤壁赋》中借助无穷无尽的江月寄托之乐,乃发自内心的恬然之乐。此时,就连上钩之鱼也变得无所谓。
对苏轼来说,人生在于体验,逆境也好,顺境也好,只要内心安乐,何处都可以是自己的理想乡。此番豁达心态更体现在他的《试笔自书》中。建中靖国元年(1101),在被流放烟瘴岭南七年之后,苏轼终于获得赦免。在生命的最后一年,他依旧步履匆匆,一路沿江西入赣水,越鄱阳湖而入长江,顺流而下东行至金陵(今江苏南京)、金山,抵达了生命的终焉之地,他最喜欢的城市之一--常州。
一路北上,已经是六十六岁老人的苏轼陆续听到了各种消息:章惇被贬岭南雷州(今广东雷州);元祐年间的同侪也多半死于贬所,其中就包括“苏门四学士”中同他感情最深厚、思想最契合的秦观。时至今日,只剩风烛残年的他侥幸生还,那些热腾腾的事业、闹哄哄的争论,正如一场梦幻泡影。途经镇江金山时,苏轼写下一首绝句:“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千年以后,变法党争已只是印在历史书上的一段前尘往事。而苏轼这位智者在黄州、惠州、儋州写下的文章,却超越了时间,如江水与皓月般永被传颂,鲜活地存在于孩子们的诵读声里。
相关推荐
逆天的冒险
我们是天生的冒险家,对冒险的爱从不会离开我们,直到我们迈入垂老之年。”博莱索写道。他认为,“胆小的老头子,在他们的兴趣当中,冒险应该是绝灭了的。”这也是为什么诗人们偏爱冒险,而法律通常是老年人制定的原 (南非)威廉·博莱索 2023-04-10 05:12:26© 2023-2025 百科书库. All Rights Reserv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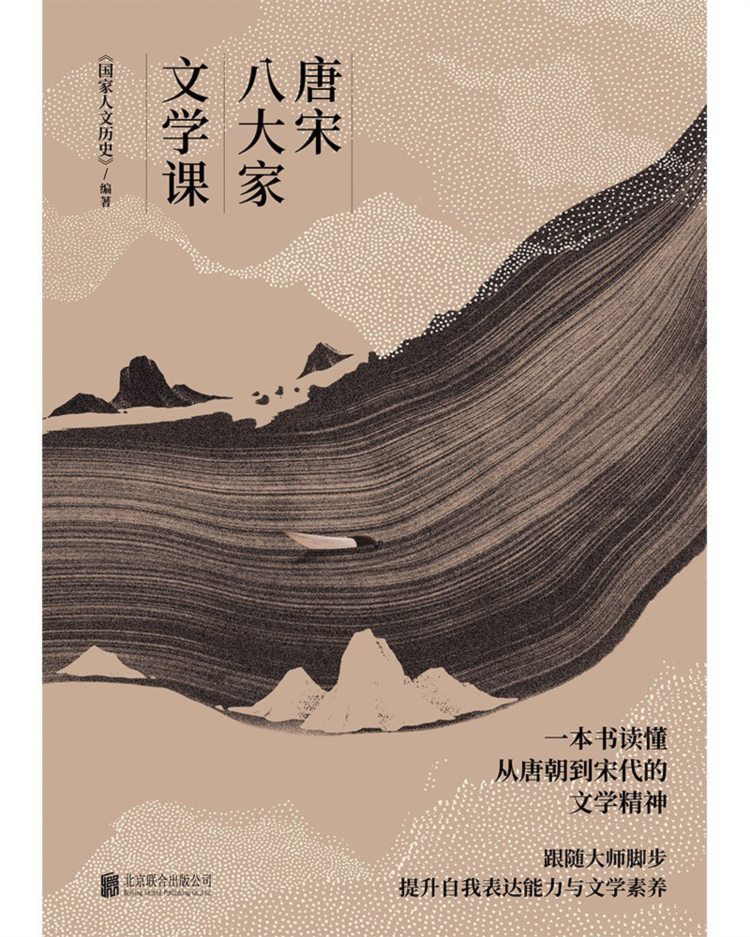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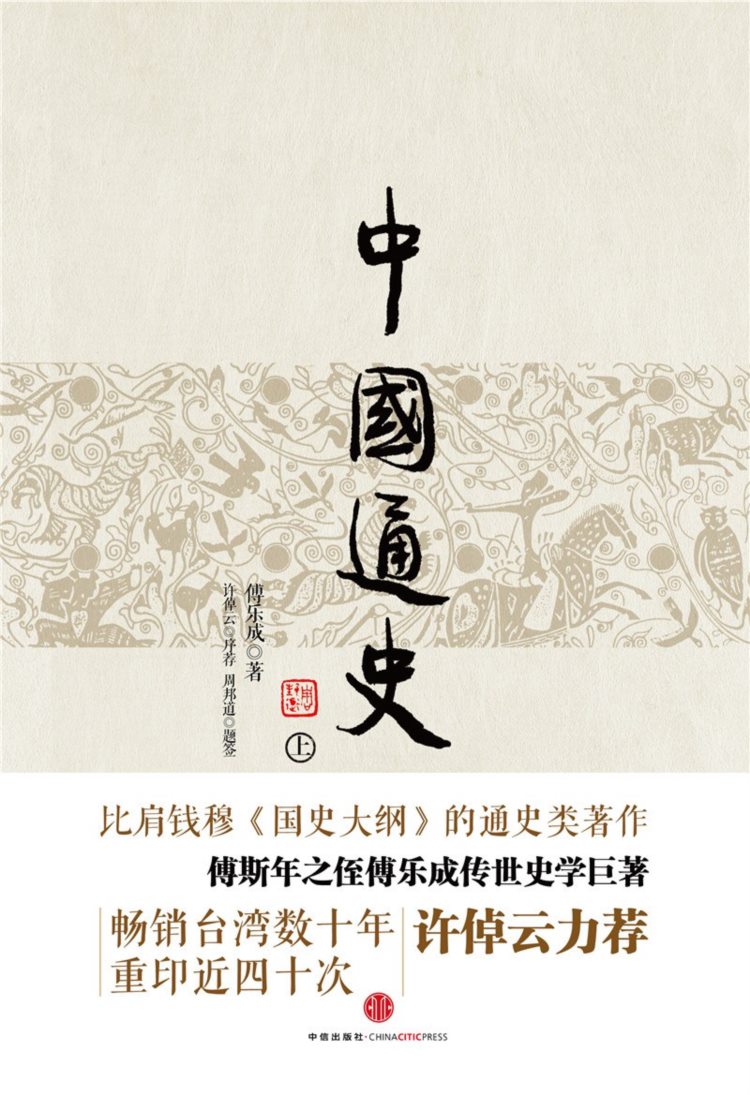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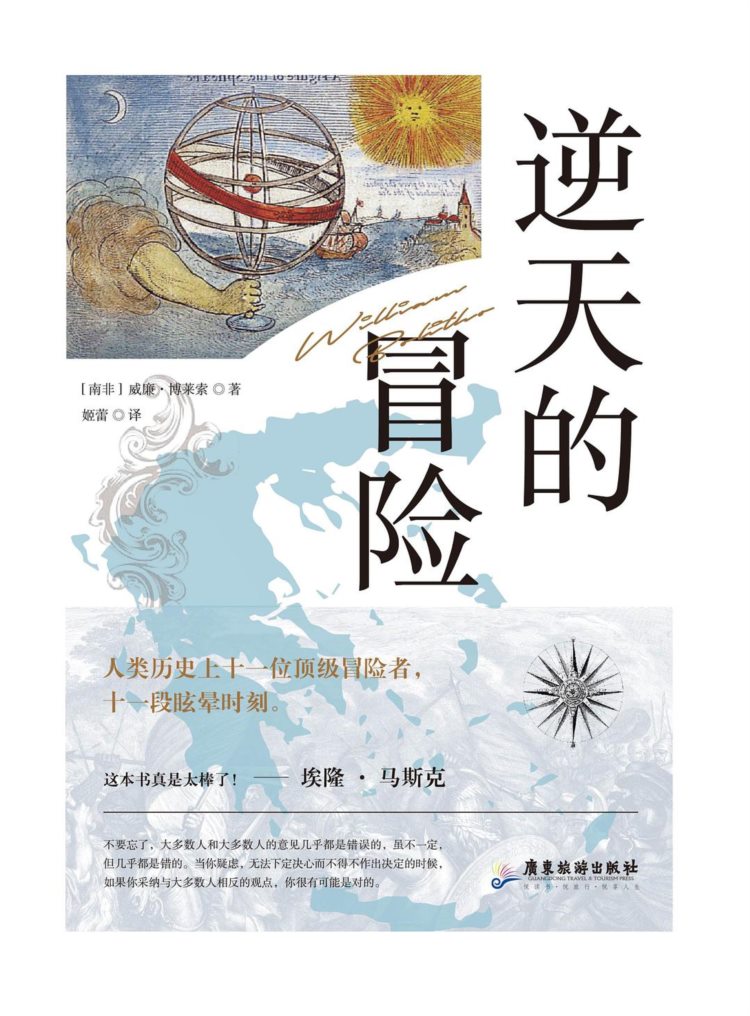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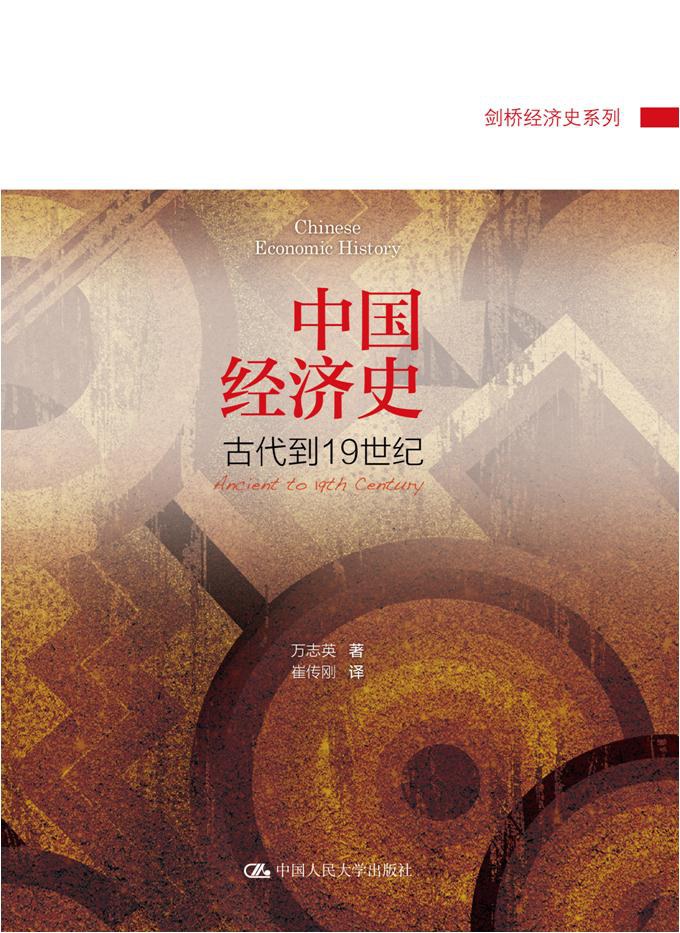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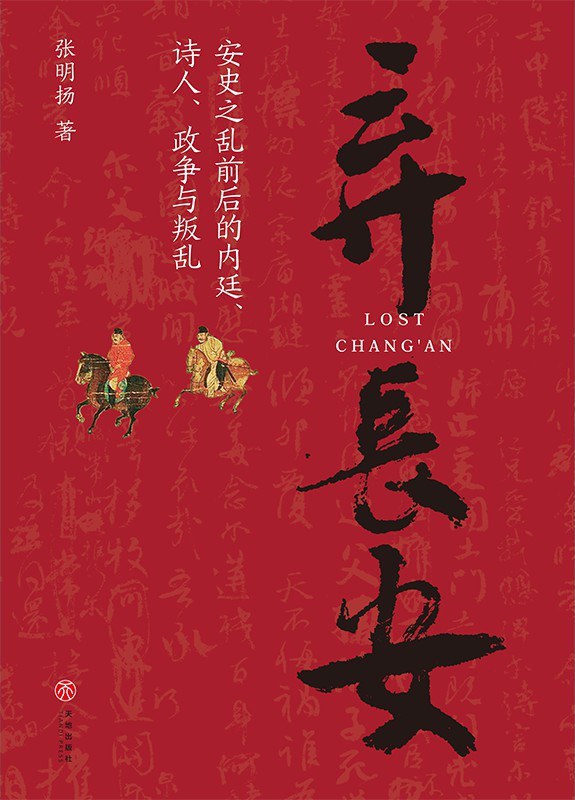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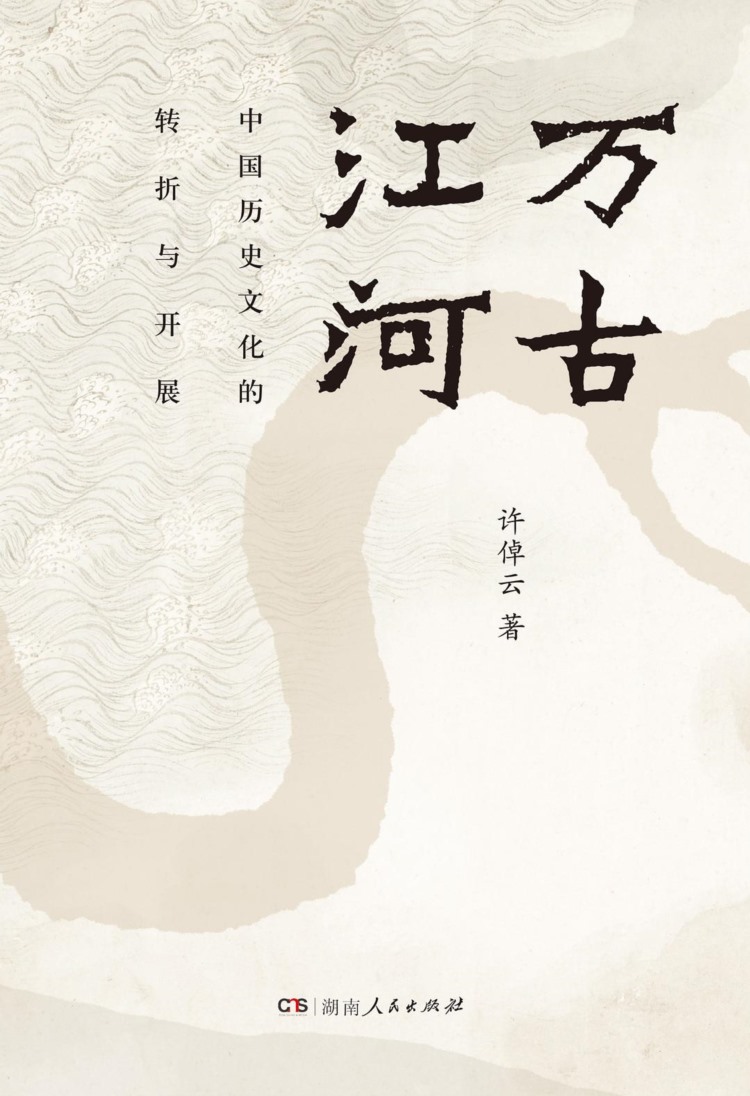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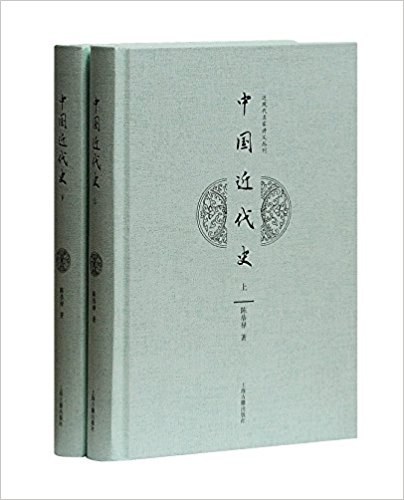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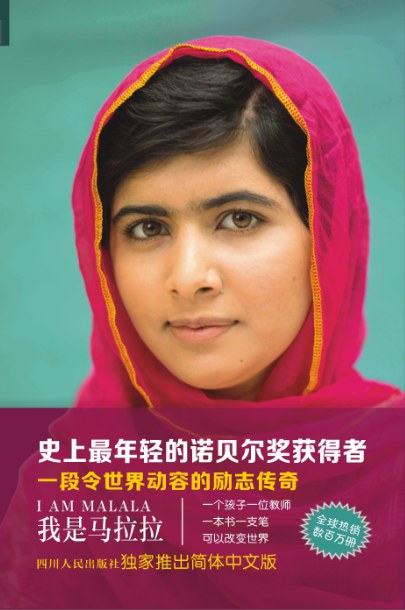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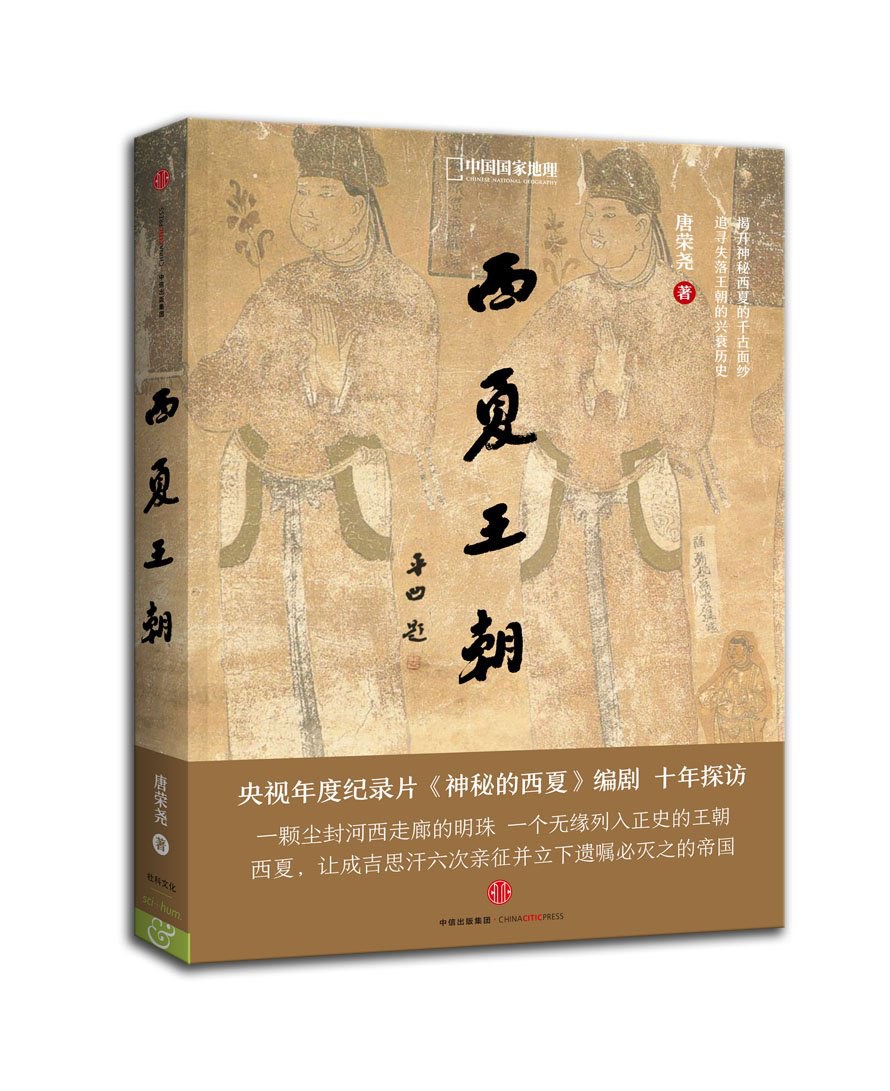
发表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