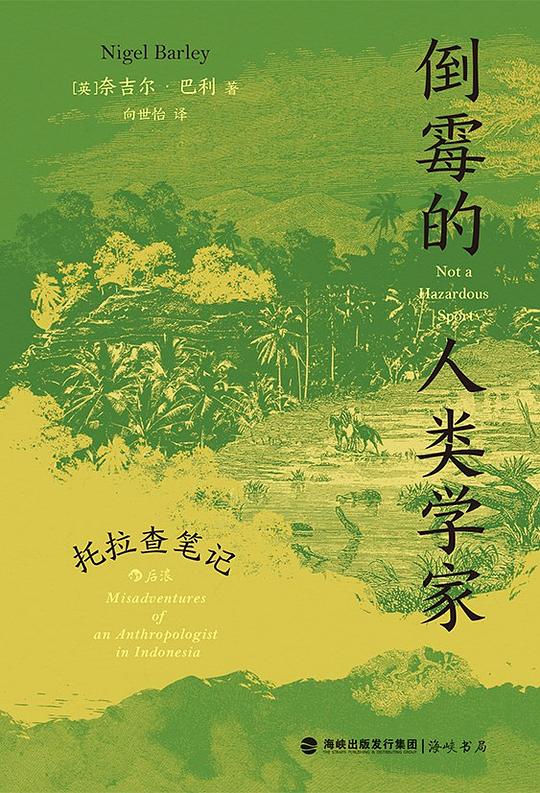
《倒霉的人类学家》搞笑不是巴利的本职工作!
书名:倒霉的人类学家
1
0

独孤求败 2023-08-26 19:29:47
英国人类学家奈吉尔·巴利的《天真的人类学家》堪称人类学门类下的畅销读物。这得归功于巴利的英式幽默,他以金色的润滑剂为只身进入异域的恐惧、忧虑、烦闷、无聊和偶发惊奇添加了一抹色彩。《倒霉的人类学家》是巴利离开非洲喀麦隆后的第二站“田野”。和《天真的人类学家》一样,巴利更倾向于接近马林诺夫斯基严格意义上的日记,而非保罗·拉比诺的高调《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然而,奈吉尔·巴利的作品质量似乎被低估了——在那些“只是笑一笑”的幽默背后,他以更深刻、更隽永的方式融入了作品的结构和意象,悄悄地触动了读者的内心。
让我们来看看《倒霉的人类学家》的结构。整本书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去苏拉威西”,占据全书一半篇幅;第二部分是“偶尔在苏拉威西”,约占五分之一;第三部分是“在伦敦”,约占六分之一。回过头来看书名,“Not a Hazardous Sport: Misadventures of an Anthropologist in Indonesia”(直译为“不是一项危险运动:一位人类学家在印度尼西亚的不幸遭遇”),我们不清楚书名是先有还是内容是先有,但它们无疑是相辅相成的。重点不在于揭示苏拉威西的托拉查人有什么神秘的习俗、深邃的宗教或独特的仪式,而在于人类学家再次踏上了他倒霉但最终得以回归的旅程。
从这个角度来看,《倒霉的人类学家》(就像《天真的人类学家》一样)仍然是一部关于“人类学家”的民族志。巴利不会将其称为“自我民族志”,那是一种以讲述者、书写者个人为研究对象的新兴方式。相反,巴利将他在印度尼西亚和英国的个人经历清晰地提升到了白人人类学家的层次,更进一步说,是(1980年代)西方文明主导下的现代化和现代人的层次。
因此,巴利在印度尼西亚各大城镇艰难度日的时光,最终以秩序转换的隐喻结束:抛弃警察,拥抱乡民;离开现代秩序,走向高山世界。这种旅程显然十分艰难,汽车无法把我们带回传统世界,就像乡村巴士带走了童年的玩伴和神仙。问题不在于汽车开向何处、停在何处,而是一旦“汽车”出现,它就不会再消失。巴利看到年轻的约翰内斯愿意学习托拉查传统雕刻手艺,并且展现出天赋。他曾希望约翰内斯能继承一系列的文化习俗,甚至成为当地传统宗教的祭司。然而,约翰内斯抓住了与英国人类学家交流的机会,最终成为一名讲英语的外交官。这是本书最黑色的幽默,也是人类学的全部奥秘所在。
相关推荐
萤火谷的梦想家
艾莉森•麦吉出生于1960年,是美国《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同时也是大都会州立大学创意写作课的教授。她的作品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并出版,也曾被提名普利策奖,并获得苏斯博士奖金奖、克里斯托弗图书奖、美国 [美]艾莉森•麦吉/[美]克里斯托弗•丹尼斯/绘 2023-03-27 16:50:25鬼马女神捕1·绝密卧底(上)
腹黑凤凰vs毒舌鸡妖——蓝翎:“小姬,跟我去人界吧!”姬十四:“干吗?让人宰了我做小鸡炖蘑菇吗?”蓝翎:“不啊,让妖怪宰了你做小鸡炖蘑菇更气派。”凤凰蓝翎和鸡妖姬十四生活在无忧无虑的灵界。他们的故乡叫 郝天晓 2023-04-17 00:22:47© 2023-2025 百科书库. All Rights Reserved.












发表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