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字》“探索姓名之谜”
书名:名字
1
0

狩猎者 2023-08-22 11:22:44
在唐·德里罗的小说《名字》中,名字被视为一种符号,命名则代表了一种权力。然而,在美国的文化霸权下,希腊的政治和经济受到严密的控制和干扰,甚至失去了对本国文化的"命名权",这导致了一群狂热的信徒将希望寄托在古老符号之上,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方式 "跃入永恒"。只有当一个社会的流浪者的名字的首字母与某个地方的名称的首字母相同时,这个流浪者才能够到达"应许之地",而只有通过血腥和死亡,才能给名字背后的意义奉献祭品......
邪教组织的凶杀理由看起来荒诞而不合逻辑,但实际上是对美国文化霸权的模仿,因为这些理由驱使他们的原因是政治的荒诞和沉重,美国的强权政治本身也没有其合理性。凶杀的本质就像是加缪的戏剧《卡利古拉》中卡利古拉那骇人听闻的荒诞暴政一样,卡利古拉通过最直接、最裸露、最血腥的方式展示了命运的无常和世界的荒诞,最终引起了民众的反抗并与荒诞对抗。《名字》中的邪教成员也试图用凶杀这种极端的方式来争夺"命名权",从而对抗政治的荒诞。没有比卡利古拉痛苦的独白更能概括他们的心境了:"这种盯住自己一生的人的孤独,这种不受惩罚的凶手的乐趣,这种把人的生命毁灭的无情逻辑,这就是幸福"。
《名字》中存在着两条叙事线索:明线是"我"对邪教凶杀案的追踪;暗线则逐渐揭示了美国霸权主义对希腊人民方方面面的"后殖民"统治。小说的叙事与拉康的"三界理论"——现实界、想象界、象征界相呼应,呈现了"结构的重复"的特点。表层结构是"被害者——我——邪教",展现了邪教成员对被害者的凶杀;深层结构是"雅典——我——美国",展现了美国对雅典人民的微观权力压迫。"我"在这两个层面的结构中都是旁观者,但同时又显示出某种无知:"我"始终没有和邪教建立更深入的联系,也始终不了解公司和中情局的勾结。邪教的凶杀是对美国压迫行为的模仿,这两个事件的重点都是争夺"命名权",构成了重复的结构。在这两个事件中,三种不同的行为主体展现出三种不同的凝视:被害者和雅典人处于现实界,他们的凝视是无知的凝视,是完全看不到的凝视;"我"处于想象界,他的凝视是被现实界所欺骗的凝视,是一种幻觉;而邪教和美国则处于象征界,他们的凝视是见到现实与想象界所未见之秘密的凝视,是一种无所不在的目光。
在巧妙的叙事结构下,小说展示了这样一个场景:政治权力话语下的一切事物都在消解。小说开头提到:"有好长一段时间,我都避免去雅典卫城"。"我"提供的直接理由极具张力:"(雅典卫城)耸立在我面前,强大而威严,几乎逼迫我们对它视而不见,或者至少抵抗它"。这个理由让人难以理解,直到小说结尾,"我"辞去工作并最终登上雅典卫城时,读者才能够理解:政治的沉重赋予了雅典卫城其他意义,雅典人民正被渗透其中的权力话语所蒙蔽,他们丝毫没有感受到自己民族文化的真正含义,也没有面对雅典卫城本身的伟大,而只是感受到一种温和的欺骗。权力话语的规训正在内化,人类正在逐渐变成征服自己本源的对象。
相关推荐
萤火谷的梦想家
艾莉森•麦吉出生于1960年,是美国《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同时也是大都会州立大学创意写作课的教授。她的作品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并出版,也曾被提名普利策奖,并获得苏斯博士奖金奖、克里斯托弗图书奖、美国 [美]艾莉森•麦吉/[美]克里斯托弗•丹尼斯/绘 2023-03-27 16:50:25鬼马女神捕1·绝密卧底(上)
腹黑凤凰vs毒舌鸡妖——蓝翎:“小姬,跟我去人界吧!”姬十四:“干吗?让人宰了我做小鸡炖蘑菇吗?”蓝翎:“不啊,让妖怪宰了你做小鸡炖蘑菇更气派。”凤凰蓝翎和鸡妖姬十四生活在无忧无虑的灵界。他们的故乡叫 郝天晓 2023-04-17 00:22:47© 2023-2025 百科书库. All Rights Reserv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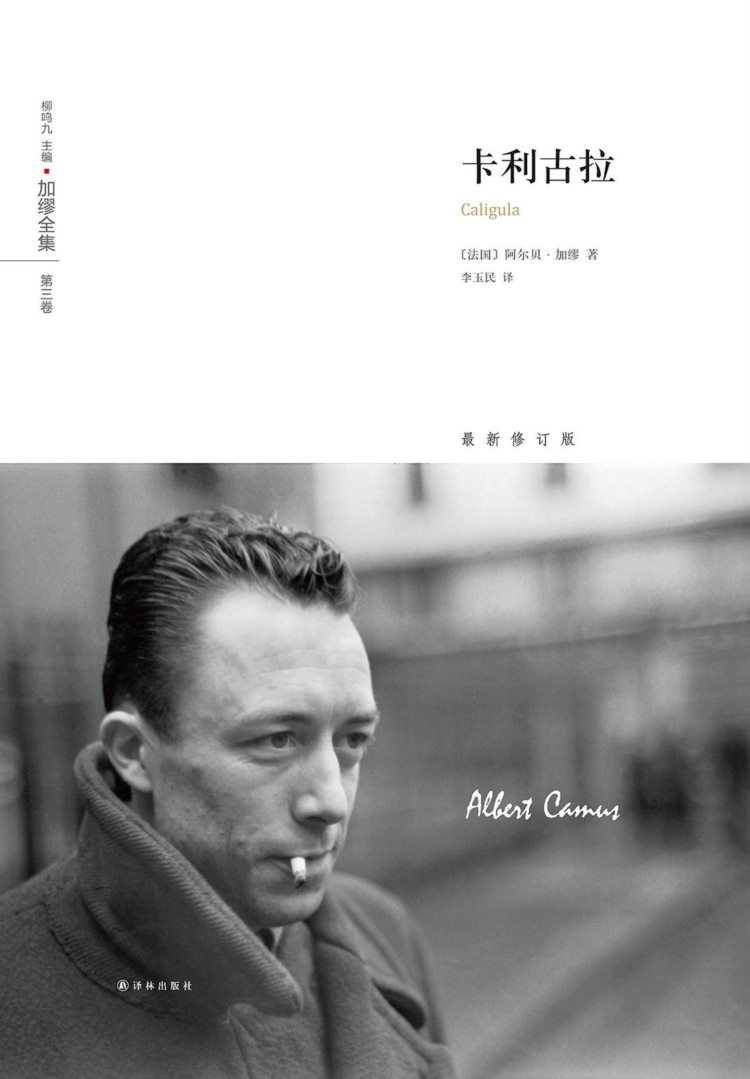









发表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