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绝境必反叛
书名: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
1
0

小懒猪 2023-08-04 03:20:37
《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以其“双线并叙”的结构最令人印象深刻。在文本中,描绘了“冷酷仙境”和“世界尽头”交替出现,但它与一般的交织的平行叙事不同——“世界尽头”是“冷酷仙境”的主人公在生命尽头自我构筑的虚幻乌托邦。
在“冷酷仙境”中,背景是一个高度异化又令人恐惧的东京,其中有计算士、符号士、夜鬼等设定,使得这座城市具有浓厚的Cyberpunk色彩。主人公“我”是博士人体实验的对象,而我和博士的命运则完全系于计算士与符号士两个阵营的对决。在这个过程中,“我”失去了成为纯粹的被支配的客体。
在“我”自我构筑的“世界尽头”中,一切井然有序,乌托邦小镇上的居民们相处和谐,生活宁静平稳。但是,“我”逐渐意识到,这只是秩序下的美化幻象,小镇居民们没有象征着本能与个性的“影子”,也没有象征着情感与人性的“心”。如果所有人都是没有个人特质、没有喜怒哀乐、没有知觉与感情的范式人,生活同样是悲哀的,没有生机。
可能由于小说的荒诞色彩,读这本书时总是会想起王小波的《万寿寺》。如果说王小波用“长安城”来指代“诗意的生活”、以进入长安城来逃离平庸,那么在《世》中,“世界尽头”并不是“冷酷仙境”的理想替代。村上春树更加悲观地认为,科技理性对抗古典理性仍然无法解决后现代的生存危机。因此,主人公最后走到小镇之外,“再也无处可去,亦无处可归”。
当生命无处可逃,反抗或许成为唯一的选择路径。
正如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社会中的艺术》中所说,具有破坏性、无秩序和消极无意义的反传统艺术本身就具有抗议、抵制和拒绝的立场。我认为,当人类被异化为单向度的存在时,反叛的艺术作为文化产品能够消解世界的物质性,增强人的精神性,从而提升人的主体性。
我猜测,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村上春树选择让“世界尽头”的主人公在故事的最后听鲍勃·迪伦(以反抗民谣而知名的歌手)。在鲍勃·迪伦的音乐中,村上构建了与“冷酷仙境”和“世界尽头”不同的另一个空间,一个精神的音乐空间。同时,它也是一个反叛失序、对抗孤独、充满诗意的精神驻地。
相关推荐
萤火谷的梦想家
艾莉森•麦吉出生于1960年,是美国《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同时也是大都会州立大学创意写作课的教授。她的作品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并出版,也曾被提名普利策奖,并获得苏斯博士奖金奖、克里斯托弗图书奖、美国 [美]艾莉森•麦吉/[美]克里斯托弗•丹尼斯/绘 2023-03-27 16:50:25鬼马女神捕1·绝密卧底(上)
腹黑凤凰vs毒舌鸡妖——蓝翎:“小姬,跟我去人界吧!”姬十四:“干吗?让人宰了我做小鸡炖蘑菇吗?”蓝翎:“不啊,让妖怪宰了你做小鸡炖蘑菇更气派。”凤凰蓝翎和鸡妖姬十四生活在无忧无虑的灵界。他们的故乡叫 郝天晓 2023-04-17 00:22:47© 2023-2025 百科书库. All Rights Reserv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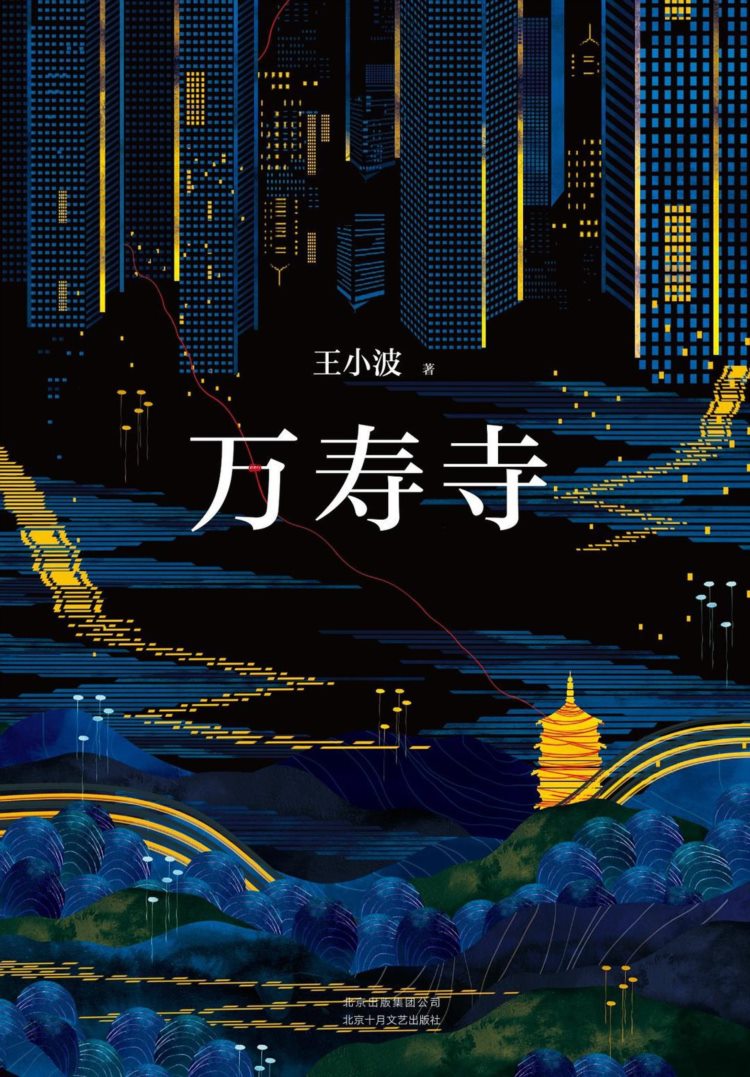








发表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