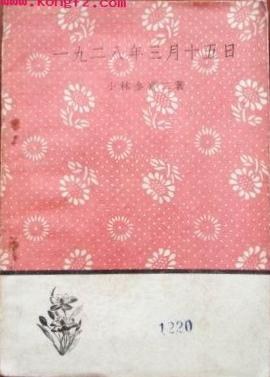
《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流弹破晓,一九二八
书名: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
1
0

酷酷小冰块 2023-07-27 00:23:39
“渡一点也没有想过自己牺牲了什么,没有想过我是在为社会的正义而斗争。只是一种天生的“仇恨心”,很自然地干他所要干的事情。这就是他从心底发出来的感觉,而且他还有坚强的意志。”
“他完全被骇住了,一边穿裤子一边踉踉跄跄的,身子站立不稳了。对于这样惊慌失措的神情,连自己也感到有点儿害羞。但他还是提心吊胆的,生怕隔一道纸壁,外边等着自己的警察的刀子碰撞的声音,会被幸子听到。他知道幸子听到这声音,幸子的“心”就会破碎的。“爸爸要同学校里的人一起出门去哩。”幸子睁开黑油油的大眼睛,向他望着。“你带些什么礼物来送给我呢”他很难过,勉强地说:“好,好,好东西,好多好多的。”幸子一下子把脑袋转到纸壁那边去了。他立刻用两手抱住自己的头。咣的一声,他好像听到瓷器打破的声音。他从心里发出一声惊叫,连忙跑过去打开幸子胸口上的衣服。在葡萄干似的两个乳头中间,一颗像瓷碟一样的心破了。一看,这心上已有了一条头发似的裂痕......”
““妈,你不懂呀。”他半带着哭音吆喝了。“是呀,妈就是不懂你的心思。”母亲畏缩地、怯生生地说。佐多感到厌烦了,就把母亲撂下,走到楼下去了。到了楼下心里还是很难受。就是妈,她折磨我的志气。“想不到母亲倒是我们的敌人。”他心里很激动地想。”
共产主义是一种叙事,凭着仇恨心来做事的渡,为女儿幸子心怀内疚的龙吉,认为母亲落后的佐多,无论他们的激情何在,最终都会被想象的大同世界、现实的阶级敌人以及纷繁的口号和运动包裹起来,捏造一个先锋队的干部,昼出夜伏地做家人们难以理解的事情。只有在禁闭期间,那种想象的世界随着群体(无论是敌人还是同志)的隔离完全被隔离,进入不自觉的冥想与反思状态时才能够露出一点自我。
至今依然记得一个非常经典的论述,“共产主义者认为权力的总量是可以增生的”。运动的主旨是试图用理性的法则去引导无序的原欲,将愤怒、不安、性欲、愧疚都当做子弹射向敌人,可是情感又不会消失,最忠诚的干部也难免跳脱出那些条条框框,权力的总量自然是不会增加的,只是会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内陡然上升,再然后自顾自地消失了。
况且,如果没有敌人的话,原欲是没有办法被引导的,所以革命运动的本质,就算被包装得再崇高,也只不过是拿石子扔自己讨厌的人的游戏。
“总选举的时候,因为撕了敌党候选人的宣传招贴,劳农党必须仔细推出一个人来让警察抓去。渡叫木村去,告诉了他许多应该注意的事情,说:“说不定会挨几下揍,你得好好忍受。”“我不干!”一句话就拒绝了。渡想不到他会这样回答,“啊”反应地叫了一声,就默默地瞅住木村的脸。“我这样干,给警察关上一两天,就没有饭吃了,我不干!”“你对咱们的运动还不明白呀。”“你们当干部的,给警察抓去了,就会更加出名,以后声望更大,我可不同呀。””
如果不被那样的丰富想象力感染的话,就只有做木村这样冷漠又现实的人了。似乎很多人一开始以为自己是渡,即使被打成阿岩脸也不会放弃理想,不久后发现自己其实是木村,顶多理直气壮地说一句“我可不同呀”。
相关推荐
我们的性
《我们的性》,现在是它的第7版,生物、社会心理、行为和文化诸多方面以对个人有意义的方式,对性做出了全面、学术观点鲜明的介绍。我们非常高兴读者对本书前几版一直反应热烈且热心;这些反应激励着我们为你们的学 [美]罗伯特·克鲁克斯(RobertCrooks)/[美]卡拉·鲍尔(KarlaBaur) 2023-05-05 06:31:19即使生命如尘,仍愿岁月如歌
优化后:想要走向自信、尊严的人生,女性可以从工作、家庭、生活等方面入手。本书将通过作者及身边朋友的经验告诉读者,一个女人是否能够实现美好的生活,决定性因素并不在于她的经济状况,而在于她有无勇气不委屈、 晚秋 2023-03-31 07:15:04国际超模的极简瘦身课
这是一本为中国女孩撰写的“易瘦体质”培养指南,作者是一名国际超模李霄雪。李霄雪曾与纽约排名第二的模特经纪公司EliteModelManagement签约,在国际模特界打拼了10年,之后她决定回到中国成 李霄雪 2023-03-31 06:29:24我有一杯酒,可以慰风尘
祝愿你的岁月平静无波澜,同时也希望我的余生不会有太多的悲欢。这里介绍的是关东野客的又一力作,它名为《我有一杯酒,可以慰风尘》,共涵盖13个故事。这些故事或许会让你感到孤独和温暖,也或许会涌起遗憾和美好 关东野客 2023-03-29 19:34:53男人不屌女人不High
男人滿足女人的方法男人必須學習更強猛的知識和工夫進行有效率的「省力性愛」──增強性能力的35個秘法增強膨脹力的30個要領、增強持久力的22個訣竅,以及24個讓女性滿足的能力。白天努力工作晚上生龍活虎不 增田豐 2023-12-04 16:47:42心灵的整饰
“情感社会学”研究领域重要著作《纽约时报》年度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学著作之一荣获“米尔斯奖”“查尔斯·库利奖”等社会学奖项情感变为一种资本要素,这是现代服务业的秘密之一。19世纪的工厂童工提供劳力,20世 (美)阿莉·拉塞尔·霍克希尔德 2023-09-08 11:40:22© 2023-2025 百科书库. All Rights Reserv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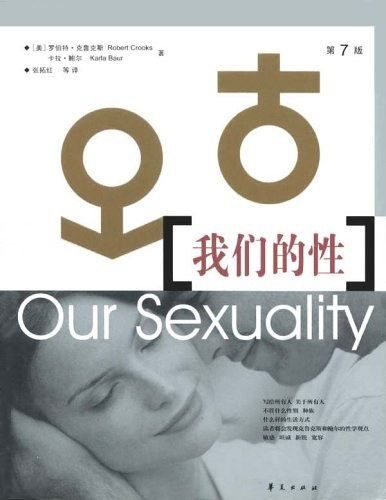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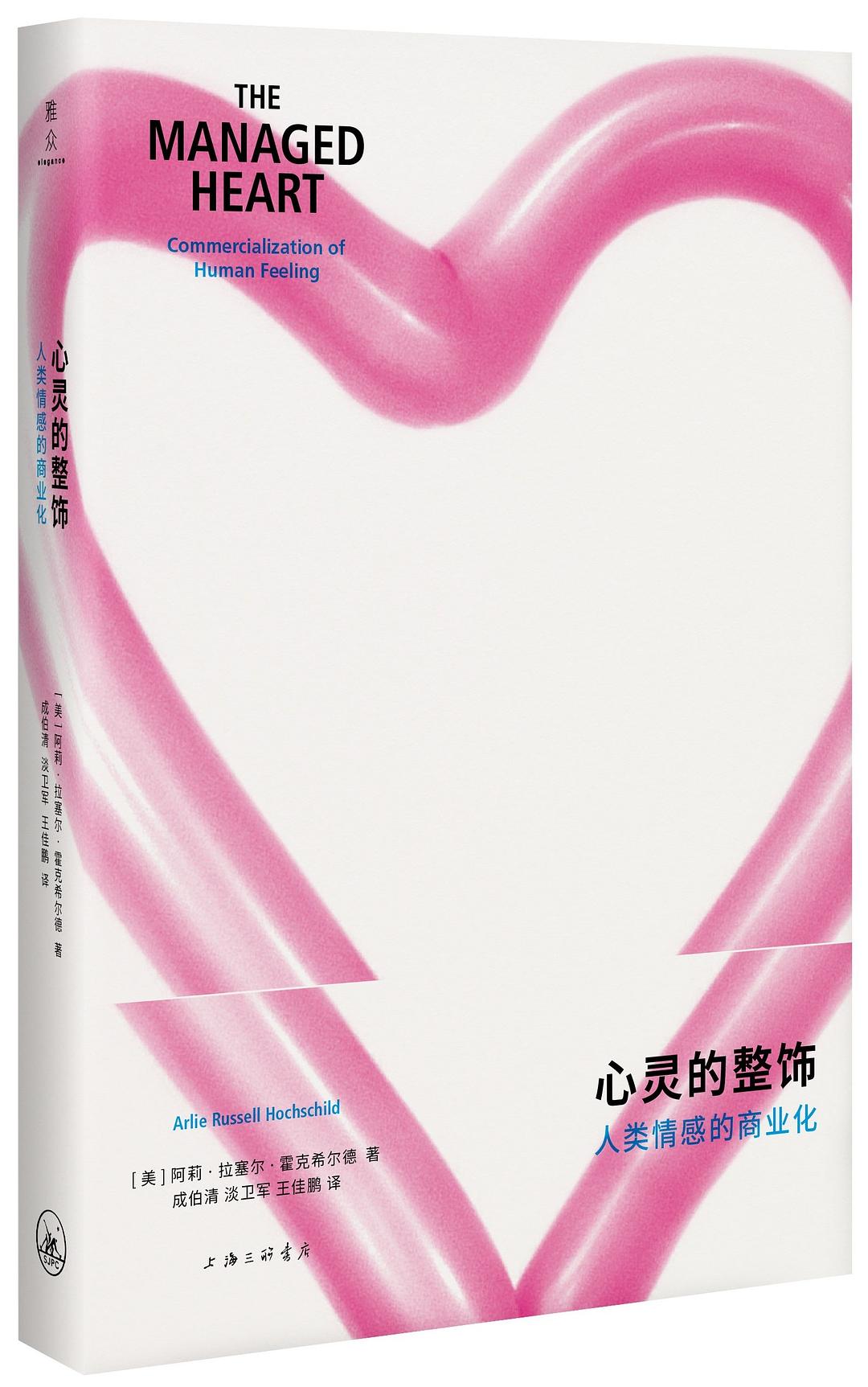
发表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