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一句话语都坐着别的眼睛》双重视角:哭泣在棍棒下
书名:每一句话语都坐着别的眼睛
1
0

开心麻花笑闹派 2023-07-17 18:41:35
赫塔·米勒在这本小集子里向我们展开了一个世界——她从罗马尼亚逃亡德国时随身携带的、无法安放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每一句话语都坐着别的眼睛不再是一个修辞,而是一个让人痛苦难安的现实。朋友访你不遇,插在你楼梯间的门把手上的字条会大喇喇地出现在你家里的冰箱里。门和门锁形同虚设,家里厕所地上遗落的烟头彰显着谁才是私人空间的真正所有者。所有人都活在全景监狱里,这个监狱甚至不需要特别去建造,就以你的私人物品、日常和言语构成:
查视者不必身体力行亲临现场才能达到威胁的目的,他是影子,本就存在于事物之中,将恐惧注入自行车、染发水、香水,放进冰箱和普普通通没有生命的物品中,实施着它的威慑作用。
在这个世界里,“必须在削土豆中学会削我的生活”,“把土豆皮削得像皮肤一样薄”,“顺着刀劲儿把土豆皮削成一根长长的圈儿。那是劳动营里的饥饿塑造的生活经验,是具身的历史——历史不仅储存于回忆和档案中,它还储存于细胞、皮肤、韧带和骨骼中。我们通过身体内外感受世界,以身体置身于特定的历史时刻,进行自我与外界的互动。它是我们与世界接触的表面,使我们进入世界,并且构成世界的一部分。身体通过疼痛和苦楚、伤疤和空洞来铭记和提醒,任凭大脑想遗忘或压制,也无济于事。
在这个世界里,一个名字里藏着两个人:
提起劳动营,她只是寥寥数语一带而过。我的名字赫塔是她在那里最要好的朋友的名字,后来饿死了,这是外婆告诉我的。我从来没问过母亲,她在叫我名字的时候,是否会看到两个人。
在这个世界里,话语有两层意思,事物的名字宛如光线般折射,在普通的日常背后暗藏恐怖:
我移居德国后,某搬家公司的广告词吓了我一跳:“我们能让你的家具长腿。”在我的记忆中,长腿的家具是秘密警察来过的标志:推开家门,发现椅子跑进了厨房,墙上的画掉到房间另一端的床上。柏林墙倒塌后,媒体上经常能看到有关东德用语的报道。这些词语在人们口中重复时,变成构词和内容都极其糟糕的“词语怪物”。在东德,圣诞树上的小天使叫“岁末飞人”,舞台下人们挥舞的三角旗叫“示意元素”,冷饮售货亭是“饮料基地”。有两个词让我感觉很亲切,使我想起木匠姑爷爷家里的情景。一个是棺木,在东德叫“地下家私”,另一个是安全局下属的一个部门,负责干部节日及忌日之类的事务,叫“悲喜部”。岁末飞人是为了避讳天使,示意元素在回避小三角旗,仿佛小化词会使旗帜受伤似的,饮料基地则是军事化了的商亭,也许东德的干部们在那里用瓶子解自由之渴。这些表达方式就像一幅笨拙无声的意识形态词语讽刺画。地下家私和安全局的悲喜部我并不感到奇怪,我在其中听到了对死亡的恐惧。死亡无所谓地位尊卑,它打破了显贵和小人物之间的界限。统治集团不愿与凡夫俗子为伍,但在这权力唯一无法企及之处,社会主义英雄和国家敌人没有分别,每个人都
相关推荐
逆天的冒险
我们是天生的冒险家,对冒险的爱从不会离开我们,直到我们迈入垂老之年。”博莱索写道。他认为,“胆小的老头子,在他们的兴趣当中,冒险应该是绝灭了的。”这也是为什么诗人们偏爱冒险,而法律通常是老年人制定的原 (南非)威廉·博莱索 2023-04-10 05:12:26艺术与观念(上册)
《艺术与观念》这本书深入探讨了不同历史时期和社会背景下的艺术观念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作者通过对自史前文化、古希腊—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以及现当代欧洲和北美等地的文化事件和艺术形式进行描述和分析,展 [美]威廉·弗莱明/[美]玛丽·马里安 2023-12-07 07:03:40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
谭其骧(1911年2月25日—1992年8月28日),字季龙、笔名禾子,是浙江嘉兴嘉善人,中国历史地理学家,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科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谭其骧于1930年毕业于暨南大学历史系,随后在 谭其骧 2023-12-07 04:11:41© 2023-2025 百科书库. All Rights Reserv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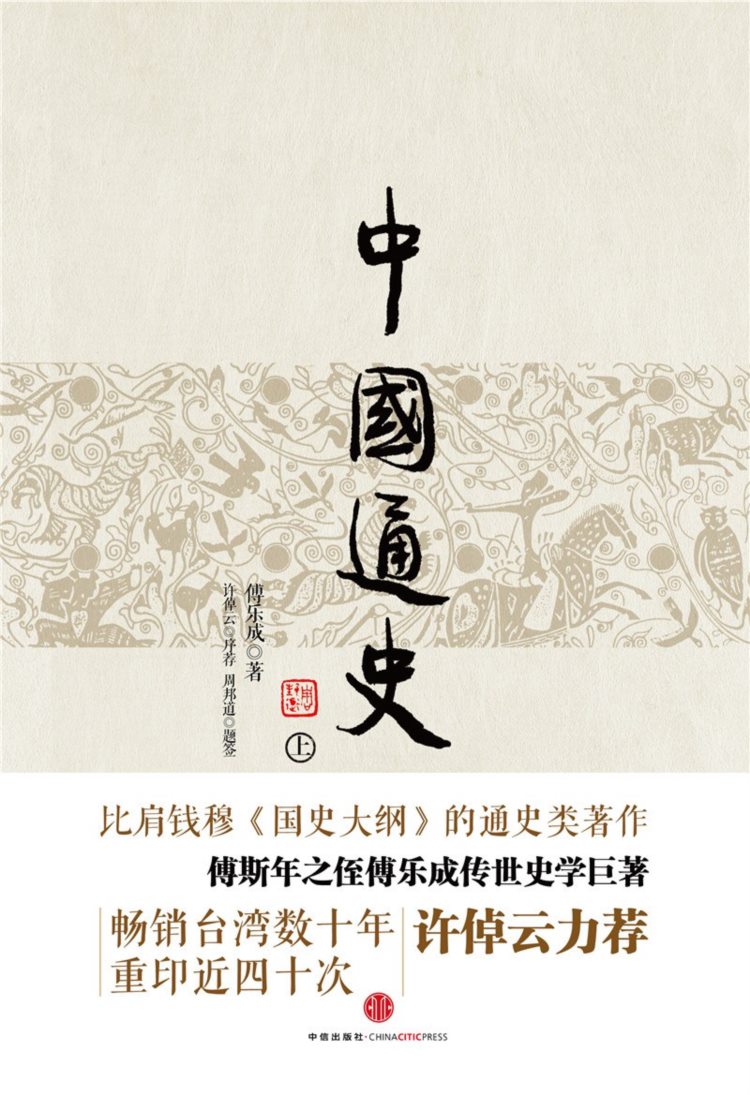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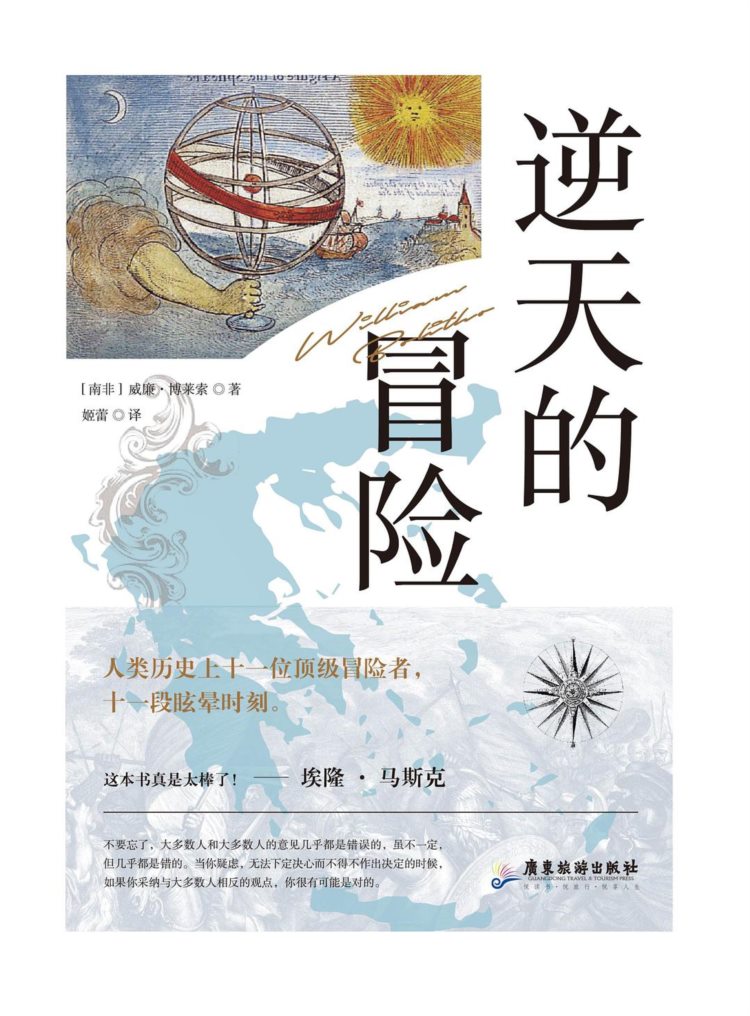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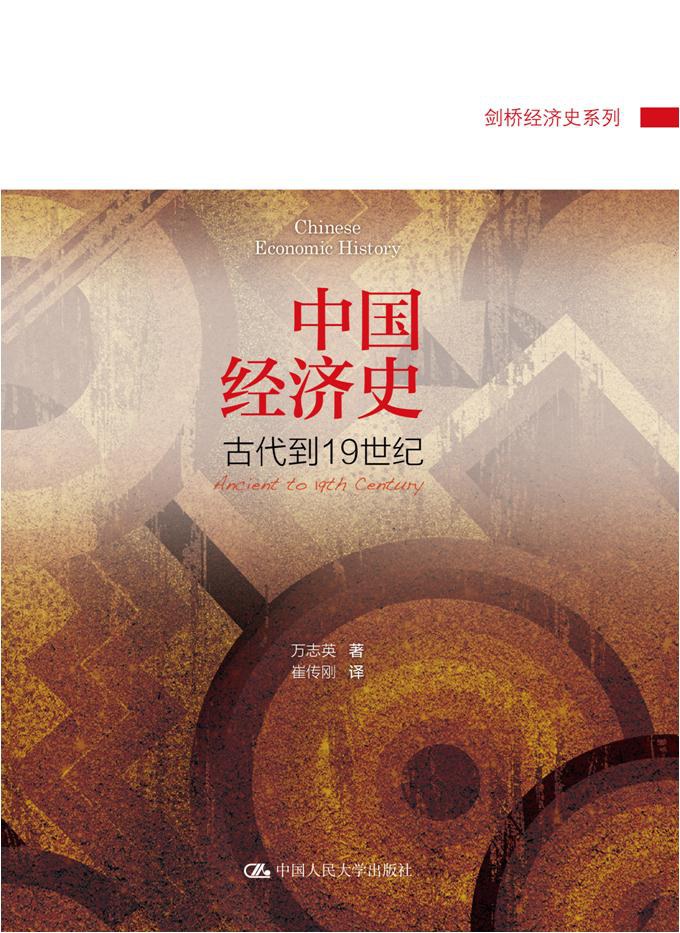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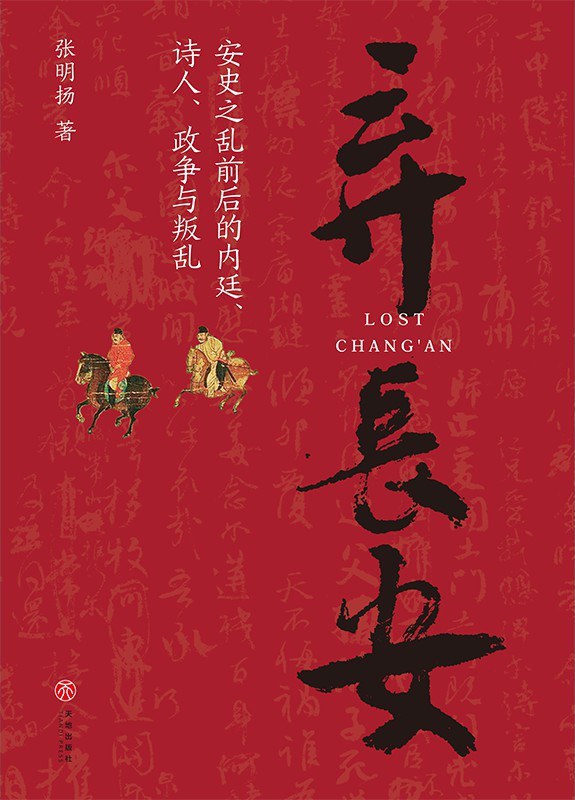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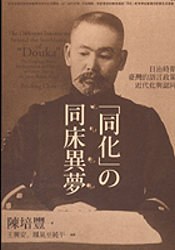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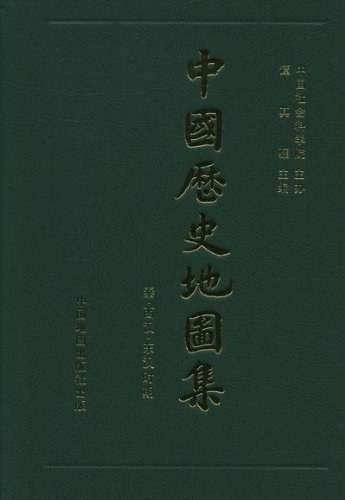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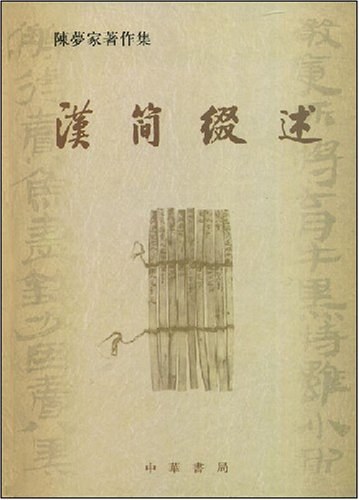
发表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