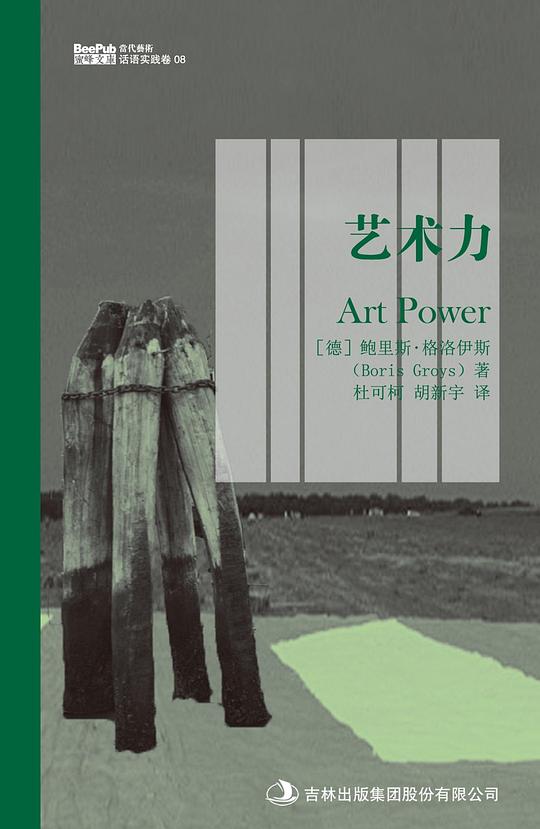
艺术力:艺术文献的灵韵与生命政治时代
书名:艺术力
1
0

白衣天使 2023-06-26 23:07:41
艺术品(artwork)是对现实的指涉,但不能指涉艺术自身,而艺术文献(artdocumentation)是对艺术的指涉。但由于艺术文献也和艺术品一起被展陈于博物馆内,艺术文献与艺术品的界限是模糊的。
艺术文献一方面可以是对已经发生和呈现的艺术品的“回收”,一方面是这种艺术不会以艺术品作为最终生产的对象,过程本身就是对象,比如艺术介入等等。
然而,不能因为艺术文献没有最终的“产出”,就将其降格为简单之物。事实上,对艺术文献的创作代表的是一种观念——艺术是和生活一样不导向结果的活动。因此艺术文献所涵蕴的价值取向几乎与博物馆对立——博物馆将艺术品视为完成之物。在这里,格罗伊斯将最终产品的创生(creation)和死亡(death)建立起了连接,对于艺术是如此,对于生活亦如此。
在这里,格罗伊斯的开创性在于,他提出艺术处理的不是现实本身,而是现实的图像。而为了远离现实,艺术始终在避免将图像建构为趋近于现实之物。因此艺术将自身建立在符号领域。
当今艺术文献的涌现是同生命政治(biopolitics)理论的流行息息相关的。生命政治表现为对生命周期的改造,对工作与闲暇时间的调配,成为“塑造当今事物呈现状态的政治意志和技术力量”[1]。因此,生命脱离了自然事件的范畴,成为政治化的产物。而由于这种对生命周期的改造本身并不可见,而只能通过对这段过程的记录进行呈现,艺术文献的流行也就找到了其在时代中的依据。
在当今时代,当生命体与机械体之间的界限已不明晰,我们发现文献能够提供机械体一种生命——只需要将其生命周期记录下来。因此,是否具有生命已经不是一个对客体来说重要的问题,因为生命是依赖于可被记录的特性,记录成为了生命的充分条件。由此,艺术文献就是一种生命艺术(bio-art)。
格罗伊斯提到的三个艺术案例分别从不同角度处理了艺术品和艺术文献的关系。
第一个例子是莫斯科艺术团体“集体行动小组”将马列维奇的绘画转变为由白雪构成的自然主义画布,而在这块场地上进行有意义导向的行为表演。这个案例将艺术品变为艺术文献能够随意处理的符号,它没有直接却是间接地回应了上文所说的“传统艺术是现实的图像”,而艺术品与它所代表的符号的关系是不稳定的,最终因艺术文献的介入而滑脱。
第二个例子是索菲·卡莱(Sophie Calle)的《盲人》,采访盲人他们心目中的美,而将他们提到的绘画作品与他们对作品的描述并置。它切割了视觉与叙述的关系,建立起了叙述的合法性,实际上将艺术品本身嫁接到了艺术文献之上。向艺术品单一的“呈现”维度提出质疑,将其作为艺术文献记录的一部分而定格。
第三个例子则是将艺术文献与艺术品的差异极端化:关在封闭空间内的、真人秀般的互动与记录,同样与格罗伊斯在上文引述阿甘本《神圣人》中,集中营“只能记录,无法呈现”的特性形成互文。在这里,彻底将生活的呈现的一面消解掉,而仅放大它的记录特性,关闭视觉,打开对生活与生命的线性叙述,用这种方式提供艺术文献对艺术界的抵抗。
因此,在分析过艺术文献的典型案例后,格罗伊斯又落脚在关于艺术体制和展陈制度的问题上,而这也是同上述案例紧密相连的——艺术文献为与艺术品拉开差距可以弃绝展示特性,那么
相关推荐
萤火谷的梦想家
艾莉森•麦吉出生于1960年,是美国《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同时也是大都会州立大学创意写作课的教授。她的作品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并出版,也曾被提名普利策奖,并获得苏斯博士奖金奖、克里斯托弗图书奖、美国 [美]艾莉森•麦吉/[美]克里斯托弗•丹尼斯/绘 2023-03-27 16:50:25鬼马女神捕1·绝密卧底(上)
腹黑凤凰vs毒舌鸡妖——蓝翎:“小姬,跟我去人界吧!”姬十四:“干吗?让人宰了我做小鸡炖蘑菇吗?”蓝翎:“不啊,让妖怪宰了你做小鸡炖蘑菇更气派。”凤凰蓝翎和鸡妖姬十四生活在无忧无虑的灵界。他们的故乡叫 郝天晓 2023-04-17 00:22:47© 2023-2025 百科书库. All Rights Reserved.












发表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