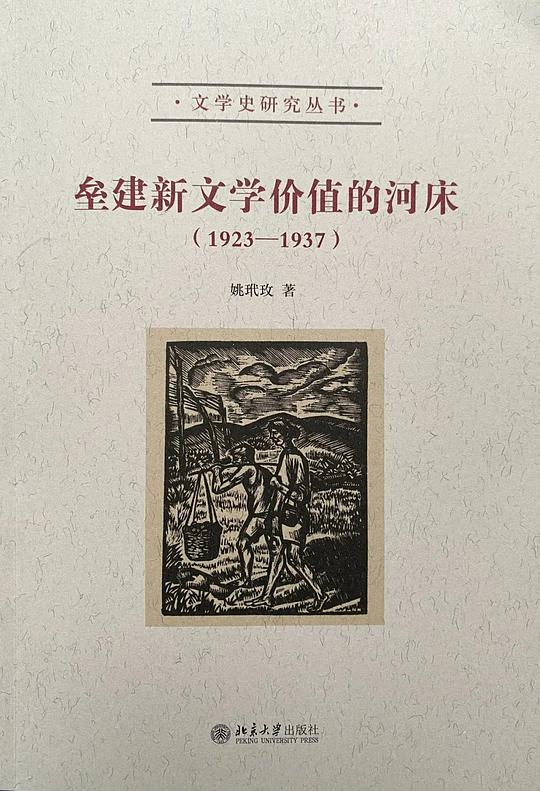
《垒建新文学价值的河床(1923—1937)》文学河床:新价值的垒建
1
0

太空穿越 2023-06-24 16:00:26
对于新文学第二个十年的详细梳理,主要利用的材料是文学期刊。文章采用了引述文字夹叙夹议的写法,近似于老派文学史的叙述方式。在绪论部分,作者提出了“新文学河床”的理论表述,即在变动中梳理“新文学”建设的各个环节。与此同时,正是这些与新文学同时形成的叙述、论断、文体感受、作家形象、文学史表达,奠定了后续学科形象、文学史写作甚至填充了新文学的意涵。尽管这种说法并不错,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学科前史之“史”,或者说是建国后现代文学史写作的史源考察。然而,作者选择在1937年进行切割,明显是认为战争干扰了新文学价值的形成。然而,1940年代才是各位文学史家进行深思熟虑表述的关键时期(如朱自清、李何林、田仲济、唐弢、任访秋等)。更重要的是,“新文学”的意涵真的能通过这样的“建设”性叙述来达成吗?从学科的角度来看,稍微了解学科史的人都知道,“现代文学”的学术化以及学科化并非自然而然、水到渠成,而是与新民主主义理论密切相关。即使30年代新文学的自我叙述再到位,没有新中国,就不会有“现代文学”。从理论价值的角度来看,认为“新文学”的理论意涵是通过某种学术操作获得的(而不是被抵消的),完全是不切实际的。摒弃战争期的断代选择和对“新文学”的学科化的僵化理解,是作者的核心观点。作者认为,第二个十年才是“建设期”,因此全书以1928年前面有青年革命和运动学生的起因,后面有革命文学的果实。这干扰了新文学的正常发展,但由于缺乏“审美价值”的构建,无法形成一种权威性的表述,因此产生了多元互动的现象。所谓的“耕耘”、“守护”、“校正”,就是全书致力于勾勒的新文学在第二个十年中完成的戏剧动作。
本质上说,这本书更像是一本中规中矩的“新文学批评史述”,尤其在第二、第三编中表现得更加明显。梳理周氏兄弟及四大文体的“经典化构建”问题,思路很好,但所谓的经典化构建,在大体上存在但在具体的定性上却缺乏支撑。只需要看一下书中引述的材料,就能了解作者大量引述的是对手的批评材料(只有对手和弟子才愿意贴标签)。难道只有被人批评才能成为一个人的“经典”吗?作家形象的钩沉似乎并不那么简单。而这本书之所以能够成立,部分原因是因为抓住了当时编辑的核心文集,如《鲁迅论》、《周作人论》、《现代中国文学作家》、《大系导言集》等,并从这个视角重新发现了阿英,这是一个很好的题目,但可惜的是仍然只是阅读记录,并没有实际的历史和知识。从根本上来说,这本书将具有史论性质的文章一概当作批评史材料来阅读,只看其学理和学科维度,完全忽略了它们创作时的具体语境(《我和语丝的始终》是它的例子,每一句回忆都有变形和省略)。这样一来,这本书的价值与《作家研究资料》又有什么不同?为什么还要额外做一番以学科性的“现代文学批评史”为导向的努力呢?这样做只会扼杀新文学的活力,使新文学失去生机。它就像是化石,是遗骸,哪里还能称之为“河床”呢?
相关推荐
逆天的冒险
我们是天生的冒险家,对冒险的爱从不会离开我们,直到我们迈入垂老之年。”博莱索写道。他认为,“胆小的老头子,在他们的兴趣当中,冒险应该是绝灭了的。”这也是为什么诗人们偏爱冒险,而法律通常是老年人制定的原 (南非)威廉·博莱索 2023-04-10 05:12:26笔误:文学大师的秘密生活
爱伦·坡小时候曾在一个墓地里上学?马克·吐温曾当着维多利亚女王大谈放屁,是怎么回事?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在派对上双手趴在地上,像狗一样大叫又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认为,作家应该是正襟危坐着写书的人,但《笔 (美国)罗伯特·施耐肯伯格 2023-04-10 10:13:49© 2023-2025 百科书库. All Rights Reserv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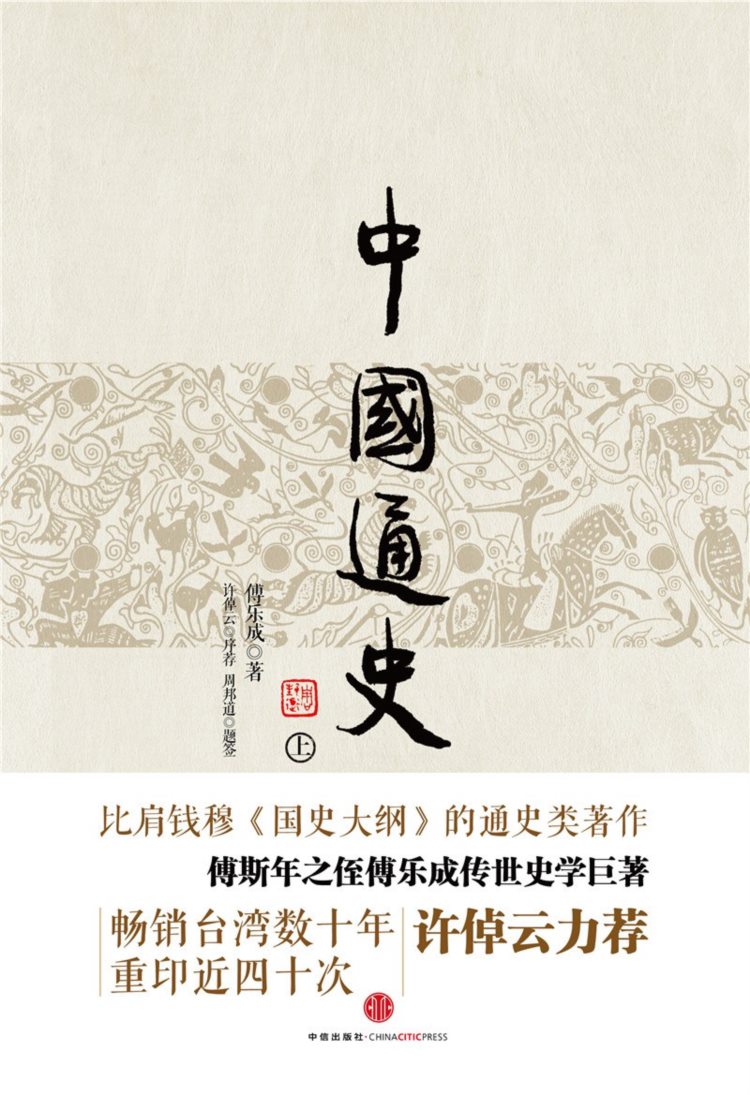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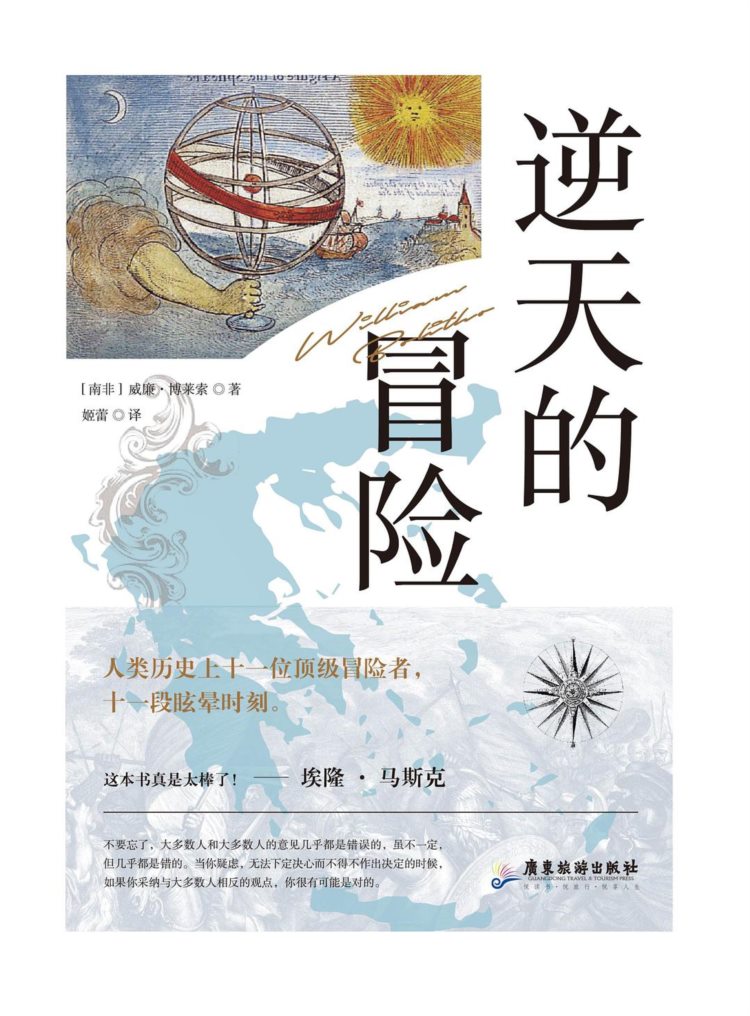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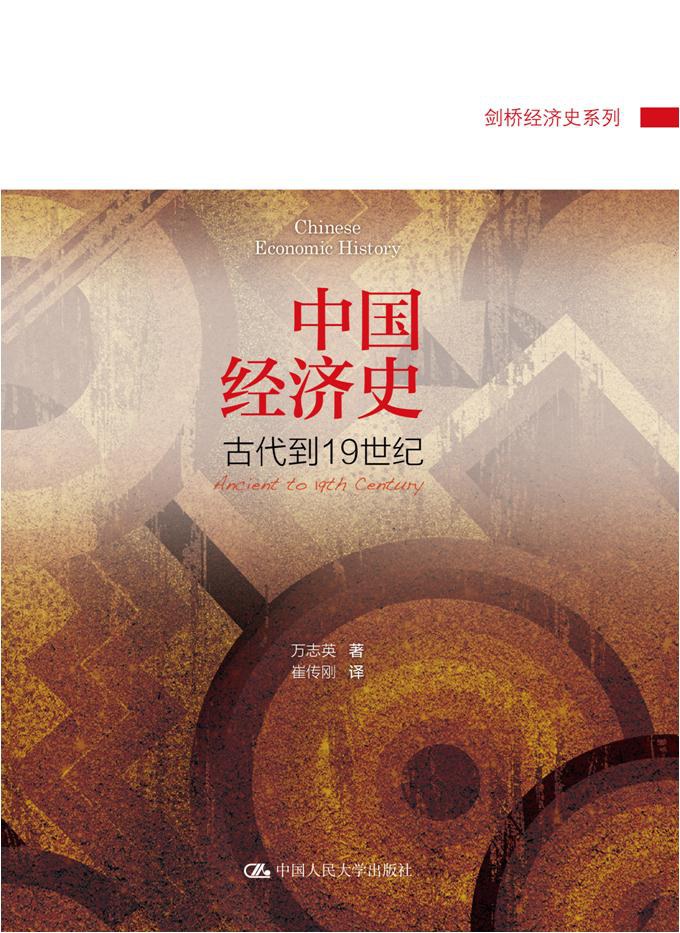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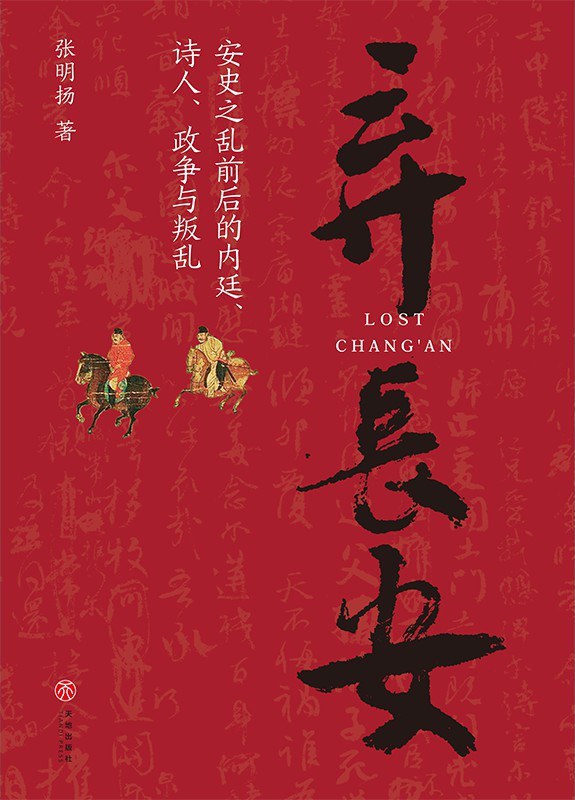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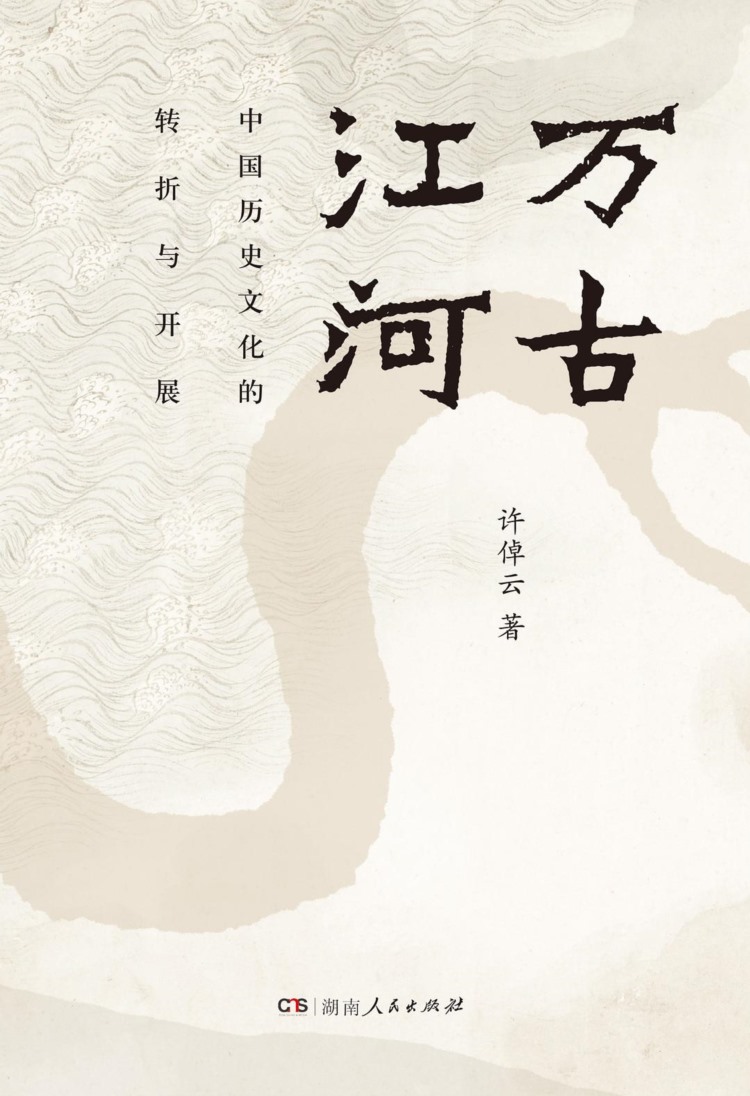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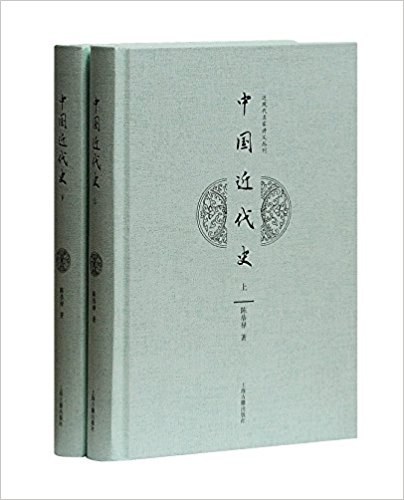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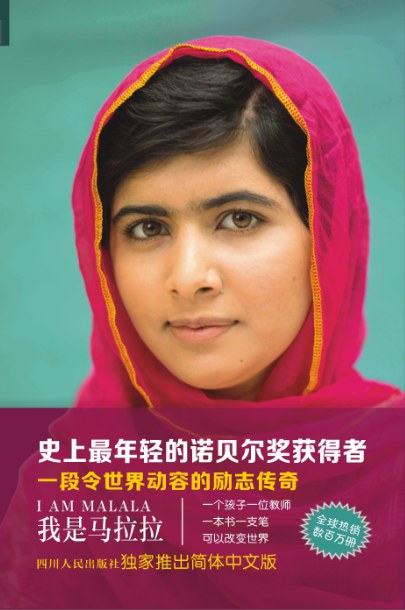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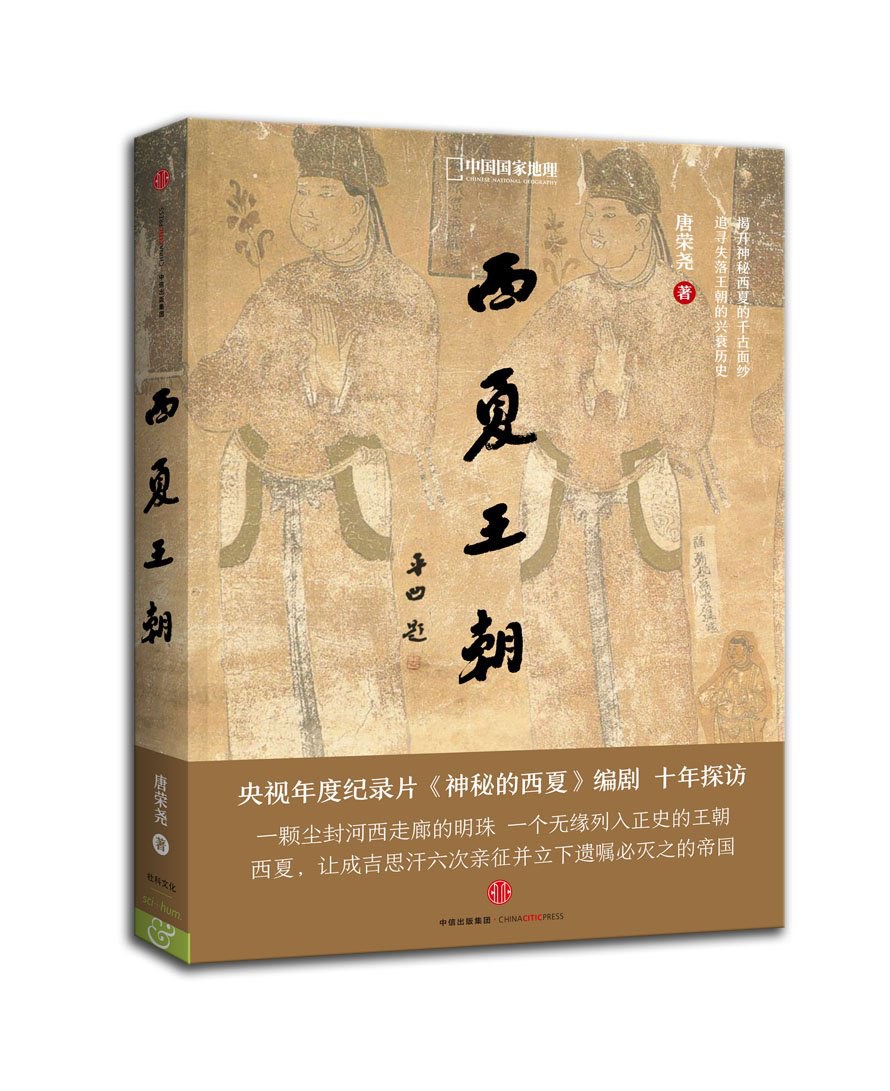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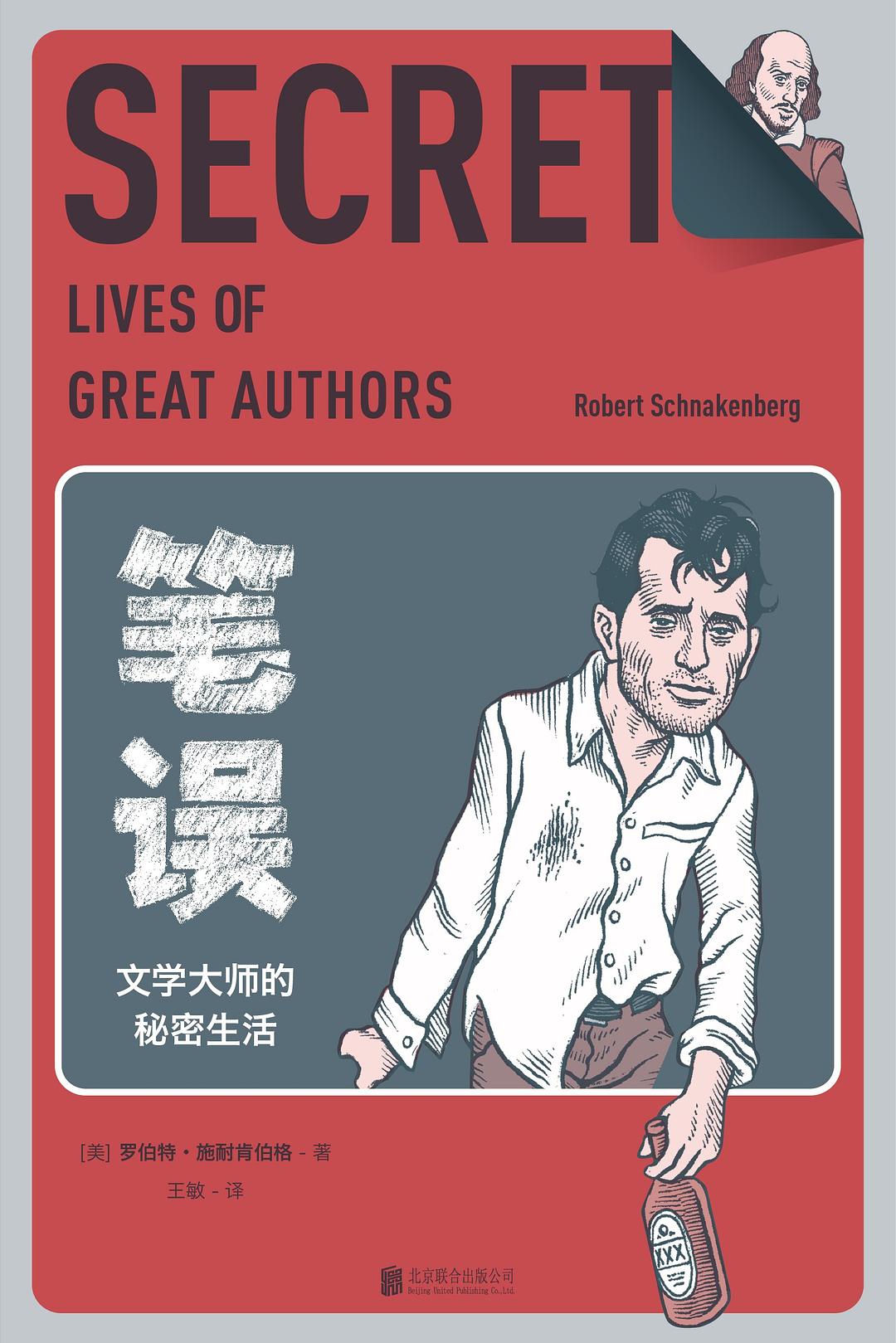
发表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