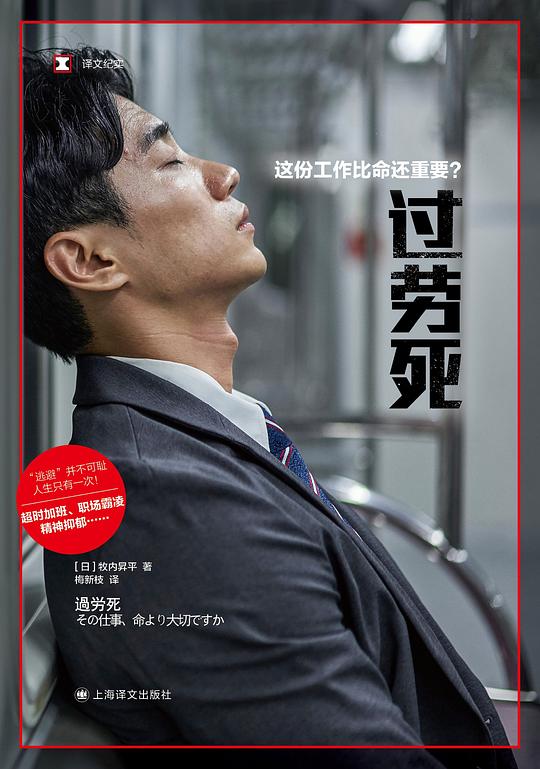
日本:“过劳死”引关注
书名:过劳死
1
0

快乐小红豆 2023-06-16 12:31:22
这本书让我对“过劳死”有了更全面的认识。我一直以为过劳死只指连续加班在工作场所或附近猝死的情况。但读了这本书后,我才明白,过度加班导致的事故死亡、自杀、心脑系统疾病等都应该算作过劳死。这里的“应该”更多地体现遗属和社会舆论的态度,或者说是劳工方的态度,而不是法律的定义或者资本的认知。因此,本书跟踪的几个过劳死案例中,往往会出现劳资双方就当事人是否过劳死而进行的长时间争执,这些争执的结果也往往因资方的应对策略而有很大不同。
一些公司(大概是因为企业形象的原因)愿意道歉、赔偿、协调遗属(但实际上恕我直言,这些公司往往并不真心,只是为了平息社会舆论),而有些公司则非常卑鄙,抓住遗属很难证明死亡与工作的直接关系而拒绝任何责任认定和赔偿,或者对管理方式进行反思和改变。
作者描绘的一个场景让我印象深刻:一位母亲因儿子过劳死而与其雇主进行了五六年的法律诉讼。为了支付产生的费用,她甚至取消了自己的保险,几乎是孤注一掷地想要为儿子讨回公道。最终,她还是败诉了。在儿子的灵前,她向儿子道歉说自己已经尽力了,只是力量有限,不得不到此为止。然后她打开了一直放在儿子灵位前的一瓶清酒,喝了一口。这瓶清酒是其他过劳死遗属送给她的,是某次遗属互相支持打气的交流会的纪念品。
这个场景聚焦折射了个人的渺小无力与资本和组织的庞大能量。资本永远是卑鄙的,组织永远是强大的打手和帮凶。资本可以设计出无数种系统,引导劳工通过自我剥削实现销售额的增长、人力成本的极度压缩和利润的增加(或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维持),使得庞大的组织可以继续攫取剩余利润。
比如,公司创造“每小时人均销售额”的指标来衡量门店业绩,并将员工的绩效和收入直接与此挂钩。比如,在合同里直接写入基本工资覆盖80个小时的加班时间。比如,默许和诱导员工以自掏腰包购买商品的方式将本应属于公司业绩指标的目标,转化为员工的“上班成本”。比如,部门领导的言语、身体和心理上的暴力式“指导”逼迫员工不断为资本的利益牺牲自己而把自己非人化为资本想要的“理想劳工”——只会干活,不吃不喝不休息,也不需要其他维护,还能对资本感恩戴德地工作996、007。
相比之下,同样是组织,同样有力量反击的国家却被资本以经济发展目标为糖衣炮弹所绑架。于是,个人只能寄希望于最后的底线——所谓的法律武器和个人之间的社会组织松散联盟,试图蚍蜉撼树、螳臂当车。
通过“过劳死”这个极端的角度,本书揭示了在当下日本社会劳资关系中各自坚守的阵地和夺取的山头。
有趣的是,书中描述的过劳死案例中,死者基本都是努力、认真、乐于奉献的“好人”。他们中有人经历了一路坎坷和来自家庭的贫困,在非正式雇用中一路靠极度努力和自我压榨走出了困境,最终获得了正式雇佣的资格。也有人因经济不景气、公司倒闭而不得不离开自己擅长的设计工作,去到运营部门一边过劳工作一边贷款养家糊口。还有一些年轻但已经成就斐然的“别人家的孩子”。
社会和资本整天制造焦虑,要求人们不断地卷。但卷这个事情确实是双刃剑。有人运气好、基因好,一路卷出了头顶,加入了既得利益的“赢家”组,有些人卷着卷着,卷没了自己。这也难怪许多有志青年纷纷选择躺下了。他们透彻地看穿了一个事实:在资本的逻辑视野里只需要两种“人”——有钱的消费者和光干活、不吃不喝、不需要维护的自动
相关推荐
销售巨人
《销售巨人:大订单销售训练手册(理论篇+实践篇)(全新升级版)》SPIN彻底改变了三个销售有关的领域:销售工作本身。SPIN销售技巧和模式基本上不受产品限制,只要是目标客户知购决策时间较长,参与策人数 [美]尼尔·雷克汉姆 2023-05-13 09:45:49文化战略
《蓝海战略》等品牌战略著作目前具有最大的影响力,认为创新在于产品功能的突破。然而,作者通过对数百个品牌案例(如万宝路、星巴克)的分析,以及与相关品牌管理者和消费者的访谈,发现了功能主义创新模式的缺陷, 【美】道格拉斯·霍尔特/道格拉斯·卡 2023-05-13 09:46:48幕后大脑
《幕后大脑》是一本收录泛广告营销领域从业痛点以及实用解决方法的小黑书。本书邀请了100多位在本行业某个点有不可替代实践经验的总监或创始人,提出自己职业生涯中普遍遇到的、长存的难题,并写下独到的见解和实 陈耀福、陈绍团、关健明、叶明桂、丰信东/赵宁、熊超、李欣频、樊苗林、空手 2023-04-01 22:44:49销售的革命
《销售的革命》能为你的事业、人生带来一场革命!“从合格到优秀,再到卓越的营销人,5本必读书,第一本就是《影响力》。”随着《影响力》的持续热销,这句书封上的宣传语已被不少营销人牢记于心。很多人不断追问, 尼尔·雷克汉姆/约翰·德文森蒂斯 2023-05-13 09:49:58© 2023-2025 百科书库. All Rights Reserv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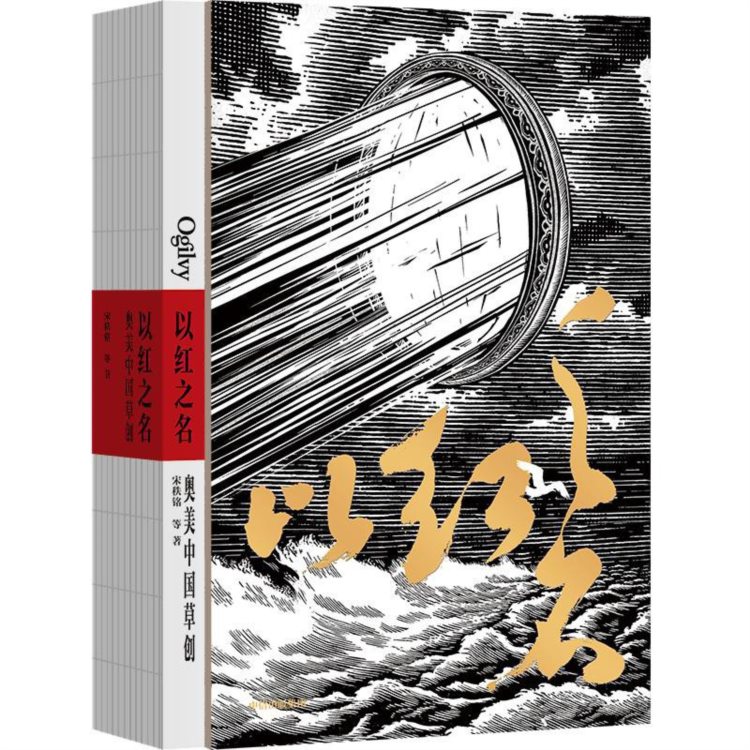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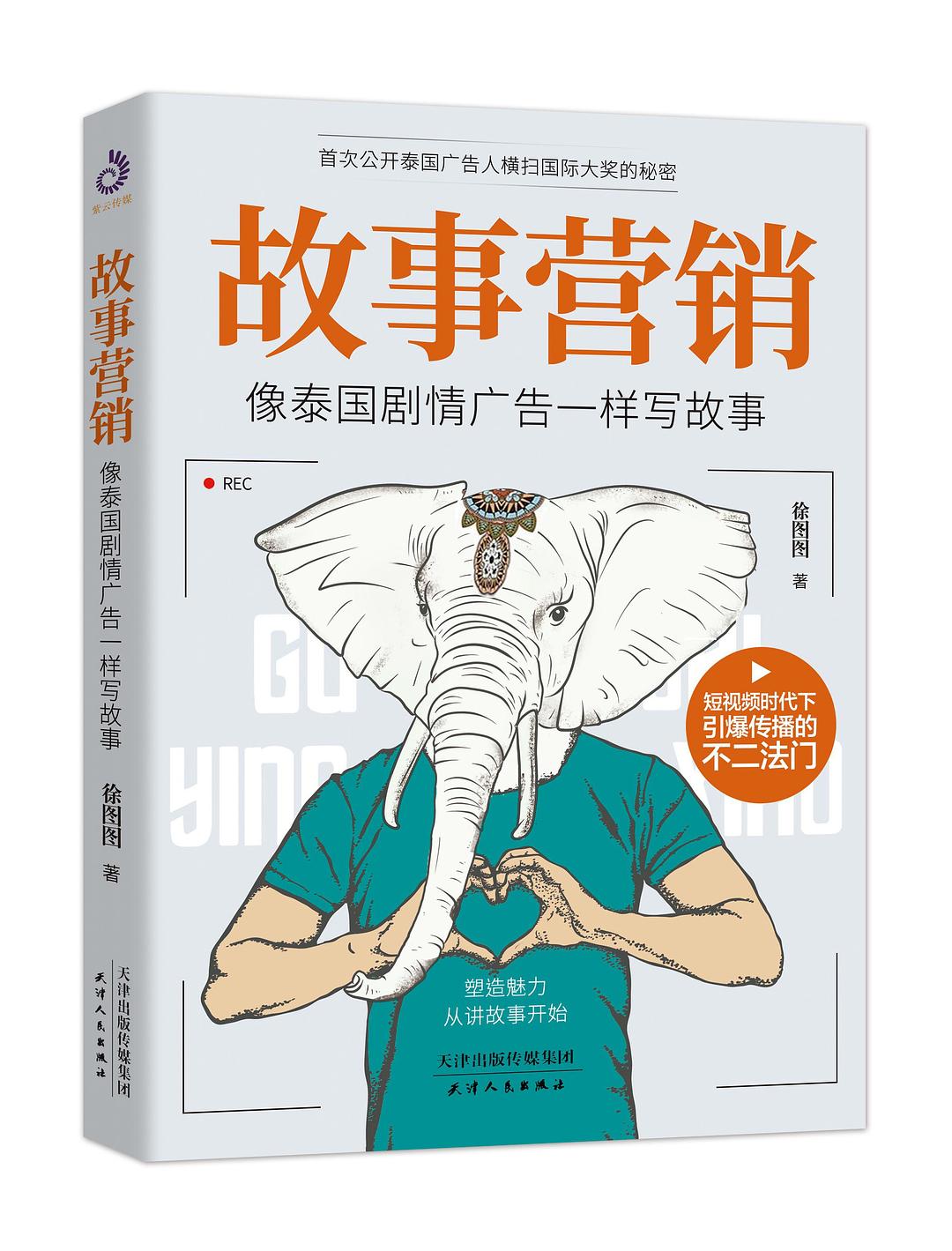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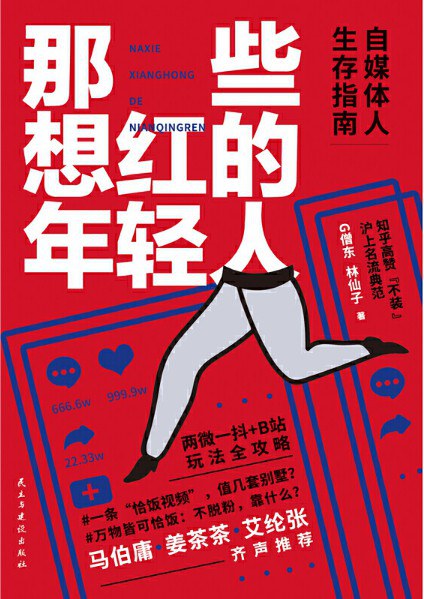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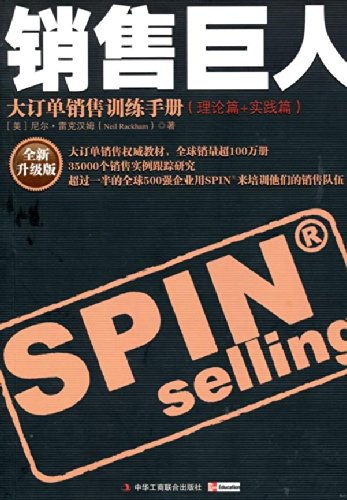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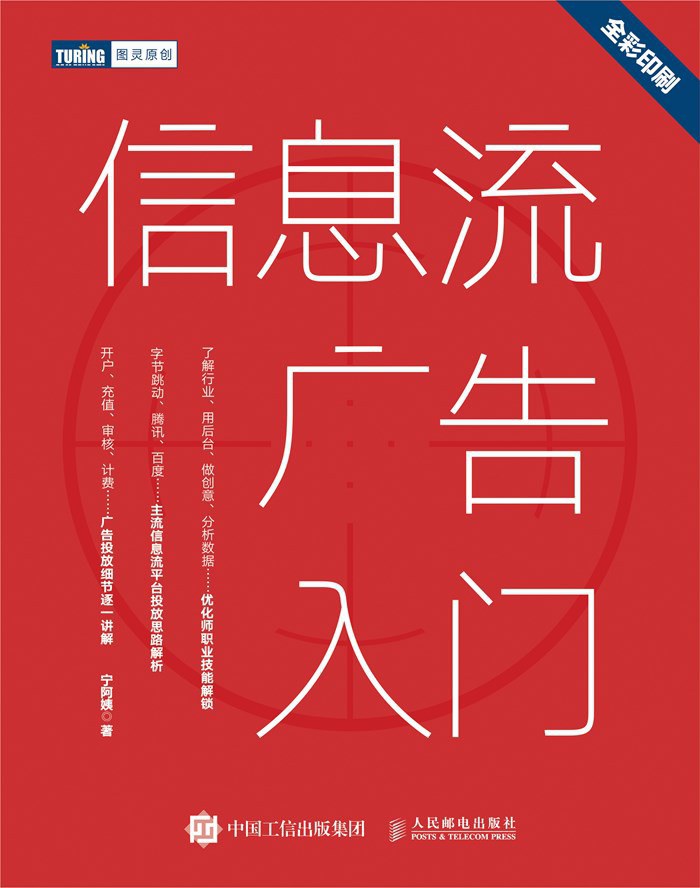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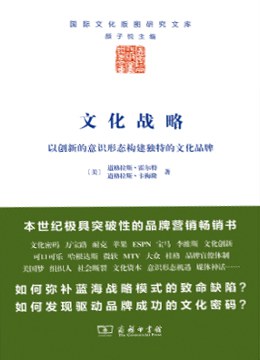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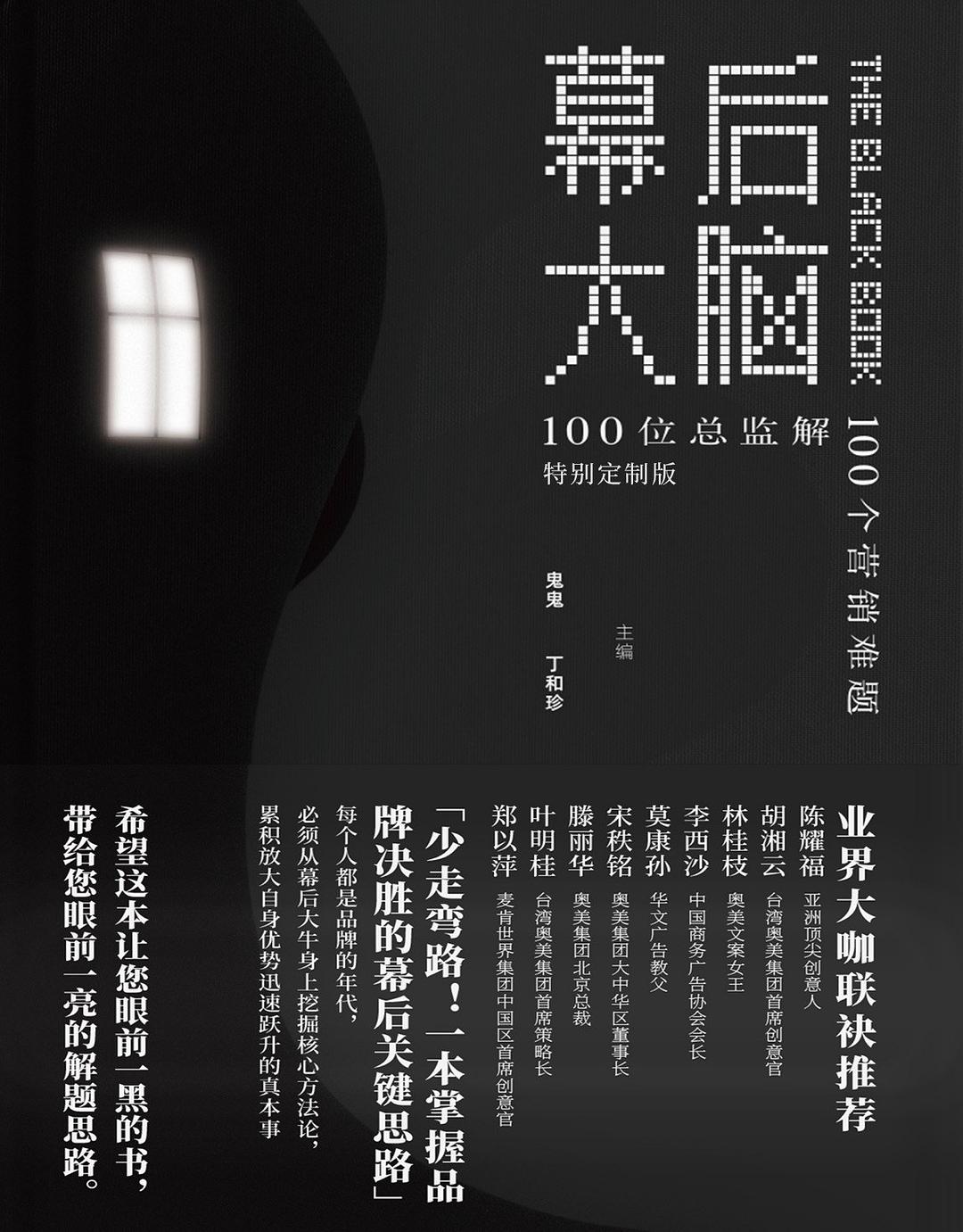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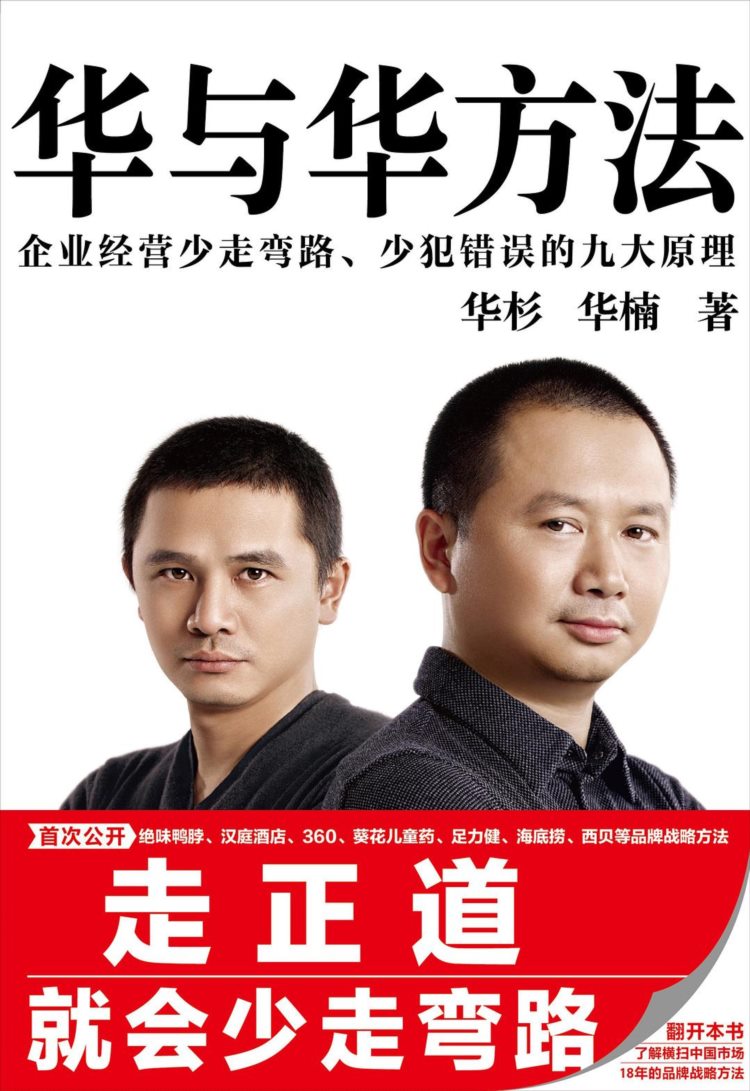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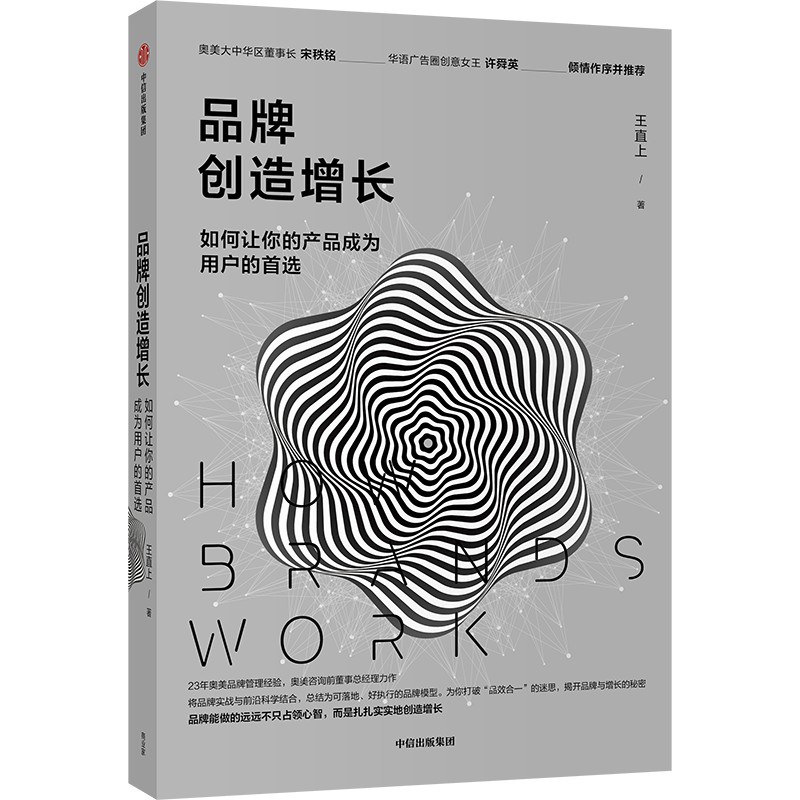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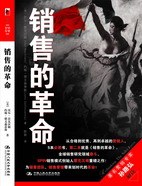
发表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