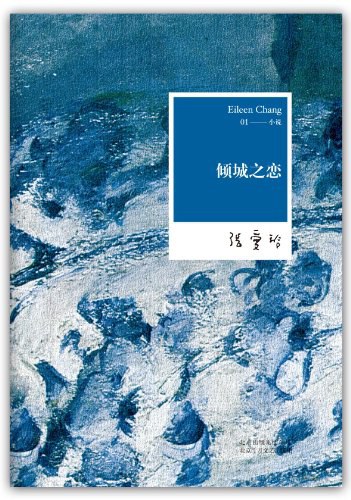
《倾城之恋》张爱玲笔下女性命运
书名:倾城之恋
1
0

跑步狂人 2023-06-13 23:13:26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伟大的作家。她的作品涉及广泛,唯一一本大团圆结局的小说却只有《倾城之恋》。《倾城之恋》发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和香港,这段社会变革和动荡不安的时期充满了硝烟与战火,女主白流苏所处的环境和作家本人一样,同样充满了挑战和危险。
傅雷批评《倾城之恋》,说它“几乎占到二分之一篇幅的调情,尽是些玩世不恭的享乐主义者的精神游戏;尽管那么机巧,文雅,风趣,终究是精练到近乎病态的社会的产物……美丽的对话,真真假假的捉迷藏,都在心的浮面漂滑;吸引,挑逗,无伤大体的攻守战,遮饰着虚伪。”诚然,《倾城之恋》中的交易式爱情故事放在今天来看也有些畸形,但傅雷的视角未免过于高傲,他不愿意承认或者根本并未觉察这段“倾城之恋”背后的运行逻辑。
如同傅雷的姿态,男主范柳原在这场爱情的博弈中同样高高在上。他冷漠地视爱情为交易,并且掌握着决定白流苏命运的权力。他对白流苏说:“我犯不着花钱娶一个对我毫无感情的人来约束我,那太不公平了,对于你,那也不公平,噢,也许你不在乎,根本你以为婚姻就是长期的卖淫”。他说了一万句动人的情话,但完全不愿意许诺“爱情”以婚姻,因为他将结婚视作一种牺牲。当然了,白流苏自然是不值得牺牲的,他更喜欢把流苏当做一个情妇来使用,以满足自己的需求。在镶金天平的另一端,女主白流苏在这场交易中处于天然的弱势地位。她需要经济上的安全和长期饭票,又无法在情感上避开范柳原设计的陷阱,因此在权衡利弊后选择妥协,只能真的扮演起“范柳原情妇”这一角色。
白流苏的形象可以被视为一个典型的“异化者”。她的内心永远充满着矛盾。某种程度上来说,她一直在反抗,她在被前夫家暴后主动选择离婚、住回白家后又努力寻找机会打破家庭的桎梏。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女性经常被视为是父兄、丈夫等男性所拥有和掌控的财产,作为附属品,并不被鼓励拥有独立思想、同时行动能力也受到限制。白流苏在家人的嘲笑、讥讽和欺辱中求活,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和道德束缚。在自由和权利本就极其有限的情况下,她努力争取和范柳原自由恋爱的机会——她知道,不攀住范柳原这棵烂木,她只能为前夫守寡。她揽镜自照,用女性的眼光去端详自己眼中、而不是男人眼中的自己,勇敢地去自爱。她在爱情中精准把握住了自己的人生准则,清楚地认识到范柳原甜言蜜语之后的冷漠浪荡,始终如一地保持着贵族小姐的矜持和冷静。尽管一直受到异化和物化,她仍然保持着自己独立思考和行动的能力、始终坚持自己内心深处的感情和欲望,敢于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在自由意志和身份问题上的挣扎、在不平等关系中寻求平等的努力,以及表现出来的坚韧、独立,也让我们看到了她作为一个女性所具有的积极面。
然而,这种反抗是迂回反转的,不彻底的抵抗在另一场景下又表现为一种妥协。耐人寻味的结局暗示了白流苏未来荒诞的人生悲剧,而为这场无止境的悲剧拉开帷幕的,正是她自己主动的妥协。白流苏觉醒的人格并不足以帮助她抵御对社会传统和男性权威的服从。范柳原在经济生活中的特权位置不可动摇,不平等的关系使得流苏变得更加脆弱和无助,她极其依赖范柳原的目光和对自己的评价,选择一次又一次地讨好和迎合这个上位者,吸引他对自己产生兴趣,这种行为又何尝不是一种自我物化呢?尽管在她人生的旅程上曾有多条岔路——她可以带着原有的财产离家、可以利用自己的才学去做一个职业女性,但她却被虚荣闪耀、刻着贵族家徽的磁石牢牢吸住,不撞南墙不回头地去寻找庇护,像中秋节的月饼胚子,被灰姑娘的模板印出一个规整的图样。
张爱玲并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但作为一个伟大的作家,她笔下的男女爱情却非常残酷而现实。她清楚地展示了一些女性对自己爱情悲剧推波助澜的影响。同时,她的冰冷和寂寥似乎在漫不经心地表意:“女人也不相信爱情,女人心中也充满着算计。”一个被隐藏的社会现实是:社会生活中女性往往扮演着弱者的身份。受限于自身的主客观条件,白流苏等人很难在夹缝中找到一条真正的出路,又无法摆脱物质和虚荣的引力,最终为了争取利益的最大化,只剩下了自我物化一条道路。而对于我们女性读者自己来说,首先应该将自己视为一个独立、完整、有尊严和平等地存在于社会中的个体;除了那些不得已而为之的部分,尽全力去撕掉自己身上弱者的标签。只有通过摆脱异化和物化,寻求自我解放才能真正实现女性的平等与尊严。诚然,时代境遇下的白流苏等人,哪怕渴望改变命运,但仅靠自己一方的努力无法实现的。但你我女同胞之间,若人人都真想奔向自由,奔向成功,又岂是谁能拦得住的?
相关推荐
萤火谷的梦想家
艾莉森•麦吉出生于1960年,是美国《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同时也是大都会州立大学创意写作课的教授。她的作品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并出版,也曾被提名普利策奖,并获得苏斯博士奖金奖、克里斯托弗图书奖、美国 [美]艾莉森•麦吉/[美]克里斯托弗•丹尼斯/绘 2023-03-27 16:50:25鬼马女神捕1·绝密卧底(上)
腹黑凤凰vs毒舌鸡妖——蓝翎:“小姬,跟我去人界吧!”姬十四:“干吗?让人宰了我做小鸡炖蘑菇吗?”蓝翎:“不啊,让妖怪宰了你做小鸡炖蘑菇更气派。”凤凰蓝翎和鸡妖姬十四生活在无忧无虑的灵界。他们的故乡叫 郝天晓 2023-04-17 00:22:47© 2023-2025 百科书库. All Rights Reserv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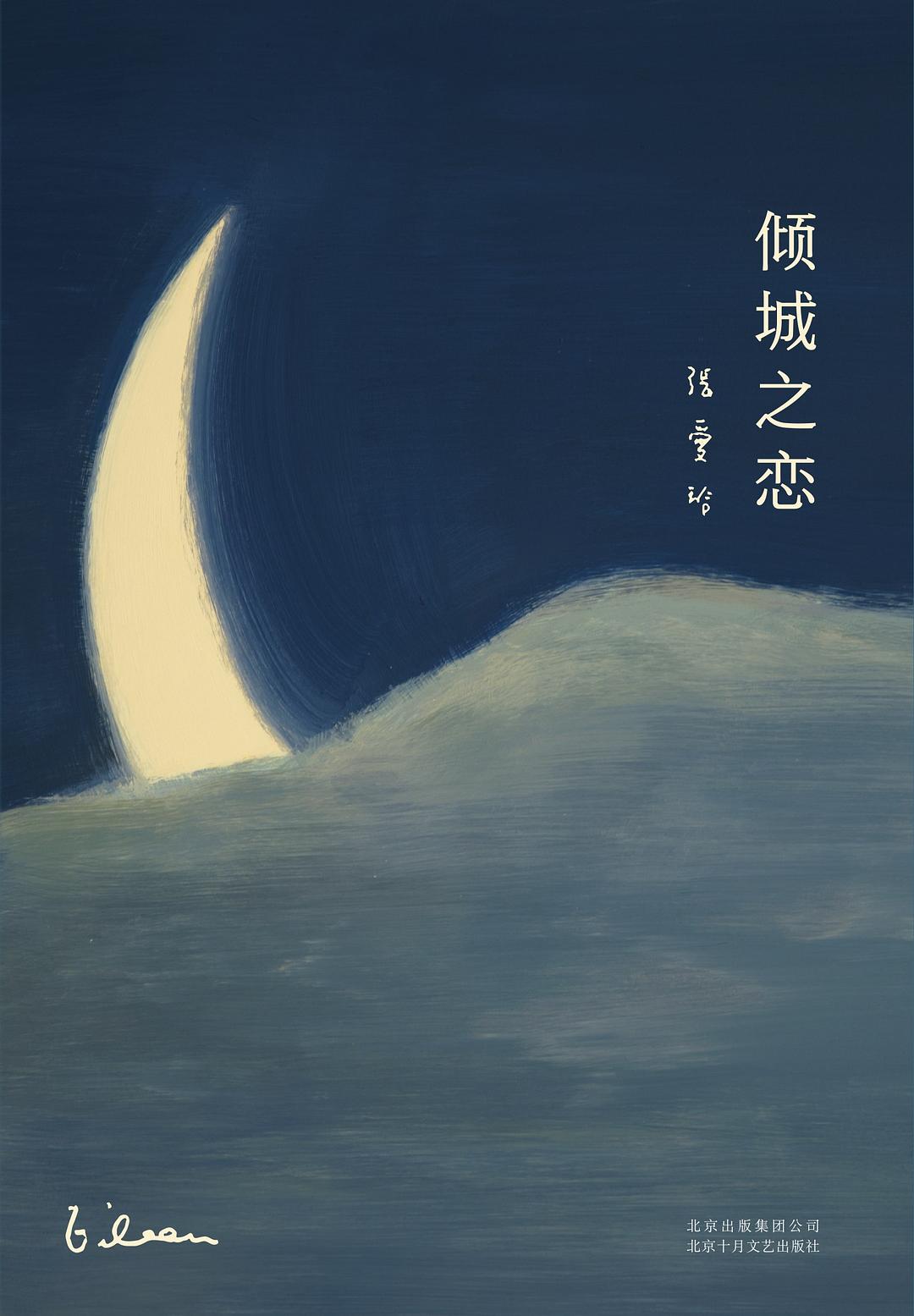









发表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