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孽子:命运背后的故事"
书名:孽子
1
0

独角戏 2023-05-14 16:56:46
抱着看耽美的心态打开这本书,阳了之后在床上一朝一夕读完,和开始时的预期南辕北辙。其实看完以后让我很迷惑的是同性恋到底在这本书中占着多少的分量,如同书名所示,小说最大的主题应是“孽”而非“欲”。横贯整本书的是刺眼的代际断裂。这种断裂的共同点或来自性取向的位移,这群同性恋少年因此被遣送到社会的边缘,承受着无法摆脱的欲望冲突和无法弥合的父子断裂。一只只奉献自己的肉体,在暗夜里游荡的青春鸟。同性恋身份的直接描述是被有意隐失的,它被自然而然地化入第一人称的讲述中。这种隐失也从潜层构造了这个黑暗国度边界的模糊,从这个朦胧的视角中将观者也半推半就地纳入了黑暗国度的隐形的轮廓。因而呈现在眼前的只是人性与生活。阿凤与龙子、桃太郎与十三号,他们是莲花池边的传奇。通过对传奇故事的口耳相传,他们建构着自己的认同感,试图以此攀缘和安栖于这个黑夜里的国,增加它的厚度。左脚追着右脚,影子踏着影子。这些公园里的少年,在依赖与生存的浮沉中贩卖着欲望,但他们并不属于欲望本身,而是欲望身不由己的私生子,是欲望的余孽,是欲望扫荡过后的废墟。他们的父亲,一部分是颇有地位的成功者,这些少年背叛了家门期待,原谅已成幻灭,只有在漂泊流亡中等待死亡为一切了结。然而更多人的父亲,却可能是素未谋面的失败者或抛弃者——早已死去、在狱中、在流亡。正如为了寻父最终偷渡日本小玉,他说:“你猜我找到他,第一件事我要干什么?我要把那个野郎的鸡巴狠狠咬一口,问问他为什么无端端地生出我这个野种来,害我一生一世受苦受难”。在莲花池,他们的客人很多也从光鲜亮丽的白天下蜕下沉重的西装革履,融化在暧昧的黑夜中。他们在床上用肌肤交媾,却因陌生而更将苦楚宣泄。遭际在话语中被一点点拖扯出来,排列成各自惨淡的命运。对于性本身的描述,反倒是冷漠无温的。无论是王夔龙、林茂雄或余浩,他们本来自这个国的外围,却因各种偶然或需求与这里种下因缘。傅崇山更是唯一作为父亲沉重的承担者,儿子的自杀使他一生在这里从事拯救。他从代际的另一面,画满痛苦的另一个半圆。一次次拯救,却有一次次背叛,这些青春鸟们不愿意逃离,因为在这里给予了他们家的幻觉和可能,这里似乎是平等的,更加安全的,尽管事实上仍然无根的。但把他们和他们破碎的家庭镶嵌回到那个规训与秩序的体面社会中,意味着再一次流放。最让人难忘的是叙述者“我”,阿青。母亲因难产而从小就讨厌他,这在掺和着民间思想的佛教观念中本身就被解释为一种“讨债鬼”的怨孽。后来她和歌舞团的喇叭手私奔,在她出走的晚上,父亲用空枪虚恫地指向黑夜,这是阿青见过最恐怖和悲怆的面容。在阿青最后一次见到母亲时,她像一堆散骨躺在床上。一辈子都在逃亡、流浪和追寻,最后在这躯满载罪孽和毒疮的肉体中等死,而阿青最终在这一刻,在他自己被逐出家门的流亡中,感受到了他和母亲的亲近。中间有一段,阿青执意收留智力障碍的小弟,给他好吃好喝,带他戏水,直到被丽月赶出仍不死心地在台风压境前夕奔走寻觅。一下想起《日出》里陈白露所守护的小东西,同样的悲悯,同样的叹息。而在阿青这里,小弟更是弟娃抓不住的幻影,他所憎厌和同情的,又在他死后无数次冲上眼帘,凝聚成那个系带情感的口风琴。在寻找小弟的台风天里,从一个摊贩打翻的柿子中,他再一次想起了母亲。柿子里是和母亲唯一温情的留忆。当他突发决定把柿子买给母亲时,发现母亲早已在药味掺着秽味的屋子里死去。她的骨灰放在寺里,老和尚指着说:“黄丽霞在这里”。在我看来这是全书最恸一刻。最后一次见到母亲,正是她临死的前一天,求他去寺庙里请求超度。而如今她只能被放在殿外,坛里的灰烬仍带着生前的罪孽。这罪孽是浮沉中的欲望,载着她一生惊惶与逃窜。阿青和母亲又一次达成了情感的深层共识。在这里,“孽”在全书的涵义被泛化,它不单单指向同性恋本身造成的(父系)代际断裂,也包含了男女之间情欲的喧嚣、母子之间的俄狄浦斯情结带来的整体破碎。它将这一切收摄。而他们是这种破碎可怜的孩子,不是破碎本身。直到最后一刻,整本书都是沉重而平静的,偶有的喷发似乎也在郁结的空气中蒸煮飘散。熟悉的闽南语,台风前的闷躁,都倒映在莲花公园燃烧的池水中,恍惚间这荧荧鬼火般互相凝视的目光竟生出一种悲怆的神圣。
这里是他们流放欲望的凄美地。
相关推荐
男人有风险,相爱需谨慎
这是一本针对女性的必读快意恋爱书。作者文字麻辣,生猛娇俏,不仅让许多无病呻吟的爱情文字打退堂鼓,更是快刀斩乱麻,毫不留情地揭露各种爱情假象和虚妄,迫使读者直面淋漓的现实。只有勇敢地清醒头脑,敢于迎接挑 曾雅娴 2023-03-29 18:46:56国际超模的极简瘦身课
这是一本为中国女孩撰写的“易瘦体质”培养指南,作者是一名国际超模李霄雪。李霄雪曾与纽约排名第二的模特经纪公司EliteModelManagement签约,在国际模特界打拼了10年,之后她决定回到中国成 李霄雪 2023-03-31 06:29:24我有一杯酒,可以慰风尘
祝愿你的岁月平静无波澜,同时也希望我的余生不会有太多的悲欢。这里介绍的是关东野客的又一力作,它名为《我有一杯酒,可以慰风尘》,共涵盖13个故事。这些故事或许会让你感到孤独和温暖,也或许会涌起遗憾和美好 关东野客 2023-03-29 19:34:53即使生命如尘,仍愿岁月如歌
优化后:想要走向自信、尊严的人生,女性可以从工作、家庭、生活等方面入手。本书将通过作者及身边朋友的经验告诉读者,一个女人是否能够实现美好的生活,决定性因素并不在于她的经济状况,而在于她有无勇气不委屈、 晚秋 2023-03-31 07:15:04我们的性
《我们的性》,现在是它的第7版,生物、社会心理、行为和文化诸多方面以对个人有意义的方式,对性做出了全面、学术观点鲜明的介绍。我们非常高兴读者对本书前几版一直反应热烈且热心;这些反应激励着我们为你们的学 [美]罗伯特·克鲁克斯(RobertCrooks)/[美]卡拉·鲍尔(KarlaBaur) 2023-05-05 06:31:19© 2023-2025 百科书库. All Rights Reserv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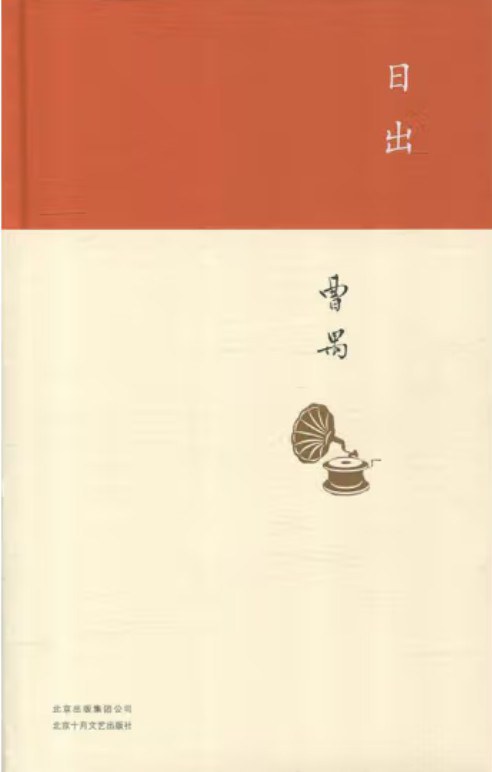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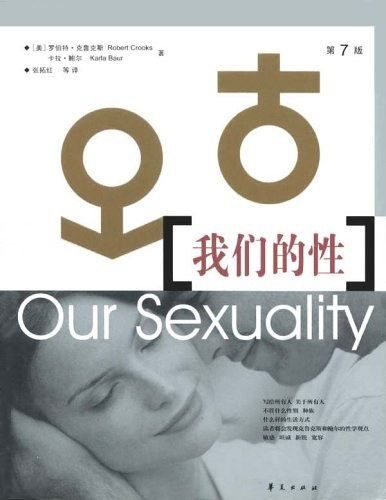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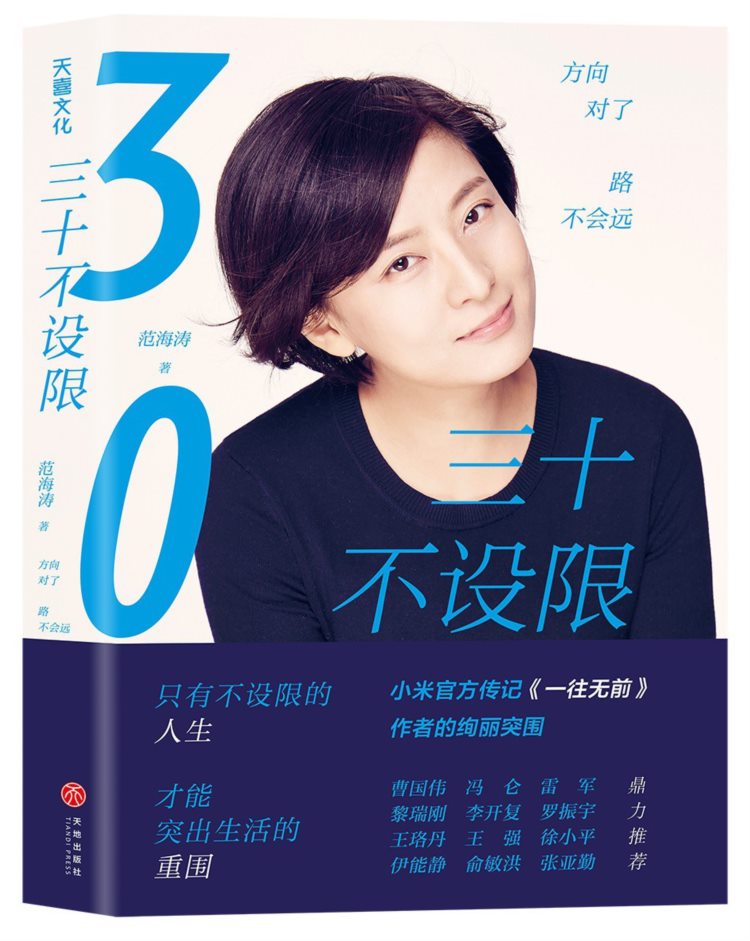

发表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