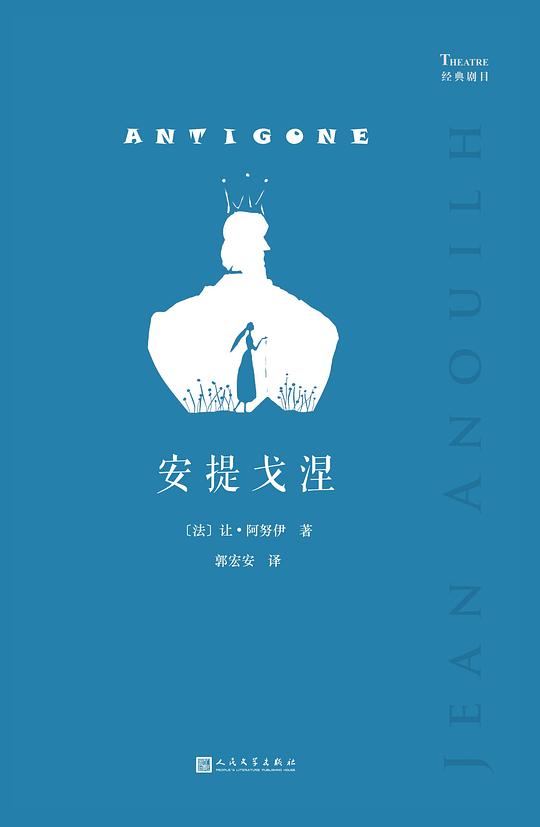
安提戈涅:古希腊悲剧代表作
书名:安提戈涅
1
0

搞笑小丑 2023-10-19 17:47:54
在克瑞翁和安提戈涅这两个人的对比中,我们看到了生活本身的荒谬和人们对于幸福的追求。克瑞翁认识到了生活的荒谬,并选择了接受荒谬而活,他相信活着就是让荒谬存在,就是见证那种没有希望和慰藉的生活的人。他鼓励人们去享受跳舞和运动,追求幸福和成功。同时,他也清醒地承担起被统治阶级施加的重负,他明白必须有人来驾驶这艘充满罪恶、愚蠢和灾难的船。
然而,安提戈涅却拒绝接受荒谬。她追求绝对的自由,坚持不妥协的幸福。如果这些都不是纯粹的,那她宁愿一无所有。她拒绝了解大人世界,因为她比别人更加敏感于生命的美好,并因此在受伤时痛苦得更厉害。她的容颜娇嫩,但却早在出生时就已泛白,她天生不合时宜,不得不时刻为此受苦。安提戈涅无法忍受克瑞翁谈论幸福。并非因为她拒绝幸福,而是因为她太渴望、太了解幸福。只是,她认为忒拜城里不可能有她心目中真正的幸福。
克瑞翁所说的幸福,是指衰老时的慰藉,是放弃自由的妥协。就像宗教法官剥夺了人们的自由,却给予了面包一样,这是跟随者的幸福,而不是反叛者的幸福。这是卫士们的幸福,而不是安提戈涅的幸福。安提戈涅是纯洁无邪、非此即彼的存在,世俗的幸福无法与她相比。
最终,我们走出剧院,醒悟到我们在人生这场虚幻的戏中受骗。我们以为我们步入了一个新天地,实际上我们只是做了一次虚假的移动。我们以为看见了自己,而实际上只是看见了自己的影子。我们像被困在洞穴中的人一样,闭着眼睛想象外面的美好,从而舒适无比地满足自己的自尊,毫不费力地拥有一切。然而,皈依并没有产生,因为皈依必然伴随着某种程度的暴力和痛苦。解除了禁锢,我们却依旧停滞不前,移动只是虚幻。
我们带着贪恋,追求着我们要去哪里。我们作为人们在“是”和“不”之间徘徊不定,我们的灵魂应该归向何方?幸运的是,我们从未将酒、药、声色视为解药,我们找到了艺术的疗愈之道。然而,艺术仍然离不开人,我们渴望被人理解,渴望某个特定的人在血缘关系或其他唯一性的联系中深刻地理解我们。这或许就是生命的意义。最终,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仍然是爱,对生命的爱、对自然的爱、对艺术的爱和对人的爱。这些或许有时被看作欺骗,但它们是永恒的。
相关推荐
萤火谷的梦想家
艾莉森•麦吉出生于1960年,是美国《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同时也是大都会州立大学创意写作课的教授。她的作品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并出版,也曾被提名普利策奖,并获得苏斯博士奖金奖、克里斯托弗图书奖、美国 [美]艾莉森•麦吉/[美]克里斯托弗•丹尼斯/绘 2023-03-27 16:50:25鬼马女神捕1·绝密卧底(上)
腹黑凤凰vs毒舌鸡妖——蓝翎:“小姬,跟我去人界吧!”姬十四:“干吗?让人宰了我做小鸡炖蘑菇吗?”蓝翎:“不啊,让妖怪宰了你做小鸡炖蘑菇更气派。”凤凰蓝翎和鸡妖姬十四生活在无忧无虑的灵界。他们的故乡叫 郝天晓 2023-04-17 00:22:47© 2023-2025 百科书库. All Rights Reserved.












发表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