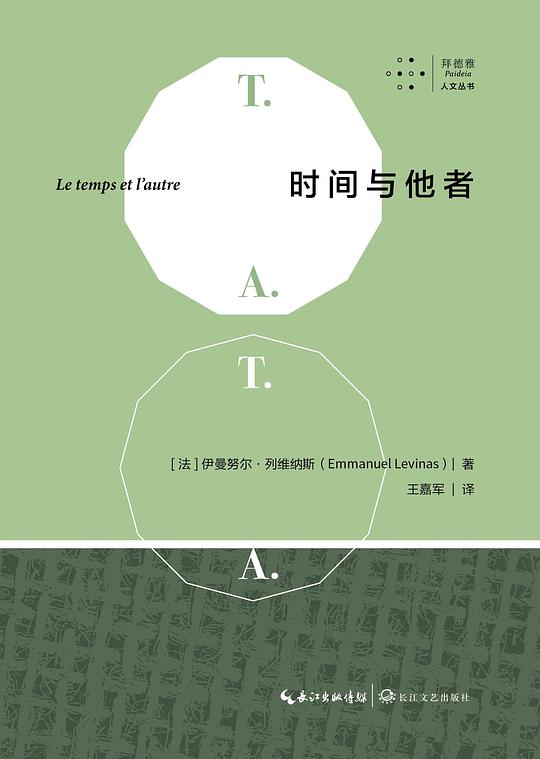
"时间与他者:书中感悟"
书名:时间与他者
1
0

暴躁小刺猬 2023-10-02 20:29:53
在《时间与他者》中,列斐伏尔阐述了他要回答的问题:“时间并不是一个孤立和单一的主体的所作所为,而是主体和他人的关系本身。”我们通过理解时间来理解主体与他人的关系,或者通过理解主体与他人的关系来理解时间。
列斐伏尔认为,实存本身就是孤独的。实存是一种“前存在”,它不是任何东西,不具有任何意义,它是一种没有意向性、没有关联性、绝对不可传递的元素,只能在自我中存在。
对应于实存的是实存者。实存者“把捉”着实存,将权能施加于实存之上,对实存者进行掌控,列斐伏尔将其视为“男子气概”的体现。
实存者对实存的掌控是孤独的来源。“孤独正是实存者的统一体,在实存中有某物这一事实。”
然而,我们往往处于实存者与实存并没有结合的状态中,这种状态在海德格尔那里被称为“被抛弃”或“被遗弃”,没有实存者的实存,一切都回归虚无。
与海德格尔的虚无不同,列斐伏尔将其视为“匿名”的状态。匿名状态不是无,而是“有”(ilya)(前存在),这种实存的匿名性如同失眠,没有起始点也没有结束点。如果实存是永恒的、绵延的,那么有(ilya)则排斥了永恒,它是“所有自身的缺场”,代表着“无自身”,没有限度。
在没有实存者的实存时刻,列维纳斯认为是“实显”被产生的地方。“意识是与ilya中之匿名警醒的断裂,它已经是实显了。”实显产生于匿名断裂的时刻,它是一个裂口,成为事件,转瞬即逝的瞬间,其中产生了时间。
此刻,实显就是自由,这种自由不是尼采意义上的自由意志,而是“开始的自由”。相较于男子气概的权能,此时的实存者对实存的把握是自由的关系,这与之前提到的孤独的把握不同。
在孤独和自由两种实存者掌控实存的模式中,我们发现,同一性既是一种从自身出离,也是对自身的回归。
实存者需要将自身安置在某处,因此必须具有物质性。物质性代表着主体的责任。这种物质性造成了不可避免的孤独,但与海德格尔的焦虑不同,列斐伏尔将其视为“一种为物质所萦绕的日常实存的伴随物。”充满物质性的日常生活不是堕落,不是对形而上学的背叛,而是对拯救的关切。
列斐伏尔将这种关系称为“享受”,既吸纳日常生活,又与其保持距离。
唯有死亡可以打破实在和实在者的关系,死亡昭示着主体不再是掌控者,是一种界限,不可把捉的。面对死亡,主体丧失了掌控的权能。
在死亡尚未来临之前,不是产生虚无焦虑感的原因是要面对死亡、被抛弃,而是劳作的痛苦,即受难。受难是不可避免的,“受难就是虚无的不可能性”。
在受难的过程中,在死亡的压迫下,我们看见了他者。只有已经通过受难达到孤独的紧张状态,处在与死亡关系中的存在,才能与他者产生关系。“主体是现在,而死亡是将来,他者是现在和将来之间的事件。”
与他者的关系是一种战胜死亡的企图,时间就是与他人的关系。
主体与他者的关系是神秘的关系。他者不像主体那样拥有实存,他对我的实存的支配是神秘的。主体不能掌控他者,他者与主体的关系永远不可能融合,他人之所以是他人,是由于其他异性本身。他异性是一种非交互的关系。
如何进入与他人的关系,使自身不被他者压垮?实存者对实存的掌控与主体与他者的关系不同。主体与他者的关系是神秘的关系,主体不能掌控,是神秘的,同时,他者与主体的关系永远不可能融合。实存者在爱欲中看到了与他者产生关系的可能性,从女性的躲藏与羞涩中看到了掌控的不可能。爱欲是存在方式,是对日常生活的吸收,同时与其保持距离。
只有通过受难而达到孤独的紧张状态,并处在与死亡关系中的存在,才能与他者产生关系。与他者的关系是一种战胜死亡的企图,时间就是与他人的关系。
光和理性是主体对自身的超越,尽管它们不会使主体成为他者,但它们是一条救赎之路,不会回归到出发点。
父子关系是主体对自身的超越,它是一种回归,关于自我的束缚与自由的辩证回归。
在读文本的过程中,我看到了列斐伏尔的纯真和柔情,因为指明本身就是一种突破口,为性别主义者带来了突围的切口。他对羞涩关系的肯定可以理解为对他者、对多元性的柔情。
相关推荐
萤火谷的梦想家
艾莉森•麦吉出生于1960年,是美国《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同时也是大都会州立大学创意写作课的教授。她的作品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并出版,也曾被提名普利策奖,并获得苏斯博士奖金奖、克里斯托弗图书奖、美国 [美]艾莉森•麦吉/[美]克里斯托弗•丹尼斯/绘 2023-03-27 16:50:25鬼马女神捕1·绝密卧底(上)
腹黑凤凰vs毒舌鸡妖——蓝翎:“小姬,跟我去人界吧!”姬十四:“干吗?让人宰了我做小鸡炖蘑菇吗?”蓝翎:“不啊,让妖怪宰了你做小鸡炖蘑菇更气派。”凤凰蓝翎和鸡妖姬十四生活在无忧无虑的灵界。他们的故乡叫 郝天晓 2023-04-17 00:22:47© 2023-2025 百科书库. All Rights Reserved.












发表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