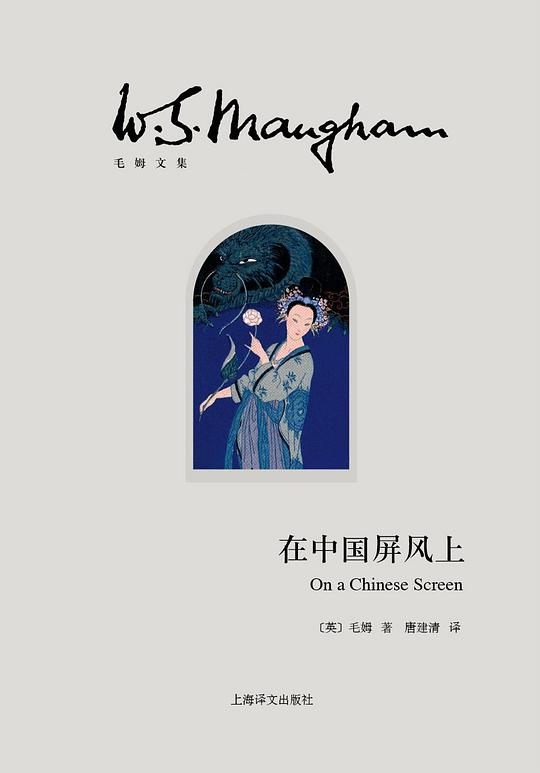
《在中国屏风上》毛姆眼中的中国
书名:在中国屏风上
1
0

红颜祸水 2023-09-20 19:42:51
毛姆的《中国回忆录》描绘了他在1920年农历春节期间穿越中国的旅行,就像一幅色彩鲜艳的水彩屏风一样,将中国的壮丽山川和庞大人口在历史长河中瞬间固定下来。
与绘画家的屏风以山水画为主不同,小说家的屏风应该以人物画为主。事实上,在毛姆通过文字描绘的中国屏风中,人物通常是前景,而山水则是远景。这些古老神秘的异国天空、大地、江河、道路和建筑构成了一个广阔而深远的文化视角,欧美旅行者乘坐远洋帆船越过子午线或换日线,首次从东方地平线上探出头来。外国的使节、传教士、修女、银行家、船长、汉学家以及本地的官僚、哲学家、商人、戏剧家、工人,这些身处不同阶层、职业和个性的人们共同生活在两个文化群体编织的世界中,毛姆对他们的生活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中国屏风像小说一样一页一页展开,默默地为读者讲述他们所见所闻。
在东西方文明经历早期激烈碰撞后,已经进入了一种更加复杂和和平的融合模式。这既是一个日渐互联的世界,也是一个新的世界。封闭数千年的中国开始向世界敞开大门,陌生国家的人们涌入这个地区,改变着这个地区。首先是沿海口岸,然后是长江沿岸和北方重要城市,随后是四川、内蒙等边远内陆地区。人口、商贸、科技和文化的交流方向和结果都是复杂的:中国通过建设铁路系统将自己融入世界;高耸入云的教堂将乡民的信仰从法律界引入天堂。
艺术作品中的人物和景色不仅仅是简单呈现,而是经过艺术家有组织地再现。毛姆在序言中说,他在描绘屏风时注重个性而不是素材。这意味着屏风上的景色是经过艺术家精心选择的,前景的人物和远景的山水并非无意呈现,因为作者在创作过程中的自由选择,有的清晰可见,有的则暗淡无光。未经加工的景观呈现第一层真实,通过光影处理的景观呈现第二层真实。
本书的译者在后记中指出,屏风既是呈现也是遮蔽。这是确实如此。因为对于过于熟悉的对象,先入之见会阻挡我们真正发现的视野;相反,对于陌生的经验,人们往往会不自觉地使用既定的认知模式,再次陷入先入之见的陷阱。因此,屏风成为视线的隔断,阻止观赏者真正进入画中人物的生活活动,理解他们所构建的世界。不可否认,这是外国观察者很难克服的文化障碍。
毛姆一贯的幽默可能会冒犯敏感的中国读者,毕竟在我们所熟知的历史叙事中,中国直到1949年所经历的要么是屈辱,要么是对抗屈辱。任何列强对殖民地人民及其文化微表情的表达都无疑来自于他们的傲慢。但是,如果读者仅仅因此而看不到作者对江边纤夫的深切同情,看不到作者对他所热爱的英国同胞的不恭瞒骂,那将再次陷入先入之见的陷阱。
现在,历史的洪流已经过去了100年,通过时代的滤镜,当我们通过毛姆这扇中国屏风回顾自己的国家时,或许我们可以在心中唤起像毛姆初次观望长城时那片模糊而神秘的薄雾。屏风既有实用功能又有审美价值,是器具和艺术作品的结合,因此屏风都是双层的,一层是真实,一层是美丽。我们对中国卷入现代世界体系并在求生存中苦苦挣扎的这段历史距离既不远也不近,此刻透过这扇屏风,也许可以在我们已经远离并模糊了细节的历史中重新思考,同时也可以在我们可能过于亲近的历史中保持距离、抛开偏见,以审美的眼光重新审视。
相关推荐
逆天的冒险
我们是天生的冒险家,对冒险的爱从不会离开我们,直到我们迈入垂老之年。”博莱索写道。他认为,“胆小的老头子,在他们的兴趣当中,冒险应该是绝灭了的。”这也是为什么诗人们偏爱冒险,而法律通常是老年人制定的原 (南非)威廉·博莱索 2023-04-10 05:12:26笔误:文学大师的秘密生活
爱伦·坡小时候曾在一个墓地里上学?马克·吐温曾当着维多利亚女王大谈放屁,是怎么回事?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在派对上双手趴在地上,像狗一样大叫又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认为,作家应该是正襟危坐着写书的人,但《笔 (美国)罗伯特·施耐肯伯格 2023-04-10 10:13:49© 2023-2025 百科书库. All Rights Reserv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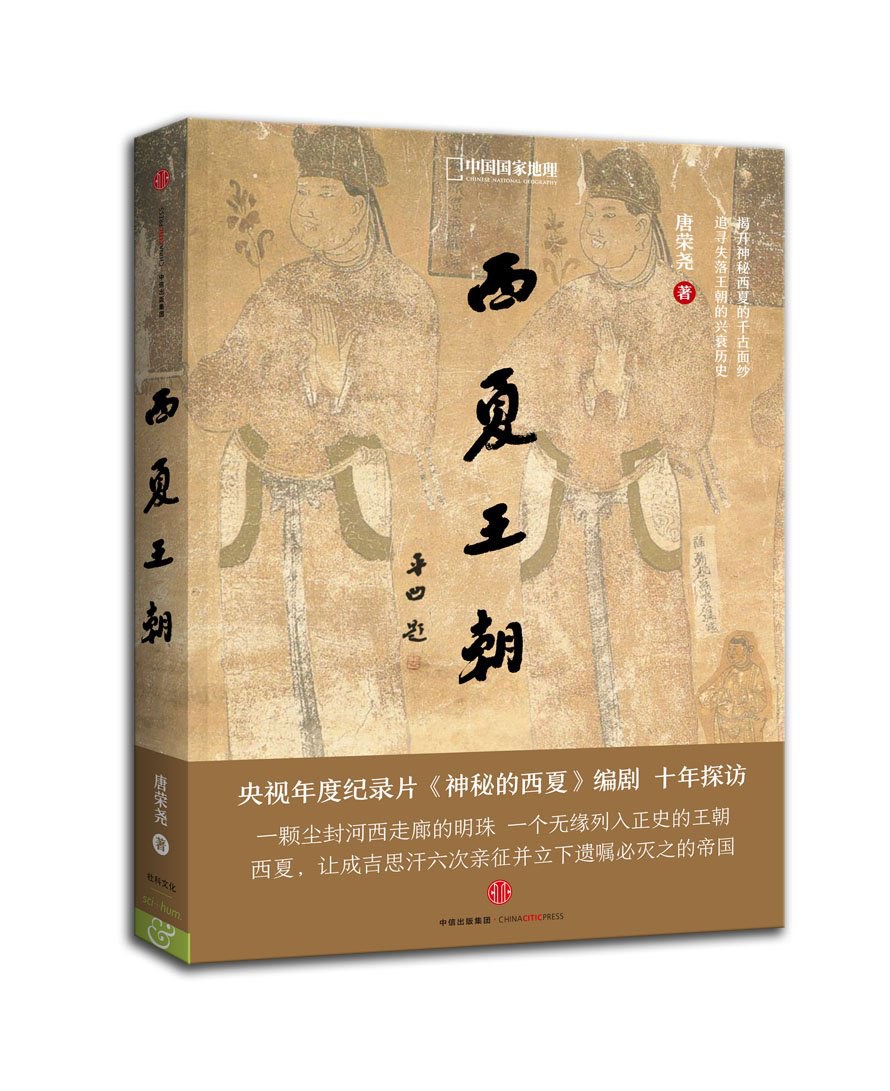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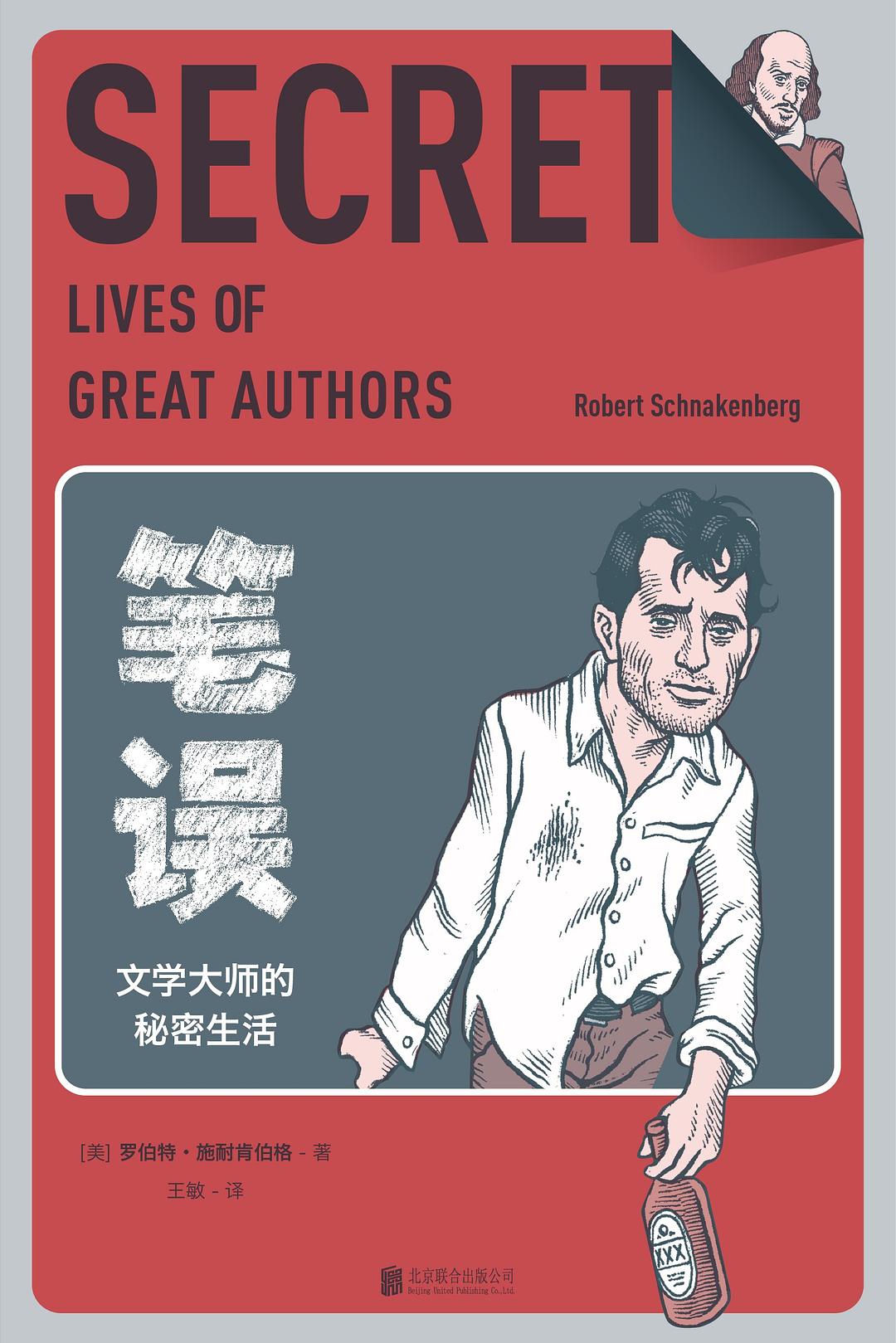
发表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