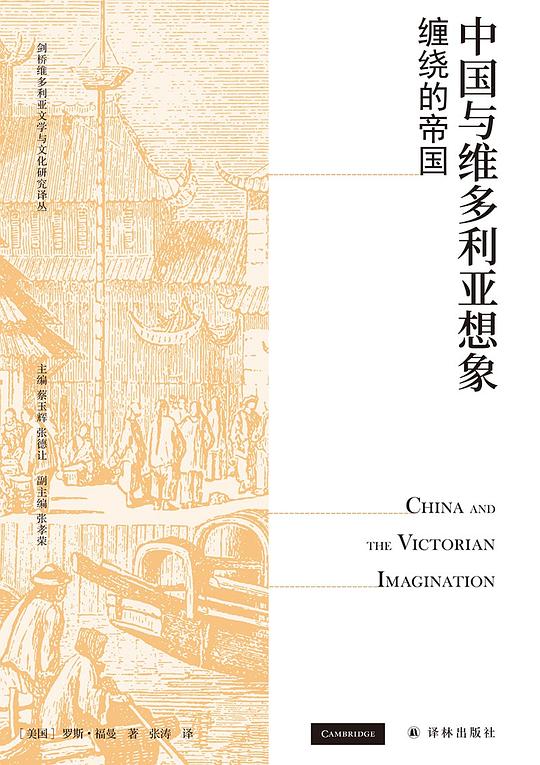
《中国与维多利亚想象》中国帝国的想象力:维多利亚时代与中国帝国
书名:中国与维多利亚想象
1
0

坦白书 2023-09-14 12:08:51
作为《剑桥19世纪文学与文化研究》系列丛书的总序,主编蔡玉辉的讲述让我大有同感。“或许是当读年月缺书甚至无书可读染上了阅读饥不择食症,或许是大学后期抢座阅览室形成了阅读狼吞虎咽的陋习,或许是求学过程中广泛涉猎养成了不拘一格的阅读偏向,每每遇到内容杂富、视角多维、述论复调、方法跨界、见解独特的读物,都会产生一种必欲厘清的冲动,恋恋不舍的情愫。细究起来,这种遇杂而珍、向杂而趋、融杂而合不只是个人的阅读偏好和价值取向,也不仅是学科发展走向繁荣之途,还有着更为普遍的客观依持,存在于自然世界的演化过程,也存在于人类社会从点到面、从聚到散、从低到高、从单一到复杂的嬗变过程,尤其是贯穿于文化产生、传布、交汇、融合的全过程。”
这套丛书的中文版目前只出版了五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中国与维多利亚想象》。对于从文学还原历史中的社会环境,我国读者并不陌生。历史学家们通过对《红楼梦》素材来考证封建社会中古人的风土人情、饮食文化、中医中药、诗词歌赋、园林绘画、官僚作风、语言风格、穿衣戴帽等细节。另一本不输于《红楼梦》的经典是《金瓶梅》。我之前读过《物色:金瓶梅读“物”记》、《食货《金瓶梅》——晚明市井生活》。《金瓶梅》中所提到的物件,比如各色金银首饰,还有其他各种生活用具,乃至各种“淫具”,都是可以通过考证的。同理,《金瓶梅》中的各种“食货”,也就是经济活动,也可以反映当时百姓的社会环境。而《中国与维多利亚想象》所记录的,是大英帝国最鼎盛时期,对中华文明的文学构建。
在19世纪,罗伯特·马克利就指出:“在西欧,没有一个有文化的男人或女人会不知道英国和中国的相对领土大小、财富和自然资源……中国已经成为各个领域竞争和投机的重要场所。”当时的英国人对于中国未来的想象基于两种路线,可以由贝蒂和贝雷斯福德的小说来分别举例:贝蒂假设在1960年时,整个亚洲东部都将是chindia,届时如果从查令十字街乘坐时速超二百英里的列车出发,花费五十个小时便能抵达宗主国最东端的直辖殖民地,香港;贝雷斯福德则认为“维持中国人的帝国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利益和荣誉的关键”,这也是英国政府的观点:支撑住清王朝,不允许中华帝国崩塌,以保护维多利亚政府在这一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但最好避免更直接的干预,尤其是在经历“义和团事件”之后。
19世纪40年代以来,外国人便纷纷涌入“洋中国”进行工作。“洋中国”中最重要的部分便是参照了印度公务员制度的大清海关。围绕大清海关的历史性叙述长期以来强调这一机构的特殊性,它出现在中国的自治范围却由外国人运作。如果没有外部的、欧洲的帮助,清政府便无法实现财政现代化,也无法克服腐败的问题。围绕大清海关形象的关切和矛盾,特别体现在海关的领导者身上。里弗斯的《人形神圣》表现了这些矛盾的对立。故事讲述了一名上海商人和一名港口领事的争斗。商人直接觉得通商口岸的苦力在女士前光着身子工作是一种非常冒犯的行为,至少应该“穿上裤子”,而领事则遵从当地的习俗认为这一行为是合理的。商人的形象表现得仗势欺人,而领事的形象却表现得十分“亲华”,非常关注人权。
在小说《鸦片箱》中,21岁的马克思先生负责管理吴江港的库存,在这之前发现了一种可疑的谋杀案,冒着巨大的个人风险,马克思发现并击败了一个鸦片走私团伙。然而涉嫌的沈先生却提前支开了马克思上司布尔,并将这份功劳占为己有。马克思的年轻鲁莽自然受制于中国人的狡黠,但最后他还是保护了大型海关。读者明白,中国人的天性是狡猾、算计和自私,而英国人的特性是勇敢、耐心和外交技巧。这些小说通常是受雇于大清海关的年长男人,写作关于刚刚来华的西方人和其他年轻人,他们因误解“洋中国”和“主权中国”之间的界限而陷入麻烦,所引发的滑稽和尴尬的遭遇。“洋中国”是文明的、进步的空间,而“主权中国”则缺乏活力、一片黑暗。小说的主人公就穿越在两者之间冒险。
温的故事《在中国的一次冒险》则打开了一个缺口,显示英国暴力是偶然的、没有明确目标的,而中国暴力是有目的的、直接针对外来者的。一位外国船医在中国打猎,被当地农民阻拦,医生执意向雏鸡射击,子弹打瞎了一旁的农民,当地官员带领农民暴动,最后船医从中国人眼中取出了21粒钢珠,给他扎了绷带,并给出了足够的补偿。于是,书中感叹“在中国内陆射鸡比在印度射老虎更危险”。这个故事表达了双重否定差异。第一,否定人和禽兽的差异,体现在医生被农民包围时仍向雏鸡射击。第二,也否定中国和印度的差异,因为这个件事无论如何不会在印度引发暴乱。事实上,从历史上看,那时的官员不可能完全无视谋杀这些英国人的后果,1897年两名传教士被杀就使得德国人获得一个殖民港口,胶州。
贝蒂的《截获的信件》中写道:“据我所知,香港的人口大约由我的丈夫威廉和大约300人组成,其中没有一个是中国人。”这从社会方面重申了1898年版的地理编年史,”当英国国旗悬挂在据点之前,几乎可以说这个岛没有什么历史。“所以异族,包括当地人和其他欧洲人在帝国描述中的香港被抹去。达克齐尔在香港写了小说《英国直辖殖民地编年史》,其中涉及了跨文化的爱情和欧洲内部合作。小说指出了正式帝国主义与非正式帝国主义之间的联盟关系,以及二者之间的松散过渡。世界各地殖民主义以典型的方式相关联,而除去精英阶层中的爱国主义觉醒人士,非正式帝国对普通中国人来说几乎不可察觉。然而,因地域和流通方式不同,帝国文本的功能不尽相同;塑造的作品以不同的方式对话不同的读者。
评论界强调“禁止通婚”,在英国统治战略中居于中心地位。越来越多的历史资料表示这种禁止只是假设,而不是实际。更多的属于官方口吻,而不是实际民间发生的。威廉·多尔顿于1864年的小说《黄蜂的海洋》,作品中的主人公男孩赫伯特拥有一半英国血统,一半中国血统,他最好的朋友迪克也是英勇的混血儿,也是美国和英国的背景。混血儿的出身给予他们独特的机会来表现他们的英勇。直到维多利亚时代结束,这种种族认同的流动性都没有消失。《英国直辖殖民地编年史》记载了各种各样不同阶层的欧亚混血儿或者次要的在种族上被怀疑的欧洲人(葡萄人)。然而,他们的性格证明他们比英国人更优越,对男性来说这种优势在商界表现得尤为明显,而女性则卓越体现在宗主国的家庭影响方面。
然而,对香港的描述背后的修辞,可以说是用帝国差异性来替代帝国相似性的乌托邦。香港的混杂性被东西方共同侵蚀。理论上讲,混杂性导致双重排斥,东西方都鄙视中英混血儿。因为这些通婚者拒绝了两个强大纯正的血统的典范。几代人(如对加勒比、拉丁美洲实施)的“漂白策略”,在香港对确保社会、法律、经济利益几乎没有作用。小说《肤色界限》中,爱丽丝面对自己的中英混血孩子,会对其身体特征进行充满厌恶的类比。她在自己孩子身上看到了一种完全的“令人反感”的自我丧失。这个婴儿完全是一个肮脏、污秽和贫穷的中国民众。这种叙述有着连续统一体的模型,解释了纳妾是如何与科学种族主义相结合的,或者一个白人女性如何爱上一个欧亚男性,与他结婚,然后抛弃他。
19世纪末在中国最震惊西方世界的,莫过于义和团事件。新世纪的第1年开始,大量义和团主题的文艺作品(包括电影),进入到了英国本土市场,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这些文学叙事所塑造的形象中,义和团运动以民粹主义为基础,因其对资本主义和交换原则的抵制获得重要意义。文艺作品中刻画群众暴力和社会停滞之间的关系。让马克思曾预言亚洲的对殖民者的反抗将会同时在欧洲引发工人阶级起义。即将到来的起义被牢牢地置于英国自己的历史背景之中:东方历史只是另一个西方历史的叙事。这些故事通过使用维多利亚时代晚期关于英国城市工人阶级的描述中常见的暴民、不守规矩和兽性的术语,巩固了中国和西方之间的这种相互关系。即使它们没有明确地提到英国工人阶级,术语上的重叠也是惊人的。
而几乎所有关于义和团小说都有这样一个场景,伪装好的英国人通过伪装成中国人逃入避难所(使馆)。此类小说都是由青少年假装成中国人,在使馆与部队之间传递信息。男孩们身体无毛,皮肤光滑,头发较长,这些都是与女性相似的中国人特征。然而男孩的少女外表,只是他们发育的一个阶段,最终能长出胡须。小说结局通常会给男孩发一个老婆以昭示成年。但是,中国男性则停滞在青春期身体发育的水平,与停滞发展的文明一样。令人惊讶的是,这个话语暗示的中国人在男性气质上偏差,实际上避免对欧洲女士的性暴力问题,这与1857年在印度兵变的情况相比有所变化。刻板印象里。大脚长、鼻子、白皮肤的女性难以引起中国人的性欲。也许对中国男人的女性气质和性衰弱的描写,阻止了这种虚构故事。
为了重申自由贸易和公平贸易的帝国主义。小说中常见的桥段是,男孩在伪装成一个本地人时会偷听到中国人对“洋鬼子”的误解。小说不断设置此类对话:英国的动机被误解了,他们想要的贸易不是战争;只有当他们的贸易受到干扰和他们的人民受到虐待才会开战。《红色北京的故事》中提到慈禧太后用邪恶巫术误导了无知的农民,灌输了外国人导致干旱的谎言。对皇太后的诋毁有利于维护帝国的意识形态目的:由头目象征的中央权力机关的腐败和颓废引发起义;然后敌对帝国必须出面调解,以恢复秩序。《红色北京的故事》一开始就告诉读者:“中国人是极其残酷、非常狡猾和虚伪的,但父亲说可以使他们成为极好的基督徒”。因此,义和团的特征是“像魔鬼附身一样”。此类小说叙事中经常将中日合并为统一的反欧战线。
然而,在义和团运动之后的几年中,民众的情绪发生了转变,尤其是在大众文学领域,乐观的情绪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强烈的恐惧感。在珀西的《当东方遇见西方》这部小说中,一开始就总结了这种转变,宣称道:“我想,我们很抱歉曾资助过黄种人。”而在马修的《黄色浪潮》中所言:“日本是头脑,中国是身体,二者在一起形成了大力神赫拉克勒斯。”中日联盟所代表的超级威胁被视为天朝与日本之间天然的“种族忠诚”的复兴。反观这些帝国主义的文本,这些故事几乎总是以伦敦作为背景或全部背景。故事涉及发掘一个隐藏的帝国文字和比喻中心的“黄色魔鬼化身”,其典型形象就是“傅满洲”。“大东方”是“大英国”的真实写照,他们在这些文本中表现了密谋统治世界。
这些小说往往将“黄祸”分为两组:第一组由知识分子和决策者组成,他们策划“黄种人”反对“白人”;第二组则是追随他们的群众。这些文本重述了义和团运动的一个关键神话,即政府官员误导暴民起来反抗外国人;然后,它引入了欧洲工人阶级内部可能发生的起义;最后,它剥夺了大众的能动性。在《假想的满大人》中,作者援引了蝗虫横扫西方的场面,即表示人口迁移。蝗虫对于持续的死亡带来的痛苦,通常无动于衷,并且能够为集体的需要牺牲自己。《黄色尖叫》的例子再次强调中国人只能大规模行动。有论述预示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亚组织技术的能力比西方更有效,但是因其贬低个人观念,东亚无法在创新方面取代西方。这些“黄色危险”是受西方教育的反面角色所做的不完美的模仿,即“半文明的工人”。
规避逆向帝国主义扩张的必然机制的唯一办法是通过新技术。这种技术采用飞艇、潜艇、生物战和其他基础的形式。尽管这些机制违反国际公约。然而,这些小说认为,无法控制的、他者的威胁允许暂停标准,野蛮的威胁使得不人道的种族灭绝的反应合理化。许多文艺作品中,为了对抗黄祸的入侵,都使用细菌战作为反击手段。由于广泛的传言说义和团运动擅长使用催眠和巫术。作为同等的对应手段,文艺作品中开始展现各种各样奇怪的拷问和洗脑手段。在电影《龙》中,黄祸定制了1.2万台电影放映机。东亚的影院们到处放着黄种人打败白种人的野蛮画面: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剖腹(有着鸡奸的暗示),语言力的丧失(割舌),亵渎神圣(在尸体上跳舞),以及野蛮的舞蹈(即狂欢展示出的身体和性交过剩)。
虽然直接提及到政治事件,如义和团运动,为英国本土的剧院提供了一个时事的卖点。然而,在流行文化中,情况也很复杂。事实上,戏剧作品成功融合了不同的东方地理位置,并在19世纪末合并了中日两国。这就好比哑剧“阿拉丁”,这些戏剧充满了从非洲到阿拉伯再到远东的东方异域风情,因其丰富的中国服饰、专制的中国皇帝和虚幻的北京和广州的街头场景而熠熠生辉。维多利亚时代的关于中国的闹剧,借鉴了哑剧的传承,共享的一个标准的意向体。观众很少了解或者并不需要了解有关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知识。公式化的中国形象和行为,比如中国长城、扣头的行为、遮阳伞的使用和“灯笼宴”等,在舞台上被传播和延续。当然对瓷器的使用也符合这些模式。中国的符号被禁锢在瓷器或者小雕像之类的刻板印象之中。
某些公式化的情节在所有剧目中反复出现。这些情节包括:盗窃珠宝和传家宝的故事,通常是由一个仆人从一尊华丽的宗教塑像中偷走的:又或是中国古怪法律引发的奇闻,尤其是那些关于婚姻方面的故事。其中最主要的是包办婚姻的桥段:一位年迈的父亲(通常是位满大人),将女儿许配给一位年老、不般配的男人,而不是女儿所爱的年轻人。面对失败的爱情匹配,有三种可能的解决方式:年轻的恋人在死亡中结合在一起,或者变成了鸽子,从而逃脱了尘世的束缚;恋人通过展示父亲青睐的求婚者有多不合适,以及女儿的选择对她本人和家庭更好,以此来逃避或克服父亲的反对;少女爱上了来访的英国人(英国军官),要么是结交了英国朋友,这些英国朋友随后介入,将少女从她被许配给的老头子手中解救出来。
许多关于中国的戏剧,都提出要把中国人逼到“合适”的位置。壮观的表演,特别是预先准备好的战斗、爆炸和特技,展示了英国人以适当的戏剧性和令人兴奋的方式来传授他们的人性课程。随着维多利亚时代的前进,英国巩固了对亚洲领土的控制权。戏剧舞台变得越来越不同情中国人,爱国主义的胜利被用来为更荒谬的舞台暴力辩护。鸦片战争在戏剧中的起因也从一场误会慢慢转变为中国咎由自取。戏剧中的另一个政治桥段是批判中国人杀女婴。《中国母亲》中一位爱尔兰女子偶然去往香港,最终为被遗弃的女孩建造了一所以修道院为基础的孤儿收容所。这部戏既维护了女性权益,也赞美了迅速壮大的传教士队伍。这种对中国信仰的刻画伴随着一些对佛教及其嗜血仪式的极其奇怪的描述(一个角色惊呼道,“佛陀爱血”)。
1878年,英国著名驻华外交官麦华陀在撰文为中国移民的辩护,之所以中国移民普通给人的印象是邪恶的,这种印象源自白人定居地的中国移民出身于下层阶级,而非他们本质上的中国人身份。麦华陀支持中国移民成为帝国劳工计划的理想劳动力。有一批作家带着对中国主人公不同程度的同情,声称要描绘出华人社区主要聚集的伦敦东区的未知世界,并利用“东方伦敦”的神秘和危险,创造出一种东方歌特式文学(莱姆豪斯文学)。这些作品开始考虑中国人在伦敦的实际生活方式以及对所带来的政治影响。在现实中他们都被同化了(与英国女子通婚),他们在伦敦东区广受尊敬,被认为是冷静、勤劳的店主,接待到来的亚洲海员。莱姆豪斯文本还强调了中国人对移民、贫困和酗酒过度集中的东区经济的贡献和分化。
西姆斯的《伦敦的李廷》系列就是典型的莱姆豪斯文学这篇小说化用了政治领袖孙中山时代在伦敦中国公使馆被囚禁的故事,与检验有关移民地位的普遍假设。李廷在伦敦码头工作,然后与老板的女儿结婚,经营了一家业绩良好的二手家具商店,从而致富,然而,当李廷回到中国解决商业事务时,他被单独监禁起来,故事出现了出人意料的转折,李廷因为觊觎皇位而被慈禧太后囚禁。后来李廷寻求获得了英国代表团的庇护,并回到英国与家人团聚。经过这场风波,李廷消除了自己对权位的幻想,一家人在伦敦过着平静安宁却满意的生活。事实上,莱姆豪斯的中国水手和店主对伦敦女性来说,是有吸引力的丈夫,因为用一个妻子的话来说,和中国男人在一起,“你总是确信餐桌上有好吃的,有漂亮衣服穿”。
因此,西姆斯的故事展现了其寓意:故事的主人公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成为“宁愿选择威斯敏斯特小街也不愿剖腹自杀的王子”。尽管李廷来自异教国家,但他明确地体现了新教职业道德的最佳特征:勤奋、忠诚、有节制、非暴力、献身于家庭。他专门避免了东区生活的许多灾难:拳击赛场、杜松子酒宫殿、音乐厅等。他也不会被性交易经济吸引。李廷甚至在财力允许的情况下,将他的家从受污染的东区搬到了更富有活力的西区。而且,尽管这个叙述似乎容忍了他的异族通婚行为——甚至对女儿的混血赞不绝口,她“以英国人的着装和谈吐,带有自己的中国特色,一直是商店里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但故事清楚地表明,这种促成混血的模式依赖于一种对李廷作为一名满大人的不寻常出身的潜在同情。
好了,读书笔记就写到这里,实际上这本书很多的构建手法一直沿用到现在。这里推荐一下我的另一篇读书笔记,读《美国的艺伎盟友》——蝴蝶夫人,也是文学构建史相关。
相关推荐
逆天的冒险
我们是天生的冒险家,对冒险的爱从不会离开我们,直到我们迈入垂老之年。”博莱索写道。他认为,“胆小的老头子,在他们的兴趣当中,冒险应该是绝灭了的。”这也是为什么诗人们偏爱冒险,而法律通常是老年人制定的原 (南非)威廉·博莱索 2023-04-10 05:12:26© 2023-2025 百科书库. All Rights Reserv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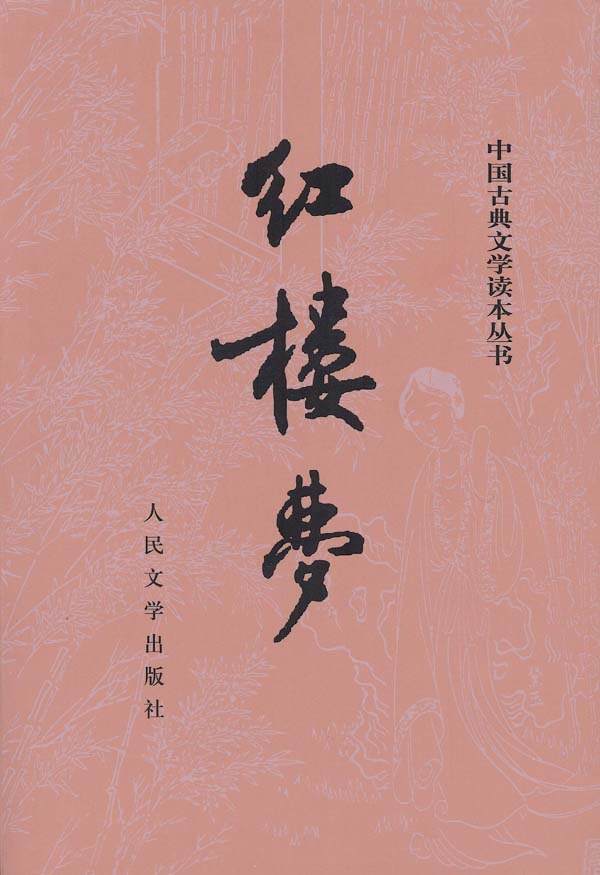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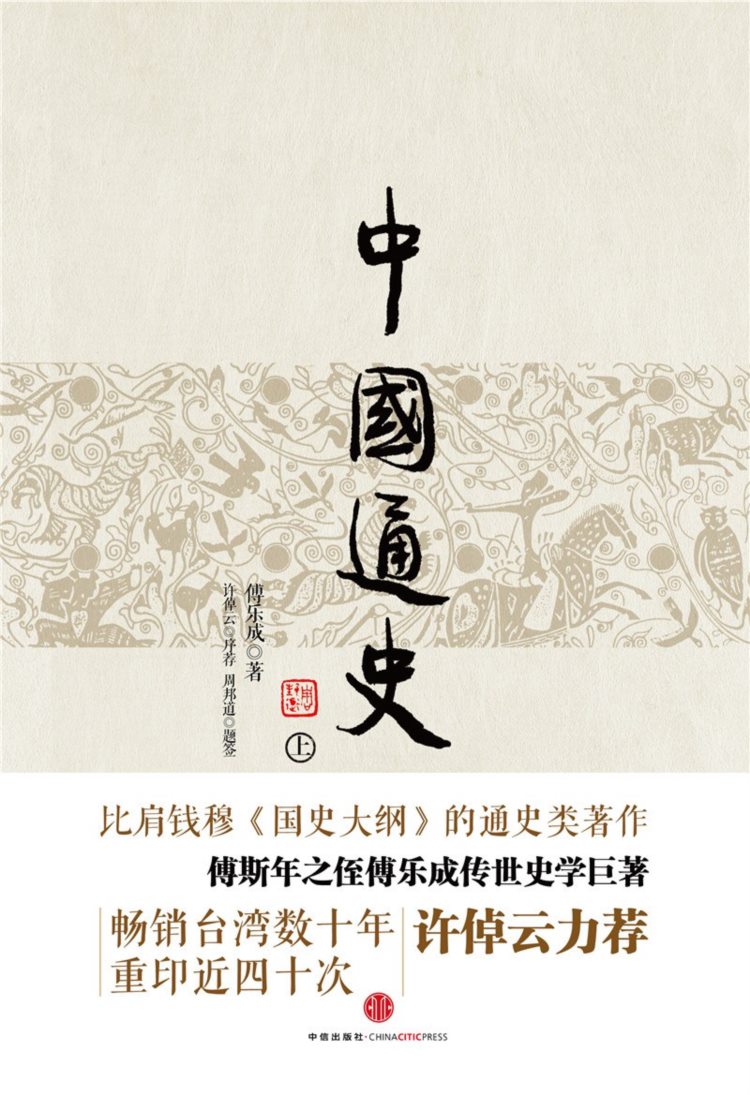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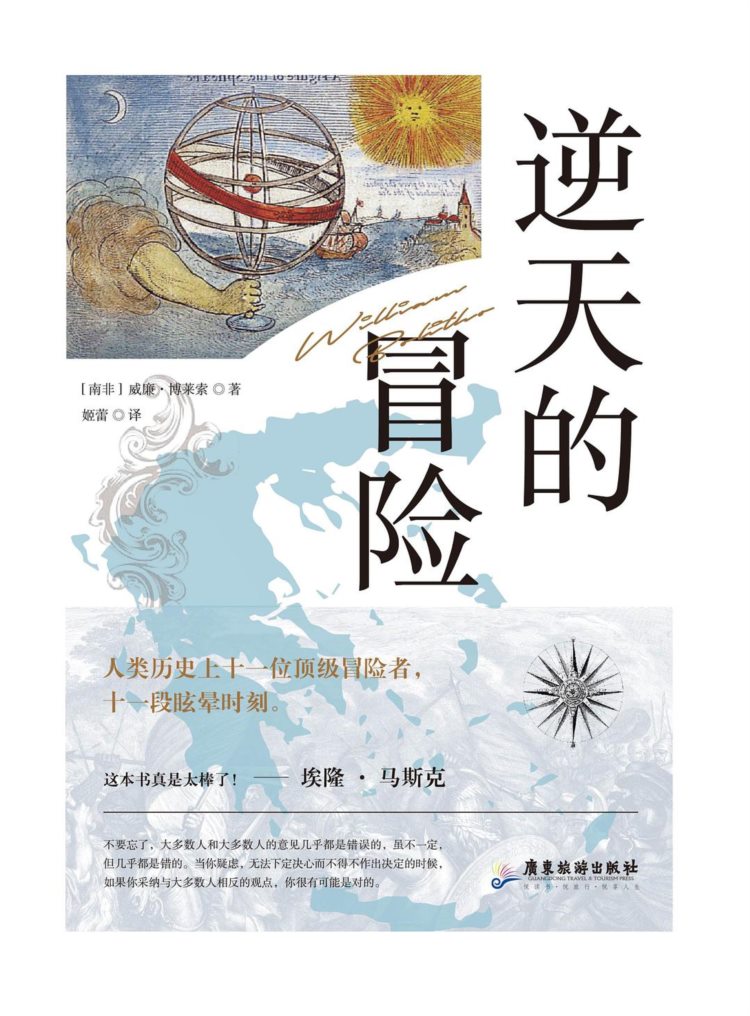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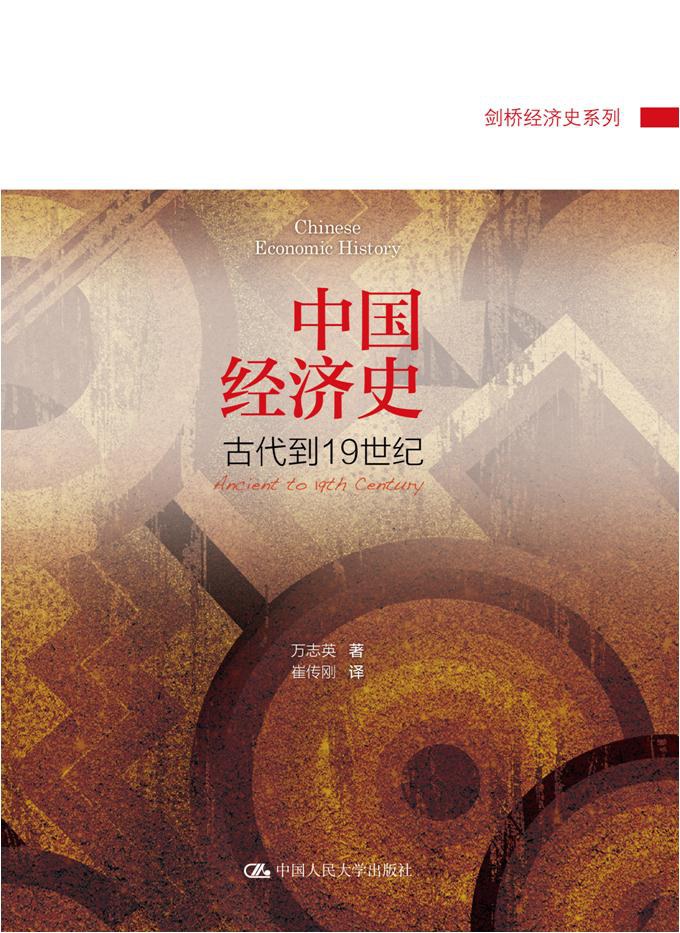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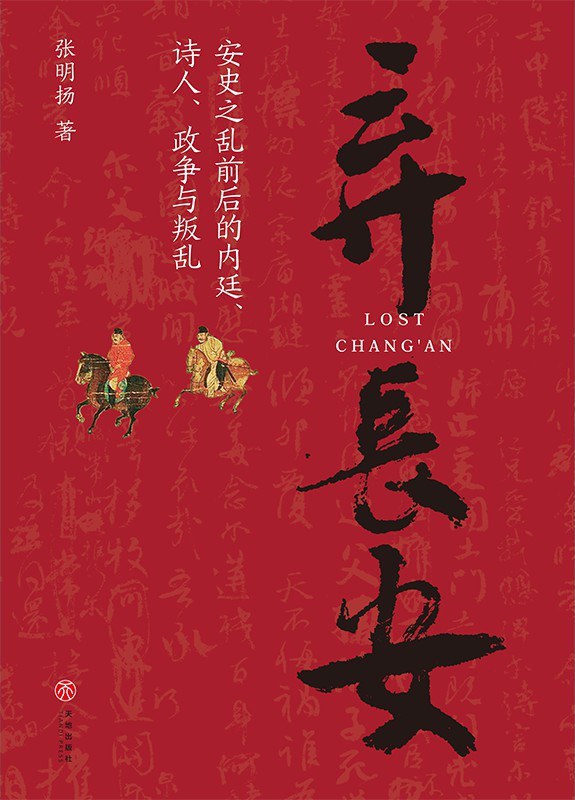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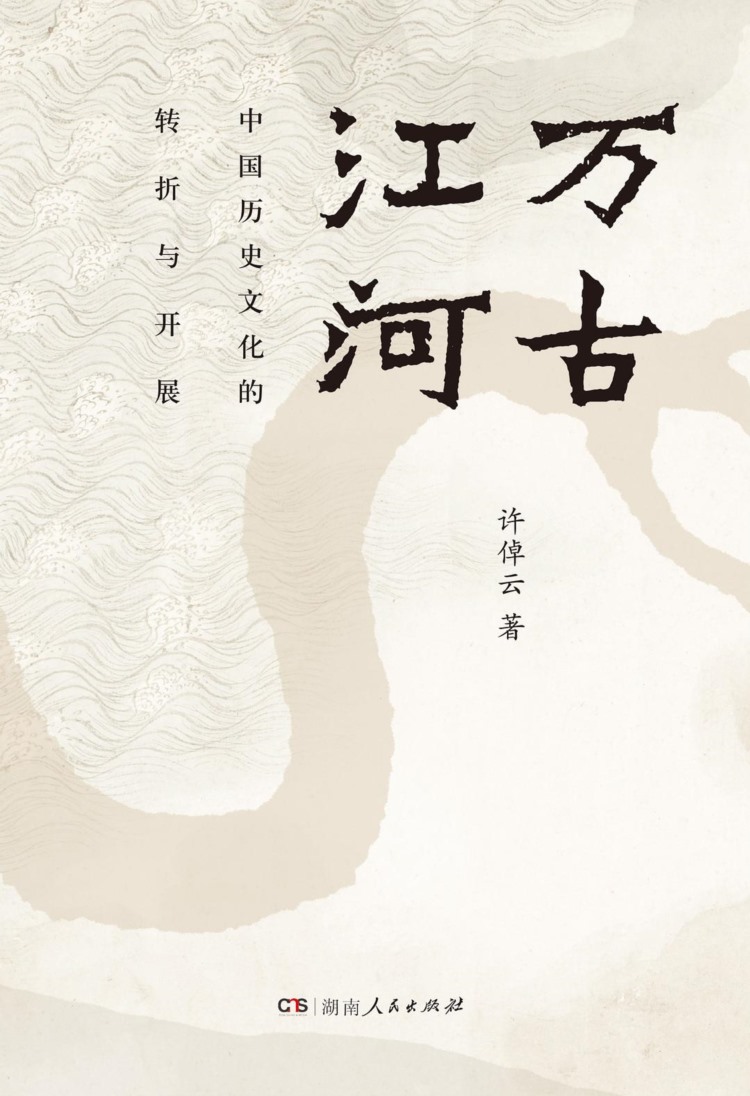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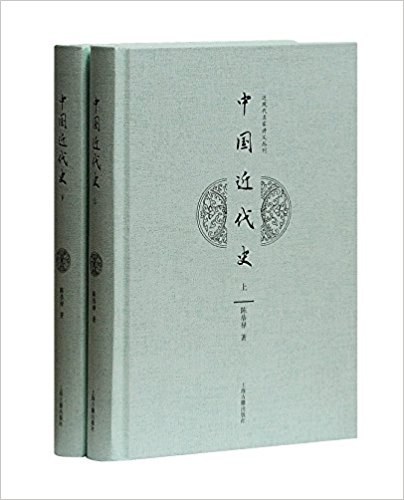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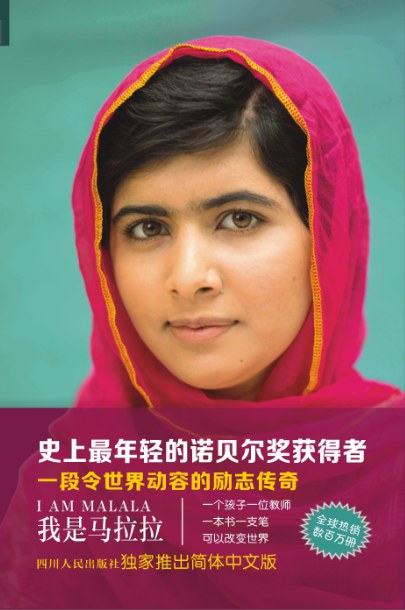
发表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