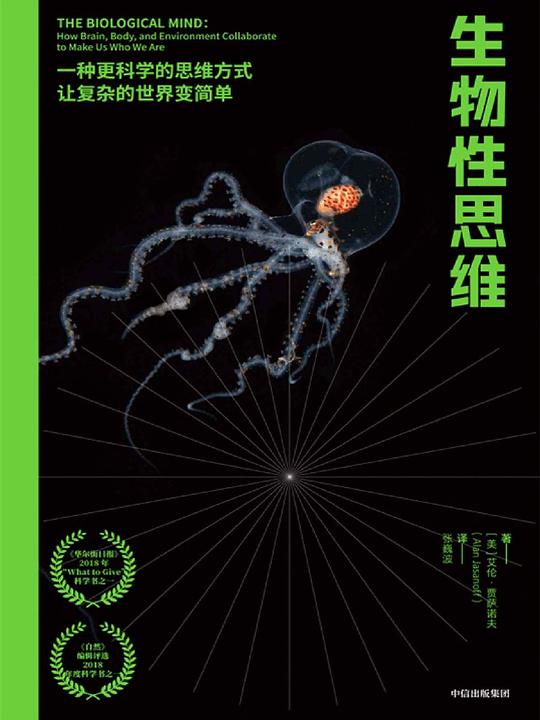
"生物性思维:身心一体与道德责任"
书名:生物性思维
1
0

萝卜白菜 2023-09-12 21:46:36
斯宾诺莎的《伦理学》探讨了存在、物质、心灵,今天来看这些都是过时的理论,受时代所局限;他关于身心一体的结论虽然正确,但是貌似是通过错误推理得到的。现在我们依然认为身心一体,简单地说是指在古典的“物质”之外,不存在“精神”这样的实体,后者是在前者复杂的结构上面涌现出来的属性、功能或效果。
艾伦·贾萨诺夫在《生物思维》中就是在说服我们去掉大脑的神秘性,我们所有的精神现象都不过是一团神经细胞实现的,里面没有隐藏着一个幽灵或灵魂。之所以会有“灵魂”的想法,是因为人们在尝试与人进行类比来理解我们头脑内的精神现象:大脑里是什么在看、在理解?由此引出了笛卡尔式的“小人”论。
吉尔伯特·赖尔在《心的概念》中针对这个说法提出反驳,他认为就像我们在大学校园里找不到“大学”这个东西那样,在大脑里也找不到这个小人也很自然。至于什么在看、在理解这个问题,他貌似认为这是个错误的提问,因此也就不用回答。但这不能让人满意。
在我看来,或许所谓的“看见”和我之前所解释的“理解”一样,如加来道雄所说,大脑相当于一个模拟器来对世界进行表征,所以当眼睛所接收的信号达到某个条件,在整个大脑构造的模型中就会当作是“看见”,就像当你对某个对象存储的信息达到某个阈值,你的大脑就把它标记为“理解”一样,不需要有小人、灵魂或其它任何东西。所以我才说J.Searle的“中文小屋”里也有一个“幽灵”在游荡。
日常我们所见是一个“人”在看、理解,推论大脑中也有个小人来看和理解,这是我们“喻”型思维的产物;这种思维就是布留尔、弗雷泽等人口中的“原始思维”,我有时把它称之为“巫术思维”。贾萨诺夫提到吃大脑的现象,有时是“以脑补脑”,就像去吃犀牛角壮阳一样,但是我总怀疑此逻辑中吃猪脑补出来的效果是好是坏;同时很多人又会厌恶吃大脑,这是因为想到了大脑的神奇,同样也是一种巫术思维。
当然,把我们的整个精神现象等同于大脑大概是不精确的,贾萨诺夫引用达马西奥等人的说法,脖子以下的身体也是整个智能的一部分,所以人们认为是“具身认知”。就日常经验而言,我们常常能真切地感到身体的反应。或许“幻肢”这类现象表明躯体问题也可能会引发大脑功能出现故障。贾萨诺夫举了一个案例,有个人进行了手术换上了别人的心脏,突然有了来自这个心脏捐赠者的感受和思想,不过这种自诉看上去并不可信,需要进一步的验证。至于玻尔马特等人的《谷物大脑》、《菌群大脑》这类“伪”科学科普基本上是在收智商税。
如果精神是生理的组织结构方式带来的现象,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改变底层的生理结构来改变其上的精神。未来,当对大脑了解得足够多,可以不仅像YuvalHarari所说的那样让拥有权力、财富的上层人士修改基因,把自己变得更高大、俊美,更聪明、伶俐,甚至还能重新设计大脑的结构以及制造“人”。假如权力拥有者想要,在技术上可制造出像蚁群中的“工蚁”、“兵蚁”那样忠于自己被赋予的角色、没有其它想法的“工具人”,到时候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希特勒的高贵的雅利安纯种种族的实现如小菜一碟。不过,人类的前景未必如此惨淡,或许未来不会走到这一步,如我反复所说,理性、知识或智慧在价值上指向公正和道德,在某个时候人类或许会想明白这个道理,从而解除自身所中的“生存竞争”之毒,扭转人类历史走向。
当我们把“灵魂”概念抹去,这样一个事实就浮现出来:每个人都是先天的基因和后天的环境造就的,她自己几乎无法对此“负责”。你长成什么样子,拥有何种天赋,喜欢什么讨厌什么,皆外在因素使然。有人从中看到决定论的影子,如柏林所说,你的选择与决定——“意志”,也由你的基因和经历所塑造的你的人格与认知所决定,这样看来人就没有意志上的“自由”,那么我们的行为的好坏善恶只有美学意义而不是伦理判断。就像是说,狼吃羊,不是狼残酷、邪恶,狗护主人,不是它忠诚,农夫救蛇,不是农夫蠢,而是自然把它们造成这个样子。人们对此的担心是,每个人对自己的行为因此不再负有责任,无论他们干了什么,包括犯罪。
我已经分析过,自由意志不仅与决定论不矛盾,甚至决定论还是意志自由的一个必须前提。决定论带来了“决定性”,我们因此才能有“决定”能力;有了做决定的能力,当我们超越自然的设计,不做像动物那样的自动机,而是自己做主来做选择,也就拥有了自由意志,由此认定每个人应对自己的行为负有伦理或道德责任也就顺理成章。但是,如你所知,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人类都不具有自由意志,在此情形下,如何确定一个人所要承担的伦理道德责任?
伦理价值中有两个基本概念或说原则:公正和道德。此处所说的伦理责任与“公正”有关,而公正原则可以应用到宇宙一切对象上或活动中:任何个体不得损害其它个体的合理利益。一块石头滚下山,砸到我的脚,就是损害了我的合理利益;狼吃了羊,就是损害了羊的合理利益,而你咬石头,石头崩掉你的牙齿,就不是损害你的合理利益,你上茅房,就一个坑,他先来蹲那儿了,也没有损害你的合理利益:所谓凯撒的归凯撒,每个人合理拥有自己利用自然而不是她人所得,即为个体所合理拥有,不得受到侵害。
由此推之,在广义上,别说一个人,就是一块石头、一头猪也对应了它应负的“伦理责任”,跟有没有自由意志没有关系,后者不过是哲学上流传千年的误解。问题是什么呢?伦理价值往往出现在个体之间的关系这个范畴之内——即在个体之间才会出现利益上的侵犯;石头、猪、无自由意志的人和有自由意志的人的存在形态不同——主要是智力差异——对应的个体之间的“关系”也不同。石头没有感受和自由意志,所以不是伦理主体,因此被石头砸到就属于纯粹的我的“运气”,我和石头之间的“公正”问题没有意义。
猪有感受,所以猪也有它伦理上的权利与责任,如果它吃了你的庄稼,要求它停止破坏、做出“赔偿”并不荒唐,尽管如何实现这种赔偿颇有难度。在合理利益被侵犯时,公正原则拥有绝对的优先权,所以在恢复公正秩序之前猪失掉了一切权利;人类社会经常有人提那些罪犯的“尊严”或其它权利,实属糊涂。如果猪有主人,主人可以代替猪做出赔偿来恢复公正秩序;如果是国家保护动物如熊猫,那么政府可以出面赔偿,总之目的就是要恢复公正秩序。
把“人”区别对待,不是因为他或她是我们的同类,以此为理由的人显然是有意无意的人类中心论者;人之不同于动物在于人有“意识”,能够理解自己的行为,所以我们对人采取了一套不同与石头和猪的实现公正的手段或说程序。对于严重的精神错乱者,由于他们不能正确理解现实和自身行为,在伦理上的角色类似智力不足的其它物种的个体,起社会规训作用的口头话语上的道德谴责并无意义,用于恢复公正的损害补偿要求对他们来说也很困难,所以这类因智力的严重缺陷导致的“侵犯”尽管是对公正的违反,也存在对应的“道德责任”,但与石头和猪一样说不上是通常我们所谓的“罪”。
我们现代生活在“国家”这样的团体中,因此代表整个社区的“国家”有责任来照看这些被看作是“病”的智力有缺陷的人,不仅是要防止他们对她人造成伤害,还应该出于“道德原则”尽可能让他们过更好的生活。除了这些人之外,其他任何人所造成的类似“侵犯”,都是日常所谓的“犯罪”,都应对自己的行为承担全部道德责任,其核心是补偿损害、恢复公正。以“基因”、“成长环境”、“冲动或激情”或“大脑中某个部位的‘异常’”来给个人的行为开脱责任,在情理上并无问题,它之所以引发争议,是因为被用于法律辩护用于减刑——这是人类所犯的一个巨大错误。
如前所述,公正的实现在于补偿损害、恢复公正秩序,所以法律的目标应该是“赔偿”和“防范”——由于某些损害无法补偿,所以在实践上不得不把“防范”作为目标。以“报复”或报复性惩罚、“威慑”、“矫正”为法律的目的,是人的原生智能中的“合作”、“抱团”等本能产出的歪瓜裂枣。且不谈无法补偿的情况以及补偿的量化问题,当侵害构成时,我们只是要求施害者补偿受害者的损失,无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施害者的“侵犯”。如在Mr.Oft的案例中,相关研究显示看上去是大脑肿瘤导致了他的娈童癖,割了之后他的娈童癖消失了,说不说是“肿瘤”导致的这一切都不影响Mr.Oft一样应对别人的损害做出对等的赔偿。只是有些人的“喻型”巫术思维突突地发作个不停,居然会认为应该“肿瘤”负责,那任务交给他们,由他们负责跟肿瘤商量如何赔偿受害人好了。
相关推荐
萤火谷的梦想家
艾莉森•麦吉出生于1960年,是美国《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同时也是大都会州立大学创意写作课的教授。她的作品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并出版,也曾被提名普利策奖,并获得苏斯博士奖金奖、克里斯托弗图书奖、美国 [美]艾莉森•麦吉/[美]克里斯托弗•丹尼斯/绘 2023-03-27 16:50:25鬼马女神捕1·绝密卧底(上)
腹黑凤凰vs毒舌鸡妖——蓝翎:“小姬,跟我去人界吧!”姬十四:“干吗?让人宰了我做小鸡炖蘑菇吗?”蓝翎:“不啊,让妖怪宰了你做小鸡炖蘑菇更气派。”凤凰蓝翎和鸡妖姬十四生活在无忧无虑的灵界。他们的故乡叫 郝天晓 2023-04-17 00:22:47© 2023-2025 百科书库. All Rights Reserved.












发表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