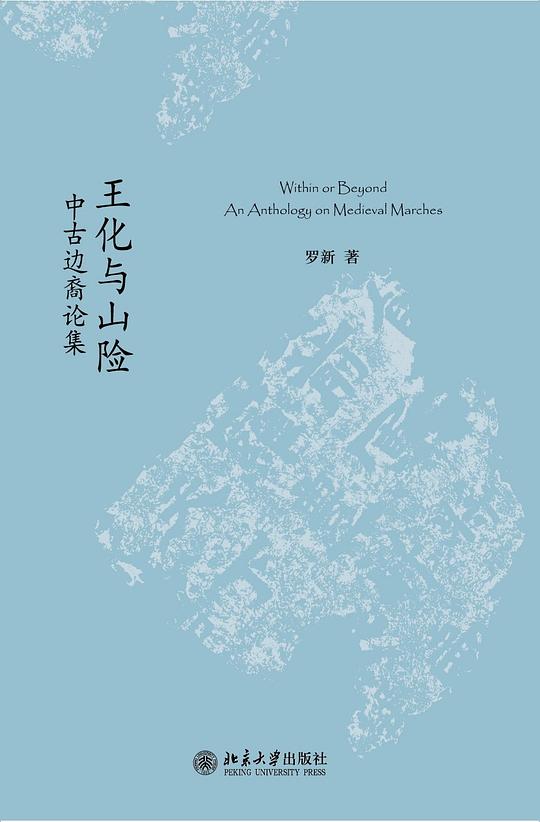
王化与山险捧心
书名:王化与山险
1
0

侠客行 2023-09-11 15:31:55
1)何德章:《建康与六朝江南经济区域的变迁》,《六朝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六届年会论文集》,《东南文化》1998年增刊2,第48—52页。在这篇文章中,何德章统计了两汉时期扬州(会稽与丹阳两郡)、赣江流域(豫章郡)和湘江流域(桂阳、零陵、武陵和长沙四郡)三个地区的户口数,得出结论说,“扬州区在西汉时人口密度高于湘、赣流域,而东汉后期大大低于湘、赣流域”,并认为六朝之初“江南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并不在扬州三吴、会稽,而是在湘江流域的长沙、零陵”。何德章的这一论点当然还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但他指出长江中游荆州诸郡(特别是其中的南郡、长沙和零陵等郡)的发展水平绝不低于长江下游的扬州诸郡,可以说是正确的和有价值的。
2)蠕蠕、茹茹,就是现代史书中统一称呼的柔然。按照《北史·蠕蠕传》的说法,蠕蠕的始祖木骨闾死后,其子车鹿会“雄健”,政治上有了较大的发展,“始有部众,自号柔然”。根据中古时期用汉字音译北族名号的规律,我猜想“车鹿会”这个名字所对应的阿尔泰名号应该是KülQan。按照这个说法,从车鹿会开始,柔然作为一个政治体就拥有了较为稳定的名称“柔然”。研究者相信,柔然的统治部族出自东胡系统,很可能本来是汉魏时期鲜卑集团的一个分支,因此和拓跋鲜卑一样是说古蒙古语(Proto-Mongolic)的。可惜现在已经无法了解“柔然”一词的语源了。
3)北魏官方对阿那瓌帮助镇压六镇的感激,以及对柔然重新崛起事实的认识,表现在尔朱荣控制朝廷后孝庄帝的一份诏书上,这份诏书赞美阿那瓌“镇卫北藩,御侮朔表,遂使阴山息警,弱水无尘,刊迹狼山,铭功瀚海”,因而“自今以后,赞拜不言名,上书不称臣”,等于正式承认了柔然与北魏的平等地位。不久北魏分裂为六镇人唱主角的东、西魏,柔然成为双方争相拉拢、不敢得罪的超级外部势力。至少在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方面,后期的阿那瓌终于为柔然争得了前所未有的光荣。当然,事实上这是柔然最后的光荣。当阿那瓌在高欢和宇文泰的眼中无比举足轻重的时候,高欢和宇文泰们不可能看到的历史大剧正在上演,在柔然的后花园里,即将改写内陆欧亚历史的突厥人已经从阿尔泰山里走出来,很快就要夺取柔然赖以虎视天下的鄂尔浑河河谷和塔米尔河河谷肥美广阔的大草原了。
4)邻和公主死后的第五年(555),西魏权臣宇文泰在突厥的压力下,把投奔西魏的柔然余众三千多人交给突厥使者,尽数杀戮于长安城的青门之外。
5)贞观二十年秋,包括仆骨(即仆固)在内的铁勒十一姓归附唐朝时,曾提出“乞置汉官”,不久又遣使至灵州,“因请置吏”。次年正月以漠北铁勒诸部置羁縻府州,诸酋长奏请置参天可汗道,“岁贡貂皮以充租赋,仍请能属文人,使为表疏”。在羁縻府州设汉官,本来也是唐朝治理羁縻府州的常例。于是,“太宗为置六府七州,府置都督,州置刺史,府州皆置长史、司马已下官主之”。都督、刺史当然是由部落酋长担任,但长史以下就可以参以汉官,特别是录事参军,用汉官者甚多,也许是因为其职责在于文书行政,即所谓“能属文人,使为表疏”。
铁勒诸部酋首在归附唐廷之初,就提出“岁贡貂皮以充租赋”,似乎是与唐廷就自身未来对唐廷所承担的义务进行带有谈判性质的沟通。貂皮作为重要的政治和经济物资,和战略性物资马匹一样,向为中原所垂涎,唐廷对于回鹘所出貂皮的重视也是广为学者所知的。仆固与其他铁勒部落一样,应该是向唐廷岁贡貂皮的,而且可能还得进贡马匹,可惜墓志没有涉及这些内容。
6)羁縻府州对唐廷所承担的另一项重要义务,就是出席重大的国家仪典,以仰沐王化的夷狄君长的身份为帝国的荣耀增加光彩。乙突也尽过这项义务。墓志云:“至麟德二年,銮驾将巡岱岳,既言从塞北,非有滞周南,遂以汗马之劳,预奉射牛之礼。”这是指高宗麟德二年至乾封元年(664—665)东封泰山之事。《资治通鉴》记高宗与武后麟德二年十月丙寅“发东都,从驾文武仪仗,数百里不绝。列营置幕,弥亘原野。东自高丽,西至波斯、乌长诸国朝会者,各帅其属扈从,穹庐毳幕,牛羊驼马,填咽道路”。这些“帅其属扈从”的四夷君长中,就有仆固乙突。乙突如此,可以想见其他各羁縻府州的首领也都奉命赶去了。
7)江左的南朝对吐谷浑物资的兴趣,从史书中有限的记载看,似乎主要集中在马匹上。吐谷浑产善马(所谓蜀马),是南朝良种军马的主要来源,学者论之详矣。我这里要讨论的,是经由吐谷浑之地,丝路贸易中由西域向南朝(甚至包括北朝)输入的另一项大宗商品——昆仑玉。
8)于阗地区玉雕业的兴起,现在比较流行的看法,是从唐代开始,唐代以前,于阗只是向外输出原料,加工玉器则必须求助于外国。研究古玉的专家杨伯达先生近来对这一看法提出了质疑,他通过对唐代的“番人进宝”玉带板的研究,认为可能在初唐以前,于阗就存在着碾玉治玉的手工行业;其治玉行业的衰落,主要是在伊斯兰化以后。
根据汉魏以来于阗与中原政权关系的变化,我认为于阗地区的治玉业可能是在南北朝时期兴起的,也就是说,当于阗国与东部地区的政权间不存在严格的藩属关系,政治上有机会脱离直接控制以后,贸易上才能有更充分的地方性发展。相对平等的政治关系,为于阗与内地(主要是南朝,当然有时也包括北朝)间发展充分而自由的贸易和商业关系提供了更好的条件。于阗的治玉业在这个政治和商业背景下得以兴起,是可以理解的。此外,中国玉文化的发展和演变,即东部地区在玉器消费方面所发生的变化,可能也是于阗治玉业得以兴起的一个原因,因无关本文宏旨,此不复赘。
9)左国史,与三国孙吴的左右国史设官相同。汉国初建,官制仿效魏晋,故置史官,以汉族士人太中大夫公师彧兼领。公师彧为刘渊所写的《高祖本纪》以及功臣传,被刘知几誉为“甚得良史之体”。所谓良史,就是据事直书,记录事情的本来面貌。刘渊的本来面貌,乃是以屠各而冒充南匈奴单于嫡裔,以胡族而冒充汉宣帝玄孙。所谓“讪谤先帝”,当是指此而言。刘聪大怒之下,兴动大狱,一日而诛七位卿大夫,却不宣露罪名,表明刘聪对此事既重视又讳莫如深。所诛七人中,公师彧领左国史,另外六人与史案的关系明朗,令人想起后来北魏的崔浩国史之狱,同样没有明确的罪名,也同样株连极广,大概反映的问题是差不多的。
10)公然以胡族后裔而称王称帝于华夏腹地,在十六国历史中,刘曜是第一个。我们把刘曜建立前赵看作一个阶段性的标志,就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这时中国北方社会胡汉之间、胡族与胡族之间的冲撞与整合,已经到了一个新阶段,对于一个胡族政权来说,其兴亡盛衰的关键不仅取决于它与汉族的关系,而且取决于它与其他胡族之间的关系,后者甚至更为重要。对于任何建立统治的胡族来说,统治者永远只是少数民族,其他各胡族在反抗其统治方面,永远是多数民族。
11)五部自身的强大和关陇其他部族的合作,是前赵政权存在的两个支点,其中任何一个支点的变化,都会影响前赵政权的命运。到刘曜后期,这两个支点的平衡就出现了问题,作为汉赵政权支撑性力量的五部精锐由于战争消耗和年迈衰老而使前赵面临危机。324年,当刘曜统帅盛况空前的大军威慑凉州时,他就对这种危机有清醒的认识,他说:“吾军旅虽盛,不逾魏武之东也,畏威而来者,三有二焉;中军宿卫已皆疲老,不可用也。”所谓“中军宿卫”,就是五部旧人,从刘渊起兵开始,这批五部之众就一直充当汉赵的支撑性军事力量,连年的战争和平阳的内乱,已经从数量和质量上削弱了这批“中军宿卫”;从刘渊起兵到这时已经二十多年了,当年的青壮已经进入暮年。刘曜说的“疲老”正是这个意思。由于军队长年征战于外,加上平阳内乱,影响了五部的人口增殖和新一代的成长,到刘曜后期危机终于暴露了。刘曜末年建立了一支名叫“亲御郎”的军队,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难题。
12)从晋惠帝元康六年齐万年反乱开始,关中汉族人民大量向外流移,从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关中的民族形势,汉族人口比例不断下降,而关中总的人口数量也因战争、饥疫、饥民外流而不断下降。外流的汉族人口当然也有返回关中的,如阎鼎率关西流民数千拥秦王业西归,但数量很少。晋愍帝的长安朝廷能够在关中撑持数年,并不说明关中的汉族势力还有可观。愍帝得立,长安朝廷在匈奴刘氏的军事打击之下居然维持四五年之久,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雍州北部各郡羌胡的支持。
13)宿白先生在20世纪70年代发表的两篇论文,阐释拓跋部南迁路线的文化遗迹,从考古学的角度,确认了拓跋部有关本部迁徙历程的记忆。宿白先生认为,考古发掘的呼伦贝尔盟陈巴尔虎旗完工墓葬遗址与新巴尔虎右旗扎赉诺尔墓葬遗址之间的呼伦池,就是《魏书》所记拓跋部最早迁徙的“大泽”,这两个墓葬遗址就是拓跋祖先推寅(宣帝)“南迁大泽”前后的遗迹。对于《魏书》所记的拓跋部第二次南迁,宿先生找到了辽宁巴林左旗(林东)南杨家营子的遗址,从而论证拓跋的圣武帝南迁,是从呼伦贝尔略转东南,出大兴安岭南段东侧的辽河支流乌尔吉木伦河流域,从而进入所谓“匈奴之故地”。
14)把新技术应用在传统学科的传统问题上,以获得传统学科在传统理论范畴内渴望获得的结论,这种做法是有必要反思的。比如,分子生物学的DNA技术,被研究者用来探索非常晚近的、历史时期的各族群的迁徙活动,就是必须警惕的。最近有人试图用所谓曹操后人的DNA来验证曹操墓的真伪,看起来荒谬绝伦,但其思想方法和理论基础,与那种以DNA技术探讨突厥人与蒙古人、汉族与傣族等不同族群间生物学差异的研究设想,并没有本质的区别,甚至可以说本来就是一脉相承的。
15)今天研究北魏佛教者,注意力多集中于金石造像和石窟,少有论及“幢幡”上的绣像、织成像者,那是因为金石质地易于保存而已,并非北魏佛事中只有金石造像。
16)影响名号贬值速度的因素应该不只是时间,甚至不一定主要是时间,还和借入这一名号的族群本身的社会发育水平以及已有的名号系统的复杂度有关。可能并州胡羯久处中原,原有的部落结构和名号系统受到华夏式名号系统的冲击比拓跋大,贬值也就更加迅速。石勒创业中,分配给下面的名号全是将军、都督、太守之类;称赵王时,所署管理胡人的官职都叫‘门臣祭酒’‘门生主书’,虽然不伦不类,却都是汉式名号无疑。只有署给石虎的‘单于元辅’和石泰、石同等(看这几个名字应该也是石勒的同族)撰写的《大单于志》,留下一点所谓‘胡制’的影子。这可作为一个证据。
17)定州大道,应该就是现今由大同市东南进入河北境内的203转382省道。这条道路的走向从北魏平城时期至今1500多年基本未变,即从大同向东南取道浑源、灵丘,然后沿太行山东麓南下直达定州,从代(蔚州)向东北则可经上谷(怀来)连接幽燕蓟辽,向东南可通青齐诸州以至再转河南和淮河流域,是贯通代北和山东的经济命脉,同时也是与南朝宋、齐往来聘问的必由之路。在史籍中,这条道路的名称有飞狐道、直道、莎泉道、灵丘道等,这些名称大抵都是分段修筑时形成的。据我所知,像盖天保墓砖这样总称其为定州大道在以往还不曾见过,因而就显得十分重要。”
盖天保墓砖铭文以“定州大道”作为盖天保墓的定位主要参数,可知在平城的对外交通网络里,通向河北诸州的主要道路被称作“定州大道”。对于北魏朝廷来说,以冀州、相州和定州为中心的河北数州,是“国之基本”,所谓“国之资储,唯藉河北”。定州大道可谓国家之生命线。也许,从平城向南前往晋阳并分别延伸至洛阳和长安的道路被称作“并州大道”,从平城向西前往盛乐并分别延伸至武川、怀朔、沃野、统万和高平诸镇的道路被称为“朔州大道”,可惜至今我们还没有见到记有这些名称的任何文献和出土史料。
18)高句丽就控制了西晋的乐浪、带方二郡,慕容廆所置的乐浪郡,是一个侨郡。清人洪亮吉已经指出,前燕的乐浪郡“皆非汉乐浪郡旧地也”。侨置乐浪郡,是为了安顿张统所率领来归的乐浪、带方二郡“千余家”,但是置乐浪而不置带方,乐浪王氏所起的作用还是相当明显的。此后历北燕、前秦、后燕、北燕和北魏,一直侨置乐浪郡,虽然郡境及郡址变动较大,乐浪郡的行政地位却迄未丧失。
19)休屠胡,一般认为是“休屠各胡”的省称,中古史料中常常写作屠各。对于休屠与屠各的关系,屠各的民族属性,学界还没有一致和明晰的意见,此处亦不加讨论。在梁元碧从凉州徙入雍州以前,高平这一带是有屠各活动的。《三国志》记载夏侯渊于建安十九年(214)进兵陇上,“转击高平屠各,皆散走,收其粮谷牛马”。高平屠各积有粮谷、放牧牛马,可见这一支屠各已经不再处于游牧状态。定居在西川的梁元碧部休屠胡及其后裔,大概就属于这种情况,虽然以畜牧为主,但也有一定的种植业,正因如此,才能维持该部族在同一地区的长期存在。
20)晋阳是尔朱荣的大本营,也是北朝后期足以与洛阳或邺城相提并论的新的中心城市,这一变化过程对晋阳士族,特别是其中那些长期被排斥在边缘地位的士族,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投靠并居住在辛家的李季凯,就参与了尔朱荣南下的策划,“肃宗崩,尔朱荣阴图义举,季凯预谋”。李季凯如此,晋阳辛氏恐怕也不能置身事外。因为家于晋阳,所以与尔朱氏有比较多的联系,这和辛叔文兄弟在孝庄帝时期的政治发展应当是有关联的。这也提示我们注意,北魏后期的政治纠葛中,由地域因素造成的某种松散的政治同盟单元,也是应当深入研究的。
21)可朱浑道元这一支,也曾经卷入到攀附华夏姓族郡望的潮流中。《魏书·朱瑞传》载瑞先后改籍青州乐陵和沧州乐陵,因为两个乐陵都有朱姓。改汉姓,附会郡望,是北朝胡族华化的一个重要途径。从孝文帝以后,可朱浑氏既对应汉姓之朱氏,则攀附行为势必不少。
22)东魏、北齐把内迁六镇镇民都以侨州郡的形式严格管理起来了,连那些显贵勋臣也不例外。这是一种户籍簿录的管理,北齐禁军兵源主要依赖这一体制,当然部分上层人员的实际居住地可能并不受此限制。
23)这个时期,大多数的内迁镇民即“九州勋人”的家都在侨州郡所在的并、肆、汾等州,许多勋贵如厍狄回洛也不例外,这才是高氏政权重晋阳甚于邺都的原因。
24)周秦之际东亚大陆主要人群的分布状况,即内亚草原的游牧民(其核心族群说古突厥语族和古蒙古语族各语言,所谓“胡”);东北亚森林地带诸民族,包括今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和滨海诸州,及今中国东北全境与长城地带的渔猎民族(其核心族群说古通古斯语族各语言,所谓“貊”或“貉”);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正在急剧扩张的华夏民族集团(其核心族群说古典汉语并使用汉字书写系统,所谓“华”或“夏”);汉水、大别山以南至南岭以北的稻作区的诸蛮(其核心族群说苗瑶语族诸语言,所谓“蛮”);以南方滨海地带的古代诸越民族(其核心族群说南岛语系百越语族诸语言,所谓“越”)。这种各主要族群集团在空间上各自连续分布并覆盖广大地区的格局,到战国后期已经有了显著的改观。华夏集团首先在政治上控制了越来越多的原非华夏地区,接着在这些地区开始了华夏化运动。
25)中古早期历史文献中出现较多的“蛮夷”,除了那些作为泛称所指的不确定的非华夏民族以外,主要是指南方诸蛮,包括共有槃瓠信仰的诸蛮族集团,其中最著名的是武陵郡的五溪蛮。无论是板楯蛮还是廩君蛮,研究者一般都归入苗瑶系民族。
26)熟悉三国史的人都知道,山越、武陵蛮和交趾豪族是长期困扰孙吴政治的三个主要的国内因素。傅乐成把这三者明确地说成三个“异族”,并强调“(武陵蛮和交趾豪族)远处边陲,为害尚小;独山越居腹心之地,为孙吴大患”。他有关山越最重要这一说法无论是否合乎史实,但基本可以得到现存史料和现代学者研究的佐证。现存山越的史料远远多于武陵蛮和交趾豪族的史料,而且在三者之中,现代学者有关山越的研究也一枝独秀。1935年叶国庆发表《三国时山越分布之区域》一文,通过整理有关孙吴时期山越的史料,排比山越活动的地域范围,发现山越所在的地区,正是西汉时闽越、东越和南越之旧壤,由此得出结论“吴之山越当为汉之越”,即山越为西汉越族之后裔。
27)华夏政权侵入南方土著族群的经济动机。唐长孺先生早已指出,孙吴伐山越的主要动机是满足其对于劳动力和兵源的需求。川胜义雄对唐先生此一论点表示完全支持。谷口房男也讨论过诸葛亮征伐南中对于蜀汉统治的重要经济意义。《三国志》记蜀汉张嶷为越嶲太守时,对于治内“夷缴久自固食”的“盐铁及漆”等重要资源,“率所领夺取,署长吏焉”,控制这些本来属于土著族群的经济资源以后,“遂获盐铁,器用周赡”。《晋书》称“元后渡江,军事草创,蛮陬赕布,不有恒准,中府所储,数四千匹”。既然把“蛮陬赕布,不有恒准”看作东晋初财政紧张的原因之一,那么此后财政状况的好转应当包括了“蛮陬赕布”的大量赋入,这也印证了陶侃“夷中利深”的判断。
28)南朝前期频繁发生的诸蛮反叛几乎都有同样的背景。更进一步,把相当数量的土著民强制变成华夏政权及其上层社会的官私依附劳动力(及兵源),是中古时期南方土著族群迅速华夏化的重要途径之一。
相关推荐
萤火谷的梦想家
艾莉森•麦吉出生于1960年,是美国《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同时也是大都会州立大学创意写作课的教授。她的作品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并出版,也曾被提名普利策奖,并获得苏斯博士奖金奖、克里斯托弗图书奖、美国 [美]艾莉森•麦吉/[美]克里斯托弗•丹尼斯/绘 2023-03-27 16:50:25鬼马女神捕1·绝密卧底(上)
腹黑凤凰vs毒舌鸡妖——蓝翎:“小姬,跟我去人界吧!”姬十四:“干吗?让人宰了我做小鸡炖蘑菇吗?”蓝翎:“不啊,让妖怪宰了你做小鸡炖蘑菇更气派。”凤凰蓝翎和鸡妖姬十四生活在无忧无虑的灵界。他们的故乡叫 郝天晓 2023-04-17 00:22:47© 2023-2025 百科书库. All Rights Reserved.












发表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