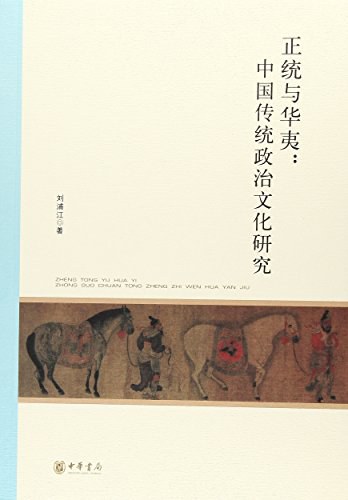
"正统与华夷: 读书笔记"
书名:正统与华夷
1
0

鬼谷子 2023-09-07 22:50:50
正统与华夷正统问题是困扰中国人长达两千年之久的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个核心观念,历来深受史家关注。秦汉以后,五德终始说成为历代王朝阐释其政权合法性的基本理论框架。魏晋南北朝时代,政治上的长期分裂以及异族的入主中原,对旧有的华夷秩序和正统观念造成巨大冲击。宋代的儒学复兴使延续千余年的五德转移政治学说宣告终结,以道德批评为准则的正统论取而代之,正统之辨成为士大夫最热衷的话题。泽案:中国古代皇权合法性的论证,也是经历了一次唐宋变革的,从五德终始的天命、灾异论到宋代开始的正统论。从神异的五德终始到道德批评为准则的正统论。这是中国古代思想史和政治文化史的重要命题。隋唐时期的法统讨论,恰恰可以看作宋代五德终始结束的先声,因此值得好好讨论。杨隋篡位自立,所以要在法统上大做文章,总体来说是肯定隋朝继承北周——北魏——西晋的法统的,也就是执着的北朝正统论。晋为金行,后魏为水,周为木。皇家以火承木,得天之统。李唐王朝继承隋朝,以土承火,并且承袭了隋朝的北朝正统论。对于唐王朝来说坚持北朝正统的理由是显而易见的,对于出自关陇集团的李唐皇室来说,继承周隋法统是不可动摇的政治立场,是一个必然的历史选择。譬如在《南史》《北史》中,其义例和书法就贯穿着以北魏(西魏)、周、隋为主角的北朝正统论。而北朝正统论在唐初代表着一种政治立场,后来它则逐渐衍生为一种史学观念,这种史学观念对隋唐直至北宋前期的历史著作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泽案:除了南北尊卑问题外,东西之争在北朝也有。譬如《魏书》中就是尊北齐贬北周的,于是隋朝时期魏澹《魏书》可以说是专为树立西魏正统而撰述的一部史学著作,此书虽早已不传。李延寿的《北史》虽然在史料上采取魏收《魏书》,但是在正统上,采取点立场是北周为尊。综上所述,隋唐时代盛行的北朝正统论,其基本立场是尊北而抑南、尊西而抑东,是以建构魏(北魏、西魏)、周、隋、唐正统王朝体系为核心的一种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北朝历史入口的问题:北朝正统论的破绽虽然通向隋唐帝国的“出口”是在北朝,但从北朝却似乎找不到一个“入口”——也就是说,北朝正统没有令人信服的来源。北朝国家法统只能上溯到北魏,那北魏王朝的政治合法性究竟来源于何方?这就是北朝正统论难以自圆其说的最大疑点。在北魏时期是怎么解决正统问题的呢?在北魏孝文帝时出现了两种声音,一是主张继承十六国的法统,即曹魏土德—西晋金德—石赵水德—慕容燕木德—苻秦火德—拓跋魏土德;另一派则主张远承晋统,即曹魏土德—西晋金德—拓跋魏水德。综合《魏书》的相关记载来看,北魏与西晋在时间距离上的悬隔,是当时双方争议的焦点所在,故李彪、崔光等人以“汉弃秦承周之义”来为魏承晋统张目。孝文帝虽然采取了这种建议,但是还是有些疑虑。在后人看来,魏承晋统最大的困难是:与北魏前后并存的东晋对北朝自诩的华夏正统构成了最大的障碍。与西晋一脉相承的东晋具有无可置疑的政治合法性来源。甚至北魏前期自己编写的《十六国春秋》都是以东晋为正统的。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捏?毫无疑问,北朝采取了抹黑东晋血统的方法。魏收在《魏书》中将司马睿是将牛金之子的传说收入。而牛金之子这个传说从史源来说是来自《宋书》,不过《宋书》中的记载是“司马懿鸩杀牛金是受到了这一谶语的暗示,而谶语之真正应验,却是后来夏侯妃与牛氏私通而生元帝一事。”很明显,魏收的说法来自于《宋书》并且将两个传说混合了(不知道是故意还是不小心的),总之史源一定要注意。刘浦江先生考证,这一史料源头早在孙盛《晋阳秋》中就已出现这个传说。《晋阳秋》成书于东晋孝武帝太元以前,由此看来,这大概是从东晋中叶开始流行的一个政治谣言。这样的谣言来攻击北朝正统是很荒谬的,所以出现了对北朝正统论的完善。王通主张东晋、刘宋为正统,刘宋灭亡之时正好是孝文帝在位时,所以正统转移到了北魏。甚至他专门编写《元经》来论述这套正统体系与隋唐时代盛行的北朝正统论的主要不同之处,就是改魏承晋统为魏承宋统,为北朝国家的政治合法性来源提供一种新的解释,使其能够与东晋南朝的历史相对接,从而解决北朝正统论所无法解决的“入口”问题。隋唐时代盛行的北朝正统论,主要是建立在北朝—隋唐国家法统基础之上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我们知道,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正统论,除了讲求国家法统的合法性之外,华夏种族的血统和儒家文化的道统也同样是很被看重的因素。在南北朝当时东晋南朝是被认作是正统的,东晋自不必说,即便在南北朝时代,南朝正统论不仅仅是南朝士人的主张,甚至也是许多北朝士大夫共有的文化观念。这和北齐北周鲜卑回潮以及南朝萧梁的蒸蒸日上有关系。所以在隋唐除了主流意识形态强行规定了北朝正统论之外。在士人阶层中还存在者传统的南朝正统的观念,但是这种南朝正统论也不是盲目的将陈作为最后,而是将萧梁之后接上北周。(如费长房《历代三宝记》皇甫湜《东晋元魏正闰论》)正统王朝谱系是西晋、东晋、宋、齐、梁、周、隋。它既能最大限度地捍卫东晋、南朝的正统性,同时又为看似走进死胡同的南朝找到了一个历史出口,从而避免了洪迈所说的那种“以宋继晋则至陈而无所终”的尴尬结局,使东晋、南朝能够与统一的隋唐帝国衔接为一个整体。将陈排斥于正统王朝之外,不外乎两个原因:其一,通向隋唐帝国的“出口”毕竟在北而不在南,闰陈而正周,才能将南朝统系与隋唐统一王朝衔接在一起;其二,如上所述,侯景之乱以后,北方士人对衰乱已极的南朝已经不抱任何希望,南北正闰的传统理念随之开始发生转变,而后杨氏代周,政权转入汉人之手,更坚定了北方士人认同周、隋正统的信念。认为江陵的梁元帝被西魏灭亡,所以北周直接继承了南梁的法统。而南陈是自树,没有法统依据。唐代南北正统论的核心就在于是否承认北魏王朝,官方的意识形态是承认北魏王朝的合法性的,但是在士人心目中,北魏的血统是很关键的问题。再加之中晚唐对于异族威胁的焦虑心理,所以可以理解为啥会强调东晋王朝的正统。径承汉统说的提出及其实践:南北正统的争论给后人留下了一大问题:北朝正统论堪称隋唐时代主流的历史观念,但因无法解释清楚其正统源头而受到人们质疑;南朝正统论虽然在士人阶层中仍具有很大影响力,但显然不可能为隋唐政权所接受。于是便有人提出一种折衷意见:不妨略过魏晋南北朝分裂时代,直接上承两汉法统。径承汉统说是王通在修正版本的北朝正统说之前提出的版本,径承汉统说被隋文帝否决的原因是:杨氏代周而立,隋朝政权的政治合法性是建立在继承北周法统的基础之上的,“以火承木”可以说是隋朝政治家的唯一选择,王通的意见未免太不合时宜了。因为这个主张行不通,所以后来他才又提出了魏承宋统的正统谱系,试图对北朝国家的华夏正统来源做出新的解释,“以断南北之疑”。很有趣的是王通的孙子王勃在唐朝提出了唐承汉统说。王勃对唐朝的正统来源做出了新的解释,按他的说法,唐朝土德当承自汉之火德,而不应承隋之火德。他把魏晋至周隋都列入闰位。但是当时这种意见尚未引起唐朝统治者的注意。到了高宗武后时期反而用了王勃的意见,将唐朝的法统直接指向汉朝。只不过到了中宗复位之后,又恢复了承袭北朝的正统。到了唐玄宗时期再次启用了直接承袭汉统的理论。过了三年,在杨国忠在位时期又恢复了北朝正统论。虽然唐承汉统说的两次政治实践最终失败,但是可以看出这种理论影响很大。当然,在隋朝及唐初的时代环境下,如此大胆的见解尚不可能为政治家所接受,因为坚持北朝正统以解决隋唐政权的政治合法性,在当时来说毕竟还是一个非常紧要的现实问题。而到了中唐以后,时移世变,大唐王朝的正统性已经毋容置疑,北朝正统论也成为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于是像唐承汉统这样“迂阔”的主张居然可以一而再地付诸实施。不过,这种政治实践肯定是难以持久的。在五德终始说盛行的隋唐时代,在宋儒提出“绝统”、“无统”说之前,把整个魏晋南北朝乃至隋朝都摈斥于正统王朝之外,这样的正统谱系很难为人们普遍接受。走出魏晋南北朝:在南北朝时期南北对立,双方各逞诋诽,互争正闰,以致南人诬北为“索虏”,北人诋南为“岛夷”。而隋唐王朝建立以后,在明确承认北朝国家法统的,另一面,却是有意识地消弭南北政治文化传统的差异,淡化华夷正闰的观念。譬如唐初官修诸史,不论南北正闰,均单独成书,一国一史。《隋书·经籍志》史部以正史、霸史区别正闰,但东晋和南北朝诸国史全都被列入“正史”,而仅将十六国史列为“霸史”。魏晋南北朝时代形成的南北政治文化传统的差异,在隋唐统一帝国得到了有效的弥合。南北正闰之争的日渐淡化,就是这一历史发展趋势的必然结果。宋元已降的南北正闰观:北宋初年承袭唐代的北朝正统论。《资治通鉴》中使用的是南朝纪年,但是司马光事先声明了其没有褒贬含义,是不偏不倚的态度。但是《资治通鉴》的强大影响力也是的唐朝以来的传统正闰观念走向式微。真正从理论上颠覆北朝正统论的是欧阳修的绝统说和朱熹的无统说。欧阳修在他的《正统论》中认为“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不符合一统天下的正统标准就会被排斥出正统王朝之外,所以正统有时断绝。司马光认为在西晋之后到隋朝是无统的。朱熹的意见也差不多,但是朱熹承认东晋的正统。泽案:很可能和朱熹身处于南宋有关系。自秦以后,五德终始说一直是历代王朝阐释其政权合法性的基本理论框架,建立在对宇宙系统的信仰之上的五运说,其基本理念是五行代替,相承不绝,故即使像南北朝那样的分裂时期,也一定要追问正统之所在、德运之所系。而按照“绝统”说和“无统”说的正统标准来衡量,南北朝皆被摈斥于正统王朝之外,故南北正闰之争也就失去了它的意义。在宋以后,南北正闰仍然被提起,但是却不再是政治意识形态上的问题和合法性的追溯,而是有关华夷观念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这里涉及到中国华夷观念的弹性问题,虽然传统华夷之辨的标准是文化,但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规律是,在汉民族处于强势地位、民族矛盾趋向缓和的时候,人们比较容易认同文化至上的华夷标准;而当汉民族遭遇异族威胁、民族矛盾非常尖锐的时候,人们往往就会强调种族至上的华夷标准。在处于后一种情况之下,往往会强调南朝的正统,以寄寓华夷之辨的价值判断。譬如南宋时人和元代的宋遗民对于北朝正统论和三国志尊魏的不满。在清代统治者的意见更耐人寻味,尽管有所谓新清史强调从内亚性来看清朝。但是乾隆对历史上北族王朝的正闰之争竟是这样一种认知!就连隋唐时代力主南朝正统论的汉族士人也从未将南朝之陈视为正统,而高宗居然认为南朝正统一脉相承以至于陈,直至文帝灭陈之后,正统始归于隋。这说明到了乾隆世代,清朝统治者的正统观念已经发生了蜕变,从北方民族王朝的立场转变到了中国大一统王朝的立场。正统论下的五代史观:五代十国当代人的五代史观:朱温自称继承唐代土德,为金德。但是当时河东、凤翔、淮南等地方实际独立政权并不承认,仍然沿用唐朝年号和正朔。而后唐在河东割据阶段一直就是奉行唐代正朔,到了李存勖灭梁建国,更是自居为唐朝正统,沿用唐朝土德。(譬如本来修《唐书》,是要下到后唐明宗的,但是由于实录限制,所以没有实现)根据樊文礼先生的论述,将唐、晋、汉、周都称为代北集团。所以他们的政治立场都很一致,将后唐看作是中兴唐朝的延续,梁朝则是像王莽一样的伪朝廷。除了到后周太祖时期由于时过境迁,政治迫切性没那么强,才下诏恢复了梁朝正统。宋儒的五代史观:宋代人的五代史观,出现了从承认到不承认的转折。北宋前期,宋人对于五代的历史地位还是肯定的,譬如,宋初就有《五代通录》和《五代会要》。这和当时明确的政治目的和迫切的现实需要,宋的政治合法性当来自于周,因此必须先正五代之统,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宋王朝的正统性问题。在承认五代的前提下,出现了关于承不承认梁的问题。不承认梁的观点以真宗朝编纂的《册府元龟》是一部历史学的百科全书,基本上可以代表北宋前期知识界的主流史学观念。值得注意的是,此书将五代中的唐、晋、汉、周四朝列入帝王部帝系门(卷一),而将梁朝列入闰位部氏号门(卷一八二),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宋初士人对于五代史的正闰之分。承认梁的观点主要是在五代史的撰写上,《五代会要》、《五代通录》这些都看不出褒贬,太祖年间修订的《旧五代史》也是将梁唐晋汉周视作正统王朝。《新五代史》亦是如此。综上所述,北宋前期士人在五代史观上存在的主要分歧,就是在肯定五代正统的前提下如何评价朱梁王朝的政治合法性问题。一种意见是沿袭后唐以来传统的正闰标准,斥朱梁于闰位;另一种意见则基本认同后周太祖的主张,承认梁朝的正统地位。一般来说,在意识形态领域,宋人惯于恪守严格的正闰之分,伪梁一派掌握着话语主导权;而在史学领域,人们显然更倾向于淡化这个问题(宋人侈谈正统,是北宋中叶儒学复兴以后的事情),北宋前期的五代史著作,无论是私人著述还是官修正史,大都不再刻意区别五代诸国的正统与僭伪、正义与非义。北宋中期儒学复兴运动及正统观念的改变:北宋中期从原来对于五代正统的承袭变成了彻底的否定五代;譬如石介首次提出五季的说法。五季就是将五代十国看成是唐代藩镇的余留。以欧阳修为个案:在早年《新五代史》的时候,还是承认五代正统的(不伪梁),到了康定元年的七篇《正统论》,依然坚持正梁之统。然而到了晚年,在其修订自己的《正统论》的时候,将七篇改成了三篇,并且全面否定五代的正统。原因是以下三点:第一,以道德批评为准则的正统论改变了传统的正统观念。欧阳修发起的正统之辨是北宋中期儒学复兴运动的产物。宋儒的正统论与前代相比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那就是除了大一统的政治前提之外,特别强调道德认同,正统的标准被归结为两点,即所谓“君子大居正”、“王者大一统”。第二,五德终始说的终结消解了五代正统论赖以成立的理论基础。自秦汉以降,五德终始说一直是历代王朝阐释其政权合法性的基本理论框架。五运说建立在对宇宙系统的信仰之上,其基本理念是五行代替,传承不绝,故宋王朝之火德必须经由五代德运体系一脉相承,就是这个道理。欧阳修在提出正统的两种要求之外,特别强调“正统有时而绝。”第三,仁宗开始,北宋正统地位已经不容置疑,所以五代的正统不再是政治意识形态的问题。所以可以讨论。泽案:我发现不管是五代正统的讨论还是南北正统的讨论,都是在王朝中期开始具有影响力的,这或许就是和政治性消退有关。到了朱熹无统论的提出,五代这个曾经一度被承认为正统的时代,最终变成了万劫不复之地。南唐正统论之泛起:李昪建立南唐,自称李唐宗室之后,或谓唐宪宗第八子建王恪之玄孙,或谓唐玄宗第六子永王璘之苗裔。但是这些在当时以及北宋初年是没有人相信的。但是从两宋时期三部《南唐书》,可以看出南唐历史地位的提升。北宋中期的《南唐书》和晚期的《南唐书》,都没有将南唐视作是正统。到了南宋陆游的《南唐书》就将南唐皇帝立为本纪了。到元人戚光,正式提出了南唐正统说。从北宋胡恢到晚清李慈铭,南唐的历史地位在不同的语境下被后人赋予了多种解释,讨论正统论下的五代史观,这是一条不可忽视的线索。五代史观为何不考虑华夷之辨:为什么批评五代一直批评道德而不是民族问题?在中国人传统的华夷观念中,华夷界限通常是文化而不是种族。自晚唐以来,代北地区的民族融合趋势十分明显,故五代时期的沙陀三王朝在时人心目中的夷狄形象已经相当模糊,人们似乎已经忘记了他们本来的血统。新的外族威胁的出现,促使汉人在心理上和文化上更加认同于入主中原的异族政权。就像北魏时代,由于柔然的崛起而导致汉人的华夷观念发生显著变化,内鲜卑而外柔然,成为时人华夷之辨的一种共识。金朝末年认为蒙古是夷狄,自己是华夏;满清时期一致对外一样。“五德终始说”之终结——宋代以降的传统政治文化的嬗变宋儒对于五德终始说的批判开始于欧阳修,在北宋中期儒学复兴的时代思潮影响下,由欧阳修发起的正统之辨使五德转移政治学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正统论》)欧阳修提出绝统说,彻底否定了‘建立在对宇宙系统的信仰之上,其基本理念是五行代替,相承不绝’,即使在天下大乱时期也要找出一个正统来传递德运的五德终始说。泽案:北宋中期儒学复兴运动之下的正统辩论,使得王朝的更迭从“奉天承运”的政治神话,变成了居“天下之正”的政治伦理。在传统的五德终始说之下,为了顾及德运的连续性,很少从道德层面去考虑“统”之正与不正的问题。宋儒就是强调:大一统的政治前提+道德认同。所以正统论在宋代以后发生了巨变——在五运说的全盛时期,政治家强调得天下以正(这个“正”不是指手段的正当,而是指来路的正统),在政权的承继关系上做文章。明清的政治家看中的是得天下以道,即看中获得政权的手段是否正当,而不太在乎这个政权是否直接来自某个正统的王朝。宋儒的正统之辨,到了朱熹集大成,朱熹提出了无统的理论。朱熹《通鉴纲目》更是直接决定了之后元明清三代正统之辨的话语权。排除反例:刘浦江先生的妙证:对于宋代理学家对于五行的肯定我们应该怎么认识呢?周敦颐的宇宙生成论,是由太极而阴阳,由阴阳而五行,由五行而万物的模式。周敦颐所说的太极,被二程、朱子称为理或天理,但“二气五行,化生万物”的宇宙生成模式并没有什么不同。我们如果从宇宙论而非正统观的角度去理解宋代理学家对五运说的肯定态度,上面提到的疑问便可涣然冰释。周敦颐所说的太极,被二程、朱子称为理或天理,但“二气五行,化生万物”的宇宙生成模式并没有什么不同。我们如果从宇宙论而非正统观的角度去理解宋代理学家对五运说的肯定态度,上面提到的疑问便可涣然冰释。实际上,朱熹等人只是在哲学思辨的层面上承认五运说的合理性,而在进行历史价值判断时,他自有他的道德准则和权衡法度。但是即使宋代出现了对五德终始说的系统批判,但是整个宋辽金时代,五德终始还是占据很重要的地位的,不仅仅是有部分士大夫仍然相信五德终始,官方也认可德运说。总之,虽然宋代的儒学复兴已经敲响了五德终始说的丧钟,但直到南宋末年,这种传统的政治文化仍然依靠它长期积蓄起来的能量和惯性继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社会影响。五运说作为一个阐释王朝嬗代的理论体系最终退出政治生活,乃是元朝以后的事情。宋代开始传统文化的嬗变——将德运说纳入传统文化变迁的视角自秦汉以来,确立皇权合法性和权威性的手段主要有四种,一是符谶,二是德运,三是封禅,四是传国玺。宋学对谶纬的扬弃——谶纬产生与西汉中晚期,是一种政治神学。谶纬和德运说的差异是,谶纬可谓是应急的政治神话,而五运说则是以树立王朝正统为目的的政治学说。在王莽篡位以后,谶纬成为历代篡权夺位的诡计,所以从曹魏以下统治者都禁止民间谶纬,但是五经纬和论语谶没有被禁止,还有很多书在引用谶纬之书。经学和纬学的彻底分家是宋代儒学复兴之后的事情(欧阳修《论删去九经正义中谶纬札子》)直至魏了翁撰《九经要义》,始将谶纬之说删除净尽,从此谶纬文献几近绝迹,纬学最终成为绝学。谶纬文献的销声匿迹,一方面是经学自身的扬弃,一方面是中古时期知识体系的变迁,在秦汉时代的知识体系中,古代的科学技术如天文历法、算学、地学和物候学、农学等等都被归入数术名下,数术集科学技术、神学迷信、宗教于一体,故《史记》既有《天官书》、《历书》,也有《龟策列传》、《日者列传》。唐宋以降,中国人的知识体系发生了重大变化,科学与迷信逐渐分家,于是天文历法、算学、地学、农学等从数术中分化出来,医学、药学以及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化学等从方技中分化出来。此后数术的地位日益低下,只在民间和术士中流传,被视为迷信的渊薮。封禅之末路——封禅本是战国后期齐国方士创制的一种具有原始宗教性质的祭祀典礼,在秦汉大一统帝国形成以后,它才与受命改制连成一气,成为“一种革命受命的学说”。其实禅让就是新兴王朝奉天承运的文化表征。从北宋中期儒学复兴运动开始,儒家士大夫就开始从根本上消解封禅的政治文化意义,宋儒对封禅的批评,在于封禅之文不著于经典。在北宋中期以后,封禅就走到了穷途末路。明清两代帝王不封禅的原因不是抖音史学所谓宋真宗太怂了,而是受到了宋儒的影响,认为在德不在封禅。(三)传国玉玺的沦落在传统政治文化中,秦的传国玉玺被视作是正统王朝的象征性符号。历代正统之争,传国玺往往是焦点所在,因为德运毕竟是一个抽象的意念,它需要一种物化的信据来加以证明。一直到宋代,哲宗时期,还因为获得玉玺而改元。宋儒对传国玺的彻底否定,使它不再被人们视为一个政治文化符号,从而决定了它走向沦落的宿命。清高宗自己撰写的《国朝传宝记》,最能反映明清政治家的看法。“朕尝论之,君人者在德不在宝。宝虽重,一器耳;明等威、征信守,与车旗章服何异。德之不足,则山河之险、土宇之富,拱手而授之他人,未有徒恃此区区尺璧足以自固者。”宋代的作用——它处在新旧两个时代的交汇点上。一方面,传统政治文化秩序在宋代仍然继续存在:两宋的政治家们始终没有放弃“宋以火德王”的正统论,真宗还在举行封禅大典,哲宗还在因为发现“秦玺”而改元更号。而另一方面,宋代的知识精英对传统政治文化进行了彻底的清算,从学理上消解它们的价值,从思想上清除它们的影响。虽然欧阳修们的政治伦理观念在宋代是高调的、前卫的,但到元明清时代就变成了普世的价值观。唐宋时代知识精英的创造性思想到明代逐步完成制度化、世俗化、常识化的过程。宋代以后的五德说:元朝水德说应是当时民间流行的一种说法。此说大概最初出自南宋遗民之口,它是以民间通行的五德相胜说为前提的,无非是因为宋为火德而径直推定元为水德罢了,这与传统的五德终始政治学说已相去甚远。明朝火德说:其目的是以复宋为号召,故宣称继承宋之火德;而当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毋需继续坚持火德之说,于是明朝一代也就不再讲求德运,五运说最终丧失了其政治功能。案:红巾军和明教徒没有一点点关系,是白莲教徒(弥勒信仰)明王”之号及大明国号均出自白莲教徒诵读的《大阿弥陀经》案:明朝火德也是不符合五德终始中相生的规律的,怎么会继承前朝的德运呢?德运的确定在明朝已不再是关乎王朝正统的头等大事,不再是一种郑重庄严的国家行为,火德也好,土德也罢,都只是朝野间流行的某些非正式的说法而已。又是他清高宗,他写了《题大金德运图说》:“元、明制度尚黄,不侈陈五德之王,其义甚正。本朝因之,足破汉魏以后之陋说。”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的正统性问题契丹王朝之正统论与德运说——辽朝虽然始终坚持草原本位,但自从燕云十六州汉地入辽后,文化的融合已是大势所趋。辽代前期,契丹人以“蕃”自居,自外于“中国”。辽朝人中国意识的觉醒,大致是兴宗以后的事情。契丹人传统的青牛白马故事反映了本民族根的意识,而道宗末年修成的耶律俨《皇朝实录》却“称辽为轩辕后”,无疑是对华夏文化的明确认同。从金章宗年间讨论德运问题时“辽以水为德”的话语,以及辽朝中期以后,契丹将从后晋处得来的传国玉玺大做文章来看,辽朝的正统是承袭后晋的金德,为水德。这样也否定了宋朝的政治合法性。金朝的德运之争及其文化选择——女真入主汉地之初,尚无华夏正统观念。自熙宗改制后,金朝迅速走向汉化道路。到了海陵王时代,女真统治者已经具备中国大一统王朝的政治伦理观念。於是可以看到的是在主張女真文化復興的金世宗手中,正統就是祖訓的金德,而到了崇尚漢文化的金章宗手中,就是承襲宋代的土德。在元代重修宋遼金的正史中國也引發了這一討論。大致說來就是獨尊宋統和沿襲修端的南北朝兩種方式。最終敲定的三史並修是一種大致類似南北朝的修法。劉浦江先生考證,南方士人堅持宋正統論,北方士人和蒙古人堅持南北朝論。在明代則分成兩個時期,明朝前期民族危機還不是那麽嚴重,於是是承認遼金正統的,但是到了明朝中後期,特別是嘉靖以後,由於受到蒙古以及後來女真的威脅,所以民族主義爆棚,要求改定宋遼金史,獨尊宋統。在清代前期有意識的抬高遼金的地位,但是從清高宗乾隆的價值判斷來看,至少在清中期以後,皇帝還是從北方民族王朝的視角轉入中原大一統王朝的視角,乾隆就認為本朝是幫助明朝復仇起家的,得天下的手段最正,所以不用顧忌民族問題。這和孝文帝承襲西晉正統,金承襲北宋正統的過程是一樣的。“倒错”的夷夏观?——乾嘉时代思想史的另一种面相问题的提出:以经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扬州学派中某些人物的异端正统论,为何和乾隆皇帝的正统观形成了强大的反差。凌廷堪:全面支持中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政权,反对汉族政权。焦循:贬低南朝、贬低宋,主张辽、金为正统。黄文旸:创作《通史发凡》,以汉、曹魏、西晋、后魏(即北魏)、北周、隋、唐、辽、金、元为正统。关于乾嘉时期为什么会有这种极端的尊崇少数民族的论断呢?过往学界有大致有汉宋之争说、反民族观念说、取媚时君说和注重绩效说。汉宋之争:认为他们攻击宋朝的正统是为了抹杀宋学,但是扬州学派兼通汉宋,他们也不仅仅只是贬低宋,更是褒扬所有少数民族政权。反民族
相关推荐
萤火谷的梦想家
艾莉森•麦吉出生于1960年,是美国《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同时也是大都会州立大学创意写作课的教授。她的作品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并出版,也曾被提名普利策奖,并获得苏斯博士奖金奖、克里斯托弗图书奖、美国 [美]艾莉森•麦吉/[美]克里斯托弗•丹尼斯/绘 2023-03-27 16:50:25鬼马女神捕1·绝密卧底(上)
腹黑凤凰vs毒舌鸡妖——蓝翎:“小姬,跟我去人界吧!”姬十四:“干吗?让人宰了我做小鸡炖蘑菇吗?”蓝翎:“不啊,让妖怪宰了你做小鸡炖蘑菇更气派。”凤凰蓝翎和鸡妖姬十四生活在无忧无虑的灵界。他们的故乡叫 郝天晓 2023-04-17 00:22:47© 2023-2025 百科书库. All Rights Reserved.












发表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