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向世界的挫折》晚清独行者:生命遭遇挫折
书名:走向世界的挫折
1
0

黑夜行者 2023-08-26 12:35:48
世上有很多聪明人,但最令人心仪的人,是那种对于自己处境有清明的认知而不悔初衷,同时又有着自嘲勇气和能力的人。这样的人历史上有很多,但不出名的不多,清末郭嵩焘算一个。
谈起郭嵩焘,很多人可能比较陌生。他出生于1818年的湖南湘阴,少年时曾到岳麓书院读书,与曾国藩、刘蓉一见如故,结为金兰,而他们的亲近跟性情有关,更跟抱负有关,用今天的话说,他们都是有志青年。
郭嵩焘一生,三次出仕,曾任驻英公使,后兼任驻法公使,这期间,他像海绵一样吸纳西方文明,寻找这种文明的动力。在数次与西方文明的接触中,郭嵩焘对于家国天下事,有了更多思考,也产生了更多忧患。并由此自我反思,感叹国家迟暮。
纵观郭嵩焘一生,他的仕途三起三落,但其对晚晴与西方文明极富洞见。按照我们今天的“后知后觉”,郭嵩焘在近代士大夫中算得上是一个“异数”,一位“先知先觉”者:
- 首先是对西洋特别是对洋人的认知。郭嵩焘认为洋人也是人,所谓“夷狄”也只是一个政治地理概念,而不是歧视性的文化概念。不仅如此,郭嵩焘还认为,眼前的“夷狄”已非“古之夷狄”可以比拟,尧舜生于今日,“必急取西洋之法推而行之”。否则,就会是人家西洋“以其有道攻中国之无道”。
- 第二个方面,是对“政教工商”所谓“本末”的认识。李鸿章与郭嵩焘虽是同年进士,但他对李鸿章并不全盘认可。原因之一,便是郭嵩焘觉得李鸿章办洋务“徒能考求洋人末务而忘其本”,派留学生到欧洲去学开船、制炮,指望买几艘铁甲船,摆到中国海口,以为如此便可以“制夷”,在郭嵩焘看来,这是儿戏,因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相强”。
- 第三个方面,对中国问题的观察。郭嵩焘屡屡直言,说“天下之大患,在士大夫之无识”,“天下之乱,由大臣之无识酿成之”。刘蓉曾经议论“非英夷之能病中国,而中国之自为病也”,郭嵩焘深以为然。除此之外,郭嵩焘在英国时便注意到,此时更全面地学习西方的日本将勒逼中国,“诸公欲以无本之术,虚骄之气,以求胜于日本,于人于己两失之”。此时距离甲午战争还有二十年。
一百年后,钟叔河先生在编辑《伦敦巴黎日记》时说,郭嵩焘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已经突破了“办洋务”的水平,率先创议“循习西方政教”,成为末世士大夫阶级中最早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人物。海外学人汪荣祖先生在《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中说,“当时人觉其独醉而众醒,但今日视之,实众醉而斯人独醒”。他的思想过于先进,同时代人鲜能接受,以致被人视为易遭物议、性格褊狭之人,终身受挫”,然而,“这个弄潮儿的挫折,很可说明那个挫折的时代”。
时至今日,我们对郭嵩焘的解读也并非关乎传主一人,而是,看懂郭嵩焘,也就看懂了晚清,看懂了中国,看懂了中国人。提起晚清,人们总是赞叹、欣赏左宗棠这样的英雄,然而,这种英雄哪朝哪代都有,特别是在中国的文化水土里;而类似郭嵩焘这种能够提供新的“世界观”,新的文化视界的人,却不多见。
求解郭嵩焘,意味着我们需要正视传统文明在近代的困境,正视与我们自身的一个独醒先驱的悲剧人生,一个“失败者”的执着与挣扎,读懂内外矛盾交织的晚清政局。“郭嵩焘的挫折,远不是个人的挫折,而是这个民族有个性的出类拔萃者的挫折,同时是整个民族的挫折。”本书情感浓郁、剖析深刻,读此书犹如进行一次漫漫的跋涉旅程,有时欣喜,有时窒息。诚挚推荐对近代史、对中国命运有兴趣的读者收藏。
相关推荐
逆天的冒险
我们是天生的冒险家,对冒险的爱从不会离开我们,直到我们迈入垂老之年。”博莱索写道。他认为,“胆小的老头子,在他们的兴趣当中,冒险应该是绝灭了的。”这也是为什么诗人们偏爱冒险,而法律通常是老年人制定的原 (南非)威廉·博莱索 2023-04-10 05:12:26笔误:文学大师的秘密生活
爱伦·坡小时候曾在一个墓地里上学?马克·吐温曾当着维多利亚女王大谈放屁,是怎么回事?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在派对上双手趴在地上,像狗一样大叫又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认为,作家应该是正襟危坐着写书的人,但《笔 (美国)罗伯特·施耐肯伯格 2023-04-10 10:13:49© 2023-2025 百科书库. All Rights Reserv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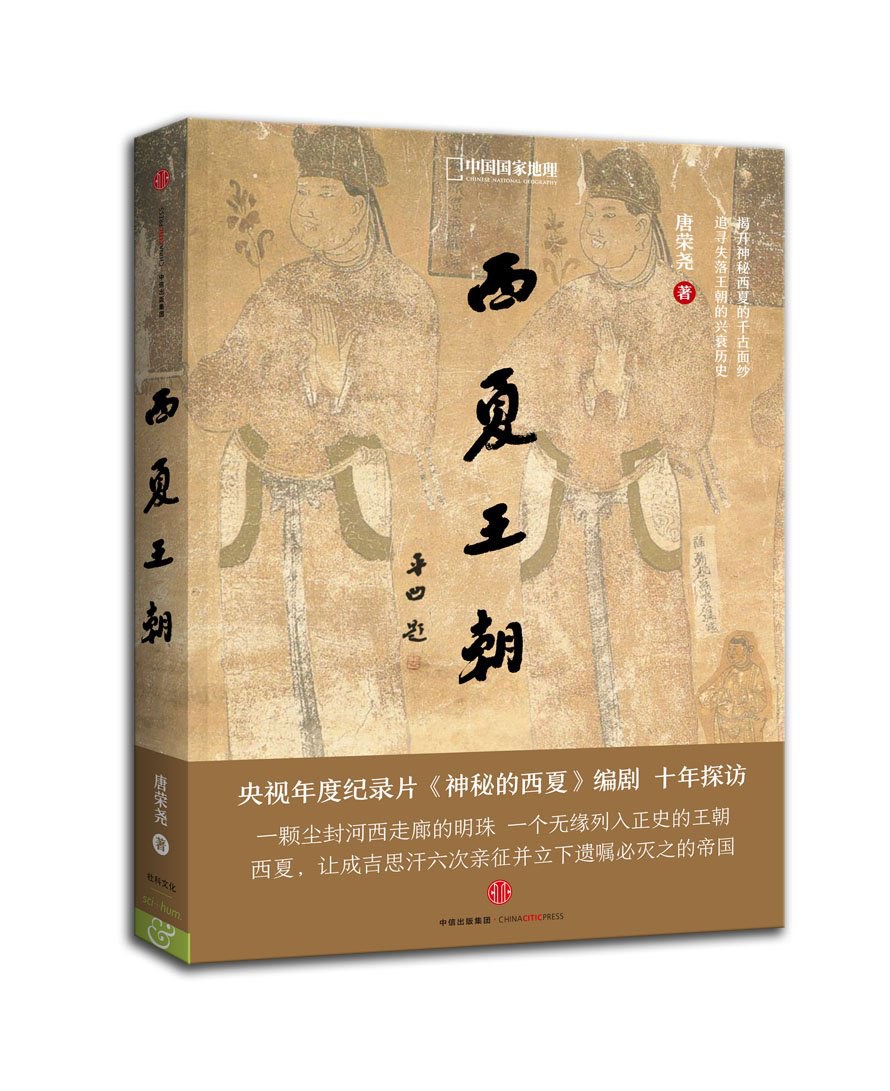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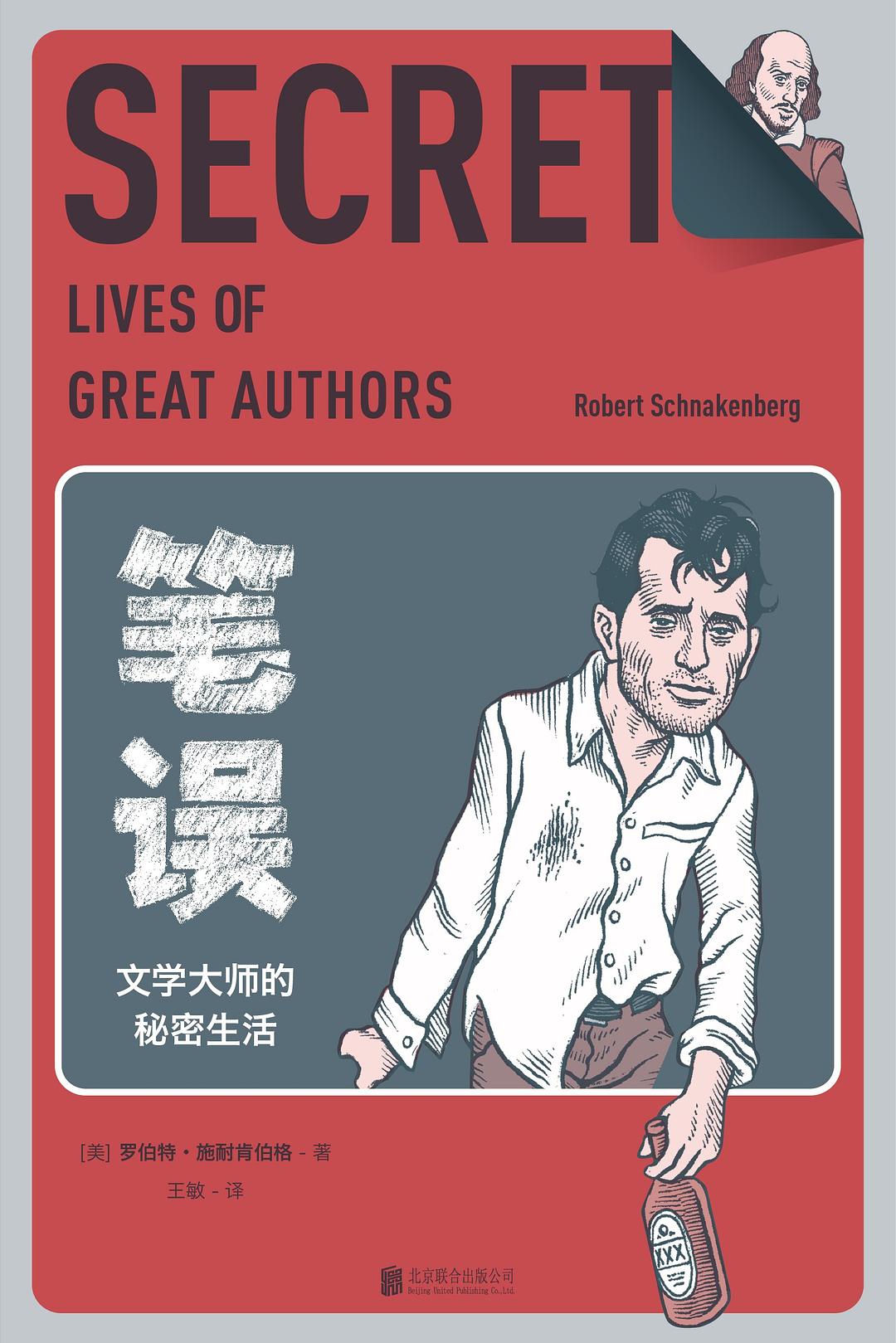
发表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