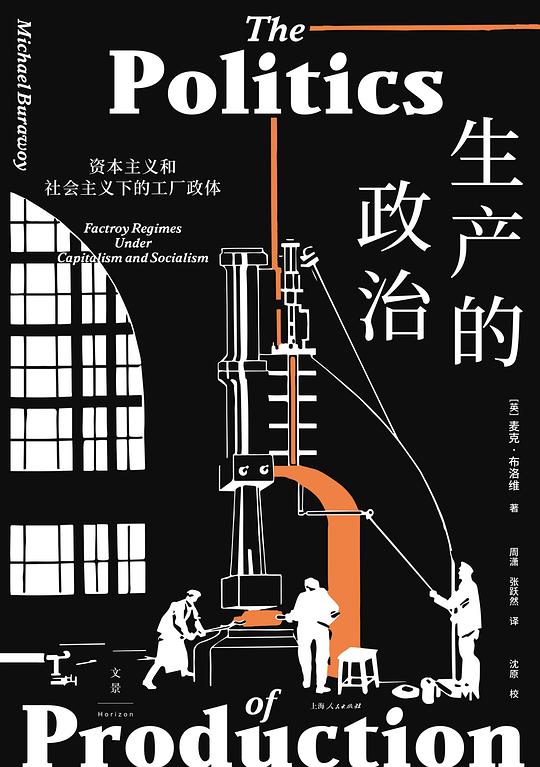
《生产的政治》“内部国家”的生产政体:不止于“以微明宏”
书名:生产的政治
1
0

神王 2023-08-23 16:56:49
与《制造同意》中对“超额游戏”等概念进行深入描述相比,布洛维在《生产的政治》中处理了庞杂的史料和田野材料,以完成对“生产政体”框架的描绘。他所描绘的生产政体遍及欧洲、非洲和美洲,虽然很多分析只提供简单的框架,但仍然具有洞察力和诚意。
布洛维首先对布雷弗曼的“概念与执行分离”理论进行了梳理和反思。布雷弗曼认为,技术剥夺足以区分竞争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变得无技能化和碎片化。在布雷弗曼看来,十九世纪的手工匠人和二十世纪泰勒制监管下的流水线工人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劳工面貌。前者是概念与执行的统一,而后者则是分离,即“把管理者的头脑从工人的帽子下拿走”。然而,布洛维指出,“恩格斯在19世纪的研究中很少有工人能够掌握劳动过程的控制权”。布雷弗曼所建立的对立是一种线性的维度划分,难免因历史境遇的复杂多变而陷入难以适用的尴尬境地。因此,布洛维对布雷弗曼进行了“解绑式”的批判,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都可能存在概念与执行的统一和分离。
相比布雷弗曼的线性思路,布洛维的研究更接近韦伯所描绘的共时性和遇合式的因果分析,思考在特定环境下特定行动模式的意义,思考意识形态、种族、阶级、教育等外部因素在车间这个“内部国家”中的交织作用。布洛维描绘了英国棉纺织厂从父权制到家长制的过渡,丰富了马克思对“专制主义”的理解,并试图描绘专制主义之外的生产政体。他通过引用大量车间内的田野材料,将宏观问题转化为劳动过程之间的互动,揭示了隐蔽的生产过程。布洛维认为,工人阶级的关键领域是生产过程本身,而生产过程则被视为一种政治政体。他不断思考不同生产政体再生产和转化的条件以及不同政体对劳工产生的影响。
布雷弗曼关注的是通过技术剥夺实现的控制,而布洛维则回归到生产过程中,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在马克思主义框架下,为什么在生产过程中对劳工的控制是必要的?他认为,原因在于马克思假设劳工和资本利益存在根本的对立。然而,历史并没有按照理论假设前进,阶级斗争的结果缓和了利益的对立。为了探究何种条件下劳工和资本的利益确实对立,布洛维紧紧围绕“强制”和“同意”、“专制”和“霸权”这两对核心概念分析田野材料。强制压倒同意的生产政体是专制的,而同意多于强制的生产政体是霸权的。
在《制造同意》的自序中,布洛维曾指出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学者过于关注共产主义理想与现实差距的思考,因此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现状批评陷入了逻辑上的错误。苏联式社会主义因未能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被拒绝,从梦想的实现变成了噩梦。在本书的第四章《工人在工人的国家里》中,布洛维引用了匈牙利社会学家哈拉兹蒂的田野材料。哈拉兹蒂在匈牙利红星拖拉机厂工作时,面临巨大的劳动负担和危险。他像其他操作工一样,尽可能运行两台机器。这种“双机系统”强化了幻觉的力量,工人在计件制度中争取更高的产量,社会主义中的就业保障与工资无法分开。第二经济的盛行导致许多工人同时参与第一经济和第二经济,然而这种双重身份进一步阻碍了工资的增长,因为“每个家庭都被看作至少有一种来自第二经济的收入”。收入不平等因此加剧。布洛维对东欧生产政体的研究充满了各种巧妙的反讽,例如“计件工资”既是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主义加剧剥削的机制,也是苏联和东欧国家管理者所称的“最适合社会主义的按劳付酬机制”。面对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国家采取“粉饰社会主义”的手段来掩盖现实。
生产政体的分析框架在国内许多劳工社会学的定性研究中常见,如酒楼中的大姐和小妹、珠三角代耕菜农等。这可能是因为生产政体框架对组织各种田野材料很有帮助。然而,将微观的框架外推存在风险,布洛维在本书中的外推与工会等媒介密不可分。在其他情况下,套用这个框架进行外推需要谨慎思考。
(以上翻译仅供参考,具体以实际语境为准)
相关推荐
逆天的冒险
我们是天生的冒险家,对冒险的爱从不会离开我们,直到我们迈入垂老之年。”博莱索写道。他认为,“胆小的老头子,在他们的兴趣当中,冒险应该是绝灭了的。”这也是为什么诗人们偏爱冒险,而法律通常是老年人制定的原 (南非)威廉·博莱索 2023-04-10 05:12:26© 2023-2025 百科书库. All Rights Reserv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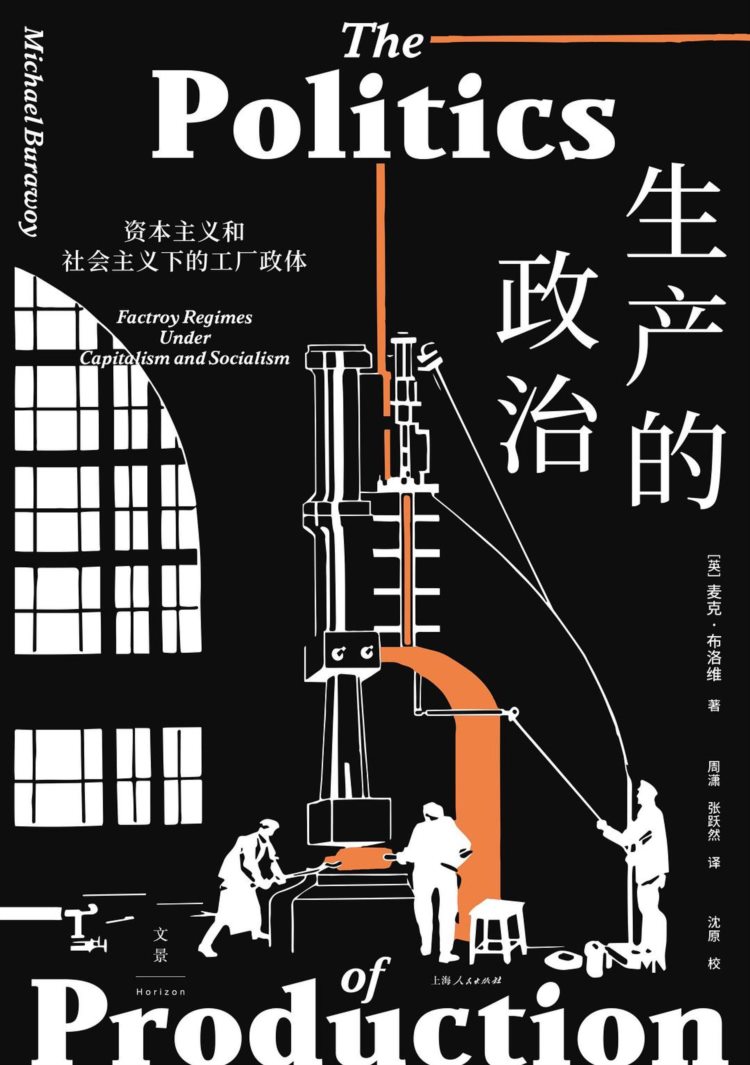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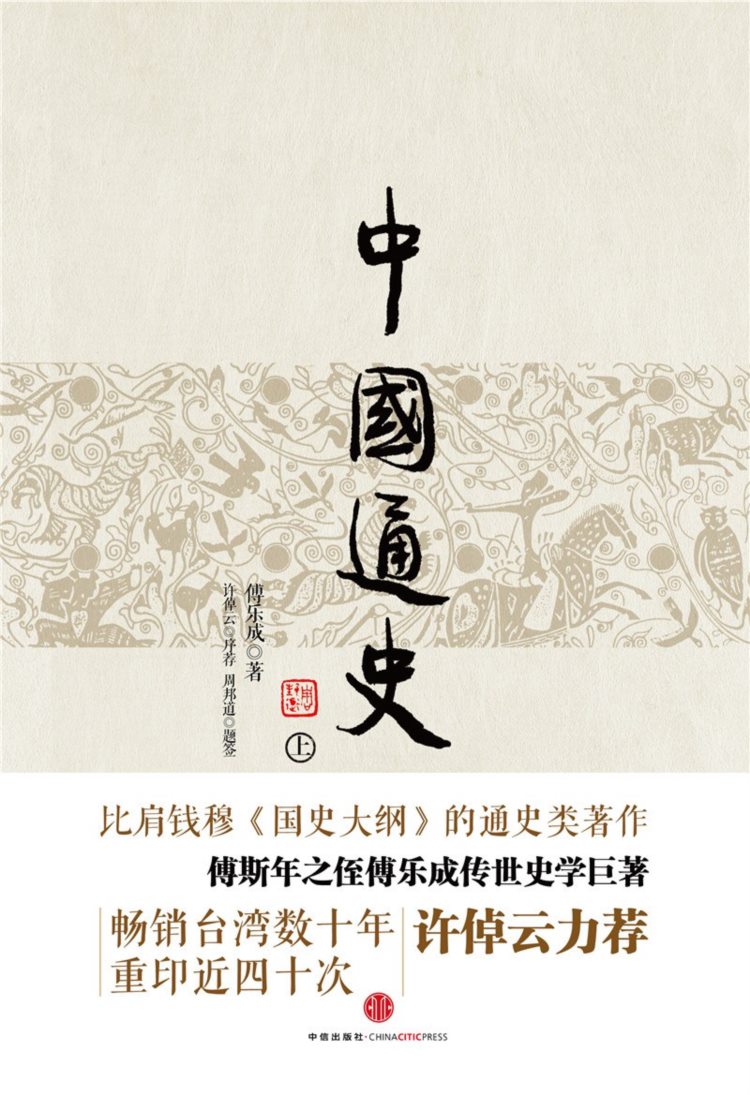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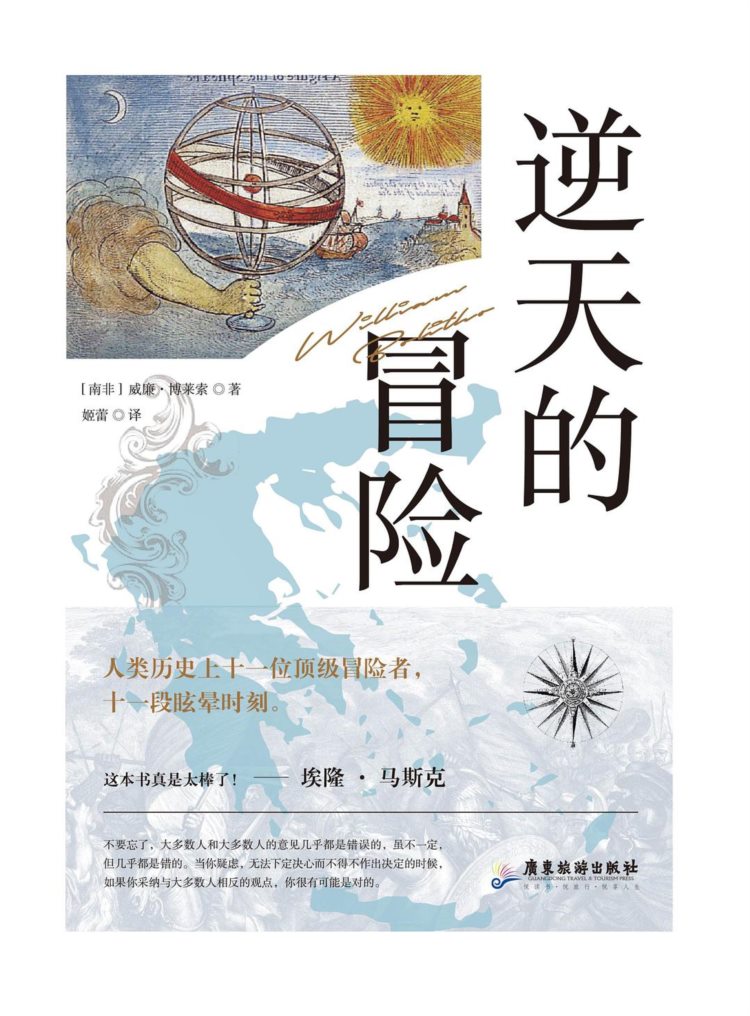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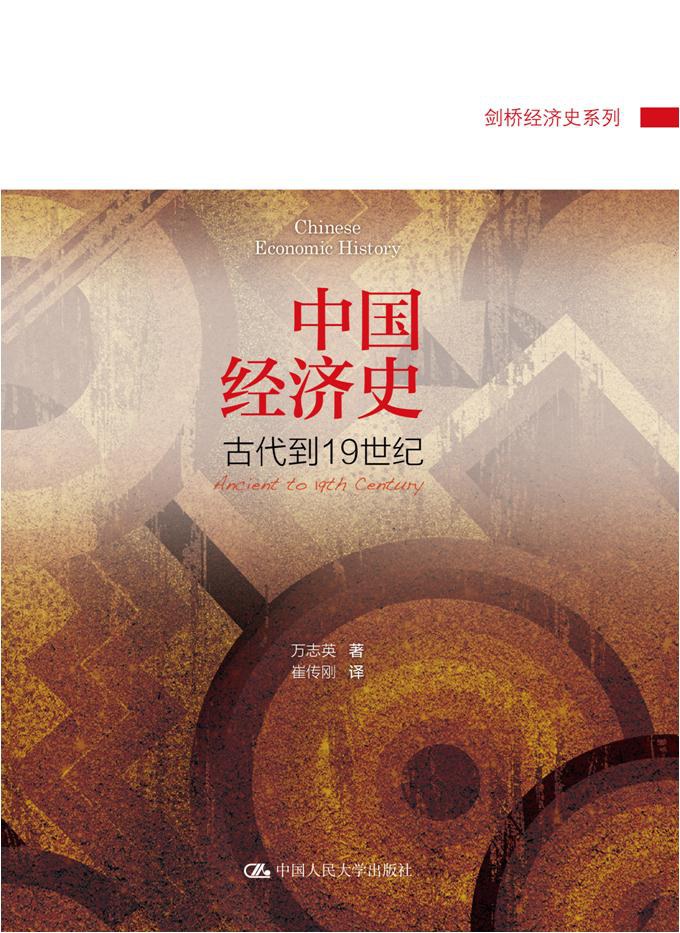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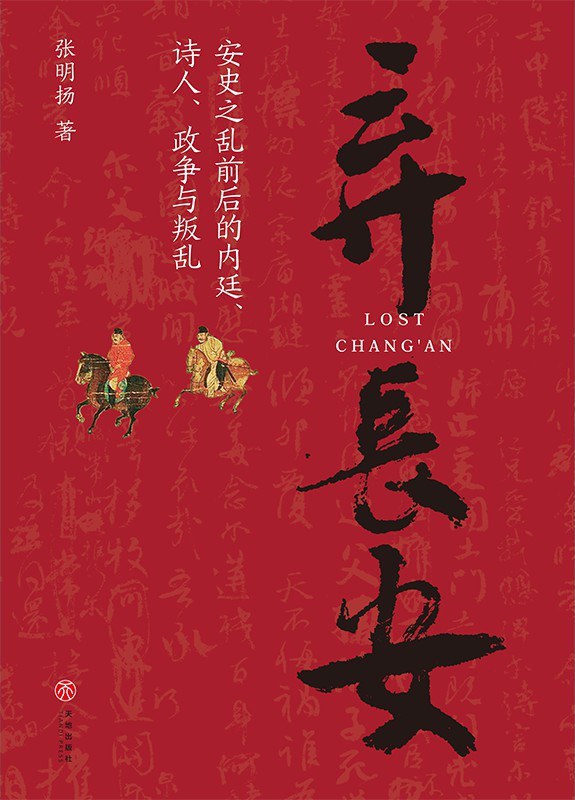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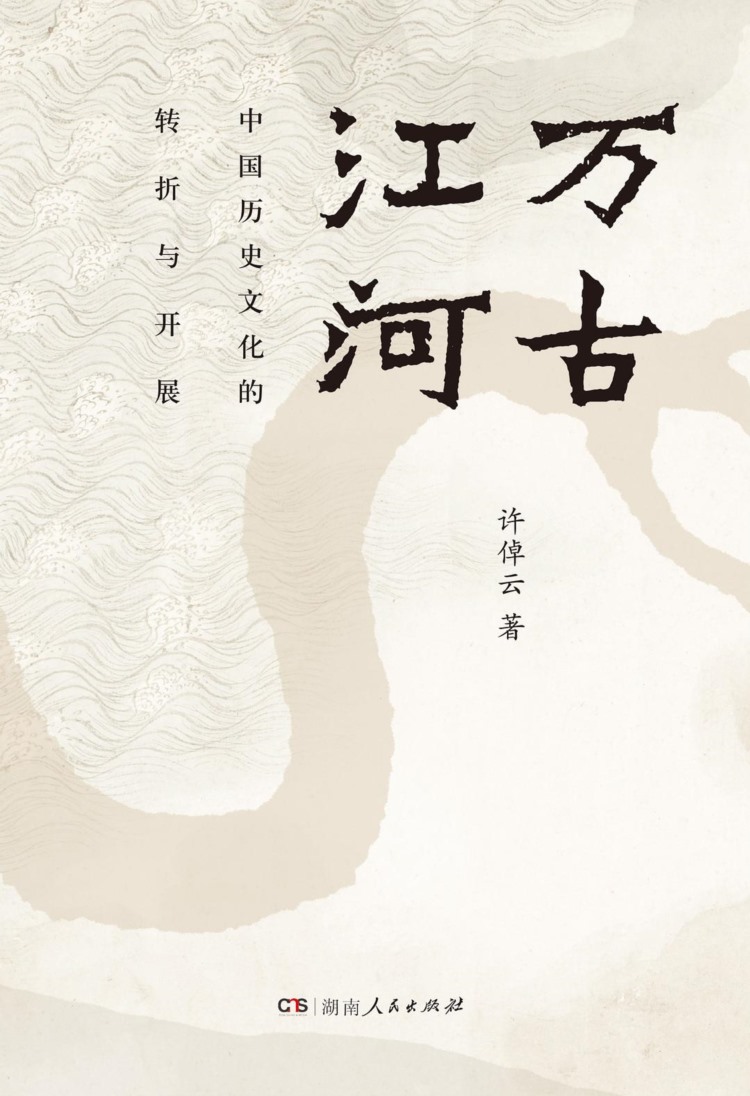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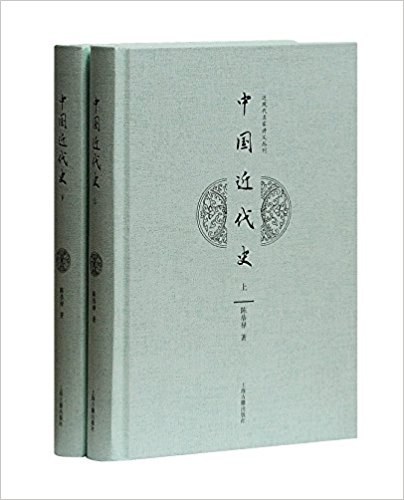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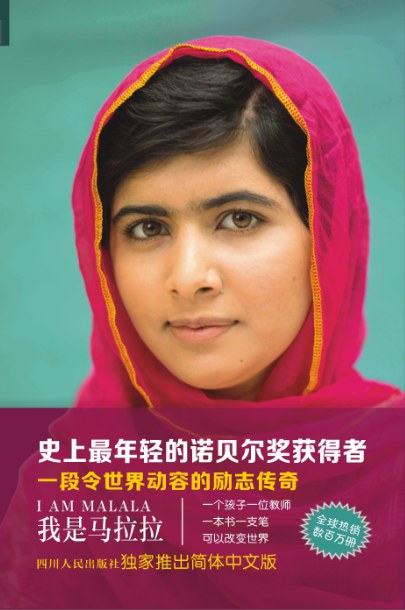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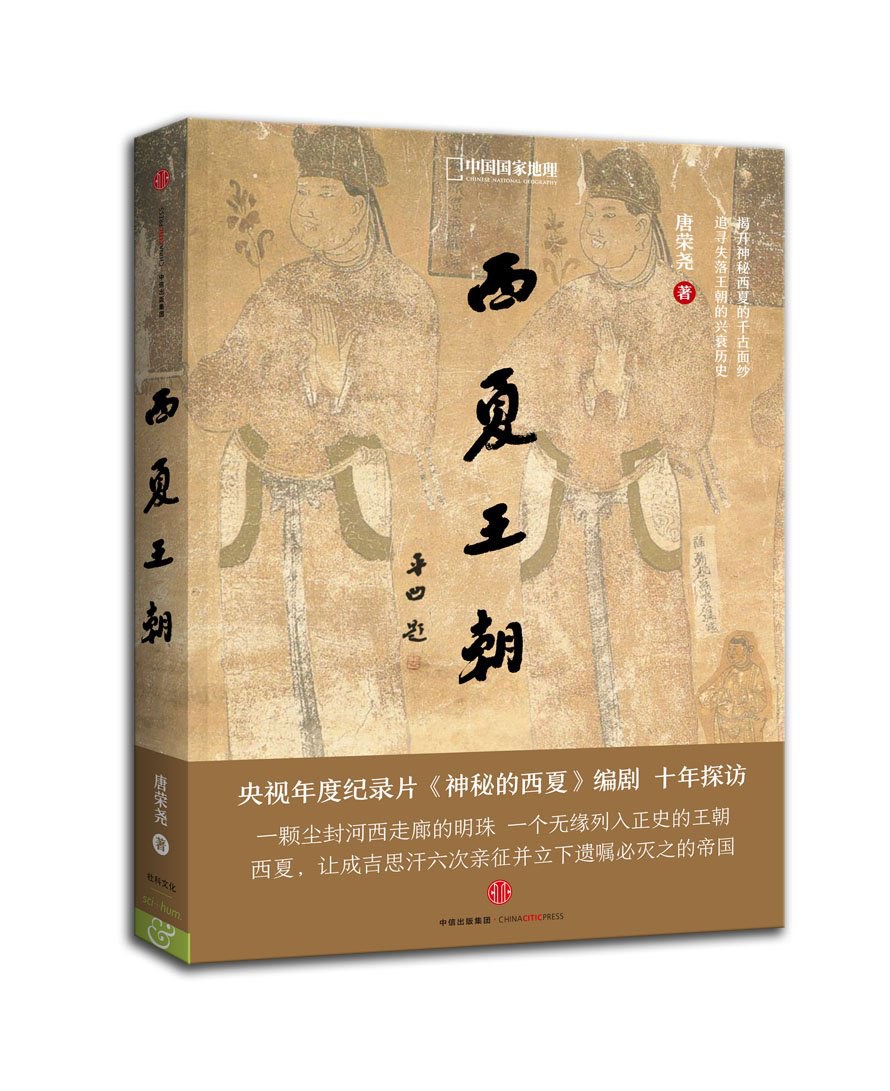
发表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