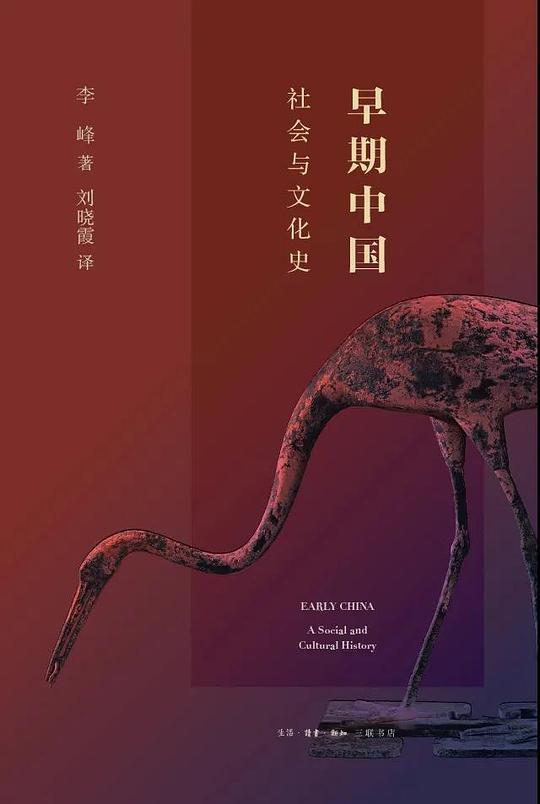
早期中国:帝、人格神与法的失序
书名:早期中国
1
0

光辉岁月 2023-08-22 18:28:44
这本书本质上是一个普及类图书。
但是在文献综述上处理的非常“周全”。
其实如果就从这本书的思想上来说,大可不必专门写这个评论。
但这本书罗列的几个“知识点”确实可以引起一些有趣的“发散“:
1,帝。
帝实际上是商人的“发明”。
一般的争论是——它是不是一个西方语境下的GOD的指称?
而在一个更具体的争论里,就是它是不是人格神的——上帝呢?
即便在商,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帝”没有留下任何被“祭祀”的证据。
商人会祭祀山川大河的神灵,可似乎唯独不会“祭帝”?
作者的给的解释是,它可能是一个“天文现象”。
有趣的来了,假如山川作为“自然现象”都会被“祭祀”,那么天文现象为什么不会?
作者仍然没有多做议论。
但到了西周,一些有趣的信息出来了。
首先周的天命观没有直接沿用“帝”,德没有配“帝”,而是直接就配了天。
而更有趣的是,帝并没有因为与天的割裂而被遗弃,实际上它反而被周人纳入了某种祖宗崇拜的——源头性设置?
帝不会象天一样出现“不配”的问题,反而成了所有周王逝去后的“原乡”。
这里面神话思维的线索,一下子就涌现了出来。
帝作为一种“天文现象”没有被商人祭祀,如果从神话思维的角度,那么很可能是因为它本身就是“祭祀的一环”而不是祭祀的对象。
商的统治者很可能仍然扮演了神王时代重要的祭祀角色。
田猎并不仅仅是征伐,而是将神王的“神圣性”传播到更大的疆域之中。
“帝”就是这个“神王的田猎”这个仪轨的最重要的一个祭祀符号。
“祀与戎”在商应该不是两件事,而很可能就是一种仪轨。
这也符合为什么商的统治者需要不停的“征伐”的原因。
在这里有一个”人格神“的动力解释问题。
那就是——是否一切民族的人格神诞生——都是不同族群神话体验的——异域性交叉?
在分享余英时的《天人之际》的时候我们就说过,把神话思维看作一种认知演化的动力,不能解释为什么会出现“人格神”。
简单的用线性进化的思想,不是解释了人格神的诞生,而是“排列了”人格神的诞生。
事物从简单到复杂,不过是个“自动化”,根本不需要“动力陈述”。
这个问题其实也出现在“酋邦”这个概念上。
这是人类学为了解释“早期复杂社会”向“早期国家”过渡而安置的一个概念。
酋邦根本没有能力从动力学上解释龙山文化到二里头文化的演化到底发生了什么,
它无非就是制造了一个“过渡阶段”来想当然的“链接”两个文化的所谓“中间形态”。
酋邦获得广泛认可的理由,和“原始宗教”这个概念获得认可的理由如出一辙。
那就是,它形式上,“链接”了几个在动力上无法解释的人类文化的演化变迁。
而“帝”这个概念,却很可能提供给我们一个动力性的去理解人格神诞生的“视域”。
其实,中国之所以人格神陈述在神话考察内部,非常薄弱的原因,很可能就是商的“帝”并没有从一种神话时代的“神王时期”接受一个外部对象的“帝”的祭祀性改造。
而到了西周,帝的人格神压力又被转译为祖宗崇拜的某种“原乡精神”,这个奇怪的神话体验与日趋复杂的文化结构的“融合方式”是完全不同于欧洲的。
赫丽生在考证它所谓的“原始宗教”(神话思维)与奥林匹斯诸神的关系的时候,就为我们展开了这样一个“帝”到“GOD”(宙斯)的过程(尽管她自己其实是为了否定希腊神话的宗教价值的)。
不仅是周,实际上很可能在商,早期中国文化的演进,就拒绝了这个过程。
这是中国神话思维的中期(神往时代)没有走向后期(人格神时代)的原因吗?
这个现象,也是我们最终拒绝了对象化思维的古典宗教的原因吗?
2,法。
一般情况下,我们会认为子产的“刑书铸鼎”是一个新秩序时代的到来。
但它的背景是什么呢?
它的背景其实是宗族制度的“大失序”。
宗族制度并不简单的是一个“统治秩序”,宗族通过“姓”的类族,和“氏”的辨物拓展的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亲族体系。
它是一种根本的文化结构的秩序。
这个秩序拒绝依赖于“外部约定”,而法与契约的关系,却是一个典型的外部约定。
在欧洲文化中,法根本的价值并不是“规范的展示”,而是规范的契约化。
也就是说,当欧洲文化寻找自身文化的秩序性陈述的时候,它们必须为契约的神圣性提供支持。
这就是为什么即便是上帝,也要和他的子民“签约”的原因。
不管是中世纪还是到了16-17世纪的自然法大讨论,法的神圣性并不建立在“明文规定”这么一个所谓的世俗效用上,更根本的原因反而是,法就是一切“神圣性”的——神圣物。
从这点出发我们才能明白为什么子产的“刑书铸鼎”并没有换来类似于欧洲的那种契约精神式的,外部规范的“神化”,反而是宗族制度仍然以礼乐的形式,要求主体性的“自律”:
法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秩序里,说白了一直不过是一种“失序”的噩兆——刑罚:
好了,这就是这本综述,能带给我的一些碎片化的发散了。
除此之外,也没什么可分享的了。
相关推荐
萤火谷的梦想家
艾莉森•麦吉出生于1960年,是美国《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同时也是大都会州立大学创意写作课的教授。她的作品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并出版,也曾被提名普利策奖,并获得苏斯博士奖金奖、克里斯托弗图书奖、美国 [美]艾莉森•麦吉/[美]克里斯托弗•丹尼斯/绘 2023-03-27 16:50:25鬼马女神捕1·绝密卧底(上)
腹黑凤凰vs毒舌鸡妖——蓝翎:“小姬,跟我去人界吧!”姬十四:“干吗?让人宰了我做小鸡炖蘑菇吗?”蓝翎:“不啊,让妖怪宰了你做小鸡炖蘑菇更气派。”凤凰蓝翎和鸡妖姬十四生活在无忧无虑的灵界。他们的故乡叫 郝天晓 2023-04-17 00:22:47© 2023-2025 百科书库. All Rights Reserved.












发表评价